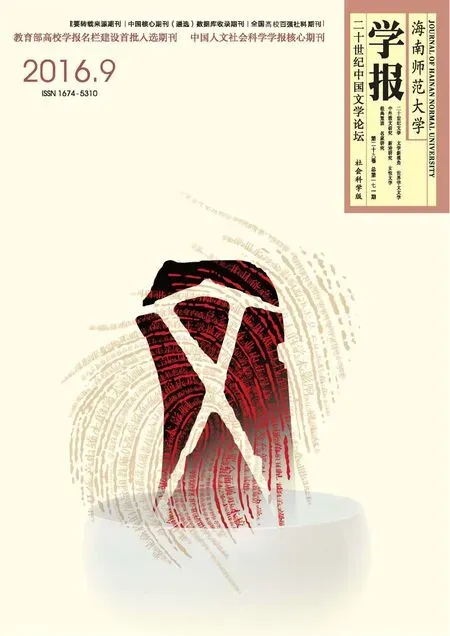日常經驗與內在超越:南宋詩人的老年書寫
戴 路
(復旦大學 中文系, 上海 200433)
?
日常經驗與內在超越:南宋詩人的老年書寫
戴路
(復旦大學 中文系, 上海 200433)
詩歌的老年書寫包括老年生理體征的描摹、生命感覺的展示和耆老集會的酬唱,它在南宋呈現出有別于中唐和北宋的新特征。首先,南宋詩人對老態病體曲寫入微,在身體經驗的表達上為宋詩的日常化開辟了新境界。長期的閑居狀態提高了詩人自我體察的精細程度,也使他們用疏狂心態消解了身體發膚的莊嚴感。其次,詩人面對衰老時體現出加緊問學的精進勤勉,在自我更新中重構人生秩序。理學開啟的內在超越為他們帶來新的生命感覺。第三,在耆老會酬唱中,詩人將序齒稱德的交往話語變為人生閱歷的真誠訴說,使年齡從文化符號變為情感紐帶。鄉居環境改變了耆老會的成員結構,也影響了酬唱主題與表達策略。
南宋;老年書寫;身體經驗;內在超越;耆老會
衰老的體驗人皆有之,無論是《離騷》“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這種生命的焦慮,還是陶淵明“素標插人頭,前途漸就窄”(《雜詩》)、謝靈運“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晚出西射堂》)這類漸衰的身體感覺,都是古人抒懷時無法回避的內容。但對老年處境進行系統吟詠在中唐杜甫、韓愈、白居易等詩人那里才開始盛行。宋人的老年書寫在題材和手法上進一步拓展。時至南宋,文人高齡化的趨勢更加明顯,正如方回所說:“予嘗羨慕近世詩人如曾茶山、陸放翁、趙昌父、滕元秀、劉潛夫皆年八十”①[元]方回:《瀛奎律髓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12頁。,“詩人而壽者,近有數老仙,后有陸放翁,前有曾茶山。亦復有二趙,南塘與章泉。年皆八九十,至今詩集傳”②[元]方回:《七十翁吟五言古體十首》,《桐江續集》卷二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96頁。。高壽的南宋詩人充實了宋代文學中的老年篇章,其時代特征及成因的彰顯,亦是人們認識兩宋文化轉型的一個窗口。宋元之際類編本詩集《后村先生大全詩集》與《瀛奎律髓》都設有“老”類或“老壽”類,包括衰病描摹、晚景呈現、耆老酬唱三個方面。南宋詩人的“老年書寫”,也主要由這三方面構成。
一、老態病體的日常化書寫
人生漸老的感受是切己的,詠老之作離不開身體狀況的呈現和描述。在傳統的文學表達中,鬢發作為年齡的標桿成為文人普遍吟詠的對象,衰鬢蒼發引起的人生遲暮之感是詠老文學中的常見主題。但除鬢發之外,描述身體其他部位的老病詩直到中唐才集中出現。如杜甫“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聾”(《復陰》)、“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月聾”(《耳聾》),韓愈“我雖未耋老,發禿骨力羸。所余十九齒,飄飖盡浮危”(《寄崔二十六立之》),柳宗元“齒疏發就種,奔走力不任”(《覺衰》)等,都是在白發之外,描述了身體其他部位的衰病狀況。比杜、柳、韓高壽的白居易在病體的表現上更為豐富,除了在以老病和年歲為題的詩中有所涉及,亦有專門描寫各部位的《白發》《齒落辭》《病眼花》《足疾》等作品。老病詩在中唐的興盛為宋人開啟了一種寫作傳統,詩人以衰變的身體發膚為關注對象,在自我認知與檢視的過程中呈現暮年經驗和生命感受。宋人對此傳統有深刻認同,如王十朋“齒疏方咄柳,牙落遽驚韓”(《齒落》),范成大“栗里歸來窗下臥,香山老去病中詩”(《丙午新正書懷十首》其八),樓鑰“只有昏花似退之”(《病目初愈張子家有詩次韻》),陸游“樂天悲脫發,退之嘆墮齒”(《齒發嘆》)、“已興工部耳聾嘆,更和文公齒落詩”(《雜賦》)等,都顯示中唐詩人老病書寫對后世的影響。但是,由中唐至南宋,書寫方式發生了怎樣的轉換?試以病目詩和病齒詩為例:
花發眼中猶足怪,柳生肘上亦須休。大窠羅綺看才辨,小字文書見便愁。(白居易《病眼花》)
火齊終無颣,泉沙暫有渾。(劉敞《尚叔父病目》)
天公戲人亦薄相,略遣幻翳生明珠。(蘇軾《次韻黃魯直赤目》)
燈迭青紅暈,書紛黑白行。(洪咨夔《病目》)
暝鵲驚飛匝,涼蟾瞥露些。(劉克莊《目疾一首》)
白居易敘述了眼花時只辨細物、不識小字的日常感受。這種對老態病體直觀描寫的方式一直延續到宋初,如李昉“衰病增加我斗諳,頭風目眩一般般。縱逢杯酒都無味,任聽笙歌亦寡歡”“容顏也道隨年改,牙齒誰教斗頓疏”*[宋]李昉:《老病相攻偶成長句寄秘閣侍郎》《昉著灸數朝廢吟累日繼披佳什莫匪正聲亦貢七章補為十首學顰之誚誠所甘心》其一,《全宋詩》第1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173-175頁。等便是用淺切平易的方式呈現老病體驗。但此后的北宋詩人并不停留在老態病體的現象描述上,而是遺貌取神,或借用審美化的自然景象進行比擬,或關注身體與疾病的文化內涵。如上引劉敞詩句便用火齊珠比喻眸子的光亮,以泉沙形容眼球的清昏。蘇軾用明珠進行比擬時,增加了幻翳空花的宗教隱喻,在超越疾病中實現個體解脫。
然而,這種遺貌取神的手法卻在南宋發生了轉變,詩人更加注重對衰容病態與老年體驗的細節呈現,從北宋詩人的審美境界與宗教境界返歸日常生活。而和白居易等人相比,南宋詩人在表現瑣細的身體經驗時更具敏銳的觀察力,避免了淺易羅列,注重展示個性感受。如上引洪咨夔詩句便是對視覺體驗的細化:青紅黑白的淆亂、燈影字跡的昏花。劉克莊亦描述了病目的切身感受,“涼蟾瞥露些”,月亮渾蒙得就像一團露水。劉克莊曾自陳病患曰:“某所患目疾,初謂偶然,今百日轉甚,八月間猶仿佛見物”*[宋]劉克莊:《與丞相書》,《劉克莊集箋校》卷一三四,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5372頁。、“向來隔幾重膜”*[宋]劉克莊:《左目痛六言后九首》其八,《劉克莊集箋校》卷三四,第1842頁。,隔膜的感覺正是“涼蟾瞥露些”。這種細致的身體經驗是中唐與北宋詩人不具備的。
除前引詩句外,這類描寫還有陸游“客至難令三握發,佛來僅可小低頭”(《老病謝客或者非之戲作》)。“小低頭”雖語出佛典,但卻直觀傳達出病人的僵硬體態。在形容齒疾上,劉克莊用“啖面賢于聘上醫”(《竹溪痔后齒痛小詩問訊》)折射痛感,曹勛用“豈惟意倦怠,咀嚙徒攢眉”(《感齒發之衰作詩自解》)描寫咀嚼時的艱難神態。楊萬里晚年患淋疾,用“君欲問淋疾,便是法外刑。刲剔備百毒,更以虐焰烹”(《送戴良輔藥者歸城郛》其一)突出病痛的煎熬。清人吳陳琰評陸游詩云:“自鉅至細,無不曲寫入微,幾于撚斷吟髭,而不屑為人所愛,然使人不能不愛,不啻親履其境,目睹其事,皆人所困難也。”*[清]吳陳琰:《葛莊分體詩鈔序》,《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8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34頁。此種“曲寫入微”的功夫在南宋詩人的老病描寫上普遍存在。宋詩在表現瑣細事物與日常生活方面的拓展性為人所熟知,但如果將觀察外在世界與自我認知進行區分,我們可以發現前者在北宋已取得長足進展,詩歌對鳥獸蟲魚、筆墨紙硯等外在事物的表現力得到提升,而在呈現自我的體貌樣態與生理經驗方面,南宋詩人實現了新的拓展,為宋詩的日常化開辟了新的境界。
如果說病痛感受的呈現側重“親履其境”的效果,那么身體形貌的描摹則令人“目睹其事”。試以病齒詩為例:
憶初落一時,但念豁可恥。及至落二三,始憂衰即死。(韓愈《落齒》)
日出暵焦牙,風來動危萚。(蘇轍《次遠韻齒痛》)
衰發如枯菅,殘齒如敗屐。(陸游《歲暮雜感四首》其一)
身似漏船難補貼,齒如敗屐久凋零。(方岳《春日雜興》其八)
在病齒的吟詠中,韓愈“豁可恥”屬整體性描述,未呈現牙齒的細致形態。蘇轍則借用草苗的枯朽情狀突出病齒的意態。陸游的“敗屐”形象地呈現出座齒的腐蝕與鄙陋狀態,方岳沿襲了這種比喻。屐是日常用品,本體與喻體處于同一生活場域,兩者的形態也較為契合。“敗屐”的意象在陸詩多次出現,如“齒如敗屐鬢成絲,七十之年敢自期”(《覽鏡有感》)、“齒如敗屐鬢如霜,計此光景寧久長”(《自傷》)、“我齒如敗屐,君發如新霜”(《箜篌謠二首寄季長少卿》其二》)等。值得注意的是,“我齒”與“君發”的句式從韓愈而得,如韓詩有“我齒落且盡,君鬢白幾何”(《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我齒豁可鄙,君顏老可憎”(《送侯參謀赴河中幕》)等。但兩相對照,“如敗屐”比“落且盡”“豁可鄙”更能體現病齒的形態輪廓。南宋詩人類似的比喻還有陸游“馘黃色類梔,面皺紋如靴”(《晨鏡》)、范成大“骨枯似枿膚如臘,發織成氈鬢作蓬”(《謝范老問病》)、楊萬里“眼添佩環帶,腰減采花蜂”(《病起覽鏡》二首其一)、“試脫中單肌起粟,俄生點隱狀如沙”(《疥癬二首》其二)等,用日常事物形象勾勒出身體的外形輪廓,顯示出詩人自我認知的精細化。
南宋詩人晚年穩定的鄉居生活為他們反觀自身、體驗自我提供了充分契機。如楊萬里“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須赤腳,才三四人”*[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63頁。,范成大“雜綴園亭,經營草木,鄉居瑣事,吳俗歲華,亦足以陶寫塵襟,流傳佳話”*[清]李慈銘:《荀學齋日記》,《越縵堂日記》,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10904頁。,劉宰“隱幾覺來,杖藜獨往。或從田家瓦盆之飲,或和漁父滄浪之唱,顧盼而花鳥呈技,言笑而川谷傳響,賓送日月,從容天壤”*[宋]劉宰:《書印紙后》,《漫堂集》卷二四,《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0冊,第613-614頁。等。這種疏離政事、退居閑處的狀態在南宋士大夫的晚年生活中較為普遍,前述方回列舉的高壽詩人,大多擁有長期奉祠家居或致仕退居的經歷,這和飽受貶謫遷徙之苦的北宋士大夫尤其是元祐文人的處境是不同的。詩人棲身于日常空間,周遭事物無不形諸筆端,生理經驗與身體印象也愈加引發關注。
與此同時,長期鄉居野處會造就一種疏狂心態,它使退居者泯除莊與諧、美與丑的界限。在儒家觀念中,身體發膚受之父母,具有莊嚴性,同時傳統禮儀通過須發鬢髻的造型、衣冠服飾的設定對身體加以規范。但對于久離官場、年事已高的村夫野老來說,外在的禮節規范已顯得不那么重要。陸游云:“一笑衰翁乃爾頑”(《病愈看鏡》),“昔聞少陵翁,皓首惜墮齒。退之更可憐,至謂豁可恥。放翁獨不然,頑頓世無比”(《齒落》),這種“頑頓”就是以無所畏懼、輕松戲謔的心態游離于典型士人形象之外。《論語·泰伯》:“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朱熹注云:“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于將死而后知其得免于毀傷也。”*[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103頁。這體現出身體手足的神圣意味。而陸游“紗帽簪花舞”(《自嘲老態》)、劉克莊“戲衫脫了無羈束,縱見三公手懶叉”(《疥癬》)、“亂插烏巾策杖嬉”(《覽鏡》)則是一副疏野散漫姿態,遠離正襟峨冠的禮節威儀。當身體發膚的莊重感被消解,老病衰殘的種種情態可以無所顧忌地顯露。劉克莊自贊云“極維摩詰之病,屈大夫之悴,壺丘子之怪,哀駘駝之丑”*[宋]劉克莊:《庚戌寫真贈徐生》,《劉克莊集箋校》卷一〇六,第4423頁。,容貌體軀的缺陷以嘲謔戲詠的方式呈現出來。儒釋道各家都存在丑怪病悴的形象,通常蘊含“行相雖惡而心術善”(《荀子·非相》)、“畸于人而侔于天”(《莊子·大宗師》)、維摩示疾顯神通等相反相成的邏輯。但對南宋老年詩人而言,此種理論預設消融在插科打諢的游戲境界之中。
二、衰老與精進:生死困境的內在超越
衰老在給人帶來身體感受的同時,也造成直接的心理沖擊,如何度過余年、實現生命價值是人人都無法回避的問題。在突破生死困境方面,儒家的內在超越、莊子的齊物論、道教的長生術、佛教的空幻觀等,為文人追求解脫提供了多種途徑,也影響到他們的處老心態。例如,白居易曾通過佛禪尋求對生命的超越*參見謝思煒:《禪宗與中國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102-107頁。;蘇軾晚年在貶謫生涯中感嘆人生的虛空,在洞徹生命本質后追尋精神自由;蘇轍退居潁昌后保持了閉門默坐的生活方式,在觀空悟道中涵養清凈本心,安享殘年余生。
對南宋文人而言,盡管佛禪思想仍是他們審視人生的必要資源,但在理學興盛的時代環境下,衰老并不意味著消逝與虛無,反而催生了人們讀書問學的緊迫感和實現內在超越的動力。朱熹面對老態病容時感嘆:“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薄臨深諒無幾,且將余日付殘編。”*[宋]朱熹:《南城吳氏社倉書樓為余寫真如此因題其上慶元庚申二月八日滄洲病叟朱熹仲晦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176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第15頁b-16頁a。衰老雖然令人悵惘,但并未帶來悲憂,而是促使他抓緊所剩無幾的時光著書治學、持續精進。朱熹曾批評杜甫《同谷七歌》的卒章“嘆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宋]朱熹:《跋杜工部同谷七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四,《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181冊,第8頁b。,當自己身處老境時,他表現出孜孜不倦的求道熱情。在“轉向內在”的時代風氣中,個體道德心性的完善愈加成為安身立命的根基,盡管問道的程度與方向不盡一致,但由理學開啟的內在超越對士人處世心態與生活情趣有著深刻的影響。朱熹式的終身持敬與勤勉精進,整合了傳統文化中惜時奮勵的成分,內化于南宋士人的精神生活,使他們在生老病死的必然命運中更加積極樂觀。這類例子還有:
白日不我待,志士心悲傷。功業一無就,雙鬢鏡中蒼。古人有遺訓,日進期無疆。讀盡天下書,拄腹復撐腸。(陳自修《白日吟》)
朝來覽鏡一何衰,發禿容枯半白髭。老態侵尋光景促,著鞭從此勿遲遲。(袁燮《覽鏡》)
志士傷心髀肉生,寒儒努力在青春。課書恨失囊螢聚,覽鏡驚呼鬢雪新。歲晚何妨勤秉燭,行迷猶可復通津。余功剩暖丹爐火,莫待幽人喚孔賓。(程公許《覽鏡鬢間兩三點雪》)
昔映仙藜臨幾桉,今栽甘菊滿庭除。不堪立馬揮新檄,只合囊螢勘舊書。(劉克莊《晨起覽鏡》)
陳自修的“日進”、袁燮的“著鞭”、程公許的“秉燭”、劉克莊的“囊螢”,和朱熹“且將余日付殘編”一樣,都是面對蒼鬢衰顏時表達出歲不我予、奮起直追的心情。鏡中衰顏與其說是自然的判決,毋寧說是生命的召喚,它使士大夫在知識更新與境界提升中超越生理機能的新陳代謝。劉克莊晚年常常以劉向校書的事跡自勵,即使年老體衰仍要“仰觀星宿俯觀書”、“燭下殘書尚覆翻”(《晨起覽鏡》),“貪校新抄數板書”、“蠅頭尚可就燈抄”(《夜坐二首》),保持了勤勉的治學態度,也找到抵御衰頹的良方。劉曰“惟詩尚有新新意,匹似幽花晚更妍”(《晨起覽鏡》),正可移評他晚年讀書撰文、追求精進的整體狀態,“新新”為凋零的生命注入活力。
理學的內在超越塑造了南宋士大夫的生命品質、處老心態與生活情趣,這一點在陸游身上可以得到集中體現。陸游曾請朱熹為其“老學齋”作銘,朱熹雖未寫成,但前述朱詩“履薄臨深諒無幾,且將余日付殘編”正可作為“老學”的注腳。《甌北詩話》在介紹陸游與朱熹的關系后指出:“是雖不以道學名,而未嘗不得力于道學也。其集中亦有以道學入詩者,如《冬夜讀書》云:‘六經萬世眼,守此可以老,多聞竟何為?綺語期一掃。’又有云:‘雖嘆吾何適,猶當尊所聞,從今倘未死,一目亦當勤。’《平昔》云:‘皎皎初心質天地,兢兢晩節蹈淵冰。’《書懷》云:‘平生學六經,白首頗自信,所覬未死間,猶有分寸進。’《示兒》云:‘聞義貴能徙,見賢思與齊。’又云:‘易經獨不遭秦火,字字皆如見圣人,汝始弱齡吾已耄,要當致力各終身。’可見其晚年有得,非隨聲附和,以道學為名高者矣。”*[清]趙翼:《甌北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第93頁。錢鍾書論及上述材料時對陸游的理學造詣表示質疑*錢鍾書:《談藝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384-385頁。,但客觀地講,“履薄臨深”的持敬與“老而學”的勤勉對陸游的晚年生活影響頗深。在持敬方面,除上引“所覬未死間,猶有分寸進”“兢兢晩節蹈淵冰”外,“兢兢死方已,寧論迫期頤”(《自儆》)、“亹亹循天理,兢兢到死時”、“道遠余生趣,常憂日影移”(《衰嘆》)等均可為證。這種內省精神為其“老學”提供了不竭動力。清《柳亭詩話》卷三十“讀書癖”評陸游云:“流離僵仆之余,未嘗一日釋卷,年已耄而志不衰,僅于此老見之。”*[清]宋長白:《柳亭詩話》,上海:上海雜志公司,1936年,第683頁。在陸游詩作中,年老激發的讀書熱情處處可見,如“殘年唯有讀書癖,盡發家藏三萬簽”(《次韻范參政書懷十首》其六)、“病臥極知趨死近,老勤猶欲與書鏖”(《冬夜讀書》)、“暮年于書更多味,眼底明明見莘渭”(《五更讀書示子》)、“窮猶可勉圣賢事,老豈遽忘鉛槧勞”(《歲晚》)等。這種勤勉奮勵有助于生命氣質的重塑。梁啟超《讀陸放翁集》云:“嘆老嗟卑卻未曾,轉因貧病氣崚嶒。英雄學道當如此,笑爾儒冠怨杜陵。”自注云:“放翁集中,只有夸老頌卑,未嘗一嘆嗟,誠不愧其言也。”*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四十五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4頁。梁啟超對陸游的贊譽令人想到朱熹對杜甫的批評。所謂“不聞道”之“道”,通過內省與勤勉的路徑,為陸游帶來“氣崚嶒”的健碩生命力。持續的自我充實與提升能夠抵消光陰流逝引起的壓抑感,建立新的生命秩序。“窮冬短景苦匆忙,老學庵中日自長”(《老學庵》),“千莖白發年華速,一點青燈夜漏徂”(《題北窗》),與自然節奏相伴的正是自我超越的速率。總之,理學的超越精神為南宋士大夫提供了老而愈勤的心理依據,這體現出宋人生死觀念在“轉向內在”過程中發生的顯著變化,讓我們看到這一時期老年生命中充分的現世感。
三、老年唱和的表達策略:從公共話語到個性敘事
上述生死問題的思考主要發生在詩人對鏡覽照、室中夜坐、燈下苦讀等獨處環境中,創作方式屬“獨吟”,而人際交往中的耆老酬唱亦是老年書寫的組成部分。南宋樓鑰《朱季公寄詩有懷真率之集次韻》云:“伊昔羊尹臨丹陽,真率之名初濫觴。香山尚齒當會昌,臥云不羨坐巖廊。七人各列官與鄉,年德俱高世所臧。丙午同甲遙相望,清談生風想瑯瑯。耆英人物尤軒昂,賦詩遠追白侍郎。文富歸休壽而康,衣冠十二何鏘鏘”,對耆老會的歷史作了簡要回顧。白居易洛陽“九老”的集會方式在北宋士大夫中引起熱烈反響,“五老”“九老”“同甲”“耆英”“真率”等聚會先后出現*參見張再林:《白居易的“九老會”及其文學史意義——以宋人對“九老會”的仿慕為例》,《廣西社會科學》2011年第4期,第129-132頁。。宋室南渡以后,耆老會的形式、主題、參與者等有所改變,如周揚波《宋代士紳結社研究》以鄞縣為中心,指出了南宋耆老會地方化、鄉土化、家族化的趨勢。從與會者身份看,北宋主要是地位顯赫的名公鉅卿,“休官致政老年閑,廟堂嘗享著袍冠。調和鼎鼐施霖雨,燮理陰陽佐武桓”(富弼《睢陽五老圖》);而南宋耆老會則多由奉祠致仕的鄉居士大夫與地方士人或家族成員組成,如危稹“請祠歸,筑屋城南嵩源,與鄉老七人為真率會”*[宋]陳思:《兩宋名賢小集》卷二百六十五,《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64冊,第153頁。,陸游“洛中九老非吾侶,且作山陰十老人”(《庚申元日口號六首》其三)等。在聚會形式發生改變的同時,南宋耆老會詩歌也呈現出更多日常化、個性化的體驗。現以周必大的一組“齊年會”詩歌為例。
南宋淳熙九年(1182),周必大用文彥博“同甲會”詩韻寄贈同年出生、同在朝廷執政的王淮、錢良臣,有意模仿文氏盛會。文彥博原詩為:“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同賦客,合成商嶺采芝仙。清談亹亹風盈席,素發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宋]文彥博:《奉陪伯溫中散程伯康朝議司馬君從大夫席于所居小園作同甲會》,《潞公文集》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0冊,第640頁。,表現出耆老相聚的雍容閑雅,并期待將集會盛況傳播出去。周必大的次韻詩為:“文公八十會伊川,盛事于今又百年。豈意蒼顏華發叟,亦陪黃閣紫樞仙。府居末至容連棟,班路前瞻愧比肩。丁丙連干支合德,君臣慶會豈虛傳。”*[宋]周必大:《文忠烈公居洛有丙午同甲會詩今執政府凡三位樞密使王季海參政錢師魏先在焉前歲夏某忝參預連墻而居適然齊年時號丙午坊次文公韻簡公》,《文忠集》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47冊,第88頁。一致的甲子、相近的官階、相同的工作環境構成了周、王、錢之間的特殊紐帶,在詩歌酬唱中周必大流露出仕途順暢的自豪與君臣際會的慶幸,這和北宋耆老會詩歌中吟詠太平、流連光景、安享閑暇的基調并無多大差別。年齡作為公共空間中的交往符號,對每一個交際者實際上只具有普泛抽象的意義,如文彥博“四人三百十二歲”或司馬光“合五百一十五歲”等表達,歲數只在聚合中才擁有價值。圍繞耆老進行的詩歌酬唱亦側重老年境遇的整體描述。
然而,十多年后當周必大真正步入耆老行列時,他的集會酬唱詩有了更多個性化書寫。每一個年歲都代表一段切身閱歷,耆老聚會不再是比肩前人、點綴太平的文化符號,而是參與者個人感受的交流分享。從慶元元年(1195)到六年(1200),周必大每年與歐陽鈇、葛潀舉辦一次“齊年會”,仍依舊例次韻文彥博詩,但聚會的地點變成家鄉廬陵,另兩位“齊年”的身份由朝廷重臣變為鄉間布衣。從聚會內容看,每年都有一個具體主題,如慶元元年是周氏家居落成,二年是“春華樓前芍藥盛開”,三年是“蜀錦堂海棠盛開”,六年是“華隱樓成,其下明農堂新接牡丹亦盛開”,其中葛潀“小圃草木猿鶴悉為賦詩,語新而事的,卷軸盈篋”*[宋]周必大:《葛先生潀墓志銘》,《文忠集》卷七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47冊,第768頁。。從吟詠特征看,周必大每次都寫出不同的人生體驗,如《慶元乙卯某與歐陽伯威鈇、葛德源潀俱年七十,適敝居落成,乃往時同試之地,小集圃中,再用潞公韻成鄙句,并錄舊詩奉呈》:
結茅近市壓平川,圍棘爭門想少年。鹿記楊侯歌始舉,鶴歸丁令化飛仙。詩場曾作推敲手,文會今隨出入肩。同甲唱酬殊未已,首篇聊記老而傳。
周必大新居是鄉貢故地,這令他回憶起與老友共同赴試的經歷,“詩場曾作推敲手”句下自注:“吾三人皆以詩賦試于此。”周必大后來為二人撰墓志時指出,歐陽鈇“學廣才瞻,銳欲拔蝥弧而先登,已乃連戰不利,士悼其屈”*[宋]周必大:《歐陽伯威墓志銘》,《文忠集》卷七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47冊,第782頁。,葛潨“鄉評所推”,而鄉評“殆與公舉相為權衡,然彼猶可幸得,而此不容力致”*[宋]周必大:《葛先生潀墓志銘》,《文忠集》卷七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47冊,第767頁。,對二人未能中舉深表遺憾。對周必大而言,貢院是他人生的轉折點,如其所記:“或曰:‘公昔以布衣舉送此地,今官一品而居之,非錦衣晝行乎?’。予謝曰:‘此安陽韓忠獻故事,君毋戲我’。”*[宋]周必大:《蜀錦堂記》,《文忠集》卷五十八,《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47冊,第614頁。雖為戲言,但考場故地的里程碑意義卻毋庸置疑。從年少的同場競技到暮年的同席賦詩,從人生的分道揚鑣到耆老的殊途同歸,世事滄桑的老年體驗具體而豐富。又如《丁巳二月甲子,蜀錦堂海棠盛開,適有惠川繡<晝錦堂記>者,招伯威、德源為齊年會次舊韻》:
曾因客夢到西川,萬戶疏封祇來年。花重錦官思杜老,鶴飛沙苑看徐仙。衰顏尚許任爭齒,淺量深慚賜及肩。照眼蜀妝依繡幌,共驚十載讖先傳。
周必大于題下自注:“楊子直秘書未相識時,從辟成都,嘗夢予使蜀。淳熙己酉春入為宗正簿,謁予相府,退語客云:‘儼然夢中人也。’是時予方自許公徙封益。”因為海棠和川繡,此次集會融入濃重的西蜀元素。周必大雖獲封益國公,但并未到過四川,只能與老友一道在海棠花下向往蜀中生活,“客夢”轉化為眾人的心愿。同時,“共驚十載讖先傳”在追蹤人生軌跡的過程中飽含對命運的感嘆。周必大《二老堂雜志》“記李秀叔夢”載有乾道年間李彥穎向他講述的夢境,夢中位至參政,后來應驗,周必大感嘆道:“信乎,官職皆前定也。”*[宋]周必大:《二老堂雜志》,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75頁。《二老堂詩話》“記夢”則回憶了自己少時的夢境:夢中來到別家書室,四周被叢竹、古柳、噪鴉包圍;后來他到金陵官舍,四周環境驚人相似、恍如夢境。這些追憶都折射出周必大晚年對人生命運的深刻體驗。體驗的分享與“共驚”,增加了耆老酬唱的厚重感。總之,在這六次耆老聚會中,周必大寫出老成人的心路歷程,和文彥博的原詩以及他十多年前的次韻詩相比,這一組創作更能展現個性特色。耆老會空間的遷移、創作者身份的變化、參與者關系的轉換最終影響到酬唱主題與言說方式。
從文彥博的“同甲會”詩到周必大在朝的“丙午坊”次韻詩,再到周必大晚年的“齊年會”酬唱詩,我們能夠以此為線索透視耆老酬唱在兩宋的演變過程。南宋士大夫的老年生活大多是地方鄉土的生活,他們與鄉間處士、家族親眷的充分接觸使原先以同僚為基礎的交際圈發生改變,交往關系的轉換促成酬唱主題的轉移。對官僚士大夫而言,耆老聚會建立在地位相當、身份對等的基礎上,耆老意味著仕宦履歷的資深,擁有廣泛的影響力與一流的精神境界,年齡成為一種文化符號。而在鄉土的耆老互動中,年齡的增長促成交情的篤厚,老者的聚合鞏固了一族一地的命運共同體。集會面向個體情愫,為創作者提供了傾訴空間,鄉土舊聞、家族事務、人生奇遇、命運感觸成為交流重點,耆老唱和的主題更加具體,表達更加個性化。
結 語
以上從身體經驗、處老心態、耆老唱和三個方面分析了南宋詩人老年書寫的主要特征,從中可以透視南渡以后士人生存方式和審美意識的改變。詩人對身體發膚和疾病體驗的描寫,將北宋詩人鮮有涉及或不愿關注的瑣細面呈現出來,這與其說是寫作風格的平熟化,不如說是詩歌表現力的拓展。他們面對衰老時的緊迫感和進取意識,在解決生死焦慮方面比前人涌現出更多的理性精神和實踐力量。詩人將老年互動空間中的公共表達轉換為個性化敘事、將稱頌標舉的話語策略變為人生閱歷的真誠訴說,使老年酬唱與日常生活緊密結合。在諸多變化背后,我們可以看到理學精神對士人生命感覺的塑造,長期的退居經歷對詩歌日常化的促進,以及對人際交往與詩歌酬唱的直接影響,這些也是兩宋文學與文化轉型的重要推動力。
(責任編輯:王學振)
Daily Experience and Internal Transcendence:The Narration of the Aged by Poets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DAI Lu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The narration of the aged in poetry comprises the description of senior citizens’ physical symptoms,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ir life feelings, and their responses in the form of poems at their gatherings, which has undergone new change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mid-Tang and northern Song Dynasties. Firstly, the concrete and penetrating description of anility and sickness has explored new areas for the routinization of poetry of the Song Dynasty, because poets have not only enhanced their elaboration in self-observation through long-term leisureliness but also secularized their body via uninhibited behavior. Secondly, poets appear more diligent and aspirant in the face of senility and death in an effort to rearrange life order in self-renewal; while the internal transcendence of Neo-Confucianism has provided fresh life feelings. Thirdly, the sincere presentation of life experiences rather than communicative discourse conducted in order of seniority and saintliness at gatherings of senior citizens has converted age from a cultural symbol into an emotional bond. The homebound environment has not only changed the personnel structure of elders but also influenced the theme and expression strategies of responding poems.
Southern Song Dynasty; narration of the aged; bodily experience; internal transcendence; gatherings of senior citizens
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第59批面上資助項目“南宋后期四六文與駢體文章學研究”(項目編號:2016M590308)
2016-07-15
戴路(1986-),男,重慶人,文學博士,復旦大學中文系在站博士后,主要從事宋代文學研究。
I206.2
A
1674-5310(2016)-09-007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