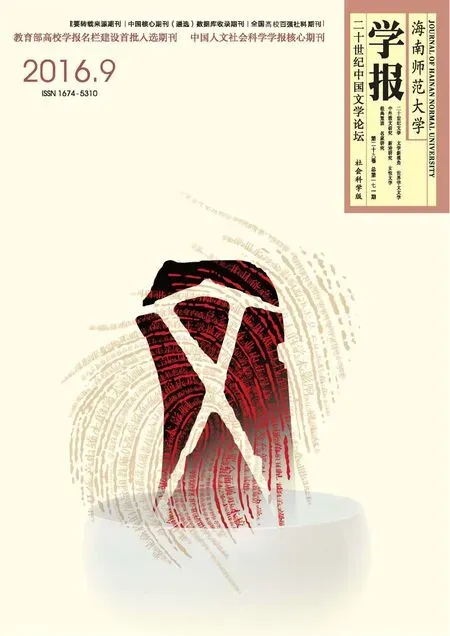索爾·格林的“詛咒”與《金色筆記》的主題
王森林
(北京外國語大學 外國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089)
?
索爾·格林的“詛咒”與《金色筆記》的主題
王森林
(北京外國語大學 外國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089)
“金色筆記”開頭部分的“詛咒”也許屬于作者有意的設計,它和“推大圓石”的故事一起,為理解《金色筆記》的主題提供了線索。萊辛認同和繼承了存在主義者的發現,認為盡管我們的存在荒謬和虛無,但唯一的出路是通過自我反省和抉擇,承擔起被詛咒的命運,做出絕望的反抗。《金色筆記》就是對這一反思權衡和痛苦抉擇的心路歷程的細致記錄。
詛咒;《金色筆記》;存在主義;反抗絕望
多麗絲·萊辛的《金色筆記》自問世至今已有半個世紀,但評論界對它的主題似乎從來沒有定論,萊辛本人對批評家關于這部小說主題的諸多揣測則基本持否定態度,她多次在公開場合嘲弄批評家們的捕風捉影,而國內外相關的一些評論文章,也確實有很多屬于神乎其神的過度詮釋。對《金色筆記》的主題,之所以會形成聚訟紛紜的看法,是因為這部小說確實足夠冗長和復雜,它包含了20世紀眾多重大議題:二戰、國際共運、非洲獨立運動、冷戰、女權問題……同時涉及個人的種種經驗——身體的經驗、兩性的戰爭、父子/母女關系的緊張、存在主義式的生存困境……所有這些都是以支離破碎和含混的方式呈現出來的,這基于萊辛自己的文學觀——她很明確指出現代小說區別于19世紀小說的地方即是“標準的含混和價值的不確定性”。再加上《金色筆記》在形式上種種處心積慮的創造,的確造成了解讀的困難——我們不可能以幾種主題窮盡它,如果批評者小心翼翼地跟著作者游移不定的思路,他很快便會發現自己被引入歧途,在這趟險象環生的旅行中,他會兩手空空,什么也不可能寫出來,更別說得出結論了;但當他試圖理出可行的線索,進行某種整體的建構時,又很容易誤解在整個寫作過程中都保持高度謹慎的作者,至少會遮蔽和刪減她有意造成的多義效果。
然而,這部小說實際上還是可以進行整體解讀的,它反映的是20世紀中期人類整體的生存處境,它在主題上的含混性折射出的是人的處境本身的復雜性,而它在形式上趨于碎片化的實驗,則是因為作者相信,面對當時的形勢和人類經驗,傳統的技巧已難以敷用。因此我們不應該滿足于對《金色筆記》的種種后現代主義的分析,以破碎為借口,放棄對意義的訴求。作為著名的左翼作家,萊辛的文學創作從來都是她介入此在世界和表達價值關懷的最重要方式,在《金色筆記》中,她同樣秉此尺度度量20世紀中期的世界大勢,并與其時風頭正健的存在主義者們達成某種程度上的共識,以一種復雜的方式關照和思考我們的存在。對此,萊辛在《金色筆記》中通過不少細節和意象,其實也做出了暗示,本文正擬通過對文本中幾個細節的設置和核心意象的分析,來闡述這一點。
在金色筆記開頭最顯要的位置,赫然寫著索爾·格林的詛咒:“無論是誰,看這本筆記/都將受到詛咒,/這是我的愿望。”①Doris Lessing,The Golden Notebook,New York :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1999,p.583. 下文中出自該書的譯文只在文中標明頁碼,注釋中不再一一注明。讓這條咒語出自索爾·格林這個人物,也能說明作者是有意為之,對索爾·格林的描寫雖然沒有占很多篇幅,但他對推動情節和揭示主題至關重要,正是他和主人公安娜在金色筆記部分的“崩潰”,使貫穿全書的分裂走向統一;并且和這條咒語相對照,整部小說的第一句話實際上也是由他所寫的。這些細節的設計證明了索爾的重要性,以至于萊辛在1971版序言中說:“在由兩人合作寫出的《金色筆記》中,你已分不清誰是索爾,誰是安娜,分不清他們與書中其他人有什么區別。”鑒于金色筆記在全書結構中的重要地位,這樣的安排也許不能僅僅被視為是索爾一時興起無意為之的惡作劇,用作者萊辛在1971版序言中的話來說:“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樣,在一本稱為《金色筆記》的書里,其中稱為‘金色筆記’的章節可以視為核心,承受全書的重量,表明作者的立場。”(序言,xv頁)盡管寫作的過程會生出種種意外,別的主旨也會進入作品的構造之中,但我們不可否認作者在創作時會有某種整體的設計和主題的定位,而金色筆記開頭的詛咒也許正屬于這樣的設計,其中包含了理解作品主旨的線索。可是要想弄清這條詛咒的含義,還得將其與小說中多次出現的“推大圓石”的故事聯系起來。
“推大圓石”故事的原型顯然來自希臘神話中西西弗斯的故事。*荷馬:《荷馬史詩·奧德賽》,王煥生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 217頁。西西弗斯因為觸犯眾神,受到諸神的詛咒,被懲罰去推大圓石上山,每當大圓石快到山頂之時,就會轟然滾下,然后又得重新去推,如此不斷重復,永無止境。沒有比這更荒謬和讓人感到痛苦的事情,可這正是受到詛咒的西西弗斯無法逃避的命運。西西弗斯究竟為何遭此厄運?加繆從存在主義的角度作了回答,并給這個故事注入新的內涵:西西弗斯被詛咒乃是他為蔑視神祇和熱愛人世所付出的代價,他選擇承擔荒謬的宿命,完成了對命運的超越,并因此成為“荒謬的英雄”。*阿爾貝·加繆:《西西弗神話》,杜小真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第 155-161頁。因此,眾神的詛咒恰恰為西西弗斯由一個存在主義所說的非本真的“常人”(an inauthentic “they”),變成“他自己生活的主人”,提供了契機。也正是這一點,將金色筆記開頭的詛咒與推大圓石的故事聯系在一起,并為我們理解《金色筆記》這部小說的主題奠定了基調。
多麗絲·萊辛在講訴“推大圓石”的故事時,顯然認同和繼承了存在主義者的發現,同樣給予它積極的意義。她正是通過這個故事揭示了《金色筆記》的重要主題之一,一個存在主義式的命題:盡管我們身處一個荒謬的世界,我們從事的事業也許只是徒勞,但我們別無選擇,唯一的出路是絕望中的反抗,明知反抗也可能毫無意義,但仍要堅持下去。這真是一種被詛咒的命運,但這是我們的選擇,也是我們的愿望。當索爾說“無論是誰,看這本筆記都將受到詛咒”時,暗示的正是這種被詛咒的命運,我們應該想到,最先看到“金色筆記”這本筆記本的正是安娜和索爾自己,因此,這種被詛咒的命運是他們清醒認識并主動選擇的結果。
加繆在《西西弗神話》中說:“當荒謬的人肯定時,他的努力就永不停止了。如果有一種個人的命運,就不會有更高的命運,或者只有一個他認作不可避免和應予輕蔑的命運。”*阿爾貝·加繆:《西西弗神話》,杜小真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第 160頁。在《金色筆記》中,安娜和索爾最后以“推大圓石者”自居,正是他們對荒謬的體認,并在絕望中對個人命運做出的肯定選擇,他們選擇的正是這種“不可避免和應予輕蔑的命運”。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是經過痛苦反省之后主動的選擇,因自己的良知非如此不可的選擇,沒有第二種選擇;為什么是“應予輕蔑”的,因為這是幾乎沒有希望看不到結果的事業,如《第三者的影子》中,當保羅對愛拉說“我們兩人都是推大圓石的”時候,他同時說“我們都是失敗者”,因為“我們徒費精力……我們在推那塊大圓石。有時候我希望自己在做這份工作之前就已經死了”(199頁),它耗費人所有的熱情和生命、讓人感到荒謬和痛苦但卻收效甚微、徒勞無功,這是西西弗斯式的被詛咒的沉重的命運。具體到《金色筆記》中的人物,無論是安娜、索爾,還是摩莉、湯姆,他們最終都從個人無望的掙扎和分裂中走出,選擇他們先前所拒斥和不屑的事業,盡管新的選擇也許并不能給荒謬的世界以意義,甚至不一定能安撫他們的痛苦,但重要的不是結果,而是他們的選擇本身,是行動本身。在金色筆記最后的部分,當索爾和安娜走出瘋狂,歸于平靜,他們終于認識到“我們必須相信我們那美麗的無法實現的藍圖(beautiful impossible blueprints)”(609頁)。索爾還對安娜說:“除非你行動起來,不然就會陷入真正的分裂和崩潰。”(609頁)雖然美麗的計劃無法實現,但還是要選擇相信和行動,因為這樣才能拯救自我,超越命運。正如加繆所認為的:“我們并不因為不存在終極希望就失去了所有的希望。西西弗斯的智慧就在于他并沒有把石頭放那兒原地不動,而是推動石頭!”*Thomas Flynn,Existenti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6,p.59.
從無所事事惶恐度日到實踐“嚴肅地列入日程表的事”(609頁),從個人的痛苦分裂走向自我認同和人格統一,從對荒誕世界的懷疑逃避走向承擔和反抗絕望,《金色筆記》中的主人公們所經歷的轉變類似于克爾凱郭爾所說的“信仰的躍遷”(leap of faith),或者薩特所承認的那種“徹底轉變”(radical conversion),憑借這種轉變,人們“會選擇實踐一種擁有本真自由的痛苦生存”*Thomas Flynn, Existenti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6,p.77.,由“不誠的存在”變成“本真的存在”,只有這種本真的自我才能負起承擔的責任,做出正確的選擇。這樣的轉變當然不是輕易就實現的,而是經過長久的反思和權衡,其中充滿掙扎和抉擇的痛苦,而整部《金色筆記》就是對這一反思權衡和痛苦抉擇的心路歷程的細致記錄。在這一過程中,主人公安娜所采取的方式類似于為存在主義者所津津樂道的現象學“本質還原”(eidetic reduction)或“范例的自由想象變換”(free imaginative variation of examples)的方法,“既要純粹地非感性地審視某一時間點的現象,又要通過自由想象,變換各種例子來反省直觀到的現象,從中找出貫穿于各種情況的不變本質”*Thomas Flynn,Existenti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6,p.20.。安娜以五色筆記本、小說、日記、剪報、小標題、括弧、刪減、特殊的文字材料等各種形式,從各種變換的角度審視自己的經驗,而她要尋找和解答的本質就是湯姆向她的提問:“我們為什么而活著?”(259頁),也就是說,生存的意義在哪里?直到她最終做出自己的選擇和解答,而這一過程的艱難和漫長通過小說節奏的沉滯和篇幅的冗長得到了最直觀的呈現。
在轉變發生之前的漫長歲月中,安娜對自我的痛苦反省還沒有完成,無法真正地決定和掌握自身的命運,她處于“不誠”甚至“自欺”的狀態,這表現在她的處境和各種行為之中。即使面對嚴肅的政治信仰問題,她也因為人格中的自欺和猶疑,而無法果斷地判斷、誠實地決定和承擔。“二戰”期間,在非洲的經歷使她意識到她的“黨或者組織的結構中,與生俱來就有一種自我分裂的規律”(64頁),因為他們的信仰已經淪落為虛偽的假面,為排斥異己而制造陰謀,只有野心,沒有責任感,所以在戰爭還沒結束的時候,他們就已經變得“心灰意懶,或迷惘失措”。當戰后回到倫敦,在決定是否加入當地黨組織時,“盡管實際上數月來我一直告誡自己,盡可能不要加入一個在自己看來不誠實的組織,但臨到決定時,我又一再欺騙自己”(146-147頁)。這種自欺并非為她一人所有,而是當時人們普遍的存在狀態,比如他們并不相信黨能使世界變得更好,但卻將之冠冕堂皇地掛在嘴上。(153頁)這導致種種見風使舵和政治投機的現象發生,如值聯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之際,安娜接連收到的三位工會官員出爾反爾的信(47-48頁),如黨魁Rex施之于記者Jack Briggs的伎倆(150頁),等等。自欺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是對另一主體的依賴,以他的判斷為自己的判斷,以他為自己的意義來源,以此逃避應負的責任,比如對于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即使在越來越多的黑幕被曝光之后,人們依然將信將疑,“對于一個偉人,我們都有這種愿望,即使在所有確鑿的證據面前,仍然一遍遍為其塑造權威”(155頁)。因為他們需要這樣的偶像,來維持自身存在的意義。這種自欺當然不可能給他們帶來真正的自我同一性,反而會加深對世界的荒誕感和對自身的分裂感,如安娜所說:“我加入黨原是為了追求自我的完整性,結束破裂的、分離的、讓人不滿的生活方式。然而,加入黨卻加劇了這種分裂。”(154頁)
安娜的寫作障礙其實也根源于她人格中的自欺。作為一個作家,當她面臨存在的尷尬和意義的危機時,自然會訴諸筆端。然而在自欺人格的促使下,她寫作的動機并不是探尋生存的本相,而是遮蔽真實,就像她自己所意識到的:“我將一切變成小說,只是為了以此來掩飾自己的某些東西。”寫作變成了“逃避和遁詞”(evasion)(217頁)。在這種情況下,寫作當然無法再繼續下去。為了改變這種狀況,為了能表達真實、反映世相和生存的境遇,她開始記日記,甚至采用剪報的形式。然而世界本身就是讓人失望的所在,“我所剪下來的都是關于戰爭、屠殺、暴亂和苦難的記錄”(239頁)。“我隨手拿起一份報紙,那上面無不充斥著令人恐懼的消息,在這種情況下,我能寫出什么有意義的東西呢?”(240頁)我們生存其中的世界如此混亂和荒誕,深陷于分裂和瘋狂之中,無法為人們提供活著的希望和意義,尤其是原子彈的出現,使我們具備了從總體上摧毀已知文明的能力,它像懸在我們頭頂的達摩克里斯之劍,隨時讓文明毀于一旦,隨時讓一切努力變成徒勞。難怪在整部《金色筆記》之中,到處充斥著諸如“焦慮”“惡心”“疲憊”“緊張”“恐懼”“瘋狂”之類的非理性的主觀情緒,在存在主義者看來,它們正是對存在的荒誕體驗的標志。這些基于生理和情緒的反應,往往并沒有什么確定的對象,無以名狀但卻擁有本體論的意義,它揭示了“我們所是和我們所無須所是”(we are and we need not be),也就是我們存在的偶然性和虛無感,如安娜所說:“那些畏懼、恐怖和焦慮似乎不在我心里,不在索爾心里,而是某些外在的力量趁機來來去去。”(584頁)那些外在的力量就是世界根本性的荒誕和虛無。但對于存在主義者來說,這些恐懼和絕望并不是消極悲觀的情緒概念,相反,它們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因為人在日常的世俗生活中囿于種種習慣勢力,往往意識不到自己的存在,“只有當他受到恐怖與絕望這樣極端激烈的情緒震動時,才會意識到‘自我’,體驗到自己的存在,從而有可能作出自由決斷(選擇),追尋本真的自我”*解志熙:《生的執著:存在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第 12頁。。這正解釋了湯姆何以在經歷自殺危機之后,反而“平生第一次找到完整的自我”(362頁),安娜和索爾何以在瘋狂和崩潰之后,反而“突破了自己過去所設計的虛假模式,突破了他們用來自我支撐或相互支撐的模式和準則,從而發生融合”(序言,xii頁)。
“金色筆記”部分的瘋狂和崩潰,是安娜自我反省和對存在荒誕感的體驗達到頂點的自然結果,也是她將那種現象學的“本質還原”和“范例的自由想象變換”的方式運用得最為純熟的時候,此時,蓄積已久的轉變力量終于爆發出來。在安娜的夢中,索爾化身為電影放映員,引領安娜去“直面人生”,去“重訪”自己過往的生活經歷。那些曾在黑紅黃藍四本筆記中被一遍遍描述過的往事和場景,以一段段快速閃回的電影鏡頭的方式,呈現在“金色筆記”中。在這種重訪和回望中,因為新的人生經驗和多重觀察視角,讓安娜進一步認識到自己對過去生活和經驗所作的記錄和敘述是“虛假”不實的,認識到自己必須“重建秩序以將自己從混亂的生活中拯救出來”(591頁)。在這種“重訪”中,一些“我曾特別關注過的事”,現在卻“快速滑過,變得無足輕重”,而以前“沒有時間去注意的一些細節”,現在因為放映員的強調,而重新被注意(605頁)。隨著影片的不斷播放,從前需要用四本筆記分別記敘的凌亂的分裂的經驗開始融合,并產生新的經驗和認識,“影片現在已經超出我的經歷,超出愛拉的經歷,超出筆記本的內容,因為這里產生了融合;所見到的不再是分割的場景、人物、面龐、活動和目光,它們都融合在一起了”(606頁)。這些夢中的自由想象和回望,在安娜看來是一種“啟迪”(illumination),使她獲得某種“洞悉”(knowing),這種“洞悉”雖然“無法用文字表達”,但是“洞悉”的時刻“如此有力”,以至于“瞬間學到的東西將教會我怎樣生活,直到老死”(604頁)。她抵達了她所追尋的本質的核心,她為“如何生活”的問題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在這種“洞悉”中她成為一個可以自由決斷的主體,而她的選擇就是做一個行動的人——“一個推大圓石的人”。
索爾說:“無論是誰,看這本筆記/都將受到詛咒,/這是我的愿望。”為什么他要說“這是我的愿望”呢?因為他希望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能理解他們的選擇,并加入他們的行列,和他們一起,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扛起命運的重負,人類社會的希望正在于此。正如他在“金色筆記”最后所說的:“我們的人遍布世界,即使相互不知道姓名,但我們仍相互支持。我們會一直相互支持。我們結成一個團體,我們從來不曾屈服,并將繼續戰斗。”(612頁)是的,不光只有安娜和索爾,那些看到“金色筆記”的人,那些對安娜和索爾選擇的“推大圓石”的命運有深刻理解的人,都將會和他們一起,肩扛起這種被詛咒的命運。這也是我們的愿望。
萊辛曾在一篇批評文章中說,巴爾扎克式的文學已經無法充分表達我們豐富的經驗,而將她的小說和19世紀文學大師們的作品區別開來的標志就是“標準的含混和價值的不確定性”*Doris Lessing, A Small Personal Voice: Essays, Reviews Interviews, ed. Paul Schlueter,New York : Alfred A. Knopf, 1974,p.5.,在1971版的序言中,她也一邊抱怨自己過于簡潔勻整的作品(small neat thing)無法表達“粗糲和無序無形”的經驗(序言,xix頁),一邊驚異于形形色色的讀者對《金色筆記》千差萬別的理解。是的,一部偉大的作品總是經得起讀者一遍遍的閱讀,因此,我在這里的解讀固然有過于拘泥的嫌疑,也只好權當是眾聲喧嘩中的一種,正如萊辛自己在序言中所說:“只有當一本書的構思、形態和意圖不被人所理解時,它才顯得有生命力和影響力。”(序言,xxvii頁)《金色筆記》在今天依然葆有生命力和影響力,因為我們還不能說,它的構思、形態和意圖已經完全被我們認清。
(責任編輯:李莉)
Saul Green’s “Curse” and the Theme ofTheGoldenNotebook
WANG Sen-lin
(InstituteofForeignLiterature,BeijingForeignStudiesUniversity,Beijing100089,China)
The “curse” at the beginning ofTheGoldenNotebookmay be the author’s intended design, which, together with the story of push boulder, provides clu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theme of the novel. Doris Lessing accepted and inherited the discovery of existentialists, and believed that although our existence was absurd and disillusioned, the only way out was to endure the cursed fate and to make a desperate resistance through self-reflection and selection.TheGoldenNotebookis a detailed record of the mental process of introspection, consideration and painful selection.
curse;TheGoldenNotebook; existentialism; rebellious despair
2016-06-20
王森林(1986-),安徽廬江人,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
I3/06
A
1674-5310(2016)-09-009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