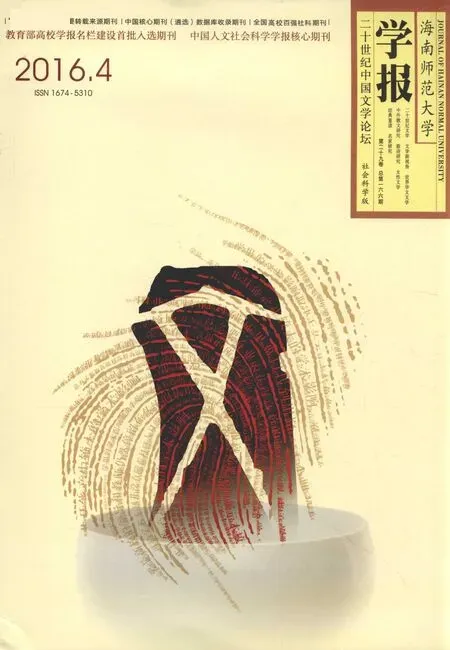“筆會”副刊上的“盛世遺民”與文人文章
張 均
(中山大學 中文系,廣東 廣州 510275)
“筆會”副刊上的“盛世遺民”與文人文章
張均
(中山大學 中文系,廣東 廣州 510275)
摘要:在“新的人民的文藝”的體制壓力下,1956年復刊的“筆會”副刊,實是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舊文人”或“盛世遺民”們展開“文化斗爭”的場所。“筆會”刊發的詞、詩、小品、筆記、賦等文人文章,廣涉歷史掌故、地方風物、酬唱應答。它們不僅復活、召喚了舊式文人遺世獨立、游離現實的審美趣味與人生情懷,且多少恢復了被“階級”重塑了的古典文學與新文學的自我形象。“筆會”由此構成當代文學內部的傳統“幽魂”與異議空間。
關鍵詞:“筆會”;盛世遺民;文人文章;文化斗爭
1950年7月15日,胡喬木在《光明日報》表示:“今天社會上有許多人感覺到沒有議論自由”,應該“使他們團結在光明日報的周圍,而使《光明日報》成為一個‘自由論壇’。做‘野無遺賢’是《光明日報》的責任”*胡喬木:《光明日報的任務》,《胡喬木談新聞出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2頁。。不過從事實看,《光明日報》在此方面收效有限,倒是地處上海的由前自由主義者徐鑄成主持的《文匯報》頗有所成。上海是“舊文人的大本營”,其“舊文人”不僅包括已被指責為以“非常腐化墮落”的故事“麻醉了許多好青年”*丁玲:《在前進的道路上》,《丁玲文集》第6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26頁。的鴛蝴派文人,還包括許多操詞章曲賦之事的民國舊派文士乃至前清“遺老”。甚至,部分因各種原因而邊緣化的新文學作家也忝入“舊”列。1956年10月1日正式復刊的《文匯報》“筆會”副刊,可謂此類在野“遺賢”的薈聚之地。“筆會”不僅如實記錄了時代劇變中部分“舊文人”淪為“盛世遺民”*據當年批判徐鑄成的文章說:“全國解放后,他的野心不能實現,表現很消極。有一個冬天,他和他的一個朋友在北京天壇看太陽,感嘆地說:‘我倆只能做“盛世遺民”。’他認為黨不照顧他,對黨表示不滿,工作一置不積極。”朱友石:《看徐鑄成的“民間報”》,《新聞戰線》1958年第2期。的情緒和經驗,而且還在“毛文體”逐漸統攝漢語寫作的1950年代,以大量七律、絕句、詞、曲、掌故、筆記等已成“封建舊物”的文人文章,重新“復活”了某種與“新的人民的文藝”頗顯“異質”的人生情懷和審美情趣。這兩方面,皆折射了當代文學內部不同文學話語和利益之間的斗爭與“協商”,具有不應被“遺忘”的文學史價值。
一
“毛文體”是學界對受毛澤東影響的寫作風格的一種提法,并不那么嚴謹。它有三點趨向(或曰“約束”):其一,語言上不再以文白雜糅為美,而以明白曉暢、老嫗能解的現代白話為追求;其二,寫作中或顯或隱地寓有階級立場,或含有李陀所分析的“建立寫作人在革命中的主體性”*李陀:《汪曾祺和現代漢語寫作:兼談毛文體》,《花城》1998年第5期。的過程。其三,樂觀氣度。此三點對1950年代寫作影響頗大。在此情況下,傳統文人文章就變得不合時宜,日漸淡出。而在此背后,則是數代“舊文人”情感與生命經驗的被抑制。恰如埃斯卡皮所言:“任何集體都‘分泌出’相當數量的思想、信仰、價值觀或叫做現實觀”,*〔法〕羅貝爾·埃斯卡皮:《文學社會學》,王美華、于沛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7年,第149頁。“舊文人”在思想與趣味上與傳統“幽魂”關聯甚密。他們多習以詩詞曲賦記述內心,且一直存在一些以填詞作句而風流相賞的“圈子”,對新時代深感疏隔。當然,這種情形或也“正常”。研究者指出:“中國革命的特點是一個完全的底層革命,革命的成本是底層社會所承擔。知識精英在革命前、革命中和革命后的地位是邊緣化的,這種邊緣化集中體現在對革命感受的陌生、與革命隊伍的遙遠,最后是在新政權中間缺乏適當的有機聯系去接受和傳遞自己的意志和愿望。”*老田:《毛澤東時代高積累政策決定的知識精英職業利益空間》(2004年5月22日),凱迪社區(http://club.kdnet.net)。而且,“隔閡和對立情緒是長期的和雙方面的”,新政權對“舊文人”(乃至知識分子)的態度亦比較淡漠。其時黨的報刊遵循的是列寧辦報思想:“少登載些政治空談。少登載些知識分子的議論,多接近生活。”*〔蘇〕列寧:《論我們報紙的性質》,《列寧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3頁。因此,黨的報刊(尤其是文學副刊)被要求“走群眾路線”,而“不是根據編者主觀的愛好和興趣,或某些少數讀者的要求來辦副刊”*哈華:《關于解放副刊》,《文藝報》1950年2卷12期。。所謂“某些少數讀者”即指知識分子。
在此情形下,奉命復刊的《文匯報》就明顯被領導和文藝界賦予“補救時弊”的期望。徐鑄成回憶,復刊之際鄧拓曾對他表示:“我們被帝國主義封鎖,也已自己封鎖多年,你們應當多介紹各國科技文化發展的新情況以擴大知識分子的眼界,有利于他們研究提高水平。也要關心知識分子的生活,他們有什么困難,你們可以反映。再如室內外環境如何合理布置,業余生活如知識分子喜歡種花養魚等等,你們不妨辟一個副刊,給知識分子介紹經驗,談談這些問題。”*徐鑄成:《陽謀——1957》,牛漢、鄧九平編:《荊棘路: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第268-269頁。“種花養魚”,毋寧是像鄧拓對“舊文人”生活方式的比喻。可以說,自復刊之日起,“筆會”副刊就是“舊文人”的再生之地。當然,它的作者未必全是“舊文人”,其實亦有重要黨政人物參與(如阿英、田漢等),但他們展示的毌寧是他們作為“舊文人”的一面。而“舊文人”的審美趣味與人生情懷,往往又寄之于詩詞、小品、筆記等文人文章。因此,“筆會”搜求在“野”“遺賢”的編輯定位,對于當代文學內部文類多樣性的重建具有重要意義。對此,胡喬木有明確期望:
文藝都應該搞一些“真正老牌”的小品文——即中國傳統的小品文。小品文同雜文似乎沒有什么區別,但從傳統的習慣看,雜文似乎斗爭性更強些,而小品文則偏重于抒情敘事。總之,都是散文。中國文學從來是以散文為中堅。中國文學史主要就是散文文學史。……副刊應該擔負起復活中國幾千年散文傳統的任務,把中國小品文的傳統繼承下來并且發揚光大。*胡喬木:《改進工作問題(1956年4月15月)》,《胡喬木談新聞出版》,第232-233頁。
“復活中國幾千年散文傳統”的任務,“筆會”無疑落實得極好。當然,散文、小品并非筆者所稱“文人文章”的全部。相對于現代體系中的小說、詩歌、話劇等文類,我們將“舊文人”所習寫的舊體詩、文統稱為“文人文章”。
從1956年10月1日到1957年6月“反右”發生,“筆會”大量刊發了“舊文人”種類繁多的文人文章。其文體,廣涉詞、詩、小品、筆記、賦等,而詞又有文人詞、民間詞之別,筆記亦有文言筆記與白話筆記(隨筆)之分。在筆記中,尤引人注目的,是以專欄形式連載的各類文字。比較知名的有葉恭綽“遐庵談藝錄”、阿英“晚清小報錄”、張伯駒“我所收藏的中國古代法書”、王統照“爐邊瑣談”、黃裳“看劇小記”、張靜廬“出版雜記”、金兆梓“逞肊之談”、吳小如“讀人所常見書日札”,以及焦菊隱“菊隱隨筆”、張文元“儒林內史”等。這些文人文章記載了各色“舊文人”或“舊知識分子”在建國初期特殊的生存感受。默爾·戈德曼認為,1949年后“大部分知識分子歡迎共產黨,因為他們厭惡國民黨,因為他們贊賞共產黨能夠統一國家,能夠在幾十年的戰亂之后提供財政保障”*〔美〕費正清、麥克法夸爾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王建朗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49頁。。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實的——即使經過《武訓傳》批判、“胡風案”沖擊,知識分子仍保持著民族主義熱情。“筆會”文章(尤其舊體詩詞)比較真實地記載了這種普遍情緒。諸如《國慶頌·調寄“浪淘沙”》(高潮)、《雙喜吟》(高潮)、《東方紅遍環瀛十六韻》(黃炎培)、《鷓鴣天·聞湛江港將開港喜賦》(葉恭綽)、《周總理出國訪問報告讀后志感·調寄南鄉子》(黃紹竑)、《南鄉子·讀黃季寬先生〈周總理出國訪問報告讀后志感〉用原韻和作》(吳湖帆)、《沁園春·歡迎伏羅希洛夫同志》(龍榆生)、《題武漢長江大橋》(吳瓊華)、《三門峽紀游·一九五七年初視察三門得句》(田漢)一類作品,都洋溢著由國家建設激發而生的盛世之感。其中,不乏詞筆、意境皆佳之作,如沈祖棻《浪淘沙·題長江大橋》:“橫渡大江中,愁水愁風。忽驚破浪奪神工。一道長虹飛兩岸,橋影臨空。形勝古今同,三鎮當沖。莫憑往事吊遺跡。平卻向來天塹險,多少英雄!”這些舊式文章,反映出“舊文人”對新興國家的共鳴,也有效地參與了國家認同的生產。而另有一些詩詞,更以日常形式記載了作者細微而真實的情緒,如王利器《北京竹枝詞》云:“今日門前家長齊,接回兒女過星期,誰家小小渾忘事,卻把媽媽叫阿姨”,“拖兒帶女學當家,百貨樓中望眼花,忽聽播音播招領,才驚身畔沒娃娃。”*王利器:《北京竹枝詞》,《文匯報》1957年1月18日。
除感奮于新時代外,這些文人文章還略施諷刺之筆,指責社會現象。不過,其批評對象往往指向已經成為“過去”的軍閥政權或國民黨政權,如“菊隱隨筆”中刊出的《如此“調查了解”》(1956年11月26日),諷刺蔣介石到冠生園“調查”物價的形式主義。時亦有針對建國初期社會眾生相的,如張文元“儒林內史”專欄中的《士別三日》,談及學生對老師稱呼的變化:入學時稱“王老師早”,畢業時稱“再見,王教授”,工作后稱“咦,王同志,好久不見了”,升官后則呼為“老王,那里去?”*張文元:《士別三日》,《文匯報》1956年10月15日。又如前《西風》主編、1950年曾在《文藝報》上作過檢討的黃嘉音的“伊索寓言新解”專欄中的《兩個口袋》一文。伊索寓言中說,每個人身上都有兩個口袋,前面口袋裝別人的缺點,后面口袋裝自己的。對此,黃加注曰:“如果你那個裝著自己缺點的口袋,還是掛在背后的話,應該把它也放到前面來,讓自己不斷地看到自己的缺點,不斷地糾正自己的錯誤。”顯然,這類諷刺在“分寸”把握上頗見用心:“舊文人”難以具備“中心作家”的批評勇氣。
比較而言,“筆會”刊發的“文人文章”之于此代知識分子經驗的記述,更具價值的是有關他們在此“天翻地覆”之時代真實內心情緒的反映。無論這批“舊文人”面對民族重新崛起有多少感奮,但他們中間多數人作為“盛世遺民”的邊緣身份(包括部分位高權輕者實亦如此)卻是更為私人的經驗。對此,陳思和表示:“以留在大陸迎接新政權的作家來說,內心世界也是各種各樣的,有的縱情歡呼,有的小心窺視,有的驚惶失措,也有的隱姓埋名,……從那時期的文學創作中我們大致可以看到,在一個比較單純的革命時代里,知識分子的心理世界卻是不單純的。”*陳思和:《重新審視50年代初中國文學的幾種傾向》,《山東社會科學》2000年第2期。并不“單純”,實在是“舊文人”的實際精神狀況。多多少少,這些心境會在“筆會”上有所流露。比如劉大杰《北望》詩。詩前題語云:“病中割腸,臥床三月,卷簾小望,滿眼春光。得何其芳、陸侃如、游國恩三同志來信,談中國文學史編寫事,寄詩答之。”詩則稱:“一病驚三月,新年復舊年。奮飛心尚遠,欲步足難前。剖腹休言苦,斷腸亦可憐。倚床常北望,朋輩自翩翩。休言文章事,能追驥尾乎?病余詩意冷,心淡筆尖枯。煙月長今古,河山壯畫圖。江南腸斷日,春色滿平蕪。”*劉大杰:《北望》,《文匯報》1957年3月29日。顯然,此詩含有不遇之怨艾。“倚床常北望,朋輩自翩翩”,是對何其芳、游國恩等舊朋“高升”當途的企羨,“休言文章事,能追驥尾乎?”是對自己被時代“遺落”的憤懣與不平。以此觀之,此詩況味與孟浩然的“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大略仿佛。而這背后,折射出中國舊式知識分子駁雜的仕宦情緒。不過,有關此類“盛世遺民”心境的記述并不多見,但它們在文人文章中的留存,是建國初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歷史“痕跡”,也是當代文學內部“毛文體”一統天下之下“縫隙”的顯現。
二
“筆會”文人文章的價值,更在于某種文人文學趣味和人生情懷的展示。按照W·C·布斯的分析:“每一部具有某種力量的文學作品——不管它的作者是否頭腦里想著作者來創作——事實上,都是一種沿著各種趣味方向來控制讀者的涉及與超然的精心創作的體系。作者只受人類趣味范圍的限制。”*〔美〕W·C·布斯:《小說修辭學》,周憲譯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137頁。而對“趣味”,董橋亦有所解釋。他認為,“趣”乃“品味、癖好之微妙”,“屬于純主觀的愛惡,玄虛不可方物,如聲色之醉人,幾乎不能理喻”,“正是袁宏道所謂‘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說品味》)那么,所謂“舊文人”的“唯會心者知之”的“趣味”又具體為何呢?可以說,它表現為中國古人一種以對世界的空無體驗為底而以對現世物象細節的涵詠品味為表的審美趣味。恰如林語堂所言:“我們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須盡歡……我們會毫不猶豫地放棄那些捉摸不定、富有魅力卻又難以達到的目標,同時緊緊抓住僅有的幾件我們清楚會給自己帶來幸福的東西。我們常常喜歡回歸自然,以之為一切美和幸福的永恒源泉。盡管喪失了進步與國力,我們還是能夠敞開窗戶欣賞金蟬的鳴聲和秋天的落葉,呼吸菊花的芬芳。秋月朗照之下,我們感到心滿意足。”*林語堂:《中國人》,上海:學林出版社,1994年,第335頁。無疑,這種閑適的、自逸于山水、文字的趣味在“五四”以后大受批評。用丁玲鄙屑的說法是,這類趣味把文學當成“一個很藝術的玩藝”,而“五四”文學恰恰反對這種趣味,而以改造社會為要緊之務:“他們對舊社會是了解得深徹些,他們深感痛苦,他們是以戰斗的革命的姿態來出世的,而且擔任了前鋒。他們要求文學革命,痛恨文言文,他們去實踐,寫白話文小說,寫新小說去反對文言文,而且他們寫小說,寫詩,不是因為他們要當小說家或詩人,也不是覺得這是一個很藝術的玩藝,也不以為藝術有什么高妙,他們就是為的要反對一些東西,反封建,反對帝國主義去寫的。”*丁玲:《五四雜談》,《文藝報》1950年2卷3期。而到了革命和“毛文體”的年代,這類趣味就更遭排斥。
在《人民文學》《文藝學習》等刊物上看不到這類“趣味”的痕跡,甚至在私人交游中也日漸廖落。“筆會”則給予這種趣味以公開、自由的空間。恰如徐鑄成所說:“為實行鄧拓同志的建議,關心知識分子的生活情趣。”*徐鑄成:《陽謀——1957》,《荊棘路: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第272頁。徐所談“知識分子的生活情趣”,即與革命相疏離的舊式審美趣味。這在“筆會”文人文章中有明確體現。這些文章據內容可分為三類。其內容或異,但“趣味”實乃共之。一是歷史掌故。為“筆會”撰稿者多有海上名宿,如開辟“遐庵談藝錄”專欄的葉恭綽,出身前清世家,祖父蘭臺(南雪)為清末翰林,曾官戶部郎中、軍機章京。葉恭綽少秉家學,京師大學堂畢業,以書畫、收藏名世。早年為“交通系”重要成員,活躍于政界,晚年別署矩園,室名“宣室”。此般人物,大有“遺老”之概。其他掌故作者如夏枝巢、鄭逸梅等實亦類似。“筆會”刊登文史掌故頗多,如《康有為進用原始》《說刻絲》《墨緣彙觀著者可確定為安歧》《詞林典故》《宋陳簡齋銅印》《陵園仰止亭詩事》《洪承疇墓志的發現》《謔名偶志》《大方善謔》《徐光啟的九間樓》《第一部油印書籍》《反面人物信札中的太平天國史料》《看南宋畫院的名作》等。掌故本身是知識性的,但談昔論往之中,自有趣味存焉。試以夏枝巢《居仁日覽》小文為例:
袁世凱之在位也,命內史諸人于史鑒中,采取有關治亂之源,民生利弊之事,及先代諸名臣奏議,分類擇錄,日進一冊,名之為:“居仁日覽”。居仁者,就所居之堂名。日覽者,仿《太平御覽》例也。聞初頗依時披讀,后漸擱置,而內史之采錄如故。余嘗見之,蓋用宣紙精裱,界朱絲為欄,繕寫亦極工整。聞當時秉筆者,為夏壽田、嚴復諸人云。*夏枝巢:《居仁日覽》,《文匯報》1956年10月3日。
袁世凱也好,洪承疇也好,這些有關“前朝舊事”的漫憶,無關批判,甚至無關感傷。如此文字中間,更多流露的是將歷史付與談議的“閑”與“遠”的精神姿態,以及由之而生的某種智慧的愉悅。另一類文人文章集中于地方風物。它的作者大都是閑散“舊文人”,如已被排斥在“文壇”之外的前鴛蝴派作家。其中,陳慎言在“筆會”上開辟了“北京俗話”專欄,范煙橋開辟了“蘇州的橋”專欄,專門介紹地方古跡及特殊風物。此類文章涉筆甚廣,其“風物”甚至還可延至蟋蟀(程小青《蟋蟀瑣談》),延及蝌蚪(周瘦鵑《閑話蝌蚪》)。無論是介紹北京櫻桃溝,還是談論江南蟋蟀,其目的都不在于啟蒙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那種“改變社會生活的作用”*〔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與后殖民文學》,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10頁。,而在于給現實中的文人提供一種疏離現世俗務的文字世界,創造“閑”而超脫的精神境界。施蟄存《閑話重陽》一文,頗可代表這種風物之“趣”。此文由王維詩句“遍插茱萸少一人”衍發開去:“不過疑問還有。到底這插戴的茱萸是花呢,是葉呢,還是果實,在唐宋人的詩詞中還看不出來。查圖經本草云:‘吳茱萸今處處有之。江浙蜀漢尤多。木高丈余,皮色青綠,似椿而闊厚,三月開花,紅紫色,七月八月結實,似椒子,嫩時微黃,至成熟則深紫’”,“這樣看來,插頭的原來是茱萸子,或者說是球果,決不可能是花也。遺憾的是,唐宋人既說這種植物是‘處處有之,江浙蜀漢尤多’,而我卻至今還不認得,真該為‘儒者所恥’了。”*施蟄存:《閑話重陽》,《文匯報》1956年10月12日。這般文字,有明末小品的風致。而夏枝巢有關北京蘭花的記述,儼如宋人筆法與心境:“蘭花,云花,太平花。閩人蔣斌,有蘭花百盆,皆珍品也。蔣逝移贈公園,未易歲而盡萎。周養庵家,某歲云花盛開,不移時而凋。惟故宮之太平花尚在,年年有往賞者。是花聞清初四川省所進,以北方不恒見,特署與佳名,然實則是玉蕊聚八仙之類耳。”*夏枝巢:《北京花事》,《文匯報》1956年12月5日。在政治運動頻繁的年代,“筆會”這些文人文章以閑遠、幽靜、不聞現世的舊式風度,復活、召喚出了中國人內心那種脫世的隱逸情懷。甚至毛澤東這種畢生致力于社會改造的現實豪杰,也為“筆會”所吸引。在接見徐鑄成時,他即以“琴棋書畫、花鳥蟲魚”八字稱贊“筆會”風格。“筆會”因此構成了“新的人民的文藝”的異數。王曉明認為:中國現代文化“從一開始就顯露出強烈的務實傾向。它的幾乎所有核心觀念,都是針對現實的社會危機設立的——怎樣理解中國的危機?中國是不是還能得救?如何才能得救?中國人需要在觀念上作哪些改變?讀書人又該對國家負什么責任……新文化滿腦子都是這一類的焦慮”*王曉明:《思想與文學之間》,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第3頁。。“新的人民的文藝”同樣承載此類焦慮。而“筆會”復活的趣味與情懷與之相去甚遠。
這類“舊文人”的古典趣味在第三類文人文章中更為突出,此即酬唱賀吊之作。唱和應答乃古人雅集之風,進入新中國后,酬唱作為文人生活方式與群體認同的一部分,仍余脈未盡,“筆會”刊發此類舊體詩詞甚多。1957年,蘇聯漢學家艾德林教授訪問中國,與中國“舊人物”多有往還。“筆會”先后刊出了夏承燾、龍榆生贈詞。夏氏贈詞《醉花蔭》云:“贈別黃花香滿袖,莫問銷魂否。翻得醉花蔭,贏得佳人,到處呼‘詩友’。欠我杭州詩幾首?問白堤楊柳。臨去看吳山,一片眉痕,濃似西湖酒。”詩里詞外,飄動著隱逸情致,仿佛舊式文人之間相互欣賞、相互交流場景的重現。而賀詩更見文人之間心心相印、彼此共享的文化精神。1956年10月,出版家張元濟逢90歲生日,友朋紛紛以詩賀壽,如葉恭綽《調寄沁園春·賀張菊生先生九十歲生日詞》,如陳叔通《賀張菊生九十生日》。后者為長調,曰:“黨錮余生幸獨全,匆匆五十九年前,滄桑歷盡開新運,紅起東方照大千。記曾科舉尚相沿,通藝開先設在燕,自是識時為俊杰,望風興起武城絃。首開風氣譯兼編,回憶書棚共硯田,事與時移欣有托,猶推耆宿領群賢”,“誼兼師生老彌堅,霜雪相看各滿顛,每歲南歸皆省視,榻首低語盡纏綿。佳兒定省最欣然,尤愛雛孫學業專,留得涉園圖卷在,故知名德紹家傳。鹿裘帶索是神仙,猶耆肥鮮足睡眠,我少九齡慚薄植,尚憑勞力駑加鞭。風光大好菊花天,掩映修髯分外妍。安得飛觴遙共醉,期頣有等續吟篇。”此詩大有古風的樸直,熔知交之誼與論人斷世于一體。較之賀詩,吊詩則另見古典氣質中的諷世之痛或“物傷其類”的喟嘆。前者如謝無量之吊孫中山。1956年11月13日,“筆會”刊出謝無量《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恭逢中山先生誕辰九十周年紀念賦此詩》。詩稱:“彌留仍受命,感激竟佯狂;執紼西山晚,韜精北海藏。微軀沾疾病,薄力愧承當;世論終思禹,孤懷昔就湯。為邦賴賢哲,盛業正開張;空慚舊賓客,重到一凄涼。”后者則如盛家倫猝逝后一時并至的哀悼之作。其中葉恭綽六絕《悼盛家倫》音韻流暢,意境古樸,而感傷尤深:
朝來灑淚獨傷神,默默無言嘆息頻,似有無窮煩惱事,誰知為慟盛家倫。家倫近歲始論交,蹤跡雖疏意自超,不以恒惰來待我,回思那禁淚如潮。老來傷逝總凄其,朝露情懷只自知,爭忍歌聲聞夜半,歌聲腸斷在臨歧。博學宏才世所希,窮搜佳籍助遐思,香煙繚繞爐灰燼,忍憶回談七調碑。千里送君終一別,況兼永別阻臨喪,不知靈爽今何托,明月依然在屋梁。家世茫茫孑一身,卅年漂泊更何因,他年若撰聲家史,莫漫篇中失此人。*葉恭綽:《悼盛家倫》,《文匯報》1957年5月15日。
這種物傷其類的吊挽,折射著與“新的人民的文藝”頗不協調的趣味、情懷以及某種舊式文化認同。由于盛家倫尚非“新的人民的文藝”中的“典范”人物,所以這種知音之唱并未引起反彈,但對魯迅就不太一樣,施蟄存吊魯迅詩就一度引起爭議。施蟄存早年與魯迅有過“莊子與文選之爭”,現人去事存,施不勝感慨,賦詩相吊。全詩對魯迅有崇高評價,尤其末四句:“感舊不勝情。觸物有余悼。朝陽在林薄。千秋勵寒操。”以物寄情,借景抒懷,深有物是人非之痛。不過,在魯迅已被“圣化”的時代,施蟄存這種知音嘆稀的傷感尤其他在小序中顯示的與魯迅平等對話的姿態,也受到非議。小序原文為:“余早歲與魯迅先生偶有齟齬、竟成胡越。蓋樂山樂水、識見偶殊。宏道宏文、志趨各別。忽忽二十余年、時移世換、日倒天回。昔之殊途者同歸、百慮者一致。獨恨前修既往、遠跡空存、喬木云頹、神聽莫及。丙申十月十四日、國人移先生之靈于虹口公園。余既瞻拜新阡、復睹其遺物。衣巾杖履、若接平生。紙墨筆硯、儼然作者。感懷疇昔、頗不能勝。夫異苔同岑、臭味固自相及。山苞隰樹、晨風于焉興哀。秉毅持剛、公或不遺于睚眥。知人論世、余豈敢徇于私曲。三復逡巡、遂愴恨而獻吊云。”對此“小序”缺乏自認錯誤的態度,蕭充頗為不滿,并撰文予以批評。
酬唱賀吊、地方風物、歷史掌故,這三類文人文章構成了復刊以后“筆會”重要的精神認同。一種屬于文人階層共有的趣味和情懷在“琴棋書畫、花鳥蟲魚”的面目下得到重建并生長。在“新的人民的文藝”的年代,它毋寧是不合法的“知識”。但在“鳴放”整體氛圍與《文匯報》作為自由主義報紙的特許下,尤其在政治領袖同樣潛藏著一顆“舊文人”靈魂的現實情形下,這種趣味又以合法方式存在著,并創造了為各式“盛世遺民”所共享的話語空間。挪用凱爾納的說法,“筆會”具有不可或缺的文學史價值——在新文學尤其是“新的人民的文藝”中,舊式文人或士大夫式“趣味”“被壓得鴉雀無聲并從主流文化中被一筆勾銷了”,但“筆會” 毋寧是以“斗爭”的方式,幫助這些“被排除在主流以外的群體的種種觀點、經歷和文化的形式”得到了適宜“表達”。*〔美〕道格拉斯·凱爾納:《媒體文化》,丁寧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6頁。
三
凱爾納提及的“文化斗爭”在“筆會”中未必有明確規劃,但其文人文章的確有這方面的事實效果。這不僅指文人文章對舊式文人趣味的復活與再現,亦指這些文章客觀上對古典文學傳統和新文學傳統的重新塑造。何以如此?其實緣于1949年后古典文學與新文學在“新的人民的文藝”主宰敘述中的被動處境,古典文學尤其尷尬。對此,周蕾分析說:
典型的世界文學大都用上一種面向未來和倡議進步的修辭,要中國文學跟世界文學并列這份熱切渴望,由是同時地產生了一個“尚未啟蒙”和“傳統”的中國,這個“舊”中國跟頹廢、黑暗和死亡等隱喻結下了不解之緣,成為“新”中國的“他者”。*周蕾:《婦女與中國現代性——東西方之間閱讀記》,臺北:臺灣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第180頁。
顯然,古典文學作為“舊”中國的一部分,亦“跟頹廢、黑暗和死亡等隱喻結下了不解之緣” 。甚至,隨著“新”的標準的推移,一度逐古典文學而代之的新文學也被推入落伍與保守的位置。故在1949年后由新民主主義主導的“新的人民的文藝”敘述中,古典文學傳統與新文學傳統都經受了異己邏輯的“再敘述”,多少都他者化、淪失了其本來“自我”。在此情形下,“筆會”就具有了不可忽視的“文化斗爭”的意義。它的作者多有在文學趣味上對新民主主義并不熱衷的“盛世遺民”,并不那么臣服于黨的文人在“新的人民的文藝”/新文學/古典文學之間建立的等級界限。故而,在他們撰寫的詩詞曲賦、筆記小品中,沒有延安文學的影子。相反,屢屢呈現著與革命不甚相同的文學記憶與審美想象。如果薩義德的話是可信的話——“知識分子的職責:挖掘出遺忘的事情,連接起被切斷的事件”*〔美〕愛德華·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第25頁。——那么,“筆會”毋寧承擔了“知識分子”的職責。
“新的人民的文藝”的文學史敘述,無論對于古典文學還是對于新文學,皆以“階級”一詞作為主導概念,這就使后兩種傳統不可避免地遭到“扭曲”,而不完全是它們自身,甚至不再是它們自身。鮑爾德溫認為:“傳統并不是中立和客觀的,不是某種等待著人們去發現的東西,傳統是文化地建構的。在建構和重構的過程中,有些東西被包容進來,而另外的則被排除出去。”*〔英〕阿雷恩·鮑爾德溫等:《文化研究導論》,陶東風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2頁。顯然,“人民性”和“進步性”分別成為古典文學、新文學被“建構”的標準,而它們作為知識階層在不同時代精神趣味和生活方式表達的特征就往往“被排除出去”。“筆會”文人文章則大不相同,它們不以“階級”為追求,而以自在性情談文析理,因此頗能見出古典文學和新文學真面目。古典文學方面,“筆會”諸多文章有所議論,如施蟄存《秦時明月漢時關》(1956年10月6日)、聞樂《詩經注解質疑》(1956年10月27日)等。施蟄存《秦時明月漢時關》文,展示了“舊文學”的精微與豐富:“明代詩人李于麟選唐詩,認為這首詩是唐代七言絕句中壓卷之作。這樣一推崇,引起了明清以下許多詩評家的議論。王世貞首先作了一個解釋:‘李于麟言唐人絕句當以秦時明月漢時關壓卷,余始不信,以少伯集中有極工妙者。既而思之,若落意解,當別為去取,若以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間求之,不免此詩第一耳。’(藝苑巵言)王世貞的意思以為這首詩好在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之間,所以它不落意解,就是說不能從字句上去解釋,所以好”,“直到明末,唐仲言著唐詩解,才對這首詩有較好的解釋。他說:‘匈奴之征,起自秦漢,至今勞師于外者,以將之非人也。假令李廣而在,胡人當不敢南牧矣。以月屬秦,以關屬漢者,交互其文,而非可解不可解之謂也。’……這一說法,因為是從修辭學的觀點來解釋,就非常切實。”*施蟄存:《秦時明月漢時關》,《文匯報》1956年10月6日。這種“交互其文”的詩歌藝術,不關階級不關“人民性”,但無疑是舊式文學“趣味”的真實表現。較之古典,“筆會”涉及民國新文學的篇什更多。在1950年代初期,黨的文學管理部門一直致力于新文學經典重估工作。一方面,通過對少數代表性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老舍等)酬以名譽性高位,以示對于新文學“過去”經典位置的承認,另一方面,又通過有限的文學史評價、作家的自我修改乃至否定,剝奪其作為現實的文學資源的意義,使之“作為風化了的遺跡而被貶降到過去”*〔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國歷史與東方主義問題》,羅鋼、劉象愚編:《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74頁。,淪為“死去的經典”,不再成其為“新的人民的文藝”的效仿對象。但“筆會”顯然沒有參與此項文化工程。相反,大量新文學親歷者在“筆會”上憶昔談往,如《子愷老人的生活》(1956年12月3日)、《回憶初期的開明書店》(錢君匋,1956年12月19日)、《我驚喜地看到了秋瑾遺像》(胡明樹,1956年10月11日)等,這類往事追懷還往往對“新的人民的文藝”的史述形成質疑。如石揮回憶唐槐秋說:“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今天,我想起了他,一位話劇界的老前輩,話劇職業化的開拓者。尤其在今天不太被人們提起而漸漸遺忘了他的時候,希望重新回憶一下他的過去,我以為是有好處的,無論是他好的一面或是有缺點的一面。……我建議在中國話劇運動史上對唐先生不能以‘一筆帶過’的態度來對待,而應以相當的篇幅來評論他,給予他以正確的評價。”*石揮:《懷念唐槐秋先生》,《文匯報》1956年10月6日。在這里,質疑的實質在于對于階級史述的疏隔甚至“斗爭”。又如若瓢和尚《回憶郁達夫》文,文字幽靜淡泊,所憶郁達夫亦只是一不拘形跡的文人,而筆不涉“反封建”之類。文末附有和尚吊亡詩一首:“毀家一怒走炎荒,骸骨未收慨鬼倀;湖上尋詩無好句,舊游處處感凄涼。”此詩也只就事言事,且充滿故人傷挽,而與“不斷進步”的階級史述毫不相涉。從某種意義上講,在新文學被“階級”不斷重構的情形下,這類回憶就不無恢復、抵制意義。這種“恢復”最集中地體現在有關魯迅的回憶與評述上。建國初,根據瞿秋白“兩期論”(從進化論到階級論)重構魯迅作為一位“階級戰士”的形象,一直是魯迅研究的核心。然而,“筆會”卻對馬克思主義邏輯下的“魯迅”深表質疑。趙儷生表示,“魯迅論美國”、“魯迅論科學”、“魯迅論婦女”、“魯迅論辮子”等研究題目令人頗感“擔心”,因為研究應當“首先深入內容,從深入中找到自然的邏輯劃分的線索,然后具體地考慮專題去進行研究”,而“從表面進行形式的劃分”,“只能對魯迅先生進行‘凌遲’,或者至少也是替魯迅式諷刺雜文提供更多的資料而已”。*趙儷生:《稍談研究魯迅的方法》,《文匯報》1956年10月15日。“凌遲”之說可謂對“新的人民的文藝”史述的尖銳諷刺。早年鄉土小說家許杰談及魯迅時,也很有意“恢復”魯迅的啟蒙者形象,大力強調魯迅國民性批判的現實意義,認為《弟兄》“自然不及《狂人日記》那樣的鮮明,但他挖掘之深,概括之廣,一直到了現在,雖然我們社會制度已經改變了,但那種由于私有財產制度長期統治形成的思想狀態,不是還深深地潛藏在我們的思想深處嗎?”“魯迅的現實主義的深廣意義,我以為,在這種地方,又體會到了。”*許杰:《魯迅的〈弟兄〉》,《文匯報》1956年10月16日。不過,較之這種挑戰性回憶,“筆會”更多是從日常細節談論魯迅,如紹興周家長工鶴照回憶魯迅舊事(見羅洪《他是個忙人》,1956年10月8日),如許廣平回憶魯迅的“樸素的戰士的生活”(見許廣平《魯迅的日常生活》,1956年10月9日)。尤其欽文的回憶,更是圍繞著魯迅睡覺、休息等瑣事細節展開:“魯迅先生當面送給我他編譯的法捷耶夫的《毀滅》,我看他親自給我包扎,是包扎得這樣齊整美好的,因為我已經買了一本,一直到抗日戰爭中遺失,我始終不忍把那個書包打開。”*欽文:《魯迅先生的工作和休息》,《文匯報》1956年10月17日。這類瑣碎而真實的回憶,與“階級戰士”無形中拉開了距離,在50年代可謂是“主導敘述”外一種有意味的“雜語”。
這種有關新文學和古典文學傳統再現的“雜語”,以及“舊文人”審美趣味和人生情懷的復活,以及詩詞曲賦等文人文章的新生,都使“筆會”在1949年后逐漸固化的文學體系中獲得了稀缺性價值——它有力地對抗著來自“主導敘述”的排斥,為久被“遺忘”的舊式文章及其情懷爭取了有限的話語空間。不過,恰如詹姆斯·卡倫所言:“各個社會集團和階級使用媒體和其他資源推廣自己觀點和利益的機會是不均等的”,*〔美〕詹姆斯·卡倫:《媒體與權力》,史安斌、董關鵬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46頁。這類盛世遺民的文體與情懷并未獲得長久的自我表達。隨著“反右派運動”的發生,它們也受到一定削弱。當然,由于這些文人文章多以閑散之態出現,由于高層領袖舊式趣味的存在,兼之“筆會”并未對當時思想秩序形成現實“威脅”,這類文章及其作者在“反右”颶風中也算是有驚無險,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續,并為“新的人民的文藝”的整編留下幾許飛地。
(責任編輯:畢光明)
“Adherents of Prosperity Era” in the Supplement of the“Pen Club” and Literati Articles
ZHANG J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new people’s literature and art” system, the “supplement” of the pen club, which resumed its publication in 1956, was virtually an arena for “cultural struggle” conducted by “scholars of the past era” or “adherents of the prosperity era” who were excluded from the mainstream culture. Literati writings published by the “pen club” like Ci poems, poems, essays, diaries, Fu, etc. mostly involve historical anecdotes, local scenery and responses in the form of dedication poems, thereby not only having revived and summoned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solitary and aloof aesthetic taste and life feelings but also somewhat restored the self-image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new literature which was reshaped by “class”. Therefore, the “pen club” constituted the space for traditional “spirits” and dissent with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Key words:“the pen club”; adherents of the prosperity era; literati articles; cultural struggle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十七年文學雜志與文學生產”(批準號:10YJC751118)
收稿日期:2016-03-16
作者簡介:張均(1972-),男,湖北隨州人,文學博士,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5310(2016)-04-0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