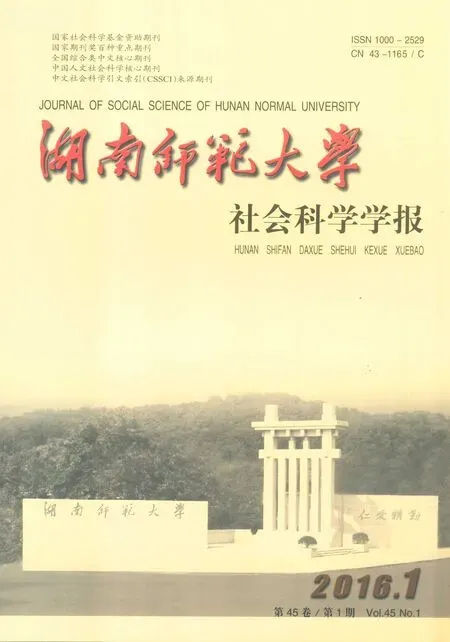辭賦對話模式的生成與展開
楊合林
?
辭賦對話模式的生成與展開
楊合林
辭賦之對話模式主要表現為三種,即人與神的對話、人與人的對話和人與自然的對話。三種模式次第展開,映射出中國歷史文化變遷與士人主體精神消長變化之大勢。上古巫術文化向周秦理性文化轉化,帶來了人與神對話向人與人對話的轉向,人的主體精神得到前所未有之開顯與發揚。此一動向生動地體現在作為辭賦源頭的《莊子》、《楚辭》和《荀子》中。漢以后之大賦、小賦共生共長,同時也構成一種此消彼長的互動關系。大賦以張揚天子權勢或國家意志為職志,在人與人的對話中,士人主體精神欲揚反抑;小賦以寄情于物或田園山水的方式,在人與自然的對話中,士人主體精神得以別開生面。
辭賦;對話模式;士人;主體精神
劉勰《文心雕龍·詮賦》說:“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這是說賦有兩大特征,一是在結構上以主客問答作為其基本架構,一是在文辭上極盡鋪張夸飾之能事。后世對于賦的后一特征強調頗多,而對于前者卻未免有所忽略。探討辭賦對話模式的生成和展開過程,不僅可以加深對辭賦這一中國文學重要文體的了解,還可由此約略窺見中國歷史文化變遷與士人主體精神起伏消長之大勢。
一、賦之源:從人與神的對話到人與人的對話
原始文化是一種巫術文化,現存最早的文字——甲骨卜辭,就是有關人神對話的記錄,如言:“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來雨?其自東來雨?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①《禮記·表記》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這表明甲骨卜辭所反映的此類情狀在殷商時代具有普遍性,是早期先民心理的基本樣態。這種狀況到西周開始有了改變,如《表記》所說:“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從西周開始,“民”、“人”開始取代“神”、“鬼”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尚書·泰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左傳》“莊公三十二年”載史嚚語:“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先進》)從聽命于神到聽命于人,意味著原始巫術文化向周秦理性文化的演變。
戰國末期是辭賦的發軔期,莊子、屈原、荀子均于辭賦的發生有所貢獻和影響。劉勰《文心雕龍·詮賦》論賦體起源:“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則賦也者,受命于詩人,而拓宇于《楚辭》者也。于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劉勰這段話,每作為賦體起源與成立的權威概括。他對荀子和屈原在賦體初起過程中的作用都有具體說明,但未涉及莊子。
宋王十朋《會稽風俗賦序》說:“昔司馬相如作《上林賦》,設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相答難。子虛,虛言也;烏有先生,烏有是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故其辭多夸,而其事不實,如盧桔黃甘之類,蓋上林所無者,猶莊生之寓言也。”清章學誠《文史通義》也說:“假設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王十朋將《上林賦》的“子虛烏有”推源于“莊生之寓言”,章學誠更進一步明確“假設問對”為“《莊》《列》之遺”,都肯定了《莊子》一書和賦體發生之間的關聯②。
《莊子》寓言之“假設問對”對賦體結構的影響確然存在。若深入《莊子》,還會發現,其“假設問對”實與神巫占卜的傳統相關,從中可見出巫術文化向理性文化蛻變的線索和跡象③。《莊子》面對上古巫術文化遺產,一面加以吸收、沿用,一面又有所加工、改造。上古神巫占問表現的是人對“天道”、“吉兇”的探問。莊子身處戰國后期,已經過人文精神的洗禮,因而他心中的神巫及其問對就有了新的內容和風貌。
《莊子·天運》:“‘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于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乎?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巫咸祒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兇。九洛之事,治成德備,臨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莊子筆下的巫咸祒不再是神秘天道的代言人,而成了“治成德備”的宣揚者。意思是天道的運行不必問,只可順,“順之則治,逆之則兇”,這顯然不再是上古神巫占問的原始形態,而只是它的一個軀殼了。借了這個軀殼,陳說的是莊子自己的思想,就像莊子虛構的其他人物一樣,都只是在替莊子說法。
更進一步,莊子還將巫祝與道家推尊的神人對立起來。《人間世》說:“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巫祝“所以為不祥”,乃神人“所以為大祥”,神巫和神人對立了起來。莊子所謂之神人,并不是交通神靈之人,而是和至人、圣人同類的得道之人。在《應帝王》中,莊子設置了鄭之神巫季咸與壺子之間的一場“斗法”,其介紹季咸說:“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但這個“若神”的神巫在與壺子的斗法中,卻一再失敗,最后“立未定,自失而走”。這都表明神巫的崇高地位已經淪落,神巫占問已為哲人的問對所取代,理性精神戰勝了巫術意識。
《莊子》書中,凡問對大抵都是得道之人對困惑、蒙昧中人的解答與開示。《漁父》中的漁父,就是作為“孔子”的人生導師而出現,孔子求教于他,就像《天道》、《天運》諸篇中孔子問道于老聃一樣。解答人生難題的不再是傳統中的神巫,而是莊子心目中的圣人。而正如章學誠所說,莊子的這些“假設問對”,對后來辭賦的結體產生了重要影響。
屈原楚辭中的巫術文化色彩較之《莊子》要濃郁得多。雖然在楚國貴族集團中,屈原最具理性精神,也是這個集團中對中原文化最為傾心的人物之一,但他生活的環境特別是他流放之后所接觸到的民間文化卻充滿了巫術文化內容。王逸《楚辭章句》說:“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辭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托之以風諫。”王逸這段話道出了屈原楚辭創作的誘因和目的,一方面是楚地鼓舞樂神的舊俗,一方面是遭放逐后的“懷憂苦毒,愁思沸郁”。鼓舞樂神,是人與神的對話,但當屈原借助這一模式來發憤抒情(“托之以風諫”)時,實際就轉向了人與人的對話。
游國恩指出,《離騷》的基本結構實際是由對話構成的,其中“女媭之詈予”、“就重華而陳詞”、“靈氛之吉占”、“巫咸之夕降”,“雖非正式的一問一答,然實際上是問答的體裁,不過為行文上方便起見,故偶然省去一方面的問或答。”④但這些都不過是他抒情的依托,并不是要對話的真正對象。他真正要對話的對象是楚王。他的另一篇杰作《天問》實為“問天”。清人吳世尚說:“其名天問者,言天下原有不可究問者也。名問而實自答矣。”⑤這是一種包含了答的問,是一種自問自答。《天問》和莊子通過巫咸祒所提出的問題幾乎一模一樣。他們的問,實際是對現存秩序合理性的懷疑,或舒瀉愁思,或表示反抗。
元祝堯《古賦辨體》說:“賦之問答體,其源自《卜居》、《漁父》篇來,前后宋玉輩述之,至漢,此體遂盛。”按照祝堯的說法,《卜居》、《漁父》二篇對“賦之問答體”即賦體結構模式的生成有直接的關聯和影響,從中尤可見出從神巫占問傳統到人與人對話的轉變。
王逸說:“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障于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楚辭章句》)面對嚴峻的人生課題,“不知所從”的屈原只得往見太卜鄭詹尹,希望通過卜人之占來解除胸中疑惑,為他困窘、煩亂的人生指出一條明路。屈原提出的疑問是:“吾寧悃悃款款樸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婾生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隨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兇?何去何從?……”這是兩種處世方式,也即兩種不同人格之間的矛盾,本身就不是卜人所能解決的問題,因此鄭詹尹聽后,只好無奈地表示:“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龜策誠不能知事”。屈原的疑問,并不能得到占卜者的解答。這實際上已否定了神巫占問的固有功能。他筆下的神巫和莊子筆下的巫咸一樣,無法決疑、解難、辨惑。同樣,《漁父》篇也是“假設問答以寄意”(洪興祖《楚辭補注》卷七),無論是《卜居》中的鄭詹尹,還是《漁父》中的漁父,都不過是由問題而假設的人物,如后來的“子虛烏有”一樣。
《荀子·賦篇》不僅最早為賦體命名,也對后世賦體的發展有直接的影響。其《賦篇》分寫“禮”、“知”、“云”、“蠶”、“箴”。它們實際也是運用的對話體,不過是一種特殊的對話方式:先說謎面,再揭謎底。又其《佹詩》二章,開篇即云:“天下不治,請陳佹詩。”他是向誰陳此佹詩呢?末章云:“嗚呼上天,曷維其同!”這和屈原的“問天”無疑屬于同一致思理路。這個“天”,也和屈原筆下的天一樣,都是接受了理性精神洗禮的天,即自然之天。但應注意的是,這個天又是從人格神的天、作為上帝的天演變而來的。
荀子是孔子的信徒,本就對巫術傳統比較地疏遠。《荀子·天論》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又說:“制天命而用之。”但他對巫術文化并不陌生,《王制》篇說:“相陰陽,占祲兆,鉆龜陳卦,主攘擇五卜,知其吉兇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他雖不相信神巫占卜,但對于在社會上仍有相當影響力,尤其是在民間仍有相當市場的巫術文化卻非常之了解。盡管《賦篇》并無什么神秘色彩,但從其所采用“隱語”這一問對形式看,卻完全可能是從神巫占卜的對話方式脫胎而出⑥。
神巫占問的方式作為辭賦的基本結構模式保留下來,實非偶然。因為在辭賦發生之初,與之相關的幾個關鍵性人物都在楚地生長或生活過,都和巫術文化有過親密接觸。《漢書·地理志》言楚地“信巫鬼,重淫祀”。屈原是楚人。莊子為宋人,商人之后,有“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的傳統;又地近于楚,在長期的陳、楚交戰中,其所在之蒙有可能并入了楚國⑦。荀子曾長期居留楚國,并出任過楚國的蘭陵令。
他們都十分熟悉作為古老傳統的巫術文化,但又并沒有匍匐在神的面前,問于神,聽于神,而是以一種清醒的理性態度,從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對問題本身作了深刻探討,或者假借神巫以明“道”(如巫咸祒),或者借神巫之口否定占卜的有效性(如鄭詹尹)。這是一個士人主體精神高揚的時代,作為這個時代士人的杰出代表,莊子、屈原和荀子將此種精神注入到了初生的辭賦之中。
二、大賦與小賦:從人與人的對話到人與自然的對話
《漢書·藝文志》說:“春秋之后,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后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侈麗宏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宋玉緊承屈原之后,但他并未能照著屈原的路子走下去。從他開始,傳統的“古詩之義”、“風諭之義”不復存在了。
宋玉絕大部分賦作,都是他與楚頃襄王之間的問對。問對的結體方式,顯然是對既有辭賦傳統的繼承。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宋玉諸人雖“好辭而以賦見稱”,但只是“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在精神上和屈原拉開了距離。宋玉與楚王的問對之作,計有《高唐賦》、《神女賦》、《風賦》、《登徒子好色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御賦》、《對楚王問》十篇。這些問對是否實有其事很難論定,但賦作都圍繞與楚王的問對進行,至少在他的自我意識中他是作為“言語侍從之臣”存在的。透過問對的內容我們不難發現,宋玉的身份和處境相當微妙。其中有三篇提到,宋玉為人所“短”(或被指“有遺行”),只是因為他善于辯解而得化險為夷。這表明,宋玉在楚王身邊,隨時都有獲罪、黜退的可能。正是這種身份和處境決定了他作品的基本品格。
在《登徒子好色賦》、《諷賦》中都有構陷宋玉“口多微詞”的話。“微詞”當即委婉含蓄之言,也即拐彎抹角之言,這實際是他在與楚王對話中采取的一種語言策略,也即《史記》所說的“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之所以采用這樣一種語言策略,當是在屈原沉身汨羅之后,面對楚王的昏庸和高壓不得已而作出的一種選擇。也就是說,在屈原之后,那種強烈的反抗意識和斗爭精神趨于沉寂,士人的主體精神大大削弱了。宋玉是一個轉折的標志,賦的基本結構方式仍在,但其基本精神卻發生了變化。
這種變化在漢大賦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作品通過虛擬三人的對話,分別鋪排諸侯和天子苑圃之盛,而到最后,自然是天子之苑圃以絕對優勢壓倒諸侯之苑圃。這之中,實際表現的是“對漢帝國及天子權勢的無上贊嘆的潛意識”⑧,這可以看作是宋玉賦作精神在漢武帝時代的持續和發展。
從司馬相如開始,結構上以虛擬人物的對話方式展開,內容上“明天子之義”,也即凸顯天子權勢或國家意志,實際成了大賦的固定模式。班固《兩都賦》設置西都賓與東都主人對話,張衡《二京賦》以憑虛公子與安處先生相對答而展開,二賦都表現出對定都洛陽的政治決策和東漢王朝中興的頌美和擁戴立場。左思《三都賦》也與當時的政治形勢密切相關,作者虛擬魏國先生、東吳王孫和西蜀公子的對話,以闡明“三國歸晉”、天下一統乃大勢所趨。這種傳統,大約到庾闡《揚都賦》遭致謝安批評之后才告消歇⑨。
在大賦中,作者的立場總是與所虛擬的某一人物的立場相一致,而這一人物的立場,又總是體現著天子權勢或國家意志。亡是公站在天子立場為天子說話,這實際也是司馬相如的立場。東都主人和安處先生力主建都洛陽的正確性,也正是班固和張衡的立場。魏國先生反對割據、主張統一,這是左思的立場,也是他創作《三都賦》的立意所在。因為目的在“明天子之義”,凸顯天子權勢或國家意志,其中的士人主體精神就相應地顯得稀薄,這也是大賦屢遭非議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大賦創制過程中,對于士人主體精神日漸淡薄的事實,作家自身對此多有反思和警醒。枚皋自言“為賦乃俳,見視如倡”(《漢書·枚乘傳》),揚雄晚年稱“雕蟲篆刻”,“壯夫不為”(《法言·吾子》)。枚皋將賦家與俳優聯系起來,揚雄晚年不再作賦,是有原因的。韓非曾說:“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韓非子·八奸》)司馬遷說:“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報任安書》)結合宋玉“口多微詞”的特點,以及其在楚王面前的種種表現,可知他于俳優是十分類似的。漢武帝對待賦家的態度,較之楚王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賦家的反思當是基于其切身之痛而發。
不僅是身份和表現上的近似,大賦的特性、功能和俳優的“談言微中”(《史記·滑稽列傳》)也是高度接近。所謂“談言微中”就是以迂回巧妙的方式道出真相或真理。《史記·滑稽列傳》所載滑稽群體之第一人淳于髡,就曾以“隱語”勸諫齊威王。荀子所作最早以“賦”命名的作品正是以“隱語”的形式出現。《文心雕龍·諧隱》論“隱”:“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之賦末。”這說明,賦家之作和俳優之言確有一定淵源。⑩司馬遷說:“相如雖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司馬遷對司馬相如之賦最后能引之節儉給予了肯定。但揚雄卻不以為然,“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司馬遷注意到在虛辭濫說之后能引之節儉,其中畢竟有賦家的主體精神在;而揚雄卻認為勸百而諷一,其中的主體精神只是裝飾和點綴,就士人創作之本意言,可能是適得其反。
班固同樣意識到士人主體精神在大賦中的中落,試圖重新振起之。《兩都賦序》說:“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喻,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后嗣,抑亦雅頌之亞也。”將大賦提高到“雅頌之亞”的高度,自然是為《兩都賦》張目,但另一面也有對既有大賦傳統表示不滿并加矯正之意。將賦家分為兩類,目司馬相如等為“言語侍從之臣”,實即暗含了對這些賦家及其賦作的不滿。但班固的做法似乎并不成功,后人論大賦言:“屈兼言志、諷諫,馬、揚則諷諫為多,至于班、張則揄揚之意勝,風諫之義鮮矣。”(劉熙載《藝概·賦概》)班固本意是要高揚士人之主體精神,但在后人看來其主體精神反而更見低落了。道理很簡單,相比之下,班固較之司馬相如,其與天子權勢或國家意志的關系是更為貼近了。
小賦與大賦其實是一種并生關系,但在漢代,小賦為大賦所掩,故而讓人覺得大賦之后始有小賦的發生。?小賦的品類很多,今僅就與士人主體精神與生命意識關系最為緊密之詠物賦和田園山水賦言之。詠物賦在荀子、屈原、莊子手中就已經有了。《荀子·賦篇》之“云”、“蠶”都是典型的詠物;屈原有《桔頌》一篇;莊子雖無專門的詠物篇章,但《莊子》中很多篇章都鋪寫到自然之物,如《齊物論》之寫“風”,就被視為詠物的杰作。宋玉有《風賦》。漢人所詠更多,如枚乘《柳賦》、張衡《鴻賦》、蔡邕《蟬賦》等。但將所賦之“物”與士人主體精神和生命意識有機結合起來,《桔頌》而外,當數魏晉而下之作了。
試以詠柳諸賦相比較,枚乘《柳賦》云:“階草漠漠,白日遲遲。于嗟細柳,流亂輕絲。”其刻寫不可為不妙,但至曹丕始將自己的生命感慨融入其中,其《柳賦》云:“始圍寸而高尺,今連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邁,忽亹亹以遄征。昔周游而處此,今倏忽而弗形。感遺物而懷故,俯惆悵以傷情。”至庾信《枯樹賦》言:“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凄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結合個體的生存感悟,提煉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人生體驗,遂成千古絕唱。
田園山水賦的出現尤為引入注目。田園山水賦的早期萌芽,自可追溯到莊子、屈原的《漁父》,其逍遙于澤畔水濱的隱逸人生無疑深刻地啟示了后人。最早在賦中表達田園山水之趣的是張衡,其《歸田賦》云:“游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在這里兩種環境(都邑與田園)、兩種人生(入世和出世)形成鮮明對比,而作者去彼取此,態度十分堅決。從“追漁父以同嬉”一語可知,作者之走向田園山水,與莊子、屈原筆下“漁父”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歸去來兮辭》是陶淵明棄官歸田的宣言書。和《歸去來兮辭》相表里的是他的詩——《飲酒二十首》(其九),無論寫法還是精神,都從屈原《漁父》而來。詩云:“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襤縷茅檐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其情節、態度和屈原《漁父》并無二致,所不同的是“漁父”換成了“田父”,遁跡澤畔轉而為田園了。
《山居賦》是謝靈運的代表賦作,其序云:“言心也,黃屋實不殊于汾陽。即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閑,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揚子云云:‘詩人之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游獵聲色之盛,而敘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詠于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臺、皓之深意,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所賦不再是“京都宮觀游獵聲色之盛”,而是“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趣味上“廢張、左之艷辭”,而要“尋臺、皓之深意”;風格上“去飾取素”,存天然而去雕飾。這實際宣示了大賦的時代已然終結,一種新的美學潮流已經興起。
在詠物和田園山水賦中,對話的結構模式仍在,但已發生變化。謝莊《月賦》稱“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乃命仲宣,仲宣跪而稱曰……”謝惠連《雪賦》謂“梁王不悅,游于兔園……授簡于司馬大夫……相如于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皆是假托古人,鋪演成篇。庾信《枯樹賦》假托古人言語,而以獨白方式出現,以殷仲文“顧庭槐而嘆曰”開頭,以“桓大司馬聞而嘆曰”收尾,又別是一番景象。謝靈運《山居賦》也是以獨白方式開頭,其云:“謝子臥疾山頂,覽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悠然而笑曰:……”這實際都可看作是對話模式的變體。這表明,在詠物和田園山水賦中,固有的對話模式在變化、消解之中。由簡單、僵硬變得風情萬種、搖曳生姿了。尤應注意的是,當作家寄情于物或投身于田園山水之時,他們本身即已在和自然親切交流和對話,如陶淵明之“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人在與自然打交道的過程中,天機流轉,詩意盎然。用劉勰的話說就是:“山沓水匝,樹雜云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文心雕龍·物色》)從“心為行役”的困厄中解脫出來,與自然親切交流與對話,這時的人無疑是最近于詩的。當賦進入到此一階段,實已開始與詩合流了?。
辭賦結構模式從人與神對話,經人與人對話,再到人與自然對話的演化過程,表明人在擺脫神的控制之后,復為天子的無上權勢所籠罩,最后只得以走向自然、疏離與超越現實的方式,表現其自由意志和獨立精神。宗白華說:“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自然”從此成為士人的精神寄托之所。對士人主體精神言,這無疑是一種張揚。但此中所呈顯的士人主體精神,相對于在大賦中所呈顯者,又有一個由“兼濟”向“獨善”、從“方內”向“方外”的變化,其于人事與人世態度的超然而淡漠,也是不言而喻。
注釋:
①郭沫若:《卜辭通纂》,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368頁。
②今人郭沫若也認為《莊子》:“立意每異想天開,行文多鏗鏘有韻,漢代的辭賦分明導源于這兒。”(《蒲劍集·莊子和魯迅》,《沫若文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59頁。)徐宗文《〈莊子〉與漢賦》(《安慶師范學院》1987年第4期)、劉生良《〈莊子〉——賦的濫觴》(《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2期)對《莊子》與賦之關系均有探討。
③莊子與巫術文化的關系,學者已有注意,此一方面的論文可參看殷志芳《畸人與巫——試論莊子筆下的畸人形象》(《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07年第7期)、鄧聯合《巫與〈莊子〉的畸人、巧匠及特異功能者》(《中國哲學史》2011年第2期)等。
④游國恩:《楚辭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33年,第138頁。
⑤轉引自游國恩:《天問纂義》,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4頁。
⑥朱光潛論及古代隱語時指出:“這種隱語大半是由神憑附人體說出來,所憑依者大半是主祭者或女巫。古希臘的‘德爾斐預言’和中國古代的巫祝的占卜,都是著例。”(《詩論》,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第31頁)
⑦關于莊子的籍貫,文獻有不同說法,《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只說是“蒙人”,劉向《別錄》明言其為“宋之蒙人”,《漢書·藝文志》承其說。大概宋之蒙地后入于楚,所以不少學者稱其為“楚人”。朱熹就說:“莊子自是楚人……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五,中華書局1986年版。)可參看馬敘倫《莊子宋人考》(《莊子義證》附錄一,上海書店1996年版)、常征《也談莊周故里》(《江淮論壇》1981年第6期)、崔大華《莊子故里的國屬問題》(《黃淮學刊》1991年第2期)、孫以楷《莊子楚人考》(《安徽史學》1996年第1期)等。
⑧興膳宏:《六朝文學論稿》,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第409頁。
⑨《世說新語·文學》載:“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
⑩郗文倩:《從游戲到頌贊——“漢賦源于隱語”說之文體考察》,《中國文學研究》2005年第3期。
?韓高年:《兩漢詠物小賦源流概論》,《中國韻文學刊》2004年第2期。
?林庚:《詩化與賦化》,《煙臺大學學報》1988年第1期。
?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3頁。
(責任編校:文建)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alogue Modes of Ci Fu
YANG Helin
Ci Fu has three mian kinds of dialogue modes:the dialogu e between Gods and men,men and men,men and nature.These three kinds are carried out one after another,which reflect the changes of Chinese history,culture and scholar-oriented spirit.The sorcery culture of ancient times was transferred into a rational one in Zhou and Qin dynasty,which brought the change from the dialogue between Gods and men to men and men,so that the unprecedented human-oriented spirit was developed.This trend was exemplified in Chuang-tzu,Chu Ci and Xunzi vividly,which were regarded as the source of Ci Fu.After Han dynasty,Da Fu and Xiao Fu co-existed and co-prospered,rising and falling alternately.Da Fu,which aimed to promote emperors’power and the will of the state,actually made the scholar-oriented spirit repressed during the dialogue among human beings.Xiao Fu,which was dedicated to things or landscape,opened the scholar-oriented spirit up to a fresh outlook in the dialogue between men and nature.
Ci Fu;the dialogue mode;the scholar;scholar-oriented spirit
楊合林,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文學研究》副主編(湖南 長沙 410081)
教育部2011年度規劃基金項目“《樂記》文本與理論研究”(11YJA751083);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樂記》文本、理論與注釋史研究”(15BZW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