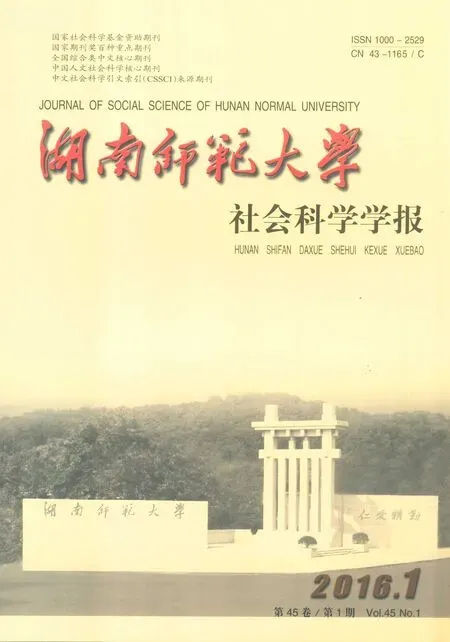論當代創業文學與絲路文學
李繼凱
?
論當代創業文學與絲路文學
李繼凱
在當今文化語境中言說“創業文學”和“絲路文學”可謂恰逢其時,二者的關聯及意義也耐人尋味。進入“新常態”,跨進“創時代”,我們仍然難忘曾經的艱難探索之路。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本質上也是“創業之路”。而絲路文學,也相應地體現了這種在開拓探索中艱苦創業的絲路精神。在當代作家柳青、周立波所代表的當代創業文學和方興未艾的當代絲路文學之間,確實存在著密切的關聯性,其異同之處也蘊含著有意味的啟示。
創業文學;絲路文學;創時代;正能量;文學書寫
進入“新常態”,跨進“創時代”,當今國人的創業使命較之于前人其實更加沉重和艱難。對個人而言,成家立業是最切要也是最基本的人生重大命題;對國家而言,國富民強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建國戰略目標。其中都絕對少不了真正的“創業”,其間也絕對需要求實創新、真抓實干,而在貼近時代、深入生活的過程中關切創業、書寫創業,也便成為積極入世的作家們高度自覺的一種文學選擇。筆者以為,從主導方面看,從古至今的絲路文學①也與創業密切相關: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本質上正是一條披上絲綢、唱響駝鈴、走向世界的“創業之路”;應運而生的絲路文學,也相應地體現了在開拓探索中艱苦奮斗、勇于創業的絲路精神,并在物欲與愛欲之間激蕩出更具傳奇色彩的詩情畫意和絲路故事。
一
筆者曾重新審視現當代文學史上以史詩之筆書寫創業的“柳青現象”,在《文藝報》上發表了短文《柳青的“創業文學”》②,認為在任何時代,“創業”都應該是個人和國家最重要的使命;“創業文學”都應該是最主要的一種文學形態,且應受到最為廣泛的關注和理解。遺憾的是,人們往往被動地進入人間迭起的惡斗與紛爭而忽視甚至遺忘了創業及創業文學,有時候甚至還假以“革命”與“戰爭”的名義,阻礙乃至破壞了人民正常的創業以及作家從事創業文學書寫的生態環境和發展進程,留下了諸多迄今都應牢牢記取的歷史教訓。
創業,無疑是現當代中國語境中傳播最廣的“關鍵詞”之一,無論是普通民眾還是富豪巨賈,無論是叱咤風云的政治家還是秉筆直書的文學家都對此充滿了期待。然而在動蕩不已、流離失所、戰爭頻仍的年代,人們從事創業的熱切期待卻經常會落空,在上世紀上半葉,多少仁人志士懷抱科技救國、實業救國的理想都很難獲得大的成功。即使到了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和延安,無論是《子夜》描述的民族工業,還是延安文學展示的生產運動,也僅僅都是困境中有限度的創業嘗試而已。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重新喚起了全民從事創業的熱情和希望,而“實驗”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思路方能得到更為積極的大膽實踐。我國從延安時期嘗試的生產互助、上世紀50年代嘗試的合作化道路,以及80年代嘗試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或者由于時代條件的限制,多少都帶有“應急實驗”的特征,直至發展到了90年代,國人才進入了比較從容不迫的建設階段,在神州大地普遍興起“新農村”建設熱潮的同時,新時代或現代化背景下的合作性集約生產則又成為非常重要的一次改革或新的實驗。從數千年農民“不納糧”夢想的真正實現到“新農村”和城鎮建設的空前加速,歷史業已證明,無論是側重于集體創業,還是側重于個體創業,抑或二者并重,都要從事艱苦的創業則是中國人必須面對的嚴峻挑戰。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具有現代性的“創業文學”便應運而生并大放異彩了。
提起“創業文學”,人們自然就會想起柳青的《創業史》和周立波的《山鄉巨變》。這兩部長篇小說,無論經過多少爭議,迄今都仍然享有較多的贊譽,在我國當代文學史上也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并被視為共和國初期“十七年”的經典作品或“紅色經典”的代表作。正是基于對合作化事業和文學使命的深入思考,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柳青、周立波代表的鄉土文學書寫進行了相當廣泛的討論。僅就《創業史》研究而言,就出現了一系列觀點鮮明而又有所爭議的論文,如劉思謙的《建國以來農村小說的再認識》③、宋炳輝的《柳青現象的啟示——重評長篇小說<創業史>》④、羅守讓的《為柳青和<創業史>一辯》⑤、周燕芬的《<創業史>:復雜、深厚的文本》⑥、劉納的《寫得怎么樣:關于作品的文學評價——重讀<創業史>并以其為例》⑦、薩支山的《當代文學中的柳青》⑧以及秦良杰、吳進、段建軍等學者的論文,其間觀點各異甚至針鋒相對,但學術性探索的意義足以證明《創業史》絕非一部簡單的文學文本,其對創業和文學的雙重審視與探索也留下了足夠廣闊的思維空間,現在和將來都仍會有一些學者從文學、審美、人性、歷史、文化乃至政治、心理、性別等不同角度對柳青《創業史》進行更加細致、深入的研究。在《山鄉巨變》研究中,也存在非常類似的情形,盡管爭議依然存在,但在筆者看來,以《創業史》、《山鄉巨變》為代表的創業文學,主要有三個方面值得格外關注,且應深長思之。
其一,創業文學范式的積極建構。事實上,“創業”確是人類創造的最偉大且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之一,也是中國人自近代以來最為熱衷的一個“關鍵詞”,但自覺地大書特書并直接以之為小說名稱的卻是柳青的《創業史》。如前所說,無論是側重于集體創業,還是側重于個體創業,抑或二者兼容并重,“合體”發力創業,都要從事“艱苦創業”則是中國人必須面對的“宿命”般的嚴峻挑戰。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與“艱苦創業”同在的“創業文學”便應運而生了。由此,作為當代中國的“創業文學”代表作,《創業史》和《山鄉巨變》等杰出小說,都在積極建構“創業文學”范式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這種文學的基本范式與集體創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史詩等時代話語密切相關。作為書寫“農業合作化”這種巨大社會實驗的“創業小說”,其書寫行為本身也是一種實驗、實踐或創業:柳青和周立波在面對史無前例的土地革命及合作化這種破天荒的歷史巨變時,都能夠深入生活本身去努力創構反映農村敘事的“創業”范式,在家國敘事、愛情描寫及風俗、方言的文學敘事中,也都體現出了巨大的使命感、責任心和藝術功力。歷史也許會證明:創業型的集體之業因其基礎薄弱、條件甚差(思想基礎和物質條件等遠未準備充分)而遭遇了實驗的失敗,其創業之路遭遇嚴重挫折。失敗是成功之母,一次性創業實驗的失敗抑或探索的挫折顯然并不一定會徹底否定探索的命題本身。值得欣慰的是,創業文學其實也是后繼有人的,僅在陜西,柳青身后就有“陜軍”或“白楊樹派”在延續著創業文學的血脈,盡管有新探和新變,但書寫創業中的精神追求、苦難考驗、改革歷程乃至創業失敗的筆觸,依然在《平凡的世界》(路遙)、《浮躁》(賈平凹)、《白鹿原》(陳忠實)、《村子》(馮積岐)及《絲路搖滾》(文蘭)等名作中繼續存在。而在湖南,著名的文學“湘軍”⑨也是創業文學的一支主力軍,周立波、康濯等作家之后,還有張揚、莫應豐、古華、葉蔚林、韓少功、唐浩明等接踵而來,聚散之間,探索不止,產出了一批又一批優秀的文學作品。其中大量的作品,包括歷史小說,也大都關涉改革創業的時代主題。
其二,創業文學母題的時代書寫。從文學主題學的角度看,筆者曾在拙著《秦地小說與三秦文化》⑩中重點分析了秦地小說的創業主題,并認定柳青是用畢生心血投注于“創業”主題文學表達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其實,創業與愛情一樣都是“文學永恒母題”。愛情不死,創業不止。迄今“創業”也仍是中國文學的一個中心主題。著名詩人賀敬之曾傾心贊美柳青的創業文學,云:“杜甫詩懷黎元難,柳青史鑄創業艱”。作為“人民作家”的柳青自然會格外關注人民日思夜想的創業興家的愿景。這樣的創作取向在周立波的《山鄉巨變》中甚至還得到了近乎“浪漫”的書寫。這里有對故鄉自然風光的贊美,更有對志在改變故鄉貧窮面貌的鄉村干部的傾心贊美,秉持人民本位的深切關懷和密切關注民生問題的創作取向至今給讀者仍能留下難忘的印象。跨入21世紀,當今的人民群眾對山鄉、家鄉的新變仍然寄予了無限的希望,從文學創作來講,感應這種希望的則是呼喚更加輝煌的“新創業史”和更加生動的“山鄉巨變”。在人類漫長的進化過程中,“變則通”的思維邏輯在追求創業的社會實踐以及作家的“文學創業”中,都得到了比較充分的體現。
其三,創業文學形象的精心塑造。從文學形象學的角度審視《創業史》、《山鄉巨變》,也會發現小說中的人物不僅活在那個紅色的創業時代,也活在文學世界和不向苦難屈服的人們心中。《創業史》和《山鄉巨變》都認真書寫了人物的過去以及曾經的苦難。《創業史》開篇便描寫逃難中的梁三老漢,苦命人于死亡邊緣的相遇使他有了婆姨和繼子,并由此開始了他們的艱難“創業”之路;《山鄉巨變》也用力塑造了貧農陳先晉老漢和家人曾經遭遇的各種苦難,提起過去的苦難尤其是開荒留下的幾畝土地,他心中就會充滿了苦澀并更加珍惜已經擁有的土地,對是否加入合作社反而更加疑慮和糾結起來。而這疑慮和糾結是如此真實地化為生動敘事并穿越了時空,令人對農村“公有制”、“合作化”的難產和夭折都會生出無限的感慨。無論所有制及生產方式如何,從梁老漢、陳老漢及其他們的后代(梁生寶、陳大春等)身上,讀者都能夠看到最樸素的中國農民對創業興家的持續追求及其引起的各種紛爭。難能可貴的是,柳青、周立波都能夠通過滿含生活氣息的農村敘事和人物形象塑造,將一系列心系創業、勇于創業的農村人物包括鄉村干部形象(如梁生寶、徐改霞、鄧秀梅、李月輝等)生動地展示在讀者面前,也將傳統型自發創業、心意復雜的人物如梁三、王二直杠、亭面糊、盛佑亭等塑造得栩栩如生。眾所周知,柳青和周立波都是那種自覺融入農民群眾中的作家,他們不僅能夠為了文學事業在農村深入生活,并且能夠抓住“創業”這樣的時代“關鍵詞”進行文學創作,創造性地書寫中國農民,尤其能夠在各類農民形象的塑造上取得突出的業績,也已經為后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時代光影以及“影因”。究其原因,他們都受過延安文藝精神的洗禮,都能夠自覺抑制業已習以為常的知識分子表達習慣,全身心地“深入生活”,努力熟悉農民的聲腔口吻,如此才能更好地塑造農民群體形象。其實,這個“深入生活”的全方位轉型對作家來說絕對是一種極為嚴峻的考驗,“深入”之后且能成功地寫出“生活”、寫活人物的作家并不多見。從創作實踐的角度看,這也不妨被視為一種探索文藝生產機制或規律的文化“實驗”,其經驗和教訓都很值得認真地總結。
二
每當時代發生巨變,常常會出乎常人的意料。比如常人就很難預料歷史上早已形成的某些固定概念居然也會如此變化或被置換:人們原來熟悉的特指概念的“絲綢之路”即被當今大時代重新建構、拓展或整合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了。在“一帶”中,最初起自漢唐長安(西安)的陸路“絲綢之路”,到了今天卻只能化作“一帶”的定語;在“一路”中,古代有限的海上商路將被重建或開拓為四通八達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個“絲綢之路”已成為中心詞,并可以作為主語或賓語來使用,昭示著中華民族復興之路能夠暢達五湖四海。然而,傳統概念“絲綢之路”也由此被徹底泛化了。但就在這種泛化過程中,卻又昭示了不斷開拓和發展的“絲路精神”和根深蒂固的“創業精神”!恰是這種精神文化的契合滋養了絲路藝術,包括其中不太引人關注的“絲路文學”。自然,被收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僅是古代的絲綢之路,而被視為中國“絲路文學”的作品,大抵也被納入了中國的西部文學,但迄今尚未擁有“合法”的獨立身份。如今關于絲路文學的廣義、狹義或概念、范疇的理解已經出現不同的聲音,筆者以為在文藝領域的概念大多具有“人文模糊”的特征,類似于人生“難得糊涂”的境界,難以給出絕對正確或明晰的定論。所以在這里仍依照慣例,在比較嚴格的意義上從三個方面討論一下筆者心目中的“絲路文學”。
首先,絲路文學是絲路開拓精神的衍生和升華。道路與貧富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這是地理環境條件嚴酷的西部人也深刻了解的“常識”。道路,往往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和創業之路。所謂“要想富先修路”似乎也并不是今人的專利。正是出于這樣的基本認知,同時也是為了“西安”(或長安)、“定西”(地名寓意“西部安定”的希冀),才有了強烈的向西、再向西進行探索的沖動。絲綢之路是我國歷史上輝煌的經濟命脈和文化大道,它的開拓和維系既促進了商品的交換、經濟的發展,也加強了異域文化藝術的交流與借鑒。其中,歷來人們關注較多的是赫赫有名的敦煌藝術,卻會有意無意地忽視了絲路文學。其實自古以來,絲路文學“就在那里”客觀地存在著,生生不息且相當豐富。在勇敢地探索、交流、開放中創業,在創業過程中不斷開辟廣闊的國際化交易市場,同時也豐富了精神文化的樣式及內涵。“絲路文學”伴隨著絲綢之路的興盛而興盛,如興盛于漢唐的“絲綢之路”催生了絲路行旅文學包括邊塞詩的興盛,也進一步激活了絲路民間文學和宗教文學,絲路上傳播的敦煌變文、民間史詩和宗教話本都成了珍貴的民族文化遺產。隨后,絲路文學也伴隨著絲綢之路的綿延而綿延,如今也伴隨著絲綢之路的進一步開拓而有了新的飛躍和發展。而人們提起絲路精神,就很容易將它與開創、開拓、開明和開放等語詞或概念聯系起來,這些都昭示了絲路文化的某種理想狀態,體現了生生不息的正能量。筆者以為,在此還可以追加一個語詞即“開心”——西部人生性放達豪爽,即使生活貧困也會努力尋求“窮開心”——多數的少數民族都是那樣能歌善舞便是證明。而這些以“開”字打頭組成的語詞概念,便是對敦煌精神、絲路精神或西部精神的一種提煉,且在絲路文學中都有相當充分的體現。
其次,當代絲路文學創作的基本狀況及其存在的問題。大致而言,絲路文學也分為前絲綢之路與絲綢之路(漢唐以來),或者古代與現代這樣兩個大的歷史階段,在文學形態上也呈現出豐富復雜的樣態,與通常所說的文學并沒有品類上的明顯不同。尤其是在共和國成立之后,古絲綢之路從長期的沉寂中蘇醒,伴隨著新時代的建設步伐,迎來了全面的復興和發展。特別是實行西部大開發以來,真正國際化的絲綢之路又重新熱鬧起來。由此,絲路文學也迎來了新的發展契機。在這條古老的絲路上,既有許多長期生活在絲路及其周邊的文人作家,也有一些外來的觀光或暫住的文人作家,他們都為書寫絲路及西部的歷史和現實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而當代絲路文學也繼承了古代絲路文學的傳統,有著相當鮮明的區域文化特色,所謂“絲路風情”所關涉的多民族文化呈現,就成了絲路文學的主要特色。相應的,豪放粗獷的敘事和抒情也便成了當代絲路文學的主要風格。其文學意象依然有大漠落日、沙海駝鈴、飛天壁畫、白楊紅柳、草原奔馬、冰川激流和帳篷炊煙,也會有雪山紅旗、戈壁車隊、高原電站和沙漠綠洲等,如《敦煌記事詩》(于右任)、《西北行吟》(羅家倫)、《塞上行》(范長江)、《白楊禮贊》(茅盾)、《奇曼古麗》(黎·穆塔里甫)、《玉門頌》(李季)、《天山牧歌》(聞捷)、《陽光燦爛照天山》(碧野)、《平凡的世界》(路遙)、《黑駿馬》(張承志)、《絲路搖滾》、《瞻對》(阿來)、《穆罕默德》(艾克拜爾·米吉提)、《土司的子孫們》(王國虎)等難以盡數的絲路作品,都重現了西部絲路自然景觀和文化景觀,也各有側重地抒寫了創業的艱難、創業的樂觀,乃至創業興家與人性情感的種種糾結及沖突。而從絲路沿線地域如關中、河套、隴右、西夏、河湟、河西、敦煌、吐蕃、突厥等區域的各民族(如維吾爾族、回族、藏族、蒙古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等)文學來看,更是奇絕多變,值得細致研究。來自絲路的深切生活體驗是絲路文學創作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民族生活、歷史地理和人文傳統深刻地影響了絲路文學,這是絲路作家尤其是大西北作家的文學趨于豪放粗獷而少有溫婉細膩的主要原因。即使是描寫愛情來臨時的花前月下,也沒有清新而又細膩的小橋流水和江南絲竹的陪伴。但當代絲路文學也存在不容回避的明顯問題,就是某種極端思潮如政治統治上的左傾思潮和宗教宗派上的原教旨主義等,都會對絲路的是否通暢、絲路文學的創作環境產生直接的遏制或負面的影響作用。
再次,絲路文學的古今中外視野和相關研究的逐步拓展。古今絲路文學創作,總體看也堪稱是蔚為大觀的,文學視野也是堪稱“遼闊”的。比如,作為絲路文學的一部總集,《敦煌文學叢書》在進一步彰顯了歷史特定時期的“敦煌文學”的同時,也顯示了今人重新編輯和研究的廣闊的文化視野。其實,歷史上的所謂“敦煌文學”只是絲路文學的一種集結或一個亮點,有其明顯的時空限制,特指在1900年從敦煌藏經洞(第17窟)發現的詩歌、曲子詞、變文、俗曲等,形式多樣,內容豐富而又龐雜。但在今天看來,我們還可以在“新絲路文學”的意義上,也可以將書寫敦煌或敦煌作家創作的絲路文學都視為“敦煌文學”(如馮玉雷《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遠》、《敦煌佚書》等系列作品)。而這種新敦煌文學勢必要體現出古今中外匯通的廣闊文化視野,也提示著相應的學術研究所應具有的宏通的學術眼光。劉維鈞在《振興絲綢之路藝術論綱》中認為,“在中國古代有兩大恢宏的實體具有舉世皆知的象征性,一是萬里長城,一是絲綢之路。前者是保守主義的象征,后者是開放主義的象征。二者相反相成結構出輝煌燦爛的中華文化”?。由此看來,絲路研究確實需要進一步拓展。而目前的絲路文學研究整體看還相當薄弱,除了傳統的敦煌學中的藝術研究比較充分之外,其他方面的研究都很不充分,特別是當代絲路文學研究,還處于初期建構階段,對研究對象及范疇、概念等,都還處于較為模糊的階段。在這樣一個階段努力彰顯絲路文學的切實存在是非常切要的研究工作,從古今最基本的相關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入手,便不失為一個必要的研究方向。
三
通過上述對創業文學和絲路文學的初步討論即可看出,在創業文學與絲路文學之間確實存在著內在的密切的關聯,存在著明顯的異同,亦蘊含著諸多有意味的有益啟示,宏觀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在創業中追求長安的價值取向,在兩種文學形態中都有充分的體現
在中國,無論古今,“西安”或“長安”都不僅僅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地名,因為追求國家尤其是西部的長治久安乃是古今相通的政治文化訴求,而勇于開創新事業的絲路精神業已演化為振興中華的“一帶一路”的宏偉發展戰略和實現中國夢的一種精神支柱。無論書寫征戰還是書寫建設,如古絲路誕生的“邊聲四起唱大風”的邊塞詩,或“春風亦度玉門關”背景下的李季高聲吟唱的“石油詩”,都表達了對和平與幸福的強烈希冀,表達了對家國安全、建樹功業的深切關注。而《創業史》描寫的也正是中國農業的再次創業,體現了對長期以農立國之“國本”的高度關注,并對亙古以來帶有革命性的積極的合作化探索或社會主義實驗,進行了空前了藝術化書寫,體現了作家跟進時代努力把握“戰略與文學”(基本國策與文學建構)的創作取向。恰恰在把握“戰略與文學”方面,當代絲路文學也走在了時代的前面,無論是對陸地絲路的書寫還是對海上絲路的書寫,都充分體現了與國家戰略及中國夢的深切契合。而要從國家戰略、國家安全角度看待創業文學和絲路文學,就必然會看重其間蘊含的強烈的創業精神和求安意識,以及對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的大力弘揚。在極為酷烈的環境中維系生命本身已經成為難題,而要發展經濟、優化環境,實現國富民安,就確實需要大開發、大無畏的氣概,需要某種義無反顧的冒險和奉獻的精神。由此也使創業文學和絲路文學帶上了神圣乃至悲壯的色彩,回蕩著激揚清濁而又慷慨悲涼的旋律。
2.創業文學與絲路文學具有交叉互補性,在豐富當代中國文學版圖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當代中國文學版圖中,無論是人性化的書寫、魔幻化的表達、荒誕性的聚焦多么受人青睞,也都難以遮蔽創業文學和絲路文學的輝光。因為以柳青《創業史》、周立波《山鄉巨變》為代表的創業文學在現實主義小說藝術探索方面,標新領異,其創造性的書寫已經造就了其作為“紅色經典”的輝煌;而絲路文學也擁有這樣的使命意識和藝術精神,以更具地域特色的文學世界表達了對創業的無限追求。這也是絲路文學對創業主題的積極呼應。如果說當年柳青們積極地“深入生活”不僅改造了自己,也創化了文學,其創業文學是“化”出來的,那么,絲路文學則是上下求索“走”出來的。從沖破關山萬重的“自然”的封閉,到沖破居心叵測的“人為”的封鎖,從古至今,以絲綢之路為代表的創業之路都是非常艱難坎坷、險象環生的,但同時這條路又充滿了極其誘人的魅力,帶有了濃厚的傳奇色彩。世代國人跋涉其間,在勇往直前的探索、交流、開放中創業,興國利家,并在積極開辟廣闊的國際化交易市場和大力推進市場經濟的同時,伴隨著各種創業文學(包括成功人士傳記報告、大學生創業故事等)的興起,也在較大程度上肯定并在較大范圍內傳播了創業經驗并豐富了精神文化包括文藝的樣式及內涵。
3.絲路文學作為與時俱進的創業文學,是更加具有發展潛力的文學形態
從傳統的絲路開創到“一帶一路”的規劃發展,其間的商業創業之艱難,興國戰略的實施,都需要勇敢的追求或探險。其中伴隨著的不僅有行旅的艱辛和危險,也常常有與外國人的交往和交易,并由此也揭示了“外交”與文學的關聯(具有“走出去”的“世界化”意義)。在絲路文學中,必然會呈現出更多的商賈形象、朝圣心態、神圣體驗以及浪漫主義的傳奇色彩,這從當代的新型創業文學也是新型絲路文學(長篇小說如文蘭的《絲路搖滾》、李春平的《鹽道》、王妹英的《山川記》等)中即可看到,自然也可以看到當代國人頗具漢唐雄風的包容氣度和中華民族艱苦創業的精神,這也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應該大力彰顯的靈魂或“文心”。這樣的“文心”自然也要契合“文學是人學”的原理,也要恰當地描寫人的欲望,而人的欲望最主要的就是人性中的物欲和愛欲?。從總體來看,中國的創業文學與絲路文學都主要是描寫或呈現“物欲”的文學。其實,成功書寫人類“物欲”的難度并不比書寫“愛欲”更容易。而能同時適度把握兩者并藝術地呈現兩者結合形態的作家更是極為少見。可貴的是,柳青、周立波及絲路作家們在從事創業文學、絲路文學創作時,業已付出了他們最大的努力,在把握民眾集體創業、絲路創業人生的過程中,也能竭力真實而又復雜地揭示出人物的物欲和愛欲(這與那些一味迎合低級趣味的絲路通俗文學或絲路網絡文學不同)。如今,當我們力圖追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時,創業的欲望沖動和火熱激情是如此強烈和充沛,當代作家們也當竭力追求,潛心經營,為大時代留下更加雄渾和輝煌的“新創業史”。
4.從創業文學和絲路文學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的創業和守業理應同等重要
總體看,人類從物的崇拜進至神的崇拜,再到以人為本,進而以“命”(廣義和狹義的生命生態)為本,其思想演變的發展史也充滿了上下求索的困惑和豁然開朗的欣悅?。但其間總是會伴隨著人對各種“創業”的渴望與努力。只是在有的時代,“創業”會被某種特定的“運動”所遮蔽、所遏制,吊詭的是,每當某種以漂亮口號為先導的政治熱潮興起時,就會有創業的趨緩及經濟的倒退。柳青、周立波們就經歷過這樣的歷史時期,“運動”遮蔽著“創業”,或者“創業”總是體現為民眾的強烈愿望和自發行為,而柳青、周立波們又總是能夠通過生活化的書寫和意味深長的“創業敘事”及相應的“勞動敘事”,揭示出歷史愿景與人民意愿的深深契合,而且總是能夠在更具有熱情和理想的年輕人身上看到未來的希望,使其“創業小說”還不期而然地帶上了勵志的意味。柳青、周立波們的創業文學,不僅當年曾激勵了一代讀者,而且如今依然能夠感動讀者,因為無比的真誠和創業的精神總是會具有超越時代局限的神奇力量。而絲路文學的當代發展進程,也必然要求絲路作家具有更加強烈的創業精神和包容意識,將創業與守業在國際化、多民族的多元文化交流中,使文學具有更多的開拓創業的正能量抒發,強調開放改革、腳踏實地、勇往直前的絲路精神對文學的影響,但同時也能使文學具有更多的護生惜命、養心怡神、反思超脫的人類學意味。如此,絲路文學將會展示出更為多姿多彩、生機無限的美好未來。
注釋:
①絲路文學是“絲綢之路文學”的略語。在學術界,習慣上將“絲綢之路”簡稱為“絲路”。
②李繼凱:《柳青的“創業文學”》,《文藝報》2014年2月21日。
③劉思謙:《對建國以來農村題材小說的再認識》,《文學評論》1983年第2期。
④宋炳輝:《柳青現象的啟示——重評長篇小說〈創業史〉》,《上海文論》1988年第4期。
⑤羅守讓:《為柳青和〈創業史〉一辯》,《文學評論》1991年第1期。
⑥周燕芬:《〈創業史〉:復雜、深厚的文本》,《西安聯合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
⑦劉納:《寫得怎么樣:關于作品的文學評價——重讀〈創業史〉并以其為例》,《文學評論》2005年第4期。
⑧薩支山:《當代文學中的柳青》,《當代文壇》2008年第5期。
⑨沈文:《文學湘軍三十年:崛起 輝煌 奮進》,《湖南日報》2008年12月18日。
⑩李繼凱:《秦地小說與“三秦文化”》,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劉維鈞:《振興絲綢之路藝術論綱》,《新疆藝術》1987年第1期。
?這種物欲與愛欲在沈從文的作品中有較好的表現,參見吳正鋒:《沈從文小說愛欲書寫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中國文學研究》2013年第4期。
?李繼凱:《彰顯生命“正能量”》,《東亞漢學研究》(年刊,日本),2015年。
(責任編校:文建)
On Contemporary Entrepreneurship Literature and Silk Way Literature
LI Jikai
In current cultural context,it is time to study Contemporary Entrepreneurship Literature and Silk Way Literature.Their relevance and significance also provide much food for thought.Stepping into New Normality and Time of Venture,we still can’t forget the previous difficult and exploring road.The historical Silk Road is essentially The Road of Entrepreneurship.Meanwhile,the Silk Way Literature also reflects corresponding Silk Way Spirit of hard struggle with deploitation and exploration.Contemporary Entrepreneurship Literature is represented by contemporary writers Liu Qing and Zhou Li-bo.Between the Contemporary Entrepreneurship Literature and the rising Contemporary Silk Way Literature, there actually exists close relevance.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mplicate meaningful enlightenment.
entrepreneurship literature;silk road literature;times of venture;positive energy;literature writing
李繼凱,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陜西 西安 710062)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延安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11&ZD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