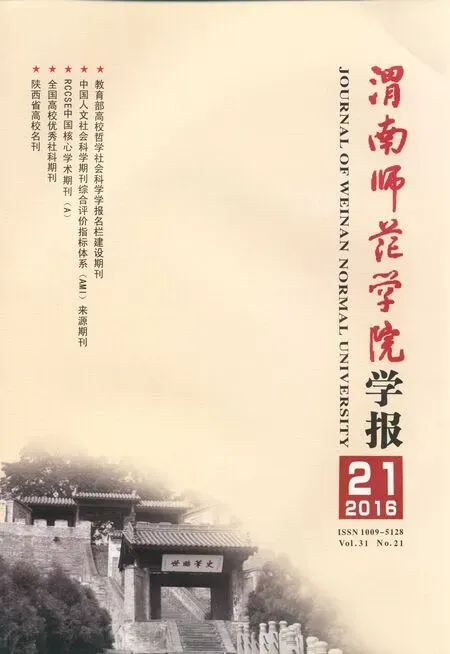論《史記》關于韓非思想淵源的判斷
韓 艷 秋
(渭南師范學院 人文學院,陜西 渭南 714099)
?
【司馬遷思想研究】
論《史記》關于韓非思想淵源的判斷
韓 艷 秋
(渭南師范學院 人文學院,陜西 渭南 714099)
《史記》中司馬遷將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韓非與先秦道家創始人老子并列于一傳,即《老子韓非列傳》,認為韓非的思想“歸本于黃老”,淵源于道家。在探討儒家、道家和法家思想的異同的背景下,就韓非思想的理論架構和基本主張進行辨析,以探討這一判斷的理論根據之所在。
《史記》;韓非;老子;思想淵源
《史記》中司馬遷將先秦道家創始人老子與法家思想代表人物韓非并列于一傳,即《史記》之《老子韓非列傳》。該傳首先對于先秦的儒、道關系,以及道家由老子到莊子的思想源流做了闡述,在莊子之后,即繼以法家前期人物申不害和法家后期集大成者韓非的記傳。并傳申不害、韓非和老子、莊子,說明司馬遷對道家思想與申、韓一系法家思想關系的看法,司馬遷并且在《老子韓非列傳》中明確闡述道:“申子之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1]4445,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1]4447。
從發展歷史考察,學術界一般將法家分為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戰國初期的李悝被尊為法家的實際始祖,他與吳起、商鞅、申不害是前期法家代表人物。前期法家與儒家有較為密切的關系:李悝、吳起都是子夏氏儒的弟子,商鞅的思想又受到李悝較大影響。[2]102而前期法家中的申不害則“本于黃老而主刑名”,與道家思想關系密切。韓非子作為戰國末年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對于商鞅和申不害思想都有批判和吸收,而其思想被司馬遷判斷為“歸本于黃老”,這一判斷是否成立呢?申不害在韓昭侯時為相,韓非為韓國公子,“喜刑名法術”,思想上對申不害一系自然有所承續,除了這一顯見的地緣原因外,更應就韓非思想的理論架構和基本主張進行辨析,并探討儒家、道家和法家思想的異同,以辨明《史記》這一判斷的理論根據之所在。
一
《韓非子》中有兩篇文章:《解老》《喻老》,對老子思想做了較為系統的專門詮釋,直接體現出老子思想對韓非的深刻影響。《史記》的評斷,應當與兩篇文章的內容有較大關系。
《解老》是韓非對《道德經》中部分篇章的解釋,在解釋時對老子思想進行了法家色彩的改造和發揮,但保有了老子的基本哲學范式。其延伸性理論架構,也仍本于老子的基礎理論,也即司馬遷所說的“皆原于道德之意”,“歸本于(黃)老”[1]4447。
老子思想的核心概念“道”,在《解老》中基本保持了形而上、無任何規定性、絕對性和永恒性的原意。韓非并且借助“德”和“理”這對范疇,共同建構和支撐起對“道”的社會性和自然性說明。
以形而上的“道”為依據,“德”在韓非的解釋中,主要涉及人的自身修養和社會生活范圍。對個體自身而言,“德者,內也”,“得身也”,“身全之謂德”,就是保有自己內在的本質,精神不游移在自身之外。那么怎樣達成“得身”呢,要“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3]187;拓展到社會生活層面,“身以積精為德,家以資材為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為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余,故曰:‘修之家,其德有余。’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余者益眾,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眾,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蒞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3]219。無論是個體修養,還是由“家”到“鄉”到“邦國”到“天下”的全部社會生活,韓非顯然都主張虛靜內斂、含藏積累、與民生息,這與老子的人生主張和社會主張的基本取向是一致的。在解釋《道德經》三十八章內容時,韓非沿著老子的“德—仁—義—禮”的說明層次,對人的存在和社會生活給出了層級性的說明:“仁者,德之光”;“義者,仁之事”;“禮者,義之文也”,而其出發點和根本依據,則在于形而上之“道”: “德者,道之功”[3]190。
在《解老》中,引文的順序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后,韓非以“德”和“道”的關系梳理了人的個體修養及社會生活的準則和指引。在“道經”引文的解釋中,韓非子特別提出“理”的觀念,意圖就“道”與世界尤其是與自然界的關系給予更清楚和客觀化的說明,并以“道”和“理”互相闡發。而韓非對老子思想的延伸和改造,也更多地借助于“理”這一范疇來呈現。
首先,從“理”的內涵來看,“理者,成物之文也”[3]208,萬物各有其理,“凡理者,方圓、短長、粗靡、堅脆之分也”[3]211,理是萬物的方圓、長短、粗細、堅強或脆弱等的區別,“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3]208,萬物各有其理,不互相混擾,理制約萬物、使得萬物各自得到確定和說明。萬物各有自己與眾不同的“理”,即各自的特殊性和特殊規律。可以看出,韓非子是從普遍規律與特殊規律的關系角度解釋“道”和“理”的,相應地,“道”是“萬理之所稽”,道完全匯合了萬物的理,從“理”的角度來反觀“道”,則“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興廢焉”[3]208。
韓非對老子“道”的形而上特性、根本性和根據性給予了充分的闡述和肯定,其對道的解釋基本符合老子的原意。“凡道之情,不制不行,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3]209。而“理”這一范疇的提出,使得“不可道”“無常名”“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的虛懸抽象的“道”,得以向下落實,并得到更明晰更切實的說明。在解釋《道德經》中“道經”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時,韓非子以“理”的具體性、明確性、暫時性,來顯托“道”的恒久性、無限定性、包容性,意圖從“理”的層面說明“道”的存在狀況:“凡理者,方圓、短長、粗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生乍死,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之‘常’。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于常所,是以不可道也。圣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不)可論,故曰:‘道可道,非常道。’”[3]211
對于事物的處理,應當先得其理,“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3]216。所以要先研究清楚所要處理事物的“理”,“理”在這里,顯現出客觀規律和法則的意蘊,能成功地處理各種事項,正在于發現和遵循了這些客觀的規律和法則。韓非對老子“不敢為天下先”的解釋也因此少了人為的思慮和操縱意味,而被闡發為:“圣人盡隨于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為天下先。’”[3]216在有些地方,韓非將“道”“理”并稱,進一步闡發掌握和遵循道理、規律,是決定各種行事能否成功的最基本條件:“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夫棄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眾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3]194對于福禍轉化、道反而復的深遠境界,只有掌握了“道理”,才可能了解其關鍵和邊際。當一個人重視生命、看重事功,就會謹慎從事、深思熟慮,“得事理,則必成功”[3]214,能夠有見必行之道的明智,行之不疑的勇氣。在這里,個體的性格特征的感性和主觀色彩變淡,人的慈愛、明智和勇氣,都得到了更客觀的分析化的務實解釋。
《喻老》用具體的歷史事例、民間傳說等解釋說明《道德經》的抽象道理和哲學思想,意圖使之與社會生活結合起來,具有較強的現實性,反映出時代精神;但另一方面也因此使《道德經》中豐富的哲學意蘊變得過于狹隘和質實,甚至干癟和喪失。[3]222《喻老》對老子思想的演繹,對老子思想中一些重要哲學范疇的解釋,指向和定位于政治思想的現實化操控和應用,并納入到其“法、術、勢”結合的政治哲學體系。如老子二十六章:“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老子借助“輕重、躁靜”相對范疇,是批判當時統治者奢恣放縱、一無效準,立身行事草率盲動的輕躁作風。[4]173而韓非則以趙武靈王“生傳其邦”進行解釋,認為“邦者,人君之輜重也”,趙武靈王在自己還活著時,就將王位傳給小兒子。“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3]225老子說:“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是說權勢禁令都是兇利之器,不可以用來耀示威嚇人民。[4]208韓非則認為“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并以田氏代齊,六卿擅權于晉,說明“君人者,勢重于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并以賞罰之權為“邦之利器”,認為君主要牢牢將這一權利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故讓臣子掌握了賞罰之權,或窺伺到君主賞罰的意圖,都會“在臣勝君”,“用其勢”而“乘其威”。[3]227
從《解老》《喻老》而論,無論是對老子原文給出較為明確的理論或實例解釋,還是對老子辯證思想中一些相反相對范疇,運用推理給以環環相扣的解說,韓非都意圖使老子思想內涵明晰化、現實化,具有強烈的現實和社會政治指向意味,也不可避免地使老子思想在被解說后,變得狹窄化和功利化。
二
《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有《論六家之要指》一文,對當時影響較大的六家學術流派:儒家、(黃老)道家、法家及墨家、名家、陰陽家等各自的思想內容和特點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總結性闡述,并對其優劣給出了評判。此文司馬遷說是其父司馬談所著,但從楊雄、班固開始,就依據此文評價司馬遷的思想,曾國藩在《求闕齋讀書錄》中甚至認為:“《論六家要指》即太史公之學術也,托諸其父談之詞耳。”盡管《論六家要指》是否為司馬遷本人所做,還存在爭議,但從《史記》全書思想來看,與《論六家要指》學術思想主張是互相通同的。[2]161
需要注意的是,以“黃老”稱道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將先秦初始道家的思想,與戰國末、漢初的黃老道家之學并為一談了。黃老之學雖然繼承了道家思想,但由于適應時代要求,融會諸家思想,已經有了較多改變和發展,不能完全等同于先秦原始道家思想。
《論六家要指》認為,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1]7636, 其社會政治主張,“雖百家弗能易也”[1]7642。但儒者以六藝經傳為本,而“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1]7636,儒家經傳典籍浩繁,從學者耗費巨大精力,卻不容易把握要領、通達究竟。正因為儒學廣博而難得要領,辛苦勞頓而很少功效,所以不能完全遵循儒家的思想主張。法家思想“正君臣上下之分”,“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弗能改也”[1]7645。重視君臣之分,尊崇君主,使臣子卑下,明確君臣的上下名分和各自的職責,不能相互逾越,法家的這種主張是不能改易的。司馬遷認為君臣父子上下的社會秩序是應當維護和不能動搖的,儒家和法家在維持國家等級秩序這一點上都有可取之處。但法家思想和法治的基本精神,是“范天下之不一,而歸于一”,“平之如水”,以法為準則治理天下,追求形式上平等,除君主外,對其他所有人“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與禮治精神的“氏所以別貴賤”,以血緣親疏區別社會等級、地位尊卑的主張是不同的。[2]101法家“嚴而少恩”,除去嚴格的君臣之分,在社會生活的其他各個層面,因為它“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實際上也對以血緣家族為紐帶建立起來的宗法社會結構,親疏尊卑的社會秩序有很大的沖擊,所以《論六家要指》認為法家思想“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1]7645。那么如何既能維持主尊臣卑的國家秩序,且能穩固親親尊尊的社會秩序,又不似儒家之“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論六家要指》認為黃老道家的思想主張能夠兼備儒家和法家之長,更兼采諸家,是最理想的,“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1]7636,黃老道家總結和吸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及陰陽家等諸家思想,能夠順應客觀時勢的發展變化,采取相應的措施,因時、因事、因地制宜。而且宗旨簡要,易于掌握實施,用事少而功效大。《論六家要指》從道家的理論立場上觀照和批評儒家思想:“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1]7637。儒家思想認為君主是天下的表率,應當君主提倡,臣下應和,君主先導,臣下跟隨,結果是使得君主勞累,而臣下安逸。至于道家的根本主張,要求去除剛強與貪欲,舍棄耳目智巧,拋掉儒家學說,任以道家自然之術。像儒家那樣將耗盡精神,形體勞弊,而想要和天地一樣長久穩固,是不可能的。道家無為而無不為,“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后,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1]7646,以虛無為本,順應萬事萬物的變化,不固定執著于某種形式,所以能了解萬物的規律。既不超前,也不滯后,所以能成為萬物的主宰。依據或不依據法規,要根據時勢而定;有限度或無限度,要合乎事物的實際情況。這種理論落實到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領域,被現實化為“因者,君之綱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奸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1]7646。如上的道家的政治理論認為,因勢利導是君主的綱領,當群臣一起來到君主面前,君主應當使他們顯露各自的本質。實際行為與言語一致的人端正,實際行為與言論不符的人虛假。不聽信假話,奸詐就不會發生,賢者與不肖者自然得到區分,就像白色和黑色一樣分明。只要君主運用這些,什么事情不能辦成功呢?這些是合乎大道的,看起來混冥,光輝卻照耀天下,又返歸于道。審視這些對于黃老道家的思想論述,可以看出,如果這種思想主張被延伸和發生裂變,很容易與韓非所主張的“君主之術”發生聯系。
韓非作為戰國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總結了前期法家商鞅、申不害等的學說。申、商各有所重:“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 “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3]620。術為君主駕馭群臣的權術,“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3]620。 韓非分析了因為“徒術而無法”和“徒法而無術”,申不害與商鞅在治理國政方面各自的失誤。在韓非看來,就如食物與天寒時的衣服都對人“不可一無也”,“法”與“術”“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3]620。韓非還認為,推行法、術必須要有權勢地位,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法、術、勢結合的系統學說,重視賞罰,提倡耕戰、主張君主牢固占據權勢地位和運用權術。法、術、勢的交互運用和互為支撐,使得君主在掌握權勢、考察監視臣下,控制國家局勢的實際操作中,確實有“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因時為業”“因物興舍”,“虛無為應、變化無為”的意涵。如在《主道》中,韓非將道家哲學思想改造和運用到政治生活層面,要達到“明君無為于上,群臣竦懼乎下”[3]35的效用,老子的“道”論在這里被闡釋為:“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3]34。明君需要始終把握作為萬物的本源、是非的綱紀的“道”,用虛靜無為的態度來應對一切,令事物以它本來面目呈現和形成。虛則可以了解事物真相,靜則知道行動是否正確。“道”與“虛靜無為”,在這里成了為政治目的服務的權術手段,“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暗見疵”[3]36。那么政治生活中何以虛靜無為呢,具體表現為君主不表現個人好惡取舍,高深莫測,讓臣下捉摸不定,“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3]35,君主不表現自己的喜好,如果表現出自己的喜好,臣下就會粉飾言行,投其所好;君主不要表現出自己的意圖,意圖表現出來,臣下就會掩蓋自己的本來面目迎合君主。所以君主去除了好惡取舍,臣下就會呈現其本真之態;君主去除自身的成見智巧,臣下就會處處謹慎對待。韓非進一步有針對性地闡述道:“函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3]37,“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賢而不以行,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3]35,君主不表現自己有智識、賢明和勇武,以使臣下發揮出他們的才能智慧、逞賢爭功,則“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正所謂“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為于上,群臣竦懼于下”,道家虛靜無為的思想,被韓非改造和實在化為政治生活領域君主馭使臣下的權謀思想,并給出細致的描述。又如在《內儲說》中,韓非具體提出君主控制臣下的七種權術:“一曰眾端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3]318“眾端參觀”和“一聽責下”是要全面掌握情況,并分別一一考察臣下,具有“勢”的意味;“必罰明威”和“信賞盡能”是信賞必罰、厚賞重罰,以確立威勢,使臣下竭盡所能,屬于“法”的范圍;其余“疑詔詭使”“挾知而問”“倒言反事”,使用假命令和詭計探測臣下;明白的裝作糊涂,知道正確的故意說錯,顛倒意圖對臣下進行考察和試探等等,都是“術”的陰暗運用。老子虛靈變化、無為無常的思想,與韓非對人性極惡的隱含認定相結合,產生出不擇手段、詭詐機變的陰謀權術。
《韓非子》一書中并沒有專門論述人性的文字,但韓非對人性的看法,可以從其引用史例的傾向,使用的比喻、寓言之寓意等看出。《說林》上下篇一般被認為是韓非為他的著述準備的資料,在其中商湯讓國于務光,宋太宰見孔子,齊桓公救邢國,趙、韓、魏滅智伯等,許多事例呈現出當人性被權力和利益的陰影所籠罩扭曲,人的陰暗險惡。韓非子認為:“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3]161醫生為了醫治病人會吮吸其血膿,并不是因為是自己的親人,而是利益驅使。賣車的人希望人富貴,賣棺材的人希望人死亡,并非是賣車的仁愛、賣棺材的人殘忍,都是為了售出自己的貨物獲取利益。太子與后妃結黨,希望君王早死,以加重自己的權勢。當人性被權力和利益的陰影所籠罩扭曲,人和人之間無所謂關愛仁義,有的只是利益關系,君主與臣下更是只有互相的猜忌和不信任,“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人主之患在于信人”。[3]159老子虛靈變化、無為無常的思想,與韓非對人性為惡的隱含認定相結合,產生出不擇手段、詭詐機變的陰謀權術,這在韓非思想中“術”“勢”的方面體現得尤為突出,并且與“法”的運用交織混成。這種實利化、權謀化的偏狹取向, 斫斷了老子思想中虛無弘遠的意蘊,喪失了老子內蘊的對當時的社會現實的深沉悲憫之情,以及對社會發展可能性的更廣遠探問。這也是為什么司馬遷會說“老子所貴道,虛無為應,變化于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韓子引繩墨,切事情,名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1]4466。
[1] [漢]司馬遷.史記[M].韓兆琦,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78.
[2] 張豈之.中國思想史[M].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89.
[3] [戰國]韓非.韓非子[M].高華平,王齊州,張三夕,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
[4] 陳鼓應.老子注譯及評介[M].北京:中華書局,1984.
【責任編輯 朱正平】
The Judgment of Historical Records to the Thought Origin of Han Fei
HAN Yan-qiu
(School of Humanities,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714099 Weinan, China)
Historical Records had the biography including Han Fei who was the Legalist’s representative figure, and Lao Zi who was the founder of Taoism, which is named The Biography of Lao Zi and Han Fei. It was deemed that the thought of Han Fei was rooted in thought of Huang-Lao Taoist. The thoughts of Confucian school, Taoist school, and the Legalists are compared to analyze the framework and basic ideas of the thought of Han Fei, and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judgment of Historical Records.
Historical Records; Han Fei; Lao Zi; ideological roots
K207
A
1009-5128(2016)21-0022-05
2016-09-06
韓艷秋(1973—),女,陜西西安人,渭南師范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哲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哲學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