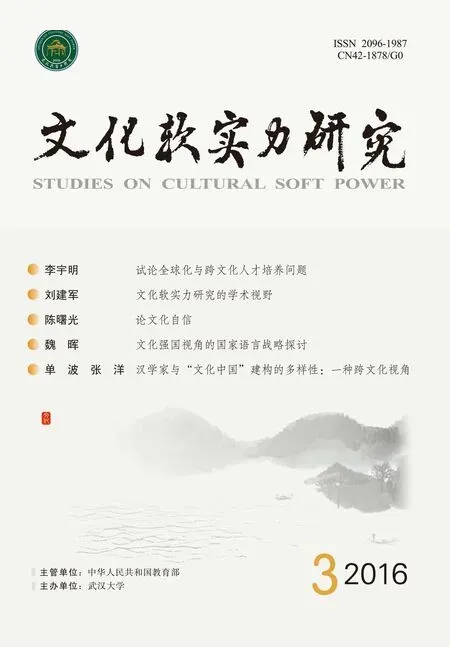漢學家與“文化中國”建構的多樣性:一種跨文化視角
單 波 張 洋
?
漢學家與“文化中國”建構的多樣性:一種跨文化視角
單 波 張 洋
從跨文化視角出發,延展了邊緣人理論的范疇,提出“文化邊緣人”的概念以涵括漢學家群體所具有的跨文化屬性,進而考察漢學家如何參與到“文化中國”的建構之中。將漢學家與中國的主體位置和情感介入作為兩個基本的維度,通過對十余位現當代知名漢學家生活經歷與學術研究的分析,總結出基于外部文化的介入者、基于外部文化的中立者、基于中國文化的中立者、基于中國文化的介入者四種文化邊緣人類型,揭示了漢學家與中國文化產生互動的多元文化機制,為思考“文化中國”的建構路徑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漢學家 文化邊緣人 文化中國 中國化
漢學家是一個涵蓋廣泛的文化概念,從最寬泛的意義上講,一切受到某種機緣促使,關注中國并與中國文化產生接觸的非華裔人士都屬于漢學家的范疇。伴隨著中西方文化交流互動途徑的變遷,漢學家的群體特征也發生了相應的轉變。最初的漢學家包括以馬可·波羅為代表的外交使者與旅行家,這些來自異鄉的人士遠赴中國探險,將在中國期間的生活體驗和觀察所得撰寫成游記。游記中描繪的帶有異域風情的中國形象,被所在國家的民眾所熟悉,構成了西方人認知中國的情感底色和知識基礎。隨后,西方教會進一步開啟了面向中國的傳教活動,職業傳教士也成為漢學家的主體。相比于旅行家們走馬觀花式的感知,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傳教士為履行傳教使命而深入中國社會,與中國的士大夫階層應酬往來,客觀上形成了與文化中國的互動關系。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漸深入,游記式的書寫已不能滿足西方精英人士了解中國的需要。在經歷了啟蒙運動的洗禮之后,歐洲國家誕生了現代意義上的大學以及專業的科學研究人員,探索自然世界與人類社會的運作規律。1814年,法蘭西學院(Collége de France)創立了最早的漢學教席,涌現出沙畹、伯希和、馬伯樂、葛蘭言等一批專業的漢學家。由此,漢學研究由業余走向專業,對中國認知的來源由日常生活體驗向文獻典籍研讀延伸,由單向的認知轉化為文化間的“擺渡者”。1955年,曾經出任駐華外交官的費正清在哈佛大學建立起東亞研究中心,繼法蘭西學院之后成為漢學研究的樞紐*曾有學者區分“漢學”與“中國學”的內涵,認為漢學研究以法國為中心,以人文學科為主體,關注中國古典語言與文學,以審美和求知為旨趣;而中國學研究則以美國為中心,以社會科學為主體,關注中國現實及對外關系,以政策研究為旨趣。本文對此持相對寬泛的界定,未對二者加以嚴格區分。。其后,漢學研究逐漸在世界開枝散葉,蔚為大觀,成為西方知識體系延伸的重要邊緣領域,同時也成為“文化中國”的重要邊緣領域。
“文化中國”是杜維明先生在全球化時代對中華文化發展前途的構想,按照其經典劃分*杜維明、劉夢溪:《“文化中國”與儒家傳統——杜維明教授訪談錄》,《中國文化》1993年第1期,第205~209頁。,“文化中國”的第一層由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新加坡等華人聚居區組成,是文化中國的核心與基礎。第二層則是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他們旅居在異文化之中但仍然保留著中國文化的身份認同和生活方式,促進中華文化在世界各地的扎根與傳播。最外的一層,是因為種種生活經驗與中華文化發生關聯、對中華文化產生親近感與認同感的非華人,從而打破了種族與血緣界限的區隔。那么,漢學家是在什么維度建構文化中國的?如何認知漢學家的文化邊緣人特質?這種文化邊緣人的特質與文化中國建構形成了什么關系?文化中國的多重建構有什么意義?這是以往的研究所忽略的跨文化問題,本文試圖做出初步的探討。
一、從漢學主義到中國化:理解漢學家的兩種維度
就研究對象和學術體制而言,漢學屬于廣義“東方學”的組成部分。按照文學批評家薩義德的經典表述,東方學是西方殖民主義擴張的產物*薩義德:《東方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51頁。,東方喪失了表述自己的能力,只有依賴西方的話語才能在世界范圍內發聲。同時,作為社會現實的東方需要經過東方學的過濾框架,才能進入到西方的意識之中*薩義德:《東方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9頁。。東方學家將東方描述成非理性的、墮落的、幼稚的、恒定不變的他者,與西方文明相對立,從而合法化了帝國主義的擴張,成為西方現代政治文化的組成部分*薩義德:《東方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6頁。。
從東方學的視角出發,漢學研究具有知識體系、思維方式和權力話語三重身份*張松建:《殖民主義與西方漢學:一些有待討論的看法》,《浙江學刊》2004年第4期,第191~196頁。。從最基本的層面上,漢學是一種以客觀面貌出現的知識體系,代表著西方學術界對中國的認知狀況。其次,在知識體系背后,是一套系統思考中國的方式,也是知識體系得以再生產的條件。最后,相關的知識體系與思維方式,都是學術政治的產物,與權力體制息息相關。漢學作為一種西方文化他者的話語,本質上是西方現代性的組成部分*周寧:《漢學或“漢學主義”》,《文藝理論研究》2004年第1期,第5~13頁。。
薩義德對東方學的建構,主要源于其對西方陰影籠罩下的中東文化的觀察與思考,當將這種思考拓展至中國時則存在一定局限。最本質的區別便是中國從未有過像中東或印度一樣被西方帝國完全殖民的經歷,因而漢學研究也并未承擔為戰略征服而正名的“殖民話語”使命,所以漢學與傳統的東方學在歷史上有著截然不同的本質和功能*顧明棟:《漢學主義:東方主義與后殖民主義的替代理論》,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16頁。。因此,20世紀末期有學者提出“漢學主義”(Sinologism)一詞用以指涉在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和認識論、方法論的指導下所進行的有關中國的知識生產。有學者嘗試以“漢學主義”來替代“東方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的視角,超越東方主義理論中嵌入的敵對的政治意識形態,轉而考察中西跨文化研究中的文化無意識現象*顧明棟:《漢學主義:東方主義與后殖民主義的替代理論》,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17~22頁。。然而,當一種文化現象被視作“主義”時,就已經被假定成凝固、封閉的觀念體系,事實上依然無法擺脫意識形態的籠罩,忽視了漢學研究作為一種開放語境下的跨文化交流的屬性,也無法充分揭示漢學研究在跨文化交流過程中所具有的積極作用。
“中國化”(sinicization)一詞用來指涉某種事物在與中國文化產生關聯的過程中接受中國文化濡染,進而具有中國特質的過程。“中國化”既可以用來描述外來思想進入中國后進行本土化改造,如許多學者研究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陶德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個前提性問題》,《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5年第2期,第134~140頁,在這種意義上,“中國化”是普遍的“馴化”(domestication)過程的特殊表現。同時“中國化”也可以用來形容個體或群體接受中國文化熏陶,由此對于中國產生身份認同的狀態。在此基礎上,又衍生出“去中國化”(desinicization)、“再中國化”(resinicization)等表述,用以形容中國文化認同建構過程中復雜的動態過程。
本文是在后一種意義上使用中國化的概念,并以此與“文化中國”的論述銜接起來。中國化正是發生在文化中國的外部圈層像波浪一樣向外擴散的過程中,他者在跨文化交流中遭遇中國文化并選擇親近中國的文化認同,從而實現了中國文化的意義輸出。然而文化的傳遞并不是風吹草偃般的線性過程,而是多向互動的文化實踐,具有復雜的作用機制。身居海外研究中國的漢學家,無疑屬于文化中國的第三圈層,漢學家因為某種機緣對中國文化產生濃厚的興趣,致力于考察中國的文物典籍或現實發展,同時通過自己的課堂講授與公共著述將有關中國的知識傳遞到自己所處的文化中,充當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而漢學家選擇以研究中國為志業,背后有著不同的文化立場與訴求,這也使之成為考察中國化作用機制的重要樣本。
如果說“漢學主義”式的思考路徑,將漢學家的中國研究視作一種凝固的權力結構的生產與宰制,關注漢學研究中集體的、連續的、靜態的、無意識的向度,那么“中國化”式的思考取徑,則將漢學研究者視為結構之中能動的個體,旨在還原漢學研究中被前者遮蔽的個體的、離散的、動態的、有意識的向度。西方國家對于中國的集體想象雖然在宏觀上制約著漢學家研究中國時的核心議題、知識語境和價值判斷,但漢學家并不完全受制于西方學術體制和現實權力政治,漢學家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的同質化群體,他們在研究中國時浸入著自己認知中國的情感體驗,不同類型的情感體驗進而賦予了漢學研究多樣的視角與立場。
臺灣學者石之瑜、吳昀展曾經借用“中國化”的理論視角考察四位亞裔離散學者對中國的遭遇與選擇,揭示他們在有關中國的學術研究中投射出的中國認同與中國形象,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啟發*石之瑜、吳昀展:《“施擬夏化”的文化機制:四位亞裔離散學者對中國的遭遇與選擇》,《世界漢學》2010年第13期,第64~82頁。該文用“施擬夏化”作為sinicization的音譯,本文則采用通譯的“中國化”。。然而該文選擇的四位研究對象均為亞裔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樣本有著較大的限制。更重要的是,該文實質上以知識社會學為底色,旨在考察四位學者有關中國的知識鏈生成的跨文化語境,并未將文化交流本身作為研究對象。而本文試圖引入跨文化傳播研究中的邊緣人理念來理解漢學家“中國化”過程中的精神世界,并據以解釋漢學家認知中國過程中潛在的多元取向與機制。
二、作為文化邊緣人的漢學家
邊緣人概念要上溯到陌生人以降的理論脈絡。陌生人概念最初由德國哲學家喬治·齊美爾在1908年提出,指涉的是一種漫游中的生活狀態,“陌生人不是今天來、明天走的流浪者,而是今天來、明天留下來的漫游者,他雖然沒有繼續游移,但是沒有完全克服來與去的脫離”。*西美爾:《社會是如何可能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41頁。齊美爾將陌生人理解為一種社會互動的形式*Karakayali,N.: The Uses of the Stranger:Circulation,Arbitration,Secrecy,and Dirt,Sociological Theory,2006,24(4):312-330.,并未受到特定地域或職業的限制,當對于社會關系的確定性感覺開始消失的時候,陌生感就產生了。
不同于生長于斯的本土人,陌生人以一種游離的心態棲居在特定社會之中,他雖然可能與群體中的成員有種種形式的接觸,但并未在根基上被所在的環境固定化。他雖然與群體成員產生了意義的共享,卻在身份上保持疏離,既沉浸其中,又可以隨時抽身而去。因此,客觀性是齊美爾界定陌生人的首要特征,陌生人可以用更加客觀和超脫的視角,若即若離地觀察身處的社會情形。這里所說的客觀,并不是袖手旁觀般超然事外,而是一種超越了確定性限制的特殊參與方式,使得外來者能夠以鳥瞰的視角來對待身處的關系*西美爾:《社會是如何可能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44頁。。
美國社會學家帕克受陌生人思想的影響,提出了作為文化混血兒的邊緣人。邊緣人生活于兩種以上的文化群體之間,具有兩種并存的文化背景,并親密地分享兩種不同的文化和生活,邊緣人不愿意同自己的傳統決裂,但種族等先天身份所引致的偏見,使得他無法融入新的社會,只好在兩種文化、兩種社會的邊緣生存*Park,R. E.: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28,33(6):881-893.。相比于齊美爾筆下超然客觀的陌生人,帕克為邊緣人賦予了文化混血兒的特質,邊緣人希望融入主流的文化卻無法實現,因此為自己混雜的身份而感到焦慮不安。
帕克的學生斯通奎斯特進一步發展了邊緣人理論,他認為移民只是產生邊緣性的原因之一,教育、婚姻等行為都可能產生相應的邊緣性,當一個人開始學習“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歷史、文化、政治、宗教和倫理規則時,其邊緣性就產生了”*Everett Stonequist:The Problem of the Marginal Ma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35,41(1):1-12.。因此,這種邊緣性將廣義的文化范疇納入考量,不再局限于早期圍繞種族或生理差異而設置的邊界,成為一種多元、流動的概念,更加富于彈性和解釋力。
隨著邊緣人概念在社會學、心理學、跨文化傳播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這一概念的意涵又發生了兩點重要的轉變。首先,邊緣人的外延不斷擴大,研究者傾向于用“邊緣情境”來界定邊緣人的身份,認為只要是在社會文化的界限被跨越的地方,就會產生邊緣狀態,由此那些由于社會關系或個人心理對于社會主流感到疏離的群體,都被納入邊緣人的范圍。這一理論上的轉變,可以理解為對現代性發展的回應,隨著現代社會的個體化趨勢以及文化間的交流活動日趨顯著,每個人都有可能處于邊緣情境,變成社群中的陌生人或邊緣人*Stichweh,R.:Der Stranger—On the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Society,Journal for History of Law,1992(11):22. 轉引自田小琦:《齊格蒙特·鮑曼的陌生人理論》,北京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
其次,邊緣人從最初的負面意味逐漸轉向中性。帕克對于邊緣人的處境給予了悲觀的理解,認為邊緣人處在初始群體和新群體的文化夾縫之間游移不定,是社會問題的潛在來源。但后續研究者發現邊緣人可以采用多種策略來調適自己的文化身份,不會遭遇文化分裂的困境。因此,當邊緣人概念應用于跨文化交流與文化身份的研究中時,通常僅用來區分群體差異,并不包含褒貶的色彩*張黎吶:《美國邊緣人理論流變》,《天中學刊》2010年第4期,第64~67頁。。
在全球化時代,早先基于熟人社群的社會關系發生重組,作為分析單位的文化,不再受到地緣與血緣的束縛,變成可以流動與伸縮的概念。基于邊緣人理論與文化中國的構想,本文擬提出“文化邊緣人”的概念。文化邊緣是一種文化的外沿地帶,是多元文化對話與互動的空間,也是文化的核心價值向異文化輸出的重要渠道。不同文化的元素在此聚合,創造出新的意義并反饋各自的文化母體,從而實現跨文化交流*滕守堯:《文化的邊緣》,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頁。。文化邊緣人,正是棲居在文化邊緣地帶,對于兩種或多種文化有著真切感知,并據以調適自己的身份認同和行為方式的人。同時,文化邊緣人借助自己在多元文化之間的實踐,在客觀上促成了文化間的交流與理解。
歷史上的旅行者、傳教士,今天的跨國企業員工、難民、婚姻移民等,都屬于典型的文化邊緣人,不同學科的研究者對于這些群體的文化適應、跨文化能力等現象也有了一定的關注*如:單波、王媛:《跨文化互動與西方傳教士的中國形象認知》,《新聞與傳播研究》2016年第1期,第5~25頁。。然而在跨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漢學家,卻沒有受到跨文化傳播研究者的關注。與上述群體不同,漢學家通常并沒有在中國長期定居的經歷,甚至有些漢學家終其一生沒有來過中國。然而漢學家通過大量的閱讀與考察,接觸并了解中國文化,對中國文化產生親近感和認同感,同時又穿梭于不同的文化從而促進跨文化交流,正契合文化邊緣人的概念所指。而漢學家如何利用所處的邊緣情境發展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的視角,如何受到中國化機制的影響進而被吸納入文化中國的范疇之內,則成為有價值的考察對象。
三、漢學家的跨文化經驗與文化邊緣人身份
本文搜集了20世紀以來較有影響力和典型性的漢學家的個人傳記、回憶文章、序言、對話錄和訪談等材料,將其生活經驗予以文本化,使之成為個人經歷與歷史進程的交匯點,從而描繪漢學家作為文化邊緣人在研究中國文化的過程中經歷的文化碰撞與融合,分析這樣的文化經驗如何促進了漢學家的中國化進程,而不同的中國化路徑對于漢學家從事學術研究的主體性產生怎樣的影響。經過對眾多漢學家的文本材料進行歸類整合,本文將漢學家與中國的主體位置和情感介入作為兩個核心的維度。其中主體位置指的是漢學家傾向于從怎樣的立場和視角出發研究中國,可分為基于中國文化與基于外部文化兩種;情感介入則指漢學家與現實中國接觸所引發的情感體驗是否介入到他們有關中國的知識生產之中。由此可以將漢學家的邊緣人經驗與中國化路徑區分成四種類型。
(一)基于外部文化的介入者
這類漢學家與中國有著豐富的跨文化互動經歷,通常曾多次來華并與中國人士有著較多接觸,他們對中國有著濃厚的感情,然而其學術底色仍然植根于本國,對中國的研究多半是出自其對于本國政治和社會問題的關懷,并不傾向于從中國本土的問題出發展開研究。在現當代漢學家中,費正清、杜贊奇等為這一類型的代表。
費正清早年以政治為志業,在1927年進入哈佛時熱衷參加學生活動,并不熟悉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從未想過研究中國。費正清與中國的機緣始于1928年,在導師韋伯斯特的建議之下,費正清才開始關注近代中國的外交史*費正清:《費正清中國回憶錄》,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6頁。。1929年費正清從哈佛畢業前往牛津深造,開始系統地學習漢語,由此正式走上了研究中國的道路。1932年費正清第一次前往中國,在中國度過了4年的時間,查找檔案完成了自己以中國海關為主題的博士論文。在此期間,費正清結識了胡適、陶孟和、丁文江等中國知名知識分子,與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感到“中國的環境包圍著我,給我以影響”*費正清:《費正清中國回憶錄》,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頁。,產生了強烈的理解中國的欲望。除在北京生活外,費正清還前往上海、杭州等地考察,以期獲得對中國的全面了解*費正清:《費正清中國回憶錄》,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66頁。。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費正清再次前往中國,與政界和知識分子展開了更深入的交往,使得費正清成為美國的頭號“中國通”。由于與龔澎、楊剛等左翼人士的接觸,費正清對于處于延安的中共政權逐漸抱以好感,并參與推動美國對華政策的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費正清因其親共立場而遭受麥卡錫主義迫害。1955年,費正清在哈佛大學籌辦了中國研究中心,奠定了美國漢學研究的制度基礎。自1966年起,費正清主編了六卷本的《劍橋中國史(1800—1985)》,成為西方學生了解中國歷史的重要來源。
作為一名有志從政的美國學者,費正清盡管對中國抱有深厚的感情,但是他在不同階段發表的有關中美關系的言論,其背后的立場始終是美國利益與現實主義原則*余英時:《師友記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74頁。。豐富的中國經歷使得費正清意識到中國的智慧與潛力,認為需要借鑒中國經驗制定美國的外交戰略,并推動中美兩國的交流與合作。而費正清的實際影響也超越了象牙塔的藩籬,直接介入了中美兩國的文化外交之中,成為促成中美兩國建交的重要人物。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印度裔漢學家杜贊奇出身于第三世界,在對中國的研究中投射了另一種現實關懷。杜贊奇的家鄉阿薩姆邦鄰近中國云南,在大理國被征服的過程中,云南本地的族群不斷向南遷徙,最終有一支阿薩姆人進入阿薩姆邦。這種流離的歷史創傷和混雜的民族構成,為杜贊奇在后半生的學術生命中關注族群問題,并努力解構民族的宏大敘事奠定了基礎*杜贊奇:《亞洲傳統:現代性發展的另一條出路》,《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10月29日第6版。。1973年,還在德里大學讀書的杜贊奇被中國的“文革”所吸引,認為“它似乎展示了另一種可能改變歷史的途徑”*劉榮:《專訪芝加哥大學終身教授杜贊奇:現代性危機的東方救贖》,《鳳凰周刊》2015年第30期。。正是在這股極“左”浪潮的裹挾之下,杜贊奇赴美深造,跟隨孔飛力學習。杜贊奇在美國期間從事的研究課題,既受到孔飛力等漢學界非革命一代學者的影響,同時也喚醒了他本人的生活體驗*李宗陶、杜贊奇:《現代性之“惡”與民族主義的“毒”》,《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1期,第80~82頁。。杜贊奇始終在探索現代國家如何構造新的文化,如何從歷史的極權話語中召回被壓抑者的聲音,前者體現于《文化、權力與國家》中對中國華北鄉村的考察,后者的關懷則在《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中得以彰顯。為了尋找超越現代性的出路,杜贊奇從中國的歷史中找到參照系。杜贊奇認為,與印度曾經完全殖民化不同,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殖民史,“這是兩國對待現代性問題態度迥異的重要原因”*李邑蘭:《“國家進入繁盛期,就沒必要過分強調民族對抗歷史了”——專訪印裔美國歷史學家杜贊奇》,《南方周末》2010年12月30日。。作為亞裔學者,杜贊奇近30年來每年都會造訪中國,去過北京、上海、成都、廈門、青島,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在中國考察期間,杜贊奇著重觀察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社會心理的變化,并因此而不斷深化對于本土現代性的理論思考*杜贊奇:《亞洲傳統:現代性發展的另一條出路》,《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10月29日第6版。。正是在對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的考察之中,杜贊奇致力于從中國本土歷史軌跡中提煉出不同于西方現代性的經驗,從而為其母國的發展道路提供鏡鑒,進而尋找中國與印度共享的特質,從而追索“全球化時代的亞洲之路”*陽敏:《全球化時代的亞洲之路——漢學家杜贊奇訪談》,《南風窗》2007年第2期,第82~84頁。。
在現當代的知名漢學家中,魏斐德、裴宜理乃至基辛格、傅高義等研究中國的經歷都可歸于此類。這類漢學家最初都是因為政治而非學術的因素而與中國發生聯系,具備在中國生活或與中國交往的豐富的跨文化經歷,同時其研究中國的深層目的是為其本國的發展路徑提供借鑒。魏斐德因為出眾的語言天賦被美國中情局招募,1974年曾作為翻譯第一次來到中國*鄒羽、徐有威:《我們這一代漢學家——魏斐德教授訪談錄》,《史林》2008年第4期。。這種在政治邊界游走的經歷,使得魏斐德與費正清一樣,關注中國政治、官僚體制、國際關系相關的議題。基辛格曾任美國國務卿,直接參與推動中美建交,而傅高義也曾在美國政府亞洲事務機構任職,他們對中國的學術研究與他們的政治經歷和現實訴求密不可分。相比之下,政治學家裴宜理則是抱著反抗美國建制的目的而關注中國。裴宜理的父母均任教于上海的圣約翰大學,20世紀30年代于上海相識并結婚,裴宜理本人也出生于上海*馮黛梅:《專訪裴宜理:海外中國研究的精彩時刻》,《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12月31日。。60年代裴宜理參與了美國學生的反越戰游行浪潮,由此而關注亞洲的革命與政治。為了更好地理解亞洲革命的意義,裴宜理前往臺灣學習中文,并走上了關注中國勞工抗爭與革命文化的道路*唐小兵:《專訪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裴宜理:安源革命的歷史記憶》,澎湃新聞網[EB/OL],2015年3月29日。。
這些漢學家的中國研究中普遍蘊含著強烈的現實關懷和變革訴求,而其本身豐富的中國體驗也幫助他們了解書本以外的真實中國。他們的主體性始終立足于本文化,嘗試通過對中國的研究獲得對自身發展的鏡鑒,但這類漢學家無論是個人情感還是學術議題的選擇,都卷入到與中國現實交往的經驗之中,這使得他們的中國研究充滿了個人經驗的浸潤,但也讓他們無法真正獲得超脫的視角來反觀中國與本國。
(二)基于外部文化的中立者
這類漢學家同樣基于自身的關懷研究中國,但他們與中國文化的真切接觸不如第一類漢學家豐富,他們對中國的研究大多是在書齋中進行的,通過對中國思想與歷史的梳理來反思自身的思想困境。法國哲學家、巴黎七大漢學系主任弗朗索瓦·于連是第二類漢學家的代表。于連畢業于巴黎高師的古希臘哲學專業,早年浸淫于西方古典學之中,對于中國文化并沒有特殊的感情。于連的研究領域轉向中國是因為其學術路徑自身的發展邏輯,于連認為哲學就是一種背叛,只有通過對此前的傳統的否定才能有更新的突破。在于連看來,迄今的所有西方哲學都是在希臘的傳統中發展的,要想與這一傳統徹底斷裂,只有求助于外部的思想傳統*[法]弗朗索瓦·于連著,張放譯:《 (經由中國)從外部反思歐洲:遠西對話》,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頁。,擁有悠久歷史的中國正是“一個在印歐文化圈之外獨立發展起來的偉大道德傳統”*[法]弗朗索瓦·于連著,宋剛譯:《道德奠基:孟子與啟蒙哲人的對話》,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頁。。因此,中國不是于連從事學術研究的目的,而只是他“反思歐洲”的工具,對中國的取徑只是一種策略上的迂回,目的是發現被歐洲理性所遮蔽的思想可能性,進而在哲學研究中獲取新的突破*杜小真:《遠去與歸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頁。。因此,于連的漢學研究背離了法國漢學重視實證的傳統,嘗試將中國作為思想而非歷史去研究*[法]弗朗索瓦·于連著,張放譯:《 (經由中國)從外部反思歐洲:遠西對話》,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頁。,倒轉黑格爾將西方歷史經驗普遍化的做法,從中國的特殊性中反思歐洲思想的普遍性*杜小真:《遠去與歸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67~70頁。。
于連的做法并非特立獨行,日本漢學家溝口雄三研究中國時的思想取徑便與之遙相呼應。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漢學界最初受津田左右吉的主導,認為中國歷史發展停滯,貶斥中國的歷史經驗。繼而同情中國革命的左翼思想家竹內好扭轉了這一趨勢,認為中國通過抵抗西方現代性的沖擊轉而重拾傳統,挑戰了不平等的霸權格局,表現出比日本更有韌性的文化轉型*孫歌:《在中國的歷史脈動中求真——溝口雄三的學術世界》,《開放時代》2010年第11期,第35~63頁。。溝口雄三則指出,津田左右吉與竹內好的思想都從自身的視角出發,只看到了中國歷史的一個側面,而中國本土的學者則基于進步主義史觀,以世界為方法,以中國為目的,因此略去了中國自身的發展邏輯。溝口雄三提出應當將邏輯倒轉過來,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通過將中國經驗特殊化,隨之也將基于歐洲的現代化經驗特殊化,在互相參照之中獲得對于現代性更為真切的認知*溝口雄三著,孫軍悅譯:《作為方法的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130~132頁。。
于連與溝口雄三等漢學家,在學術研究中力求與中國保持距離,懸置自身的情感和位置,從而將中國徹底客觀對象化*孫歌:《“漢學”的臨界點——日本漢學引發的思考》,《世界漢學》1998年第1期,第46~63頁。,從某種意義上也將中國轉變為一種認知世界的客觀工具,透過中國的視角來考察世界的多樣性。這類漢學家在研究中對中國的情感浸入最少,他們一方面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受到中國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卻又極力避免情感的介入,他們在與中國疏離的同時,也借助中國經驗實現了與本國文化的疏離,試圖獲得不受任何文化遮蔽的游離視角,成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陌生人*王銘銘:《作為“陌生人”的人類學家》,《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三)基于中國文化的中立者
這一類漢學家對于中國文化本身抱有濃厚的興趣,力圖通過學術研究來浸入中國文化的語境,因而中國文化對他們而言即充滿意義的研究對象,并不像前兩類漢學家一樣希望借助中國文化來實現外部的思想或現實訴求。另一方面,他們在研究中國時傾向于保持冷靜與疏離的姿態,避免將本人與中國的跨文化經驗投射在學術研究之中,同時也盡力克服本文化所造就的認知中國的成見。
漢學家史景遷屬于這一類漢學家的代表。史景遷1936年出生于倫敦的書香門第,根據其本人的講述,在史景遷出生時,他的母親便在閱讀與中國有關的書籍。史景遷6歲時讀到有關中國藝術史的著作,對于水墨畫產生濃厚興趣,并“通過這些畫冊,對中國產生感情”*吳從周:《史景遷:中國人的生活有許多晦暗不明之處》,《看天下》2014年7期。。然而冷戰帷幕的落下,使得史景遷無從接觸中國文化,他最初的研究對象也是英國自身的歷史。直到大學期間一次偶然的獲獎,使史景遷有機會去美國的東亞系交流,在那里史景遷遇到了前輩漢學家芮瑪麗和芮沃壽,其后又赴澳大利亞師從清史學者房兆楹,走上了中國研究的道路。1963年,史景遷前往臺灣,首次踏入華人社會。1974年,史景遷跟隨代表團訪問大陸,面對“文革”中的中國,史景遷感到自己猶如“坐在潛水艇里觀看外面的魚”,受到跨文化的沖擊。1985年在導師房兆楹的葬禮上,史景遷結識了《合肥四姐妹》的作者、華裔學者金安平,后來與之結為夫婦,由此獲得了認知中國文化的更真切的體驗。
史景遷意識到作為一名跨文化觀察者,他的主體認識必然影響對中國的客觀描述,但他希望能夠克服自身文化視野的遮蔽,認為“研究中國歷史,對我來說,就是一場習得知識繼而自我修正的持久戰”*季星:《“想象中國這份工作,是如此令人興奮”——專訪史景遷》,《南方周末》2014年3月21日。。因此,史景遷非常重視中國地方性的檔案材料,希望由此而浸入中國自身的歷史語境,從中窺測中國的古典生活*張潤芝:《美國漢學家史景遷:中國近代史課本不應該從屈辱講起》,《時代周報》2011年12月1日。。通過對一手文獻的閱讀,史景遷“瞬間獲得一種能力,可以獲得別人的視角,你將成為另一個人,通過這個人的眼睛看到世界,看到那段歷史”*吳從周:《史景遷:中國人的生活有許多晦暗不明之處》,《看天下》2014年第7期。。因此,史景遷在學術研究中傾向于以個體的視角切入來理解中國文化,不管是張岱、利瑪竇等文化名人,還是王氏、胡若望、沈福宗等被主流歷史書寫所遺忘的小人物,都是當時中國社會文化情境的縮影,試圖以小見大還原真實的中國歷史,并在文本中建構出可以代入情感的歷史氛圍,喚起讀者更多的歷史體驗*張耐冬:《充滿爭議的史景遷》,《環球人物》2013年第33期。。
與史景遷類似的還有其同輩漢學家柯文。柯文是“在中國發現歷史”的提出者,認為應當糾正費正清、列文森以來的“沖擊—回應”“傳統—現代”式研究模式,將中國歷史從國際體系中解脫出來,進而從中國自身的歷史進程中發現其內在的邏輯*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4~15頁。。為此,柯文倡導研究者應當進入中國內部,從區域史的角度發現中國歷史的微妙之處。與史景遷一樣,柯文同樣倡導文化移情式的研究方法,認為研究者需要“卸下那張緊緊地裹著史家自身的文化的、歷史的乃至個人的皮,鉆進他所研究對象的皮中去”*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2頁。。
這一類漢學家還包括孔飛力、宇文所安等,他們通常并沒有豐富的中國生活經歷,也相對游離于現實政治格局之外,是因為種種偶然因素才走上了中國研究的道路,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中通過對文本材料的解讀與中國產生共情感。宇文所安曾坦言在研究中國之初對中國并沒有濃厚的興趣*季進:《海外漢學訪談錄》,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頁。,孔飛力甚至曾因現實的阻隔而險些轉去研究日本*周武、孔飛力:《孔飛力談中華帝國晚期的國家與社會》,《東方早報》2016年2月28日。,對他們來說,并非先接觸中國而后了解中國文化,而是以中國文化為媒介進而認知中國。這一類漢學家的著作大多不以政策研究為旨趣,而是尊重中國內在的發展邏輯。另一方面,這類漢學家在研究中國時傾向于保持冷靜、超然的立場,中國是一個等待發現與對話的客體,與中國文化有關的體驗有助于他們更好地理解中國,但這種體驗本身并不會成為主導其學術研究的要素。他們在認識論層面試圖進入中國文化,但是其主體論的位置仍然是基于本國文化的,學術研究與生活體驗呈現出相對的分離。
(四)基于中國文化的介入者
這一類漢學家同樣傾向于發掘中國文化中原本蘊含的價值,但不同于第三類漢學家,他們的學術研究與中國文化緊密聯系在一起,與中國的跨文化體驗滲透進了他們的研究之中,同時他們也利用自己的文化實踐將中國文化傳播到西方世界,促使中國文化在國際范圍內得到認可。這類漢學家的代表是顧彬與葛浩文。
顧彬是德國漢學家,也是德國學術界唯一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顧彬:《中國當代作家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搜狐文化[EB/OL],2015年9月14日。。1967年,22歲的顧彬讀到經過翻譯的李白詩歌,非常著迷;1974年顧彬第一次來到中國,其后開始學習漢語,走上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和當代文學的道路。顧彬對中國文學有著深厚的感情,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序言中自稱“四十年來,我把自己全部的愛奉獻給了中國文學”*顧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在顧彬的文學史研究中,中國文學自身的價值是其關注的焦點,他試圖將中國文學放置在世界文學的坐標系下進行觀照,在中西文化比較中發現中國文學的特征與優劣*顧彬:《中國當代作家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搜狐文化[EB/OL],2015年9月14日。。這就使得顧彬的研究路徑迥異于于連、溝口雄三等以中國作為方法的漢學研究。
顧彬對中國的研究并未止步于書齋,而是與中國的文化人士保持密切的往來,與北島、顧城等中國當代詩人和翟永明等小說家有著長期的接觸。這種“在場”的身份,也使得顧彬的觀點、言論備受中國文化界關注。2006年顧彬曾在接受訪談時批評幾位當代中國作家的作品,被中國媒體報道后引起廣泛反響。而這種與中國文學界的密切往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顧彬對于文學史的書寫和評判,他曾自稱“學會了中國人的圓滑,不好意思批評老朋友”*《娶中國老婆,漢學家顧彬出書談中國文學》,新華網[EB/OL],2008年9月17日。。學術研究之外,顧彬在中國海洋大學、汕頭大學等中國高校擔任講座教授,同時也曾將十余部中國當代文學引介到英語和德語世界,以實際行動參與中西方文化交流,更因為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所做的貢獻而獲得2016年度中國政府友誼獎*李偉烽:《汕大講座教授顧彬獲中國政府友誼獎》,《汕頭特區晚報》2016年10月16日。。
以翻譯中國現代小說而知名的美國漢學家葛浩文,則是越戰期間因偶然機緣去臺灣服役,由此而學習中文,接觸中國文化,后來又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后前去北京與哈爾濱考察,對中國文化產生了真切的體驗*河西:《葛浩文和他的漢譯之旅》,《新民周刊》2008年4月9日。。葛浩文一生翻譯中國文學作品數十部,許多中國當代作家都是借由葛浩文的翻譯才進入西方文學批評界的視野,顧彬更認為莫言獲得諾貝爾獎直接得力于葛浩文的精彩翻譯*馬伯楊:《翻譯家葛浩文:20世紀中國文學的情人》,經濟觀察網[EB/OL],2015年3月2日。。在翻譯之余,葛浩文同樣進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著力于中國文學的史料考辯和語境復原。與顧彬一樣,葛浩文也直接介入到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進程之中,其文學翻譯、學術研究與其本人的中國文化經驗交織在一起。
第四類漢學家中還包括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瑞典漢學家馬悅然等,茲不一一列舉。這類漢學家深度介入中國文化之中,其文化實踐對于研究對象有著直接的影響,而與研究對象的情感關聯,也影響著他們研究與實踐的議題選擇。另一方面,這類漢學家對中國的研究主要出于對中國文化本身的熱愛,外在的訴求處于次要位置,從而區別于第一類漢學家,反而與中國本土的研究者較為接近。但是這類漢學家豐富的語言和文化經驗,又使得他們可以將中國文化放置在世界的坐標系中參照,填補了本土研究者視角的空缺。
四、結論與討論
對于邊緣人歸化的機制,現有研究大多考察移民等實際生活于兩種文化邊界的群體,本文則將文化邊緣人的范疇拓展到具有各自文化接觸經驗的漢學家群體,考察了漢學家接受中國化(sinicization)的不同路徑和特征。總體來看,與通常考察的邊緣人群體相比,漢學家具有三點特征。首先,漢學家未必都具有來華交流的經歷,更談不上長期脫離母國在中國定居,而是因為職業或興趣的緣故,通過中國的文物典籍或者對當下中國的觀察,與中國文化發生碰撞和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抽離于本國文化,在文化的意義上成為身處兩種文化之間的邊緣人。其次,漢學家進入中國文化,往往是自身主動的選擇,而不像難民等群體被迫變成文化邊緣人,因此漢學家能夠更加主動地調適自己在兩種文化中的身份認同。再次,相比于一般群體,漢學家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和反思意識,以研究異文化的歷史與社會問題為己任,這使得漢學家能夠最大限度地克服文化偏見,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位置與視點。對于中國文化中不同于西方的體系,漢學家的態度往往是懸置先在的理性,對其文化的細部作精細探究*張西平:《他鄉有夫子》,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頁。。因此,漢學家可以積極地利用身處的文化邊緣情境,從異文化的視角發現中國學者和民眾“只緣身在此山中”而未曾意識到的問題,身居外圍建構文化中國。
另一方面,通過研究發現,漢學家并非同質化的群體,內部有著多元的類型,因而在認知與解讀中國文化時也呈現出差異。本文通過考察漢學家的跨文化經驗,提出以主體位置與情感介入作為區分漢學家接受中國化的程度與類型的標準,提煉出基于外部文化的介入者、基于外部文化的中立者、基于中國文化的介入者、基于中國文化的中立者四種類型。值得注意的是,主體位置與情感介入這兩個維度并非截然對立的兩個極點,在強與弱、高與低之間是一道連貫的光譜,由此而劃分成的四種類型象限也不是彼此絕緣的。事實上,很多漢學家的跨文化經歷都處于不同類型之間的模糊地帶,本文提出的劃分標準僅僅是一種理想形式的提煉,旨在清晰地勾勒出漢學家認知與解讀中國的不同取徑,也顯現出文化中國外部圈層構建的豐富可能性。
傳統上多以學術立場、學科歸屬、年代或者國籍為標準對漢學家進行區分,本文則是以跨文化研究的路徑切入,但仔細審視可以發現,本文所提煉的漢學家認知中國的四種類型,與漢學家的學科歸屬有著微妙的聯系。在情感上傾向于介入的漢學家,往往關注現當代中國的文化與政治,而相對情感中立的漢學家,則更多將目光投注于古代或近代的中國文化。在主體位置上選擇基于外部文化的漢學家,更愿意研究中國的思想、哲學、文化等相對抽象的議題;而在主體位置上選擇基于中國文化的漢學家,則傾向于關注中國的微觀歷史和文學作品等更為特殊、更富于中國文化特質的議題。在漢學家的跨文化認知機制與學術研究路徑之間,呈現出相互建構的復雜關系,本文僅僅從跨文化研究的角度提供了一種思考的可能性,在這一問題上還可以展開更為細致和專業性的考察。
Sinologist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Cultural China”: From an 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
ShanBo(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Wuhan University,Wuhan,China)
ZhangYang(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Wuhan University,Wuhan,China)
This article extends the meaning of“marginal man” from an 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 proposes “cultural marginal man” to summarize the intercultural attributes of sinologists, and studies how sinologists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hina”. This article takes subject positions and emotional involvement between sinologists and Chinese culture as two basic dimensions. Through analysis of life experience and academic researches of more than ten contemporary famous sinologists, we sum up four types of cultural marginal man, namely intervenor based on external culture, neutral based on external culture, neutral based on Chinese culture, intervenor based on Chinese culture. These four types reveal the multi-mechanism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inologists and Chinese culture, and provide new possibilit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hina”.
Sinologist;Cultural Marginal Man;Cultural China;Sinicization
10.19468/j.cnki.2096-1987.2016.03.005
單波,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長江學者,主要研究比較新聞學、跨文化傳播。 張洋,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13級研究生,主要研究跨文化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