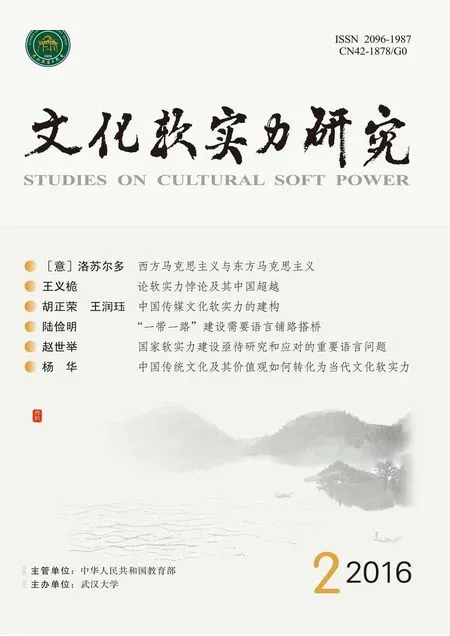一個“海歸”保守主義者的文化觀
——辜鴻銘對晚清中西沖突和政局變化的看法
羅福惠
?
一個“海歸”保守主義者的文化觀
——辜鴻銘對晚清中西沖突和政局變化的看法
羅福惠
辜鴻銘的保守主義思想,來源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流行于歐洲的浪漫主義,再加上他忠于清王朝、忠于“中國政教、文明目標”而形成自己的政治觀、歷史觀和文化觀。他以內在的道德精神和外顯的秩序與安寧作為評論晚清歷史事件的基準,其分析結論“大疵而小醇”。在對待中西沖突的看法上,則堅持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主要引用前述浪漫主義和若干國際法學理,從道德和文化的角度對西方列強加以譴責,成為中國最早“以西學反西方”的嘗試。他還對清末中國的發展之路提出了自己的設想,其保守思想實開“東方文化派”與“當代新儒家”之先河。
辜鴻銘中西沖突政局變化看法
辜鴻銘在國外生活學習20余年,對歐美歷史文化相當了解。1884年進入張之洞幕府后,又刻苦鉆研中國儒家經典,因而為學兼通中西。清末他追隨張之洞近20年,長期生活在武昌、上海、北京三地,除充當張之洞的幕僚之外,還充任過湖北方言學堂監督,擔任過上海疏浚黃浦江工程局中方總辦、清廷外務部的郎中和左丞,直到1910年秋才脫離政界。辜氏除關心中西文化、中外關系問題之外,對政治尤其是晚清和民國初年的政局和人物有許多思考和議論,反映出他對近代社會變遷的獨特感受。包括他在中外關系方面譴責外來侵略、拒斥西方文化的主張在內,盡管其觀點是“大疵而小醇”,但仍然值得研究者加以梳理。辜氏此類文章和專著,都用外文書寫,發表在歐美和上海的外文報刊上。黃興濤教授將其譯為中文(上下兩冊),但估計讀者不是很多,因而少見引用。
一
雖然辜鴻銘在歐洲學習11年,通曉多種語言文字,得到文、哲、理、工、神學等多個博士學位,但對其思想產生決定性影響的,卻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一度在歐洲流行的浪漫主義。辜氏在其文章中引用最多的卡萊爾(辜氏是卡萊爾的嫡傳弟子,卡萊爾著有著名的《法國革命史》)、阿諾德、羅斯金、愛默生、海涅和歌德的文句和詩歌就是證明。這股浪漫主義思潮從多種角度批判和否定發展中的資本主義文明,反對資本主義對個性的壓迫,抨擊物質主義、功利主義和自私自利,視其為庸俗、卑鄙、無聊的資產階級的平凡興趣,還揭露批評社會的貧富懸殊、拜金主義、人性異化及民主政治的虛偽;與此相對,他們大多強調情感、精神或心靈、道德和正義。他們以一種精神貴族的態度,同情人民大眾但不相信大眾的知識和智力,只崇拜賢者和英雄。而且這批人多數贊賞中國文明,甚至稱“人類的一線光明,是中國的民主思想”,尤其稱贊孔子是“哲學上的華盛頓”,“孔子的人格可以作為人類努力方向上的榜樣”。辜氏受到這些觀點的影響,回國鉆研了“儒家傳統文化之后,兩相印證,共同啟發”*黃興濤著 :《文化怪杰辜鴻銘》,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20~27頁。,從而形成了他保守主義的歷史變遷觀和政治文化觀。一位以“真正的中國騎士”自居,極度頂禮膜拜中國傳統文化、反對學習西方文化的保守主義者,其最先的理論武器卻又來自西方,這不能不是一個吊詭與反諷。
辜鴻銘在分析晚清歷史進程時相當注意列強對中國的干涉和侵略這一要素,他依據“一國主權不可侵犯”的國際法學理和維護祖國尊嚴、珍視民族文化的立場,對列強的種種行徑多有批評抗議,這是應該肯定的。可惜的是他作為一個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又常常把維護國家主權與維護清王朝政權、維護民族文化與刻意為一些思想糟粕和陳規舊習辯護混為一談。
辜鴻銘指出,晚清中國的混亂在很大程度上“是列強對中國內部事務的干預”所造成的*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頁。,委婉地說是歐洲人“不能像兄弟一樣看待和對待”中國人,不能 “在上帝及其道德法則面前人人平等”*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頁。,嚴重地說則是“現代歐洲實利主義文明可能即將占領中國并毀滅中國文明”。*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頁。在19世紀90年代長江流域普遍發生教案期間,辜氏就批評西方傳教士依仗本國政府“炮艦政策”的支持而“無惡不作”,對“中國人蠻橫、放肆,到處插手和施展小小的暴虐”,因此所謂“教案”的“騷亂正是日積月累的侮辱和傷害所激起的憤慨的暴發”。*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頁。到了義和團事件和八國聯軍入侵時期,辜氏遂更激烈地為祖國和人民伸張正義。他說 :當中國人“感到有人要滅絕他們,不讓他們活下去的時候,就會做出可怕的事情來與之對抗,而且,中國人也有一種民族感情,這種感情一旦遭到蹂躪和傷害,他們將對此產生怨憤”。*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頁。他形容列強對中國的所作所為“是富人搶窮人,強者搶弱者,但都明顯違反了上帝正義的法律。正因此,中國人紛紛起來參加義和團”*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并稱義和團事件“是一場人民的戰爭”。*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頁。
他譴責列強出兵中國,“外國使臣首先也無恥地侵犯了一個同樣重要的國際法——中國國土的神圣不可侵犯權。他們竟然把兵派到中華帝國的首都來”。*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60~61頁。然后,“在北京和天津,外國平民、傳教士甚至還有官員,公然無恥地搶劫財物”。*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頁。所以他說八國聯軍行為“是一場反對中國人民的戰爭”。*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頁。在中國政府飽受羞辱、中國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生命財產犧牲之后,列強才同意議和,辜氏尖銳地指出這種議和是“虛假”的。他引用牛津大學外交學權威蒙塔古·伯納德的話說 :“一個和平的條約,必須包括由雙方裁決、以期消除戰爭爆發根源的必要條款,調節不平,平息怨氣,防止它的再度復活。……如果這一點沒有明確有效地做好,那么和議就是虛假的”。但是,“眼下北京的外國使臣們非但不努力去消除中國目前事態的根源,甚至連根源何在也全不了解。他們試圖消除的是吳淞(應為大沽——作者)炮臺”。*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頁。還有在北京附近要害之地允許列強駐兵,尤其是還要中國承擔巨額賠款等等,這一切被辜氏比喻為 :“所有流氓無賴,搬弄是非之人和愛管閑事之徒不受限制地任意出入、胡作非為。結果我的家失火了,沒有人給我賠償,相反我卻必須向事端的制造者道歉并賠償損失!”*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78頁。他認為這一切使得西方的“文明”、“公理”、“平等”等“人道說詞”不攻自破。
辜鴻銘對列強罪行的批評,沒有停留于事實層面,而是將其上升為宗教、文化精神和政治學的分析。他認為中世紀歐洲的基督教精神以人性為惡,故把對人心的規范建立在“以希冀和敬畏(上帝)之情的道德文化基礎之上”,宗教改革之后,希冀和敬畏之情逐漸消解,一方面是自由主義思想發展,另一方面是“無政府主義”流行,使得“保持國民秩序的約束力量……在根本上不是通過道德力,而是靠警察或稱為軍國主義的純外在力量”。*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77頁。18世紀以法國大革命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曾經推動了歐洲的改革和發展,但進入19世紀后,“上世紀歐洲的那種自由主義確已衰退”,并且對外部世界采取“帝國主義”和“吃人的殖民政策”。辜氏具體稱之為“耶穌會教義和馬基雅維利主義”*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頁。,意思是傳教士和西方政府一面向東方民族宣傳他們自己都不信以為真的宗教或民主、自由等信仰,一面為了達到自私的目的而不擇手段。如同前述辜氏運用歐洲的浪漫主義,引用伯納德關于和平條約的定義一樣,辜氏是最先分析和評論從中世紀到20世紀歐洲宗教思想和文化精神發展變化過程的中國人,他運用“軍國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資產階級”等概念,也略早于孫中山、梁啟超和20世紀初年出現的留學生報刊。只是由于他的此類文章系用外文撰寫,故不大為中國人所知罷了。這種情形不僅使辜氏批評列強的作品具備了一種思想深度和理論高度,而且套用近幾年人們已經習用的“以傳統反傳統”一語而略加改變,可以說辜鴻銘是中國“以(部分)西方之學反西方”的先驅之一。
二
保守主義者的一個共同特點,是他們必然把歷史上或現實中的某種文化思想、制度設施或文明成就高度理想化,然后對此加以“保守”,并以這種建構的理想之物為標準,來衡量和批判歷史上或現實中的社會變遷與人物事跡。辜鴻銘所要“保守”的,一是孔子開創的“良民宗教”。他把孔子建立的社會秩序構想以及發自人本性的注重道義和心靈生活的人格規劃視為人類最高的智慧,認為這種“建立在一個依賴于人的平靜的理性基礎之上的道德文化”,“是個極其博大的文明。這一文明人類更難達到,而一旦實現,就將永恒持久,不衰不滅”。*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77頁。他極力贊揚中國文明的“深沉”、“博大”、“純樸”和典型中國人的“溫良”(或譯為溫文儒雅)。*辜鴻銘著、黃興濤等譯 :《中國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5、30頁。盡管他承認“宋代理學家們把禮教弄窄了,使其變得狹隘和僵化了……孔教精神,中國文明的精神被庸俗化了”*辜鴻銘著、黃興濤等譯 :《中國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頁。,但他始終沒有明示“狹隘”、“僵化”、“庸俗”的具體表現。二是中國的君主制度。辜氏認為,在歐洲是教會負責人民的道德,國家則主要負責秩序;而在中國是國家監管二者,“國家得以促進人民道德的權威本源,是皇帝”,因而“在中國對皇帝的忠誠是一種宗教,可以說它是儒家國教的基石”。辜氏聲稱不怕外國人笑話自己“對滿人朝廷愚忠”,并表明這種忠誠不僅是對“王朝的忠誠”,也是“對中國政教的忠誠,對中國文明目標的忠誠”。*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88~291頁。尤其是喋喋不休地贊美慈禧太后,稱其為賢明、仁慈的“國母”、“偉大的女性”等等。*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2、325、329、392~394頁。他還贊揚那位為把自己的兒子送上皇位而不惜以國運相賭、欺騙利用義和團的端王載漪,把別有用心的慈禧太后、端王和出于義憤、采取簡單落后的排外方式的義和團等同起來,稱“皇太后、端王和他的義和團小伙子,正奮起反對歐洲和全世界的真正文明的敵人”。*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85頁。把當時西方國家批評慈禧,要求她“歸政光緒”的輿論和談判中要求懲處端王等“禍首”都視為“干涉內政”,由此可見辜氏不能把維護國家主權與維護專制王權加以區別的嚴重思想局限。在這一點上,病逝于1928年的辜鴻銘與早一年在頤和園自沉的王國維,實有相近之處。
另外,辜氏還為中國傳統的司法審判中濫用刑罰,如1903年7月在北京刑部大堂亂棍打死維新人士沈藎的野蠻行為辯護,否認“中國對政治犯和煽動犯判刑過嚴”,強辯“用棍子打死的嚴峻和殘酷程度比砍頭處死要輕”。他甚至說 :“如果人們認為中國的法律殘酷而野蠻,那也不應該歸咎于中國現政府,而應歸咎于中國人民和他們的文化”*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191頁。,看來辜氏還是愛清王朝勝過愛中國文化,否則怎么會拿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去當替罪羊?而且辜氏既然認為中國文化“純樸”,中國人“溫良”,那么殘酷而野蠻的法律就很難歸咎于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此外諸如辜氏“所謂‘三從’實際上指的是三種無私的犧牲或‘為他人而活’”的“女德論”,因為丈夫“極其愛他們的妻子,才有納妾的權利和自由”的納妾合理論*辜鴻銘著、黃興濤等譯 :《中國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82、86頁。,則是為文化和習俗的糟粕強為辯護的表現。
辜鴻銘沒有滿漢種族之見,他認為在清王朝的前、中期,“中國在滿人統治下變成了一個美麗的國家”。*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頁。這個國家的社會由三種力量構成,上層是滿洲貴族,他們以“英雄氣概或高貴品德”來“指導”國家和民眾;中層是“文人學士”等“受教育者”,他們以“知識能力”來“訓練和管理民眾”;下層是“中下層市民和勞工階層”,他們以“勤勞的力量”“生產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保證國家物質充足”,當時舉國過著“高貴的生活、享有高尚的文明”。*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300頁。
但是承平日久之后,滿洲貴族的“高尚品格或英雄氣概……不免衰退、萎縮”*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頁。,“他們逐漸地不把具有古老文明的大帝國視作人民托付給他們照管的神圣之物了,而只把它看作祖宗的遺產或既得利益,認為有特權享用,而沒有任何責任,因此一味地花天酒地”,從而“無法給予國民所期望的高貴引導”。*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58~359頁。而文人學士的“智力也大大衰退”,“喪失了優雅,而變得卑劣和粗俗不堪”,使得“中國勞工階層的勤勞力量,被卑劣的目的所浪費”。*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301頁。于是還在西方人來到中國之前,“城市里紙醉金迷的安逸、豪華生活已明顯地表現出國家業已存在浪費性消費的癌癥”,這樣“不僅白白浪費了人民勤勞的生產力,而且使人民的勞動果實難以得到公平的分配”,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那么留給貧苦大眾的“唯一生路,就只有發瘋發狂,起而猛烈地蕩滌那民族的癌癥了……(這)便是著名的太平天國暴亂”。*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304頁。
顯然,辜鴻銘僅從道德教化的角度解釋“康乾盛世”的形成和清王朝由盛轉衰的本質原因,未必能說明歷史的全部真相,但他從貧富不均、分配不公的社會現象入手理解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卻大體不誤。而且辜氏出于社會正義的原則,承認“上帝的正義,總是我國革命和上海騷亂這類事變的最終根由”,并且稱贊太平軍將士表現出了“陷入瘋狂之中的高貴人性,對于社會弊病的強烈義憤感”和“勇武的高貴品質”,甚至說“太平天國叛亂相當于歐洲的法國革命”。*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04~305、307頁。當然,太平天國“暴亂”破壞秩序與安寧,尤其是其信奉西方式的“拜上帝教”和毀滅儒家經典,使得辜氏更贊賞撲滅太平軍、重建社會和行政管理的曾國藩。但他仍然強調了因這場革命而產生的客觀效果,一是“國家的統治權從貴族轉到中產階級手里”;二是“一場革命之后,人們往往能夠以一種比較自由和獨立的方式來看待事物,這種方式就是所謂自由主義。一個民族的才智,一旦擺脫常規和舊習的束縛,就立即變得積極活躍,生機勃勃”。*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07頁。辜氏對“同光中興”時期統治權力的轉移和思想背景的理解,表明這個保守主義者仍然贊同一定限度的變革——但不能動搖孔子之道和皇權這兩個基礎柱石。
但是辜氏認為曾國藩在“對付現代歐洲文明的破壞勢力問題上……則完全失敗了”,他只是“派學生出國學習制造槍炮,掌握駕駛戰艦技術”,而沒有注意“歐式教育”。*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頁。從表面上看,辜氏似乎是批評洋務運動只學習西方物質層面的船堅炮利而沒有“擴展”到文化教育制度等方面,似乎要更全面地學習西方,其實其思想實質正好相反,他是鄙薄物質和技術層面的學習,他的“擴展”雖然包括了解更廣泛的西方文明,但目的只是“知彼”而能更好地“抵制”它們,絕不是要仿效和師法西方的制度和思想文明。正因為如此,當李鴻章在形式上比曾國藩更多地借鑒仿效西方事物時,辜鴻銘就斥之為“粗俗和丑陋”,不滿李氏“將那些富人、中小商人和買辦階層,那些在對外貿易中掙錢獲利之徒吸引到自己周圍”,形成一個把持權力的“狹隘、卑鄙和無恥”的“自由主義”集團。*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311頁。他尤其反感“李鴻章之流的人,他們與歐洲人親昵并向其百般諂媚”。*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頁。也正因為如此,辜氏贊賞李鴻藻、張之洞等反對李鴻章的“清流派”活動,并將其視為中國的“牛津運動”,即肯定他們反對所謂“自由主義”,反對西方物質實利主義,更嚴格地按照儒家原則行事的傾向。后來辜氏還一直為這一“運動”的失敗,尤其是為張之洞轉向調和折中、投入洋務新政而惋惜。
辜鴻銘視19世紀末的維新主義如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雅各賓主義”,稱康、梁為“渴望太平盛世立即實現的雅各賓黨人”*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71頁。,中國雅各賓主義在辜氏筆下具有貶義,它不僅“兇猛暴烈”,而且“要使中國全部歐化”,而“中國的全部歐化意味著輸入粗鄙和丑陋”。*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17頁。辜氏還認為,甲午戰爭之后,以李鴻章為代表的“中等階級自由主義及其寡頭政治集團”失勢,“文人學士階層中”的“群氓”登上政治舞臺。“群氓”是辜氏政論中常用的一個名詞,意思是指“半受教育”、“粗俗不堪”而且“無法克服和抑制自身的欲望”因而“過激”的政治活動人物。*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70~371頁。群氓煽動和利用民眾,但群氓不包括民眾。辜氏視康有為、孫中山、袁世凱為群氓的幾個代表,從道德上批評康有為“人品卑劣,計劃虛夸不實”*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19頁。,“只想通過一個單一的改革行動,僅憑皇帝的一張‘上諭’來歐化中國”*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頁。,因而必然失敗。
對于20世紀初年的“新政”改革,辜鴻銘也不以為然,稱之為“走上了歐化的道路”。他尤其反感隨后的“立憲運動”。在他看來,中國的確從來沒有過“代議政府”,但中國政府又是一個得到人民擁護、反映人民意愿的地地道道的“立憲政府”,“中國的憲法是一種‘道德上的’憲法,而不是‘法律上的’憲法”,這就已經足夠了。鑒于西方的“代議士”(議員)起碼是“中產階級人士或舞文弄墨、欺世盜名之人”,故他聲稱希望中國的商人和“文人學士……永遠也得不到(它)”*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26頁。。辜氏還曾以諷刺的語氣總結說 :“中國自咸同以來,經粵匪擾亂,內虛外感,紛至迭乘,如一叢病之軀,幾難著手。當時得一時髦郎中湘鄉曾姓者,擬方名曰‘洋務’清火湯,服若干劑未效。至甲午,癥大變,有儒醫南皮張姓者,另擬方曰‘新政’補元湯,性躁烈,服之恐中變,因就原方略刪減,名曰‘憲政’和平調胃湯,自服此劑后,非特未見轉機,而病乃益加劇焉。勢至今日,恐殆非別擬良方不可”。*辜鴻銘著、黃興濤等譯 :《中國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127頁。可見辜氏對“洋務”、“新政”、“憲政”均不以為然,而寄希望于“別擬良方”。但是未等“憲政”藥湯喝完,辛亥革命就爆發了。
三
辜鴻銘陸續寫于辛亥革命爆發和袁世凱獲得政權這段時間的文章表明,他對于辛亥革命的分析評價比太平天國還低。他說“太平天國叛亂像法國革命一樣,是一場社會革命,它意味著機體器官本身出了毛病(指養尊處優的滿洲貴族集團只管享樂而不負責任——作者),而目前這場暴亂則是一場政治革命,它只意味著器官功能的失調而已”。辜氏此處所說的“政治革命”并非革命黨人所說的要改革政治制度,變君主專制為民主共和的意思,而是貶之為政治權力之爭,如同19世紀80年代日本西鄉隆盛領導的反對大久保利通寡頭政治集團的薩摩藩叛亂(日本史上稱之為“西南戰爭”)。辜氏強辯地自問自答說,這場革命是“反滿”嗎?“滿人作為一個階級,甚至比我們漢人還要窮”;是反官僚階級嗎?當時的“官僚階級也比上海的買辦階級要窮”。他甚至說,“現在中國一切罪惡的根源不在于官員的貪污腐化,而在于他們的無能”,這種無能尤其表現為聽任“盛宣懷寡頭政治集團接管國家事務”。他說,革命者認為滿人的朝廷阻礙了本民族充分和自由的發展,但他認為“滿人并不是造成這一障礙的原因,盛宣懷及其同伙的寡頭政治集團才是導致這一障礙的真正原因。因此,我認反朝廷只是這場革命的表象”。*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478~479、481頁。
出于這一錯誤的判斷,辜鴻銘一度很樂觀,他告訴外國朋友“對目前的局勢完全不必持悲觀態度。盡管形式嚴峻,但卻并沒有絕望,甚至于還大有希望。……它是新中國誕生之時的最后陣痛”。他斷定“武昌革命作為一場革命來說也將要失敗,但是它將會、至少我真誠地希望它將摧毀盛宣懷寡頭政治集團”*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477、479頁。,從而把清政府的“器官功能失調”恢復正常。辜氏的“新中國”僅此而已。而且他出于清王朝一定能獲勝的預計,反對“外國列強對于中國不明智地加以干涉”,因為“外國對于保皇者的任何幫助,除了會大大降低現政府的威望以外,還會……因此激生一種比上次義和團事變還要大還要嚴重的排外暴動”。*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480頁。
但是事態的發展大出辜鴻銘意料,短短幾個月之后,革命黨失敗了,盛宣懷倒臺了,可是清王朝也垮臺了,袁世凱掌了權。辜氏對于這后兩點難以接受,他反復表示,“災難現在來臨了”,并說真正的災難“還不是伴隨著流血和破壞財產的革命,真正的災難是革命以袁世凱成為共和國總統而告終”。因為袁世凱“是群氓的化身”,“他的統治將不會長久”,但這個毫無道德的“卑鄙無恥之徒”居然掌權,就“不僅毀棄了中華民族的廉恥和責任感,而且毀棄了中華民族的政教和文明”。*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290頁。辜氏切齒痛恨袁世凱,最根本的原因是認為袁沒有忠于清王朝,反而大耍兩面手法,投機逞私,從清王朝和革命黨手中盜得了政權。所以他的“中國革命以袁世凱當上民國總統而告終是一場巨大的災難”的結論雖然正確,批判袁世凱的人品也沒有什么不對,但他的出發點卻是錯誤的 :辜氏要維護君主制度,認為“共和國在中國的直接后果,甚至于比法國的(雅各賓主義)‘恐怖統治’還要可怕”。*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92~293頁。
總結過去和分析現在,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規劃將來。辜鴻銘也不例外,故他的有關評論中也有不少怎樣解決“中國問題”的設想和主張,而且因為他始終認為晚清歷史進程就是“自從歐洲人進入中國之后,我們中國人怎樣努力與那現代歐洲強烈的物質功利主義文明的破壞力戰斗……然后我們又如何遭到失敗”的過程*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86頁。,所以他的設想和主張不僅涉及對外和對內兩個方面,而且兩者難解難分。
對外,辜鴻銘要求列強“讓中國人獨立”,不要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因為“除非一個國家的政府有絕對的權力去做它認為正當的事情,否則在那個國家,良治便無從談起”。*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9、211頁。還有,最好是能廢除領事裁判權(當時通稱治外法權),現時即使不能廢除,也不應該“企圖將其范圍擴大”。還應“廢除那愚蠢的獨立租界”,不能把中國的每個通商口岸都“變成小國林立的巴爾干半島”*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頁。等。當然從根本的文化意義上來說,列強應該認識到,他們是在同一個具有高度文明的國家和民族打交道,應該尊重這種文明,把中國人“視為同一類中親如一家的兄弟”。*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頁。辜鴻銘還說過 :“未來的中國到底將獨立還是受外人管轄支配,將取決于它是否從此擁有一支強大有效的軍隊。而是否能擁有強大有效的軍隊,又取決于是否讓中國那有教養的統治階級……不做文士,而是去做一種當兵服役,能保衛他的祖國免于侵略的武士”。*辜鴻銘著、黃興濤等譯 :《中國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頁。可見辜鴻銘關于怎樣使中國獲得并保持獨立的設想,也不全是迂闊之談。
對內,在辛亥革命爆發之前,辜鴻銘始終認為急務是要“消除”中國人“面對現代歐洲各國那種物質實利主義文明的破壞力量,中國文明的應戰能力不足,無效無用”的認識“錯誤”。他總結了晚清以來中國應對西方挑戰的幾種方法和態度,認為“端王及其義和團員”式的方法、張之洞“調和”式的方法、佛教徒或托爾斯泰式的“消極抵制”方法,都不能奏效。而唯一切實可行的方法“就是孔子制止某種社會或政治罪惡及其改革世界的方法,即通過一種自尊和正直的生活,贏得一種道德力量”。*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87~389頁。具體地說,是依靠孔子的“良民宗教”,保證“和平、秩序與安寧乃至國家本身的存在”,人人都過一種“道德生活”,“盡義務而不是爭權利”,并且服從“權威”。*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546頁。以為如此一來,就會如孔子所說的“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如孟子所說的“愛其親,畏其上,世永昌”。總之,在辜氏這個道德至上論者或道德決定論者看來,盡管來自西方“物質力”的沖擊或誘惑強大無比,但只要中國人始終以“道德力”作為心靈的支撐,就能“重建和平與秩序,而且還能支持世界上真正的文明事業,支持真正的進步和真正的自由”。*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547頁。
當然辜鴻銘也說過,中國需要改革。首先是知識、智能和思想的“擴展”,“如果缺乏智能方面的修養,你就無法有思想,無法了解思想。進一步說,若沒有深厚的智能修養,你就不能有正確的思想;而沒有正確的思想,便無法對現實作出說明”。*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頁。正是從這種意義出發,辜鴻銘認為開辦同文館比開辦船廠、機器廠、兵工廠更有價值,而且為同文館僅學西方語言文字及天文歷算,而沒有深入了解西方的宗教和文化精神而對主持人大加批評。辜鴻銘在辛亥革命前還說過,“如果中國一定要鬧一場革命——目前的歐化實際上就真正等同于一場革命,它必須是‘一場合乎法律程序的革命’”。*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85~386頁。
那么這種所謂的“改革”甚至“革命”應該由誰來領導,或者說中國人應當服從現實中哪種群體或個人的“權威”呢?辜鴻銘自然不會考慮他所指責的“群氓”、“雅各賓主義者”,如康有為、孫中山、袁世凱等,相反一直對他們持批判態度。對于“中國的民眾”,辜氏稱贊他們為“辛勤的工作階級”,“他們的道德至今也沒有受到太大損害”,但“卻是一種粗陋、殘暴的力量”,是“一旦真正的民主被用于維護它的‘否決權’,正如在太平天國叛亂和義和團暴亂中一樣——那種否決權只能成為一種可怕的破壞力量”。對于“文人學士”,辜氏則認為他們“庸俗”、“丑惡”,“已經是徹底喪失了道德,除了虛榮和狂妄之外”,只剩下“自大和不切實際的迂腐”。*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64~365頁。而包括商人、買辦階級在內的“中產階級”,辜氏視他們為“渴望歐洲文明的物質享受,因而叫囂要歐化中國”,只有“粗俗”的“庸人智慧”而缺乏“高貴天性”。*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25頁。于是他寄希望的只剩下滿洲貴族群體。
辜鴻銘承認,滿洲貴族在承平日久之后,只把中國“看作祖宗的遺產或既得利益,認為有特權享用,而沒有任何責任”。*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58頁。而且“中國的滿洲貴族,跟所有的貴族一樣厭惡知識修養,是些最不懂思想的人。*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64頁。他預計,“除非從外部來人,或從他們內部出現強有力的成員,著手改造滿洲貴族,給其體內注入新的生命力……(他們的特權地位)將不得不被廢除”。*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60頁。但辜鴻銘仍然認為滿洲貴族的“英雄主義”和“高貴的道德品質”是“群氓”、“文人學士”和中產階級無法企及的,所以可以“憑借它產生出一種新的更好的事物秩序”。在“舉國無人”之際,他寧可勉強地選出滿洲貴族鐵良或攝政王載灃來擔當大任,或者幻想“滿洲貴族將可能從一個留過學的中國人中找到他們的領袖”,而這個人應該“是一個對古老的中國文明中的道德價值和美的觀念有真正的認識,又具備說明現代歐洲文明中‘擴展’和進步思想能力的人”。*黃興濤等譯 :《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366頁。由此可以明顯看出辜鴻銘對清王朝的愚忠,以及對他自己“一個留過學的中國人”的自戀情結。
歷史發展未如辜氏所期,“群氓”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鐵良鉆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羽翼之下,載灃玩世不恭地表示“正好回家抱孩子”,被辜鴻銘罵得一無是處的袁世凱卻當了大總統。于是此后他反對袁世凱的帝制自為,卻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地作為“辮吏”參加了“辮帥”張勛擁戴廢帝溥儀的短命復辟行動。
辜鴻銘是政治和文化的雙重保守主義者,加上他自命名士風流,性格桀驁,行為古怪,因“忤時”而遭冷落譏笑正是他的宿命。不過正如有“千慮一失”,也有“千慮一得”一樣,從以上的文本敘述中可以發現,辜氏對清代史尤其是晚清史的分析評判,無論是宏觀層面的把握,還是微觀的、個案的分析,仍有若干值得后人思考之處,而在批判西方現代文明,主張保守中國文化等核心觀念上,似乎已開“東方文化派”和“當代新儒家”之先河。
Cultural View of a Conservative “Overseas Returnee”—ViewofChineseandWesternConflictandPoliticalChangeinLateQingDynastyfromGuHongming
LuoFuhui
(Institute o f Modern Chinese History,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China)
Gu Hongming’s conservative ideology originated from Romanticism that prevailed in Europe during the late 18th century and the early 19th century. In addition,he was loyal to the Qing Dynasty,true to “Chinese Political Programme”,”Civilized Goal”,and therefore he got his own political mentality,historical mentality and cultural mentality. He took internal spirits of morality and external order and tranquility as criterion to comment upon historical events in late Qing Dynasty. His conclusion had many defects and few merits. To the problem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he defended state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honor and condemned the Great Powers of the West with scientific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from moral and cultural angles. And so there was the earliest attempt at “Opposing the West with Western Learning”. He also put forward his plan of Chinese development road in late Qing Dynasty. His conservative ideology was the first signs of “the Eastern Culture School” and “ the New Confucianists of the Present Age”.
Gu Hongming;Chinese and Western Conflict;Political Change;View
羅福惠,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中國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