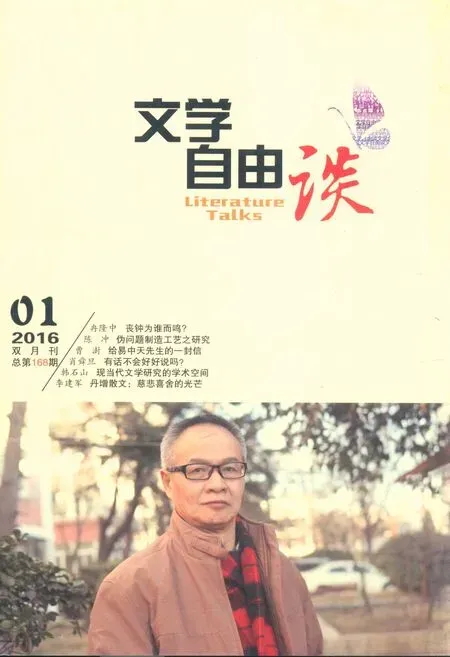有話不會好好說嗎?
肖舜旦
?
有話不會好好說嗎?
肖舜旦
一
在第四屆《文學報》“新批評”專刊“優秀評論獎”的獲獎名單中看到了耿占春的名字,雖然是預料中的事情,但我依然驚訝并且更加困惑。
之所以說是“預料中的事情”,那是因為耿先生在“新批評”甫一亮相就顯得與眾不同,他是“新批評”創刊四年以來第一個以“開設專欄”的名號推出的,其獨特尊貴身份不容置疑,因而,其大作《隱形書寫(一)》獲獎,自是理所當然之事;而之所以“更加困惑”,那是因為當時懷著熱切虔誠之心讀《隱形書寫》不到兩分鐘,就感到頭腦發脹,硬著頭皮強讀下去后,其矯揉造作、故作高深的“學院體”風格直讓人天旋地轉,不知東西南北,莫名其妙。而我的困惑就是:這種典型的“學院體”文章何以在備受詬病多年后又重出“江湖”?而且還偏偏是在以“反對故作高深、艱澀難懂的‘學院體’”著名的“新批評”上露面,這意味著什么?
不客氣地講,《隱形書寫(一)》除了矯揉做作的“學院體”風姿由于暌違多年后的重新露面可以助其暫時奪人眼球外,其他方面可謂乏善可陳。不信,我們不妨試揭其“冰山一角”,以窺其“隱形”背后的“廬山真面目”。
二
《隱形書寫(一)》是以片段性的札記、隨筆形式結構而成,每個小段幾十或一二百字不等,內容各自獨立。作者明顯是在刻意追求一種哲理感悟、妙語靈思類效果,所以,從語言表現形式來看,文字在顯得“深沉”的同時又披上了一件似乎“高深莫測”的時尚華麗的外套,使它在“裝酷”的同時又不免露出了某種輕佻的底色,加上那些“學院派”的術語和有話偏不肯好好說的裝腔拿調、故弄玄虛,整個文體風格就顯得極其詭異:本質晦澀、深奧的同時又有些心靈雞湯式的輕盈、亮麗色彩,而學院體的故弄玄虛、高深莫測的“隱形”風格終究占了上風,讀者或許最終都不免被這些“高深”的“玄虛”攪得如墮云里霧里,莫名所以,不得不“敬”而遠之。套用一句唐詩:此“文”只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見”?
《隱形書寫(一)》的每小段都有一個小標題,似乎唯恐讀者不明意旨,可見其“隱形”立場欲遮還露,端的一副忸怩作態狀。
我們就以他的第一段“寫在前面”為例,看看這種“學院體”的學術成色究竟幾何。
“寫在前面”可以視為其“隱形書寫”專欄文章的“宣言”,窺一斑而見其全貌,讀者不可不察。它是這樣開篇的:
這個時代悄悄發生了與時間的非連續性意識相匹配的短小化風格。這里指的是一切表述的短小化。長篇小說、理論著作都壓縮了敘述。它以另一種秘密的形式保留了長和深的要素。每一個敘述都在盡可能短的篇幅內完成,它欲將簡潔、濃縮變成一種承諾,一種責任,卻要求著比實際篇幅看上去更多一些的逗留,或許它提供了深入瞬間經驗的契機。
這樣的開篇簡直會把人給攪懵了:它究竟表達的是什么?這個時代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按下性子,再仔細“研究”,意思大概明白了一些,但在邏輯上依然漏洞百出。
首先這“時間的非連續性意識”指的是什么呢?“時間”難道具有“意識”嗎?而所謂“非連續性”指的又是什么呢?是說時間的“意識”上出現了“中斷”“非連續”情況?怎么會這樣?是科幻小說的大虛構嗎?我們只知道按照常識來講,時間、空間均為宇宙中客觀存在的一種物質形式,它的存在是獨立、永恒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只有生活中具體發生的事件,過程中才會出現時間上的“連續性”和“非連續性”情況,但這種情況與“時間”本身的“意識”無關,完全是人為造成的,而這種情況出現在小說家寫作中之后,就有了“按時間順序敘事”和“不按時間順序敘事”兩大類別。當然,從后面的文字意義來猜測,所謂“時間的非連續性意識”指的大概是“不按時間順序敘事”這種情況。只是不明白耿先生為何偏要如此“繞”,“繞”得如此不近情理、不合邏輯。
現在再來看第一個句子的完整語意表達。“時代”發生什么事情了?從句子主干分析,是“時代……發生了……短小化風格”,姑且不討論這是否病句,光從語感上就會有一種非常別扭的感覺。通常應該說是“時代”“出現”了某種“短小化風格”才比較通順,但即便如此,這“短小化風格”依然讓人費解。還要看到后面,意思才又“扭扭捏捏”地出來了一點,原來說的是“一切表述的短小化”,而這“一切”又指的是今天的“長篇小說、理論著作”都“壓縮”了敘述,但同時又以“另一種秘密的形式”,保留了“長和深的要素”,而且,“每一個敘述”都在“盡可能”地“欲將簡潔、濃縮變成一種承諾,一種責任”……說實話,如此解讀耿先生的文字,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現在我們把它通俗化的理順一下,這意思應該是這樣的:
我們的時代在文學創作、學術理論上已經出現了一種簡潔、深刻的文風,而這種現象的出現是通過“另一種秘密的形式”而實現的,且當今“一切”寫作者都已“承諾”在寫作中要追求“簡潔、濃縮”,并把這當成了一種“責任”。
好了,現在作者想要表達的意思總算“理”出來了(雖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是,新的問題又出現了:作者說的事情難道真是我們時代正在出現的事情?我們今天的文學界、學術界中人難道真的如作者所說的變得那么純正、自律、有修養、有追求了,用一句時尚的話來說,大家伙都變得這么充滿“正能量”了?中國人都知道,今天的文壇假貨、水貨實在太多,包括許多文學評獎都已變得噓聲四起,小說創作從篇幅上來看也是越寫越長,短篇湊成中篇,中篇拉成長篇,長篇更向系列多部頭“史詩”方向挺進,何曾在追求“簡潔”“濃縮”的“短小化風格”的同時還“保留”了“長和深的要素”?而在學術界,更是抄襲剽竊成風,“學術腐敗”早已是不爭的事實,何曾有過追求“簡潔”“深刻”的“承諾”和“責任”感?
僅此一例,就可見作者的“學院體”表述是多么荒唐,多么虛妄!表達方式上如此陰陽怪氣,表達的內容又是如此罔顧事實,真正像是在白日做夢!
再看接下來的一段作者關于“札記”的闡釋:
札記類似于某種“引文”性質的寫作:摘要式的,而非展開式的,克制的,適可而止地透露一點思想的背景信息;引用的或轉述的,而非自身的話語,引文是對“經典”的一種致敬;引文是眾多聲音的匯聚,而非單純或單一作者的,沒有整體語境的,片段的,集合的,零碎的。這些合起來成為“引用性的”。“引文”式的寫作省略的是可以意會的展開部分。但“引文”是對多重語境的另一種形式的開放。
對于這段又是典型的“學院體”繞口令,我實在不愿意再去逐字逐句地“翻譯”解讀,因為這實在太無聊了。且無論作者在這里關于“札記”說出了多么“深刻”的觀點,稍有常識的人都明白,札記,不就是一種隨感式的思維片段式的文字記錄嗎?它可能深刻,也可能淺薄,這取決于札記作者的思想深度和文學才能。《現代漢語詞典》上關于“札記”的定義是:“讀書時所記的心得、體會或摘記的要點。”“百度”上的解釋是:“讀書時摘記的要點、心得或隨筆記事等文字。”比較這種簡潔明了的定義、解釋,耿先生的“學院體”繞口令是不是有些面目可憎了?他說這么多的繞口令究竟為的是什么?為何要把簡單的事情攪得這么復雜,這么荒謬?
再看一段作者正面解釋他的“隱形書寫”含義的文字吧:
我夢想的“引文”式札記是這樣一種引用:對自身經驗和記憶的引用,對沒有文本化的語境的引用,對語境的壓縮和移位。因此這些札記是一種隱形書寫。需要一種使用顯影劑的閱讀。需要透過一種光,看清這些水印的文字。
這段話里的“對自身經驗和記憶的引用”好像還明白些,大概是指好的“札記”應該是來自作者自身的真切體驗。但后面的“對沒有文本化的語境的引用,對語境的壓縮和移位”說的又是什么呢?“沒有文本化的語境的引用”是說這種“引用”不露“文本”的印跡,但又牢牢抓住了“文本”的“語境”“神韻”?而其實質就是對這些“文本”“語境”進行壓縮并遷移,或者說是將其改頭換面,以另一種不暴露“文本”出處的方式展現?難道這就是所謂“隱形書寫”的真諦?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么,作者的這種“隱形書寫”就具有變相剽竊、抄襲他人文學(或學術)成果的嫌疑,充其量就是將自己的經驗感悟和別人的東西融合在一起,并且又極力隱藏引用了別人東西的痕跡,有意將別人的東西化為自己的“原創”,這是什么行為?難道不是文學剽竊或學術造假嗎?至少,其“原創性”價值已經大打折扣了。
或許我的這種“解讀”在作者看來有些胡攪蠻纏,故意曲解;但是,誰讓你不肯把話好好說清楚呢?你一味地繞的結果就是把讀者給繞糊涂了,自己也不免繞得不知天高地厚,以為自己就是玉皇大帝,想怎么說就怎么說了。這豈不荒謬?
當然,還可有另一種解讀,作者自己想表達的真實意義或許是說自己的批評是“隱形”的,是沒有明確的“文本”參照的,但其實依然是圍繞著某種“隱蔽”的文學“文本”展開的,只不過讀者要想真正解開“隱形”謎底,卻需要一種“顯影劑”。看來,耿先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不把讀者給繞迷糊就決不罷手了:話都說到這份上了,卻又冒出個“顯影劑”來,似乎是想指點迷津;但是,話卻說到一半又戛然而止了,究竟這“顯影劑”、這“需要透過”的一種“光”是什么?讀者該如何獲得?倘若你不告知,讀者如何讀懂你的“隱形書寫”?如何看清你這精心布下的“學院體”文字謎局?
三
《文學報》的“新批評”對耿先生有這樣的贊語:“耿占春以他富于詩意和創見的寫作,把批評重新解讀為對想象力的發現,對自我感受的檢驗和表達:在知識的面具下,珍惜個體的直覺;在材料的背后,重視思想的呼吸;在謹嚴的學術語言面前,從不蔑視那些無法歸類的困惑和痛苦。”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們至少見識了耿先生的所謂“創見”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善于”把簡單的常識通過“學院體”的“饒舌”給“創見”得曲里拐彎,異常復雜,甚至面目全非。下面我們再通過一例來見識一下他的“詩意”和“思想的呼吸”之特點,這就是他《隱形書寫(一)》的第二則文字“結束”。這一則文字不算長,屬于作者說的那種“時代”“發生”了的一種“短小化風格”,我們就不妨把它全文引出來:
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創造都似乎是一種結束,而不是開端。是離去而非來臨。最耀眼的作品都昭示了一種衰落著的輝煌而非一個黎明的世界。
這是一種奇怪的結束。沒有人能夠寫出結束一切詩歌的詩歌,沒有人能寫出結束文學的文學,結束哲學的哲學,或創造出結束宗教的宗教,結束一種制度的制度。然而它的各種后繼活動依然是一種結束。人們已經寫下了難以計數的以“終結”為主題的著述。由于沒有希望的維度,“結束觀”意味著我們的現在一開始就屬于過去的范疇。但似乎所有的“結束”宣告都想把影響投向未來的地平線。
從表面來看,這段文字詩意盎然,且似乎“韻味”深刻,一副高瞻遠矚的“哲學家”深思狀,簡直是“酷”斃了!但是,我不明白作家如此強調這種所謂“結束”的意義是為什么?一種裝腔作勢、莫名其妙的“虛無主義”情結,似乎迷戀“結束”,又似乎害怕結束,既有些惆悵地否定“創造”的意義和價值(“最耀眼的作品”也不過是“昭示了一種衰落著的輝煌”,并且“沒有希望的維度”),又似乎僵尸般地迷戀著一種頹廢式的“結束”或毀滅,大唱“結束”的贊歌或衰曲。似乎蕓蕓眾生如群氓般無知無覺,天下皆醉吾獨醒,唯吾慧眼獨具,能預知世事前程吉兇,能先天下之憂而憂。
然而,耿先生或許沒注意到,在他這段關于“結束”的“安魂曲”里,他在強調“結束”的絕對終極意義時,卻又同時陷入了一個自己無意中設下的邏輯悖論黑洞。當他在宣稱“沒有人能夠寫出結束(或創造)一切”的詩歌、哲學、宗教、制度的同時,似乎已經確切無疑地肯定了自己的“思想的呼吸”的創造性和深刻性;但是,當他在自以為“深刻”地極力否定、嘲諷人們具有“創造”性的“后繼活動”“沒有希望的維度”的徒勞性時,卻沒有意識到人們這種“難以計數”的“后繼活動”雖然不免“一開始就屬于過去的范疇”,且最終都不可能實現“把影響投向未來的地平線”的目標。不要忘了,正是人類這種生生不息的“沒有希望的維度”的“創造”性“后繼活動”,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達,正是這種不斷“結束”的“創造”將人類“未來的地平線”接力火炬似地燃燒得輝煌無比,雖然這每一次的“創造”的“影響”都不能抵達“未來的地平線”,都將不免“一開始就屬于過去”地面對“結束”,但是,這種所謂的“結束”真的就意味著“結束”嗎?誰有權力否認人類文明的薪火相傳的偉大“創造性”意義?
其實,耿先生在這里提出的所謂“結束”的思想并無多少新意,也只是一種常識而已。這個世界固然沒有永恒的東西,所謂的創造、詩歌、文學、哲學、宗教、制度等事物,也不過是滄海之一粟,都會轉瞬即逝,并必然“結束”成過眼云煙。盡管如此,對這些事物的追求卻依然是人類的不二之選,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人類的思考,就如同誰都知道每個個體都難免一死,但沒人會無緣無故地嘲笑甚至毀滅新生命的誕生。在這里,耿先生如此渲染所謂“結束”的“宿命”性意義究竟為何呢?是想諷刺人類“創造”行為的徒然和渺小嗎?所以,在這里,耿先生并沒有說出任何有價值的新思想,除了一種自比上帝式的狂妄,還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東西呢?
四
想對《隱形書寫(一)》的所有內容一一做出詳細的分析和解讀,那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以這種“窺斑見豹”的方式作一種選擇性的個案分析。縱觀《隱形書寫》的所有文字,幾乎全是這一類隨筆式的片言短語,貌似深刻雋永的心靈雞湯類的哲思妙悟,加上語言風格上“學院體”的裝腔拿調,表面上看非常時尚、很有品位,但并無多少真正的有價值的思想。看一看它的一些小標題,就大概可以明白其性質所在,如“給痛苦一個名字”“言與道”“稀缺與過剩”“疑似經典”“生活的球體”“隱喻與概念”等,這些文字你可以叫它為散文、雜感,甚至散文詩之類,但就是無法將它歸類于文學批評。所以它的“新批評”專欄文章的身份,就凸顯出一種完全不相容的異類特質。殊為難解的是,“新批評”何以對這種“異類”特點竟然毫無感知,竟然還為其找到了一條理論依據?在其“編者按”的推薦語中,有這樣的表述:
茨維坦·托多洛夫在《批評的批評》里寫到:“批評并不應局限于對文本的解讀。作為批評家與世界、時代、文學對話的重要方式,文學批評不應忘記它也是對世上真理和價值的探索——一種揭示性的探索。”
僅從這里所引用的一段文字來看,編者對這段文字很有斷章取義之嫌,理解上也可能存在某種誤區。雖然我沒有讀過茨維坦·托多洛夫的文章,也不明白這段文字的語言環境,但我敢斷言,他所說的“批評并不應局限于對文本的解讀”所包含的意義,首先就應該有立足于文本這一前提,只有在保證這個前提的條件下,才可以展開“不應局限于對文本的解讀”,才可以實施文學批評“對世上真理和價值”的“揭示性的探索”;也就是說,批評家無論在自己的文學批評中想做怎樣的“揭示性的探索”,都必須是依附于文學作品文本本身而發的。如果完全缺乏文本基礎,而只有即興式的海闊天空般的品評議論、妙語哲思,那么,文學批評與所有的具有“揭示性探索”意味的散文、小品、隨筆、哲學思考一類的文字又有何區別?而《隱形書寫(一)》就正是這種完全缺乏文本基礎的隨意式的“哲理”隨筆、小品類文字,他的作品里,幾乎沒提到任何一個作家的名字,也與任何一部文學作品的內容無關,這如何可以稱之為“文學批評”呢?
“學院體”最大的弊病就是故弄玄虛,矯揉造作,以“學院體”的“彎彎繞”文字游戲方式裝腔作勢,舍近求遠,化簡單為復雜,變明白為晦澀,有話不肯好好說,玩弄名詞術語,故作深沉,以掩飾自己思想的平庸。為讓讀者再見識一下“學院體”的故弄玄虛,我再引兩段耿先生的“新批評獎”獲獎感言(刊于2015年6月4日《文學報》“新批評”),作為本文的結束:
某種狀況常常讓人陷入沉默。一次出門的時候我想,心中的第一個句子藏在哪里呢?如何我才能夠再開口說話呢?既然話語是這樣的軟弱無力。
每天每天瀏覽信息,了解那些令人憤怒不已的并不明朗的事態,伴隨著的是語言的平庸性,在關切著社會諸多狀況時,語言已經在和它一起墮落。
多么矯情的“詩人”的“沉默”,多么令人莫名其妙的“憤怒”以及和“語言”“一起墮落”的“社會諸多狀況”!是詩人在深沉地抒情,還是哲學家在為世象擔憂?我不知道耿先生在這里究竟想表達什么,真希望有人來為我指點迷津——只是我更不知道耿先生肯屈尊賜教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