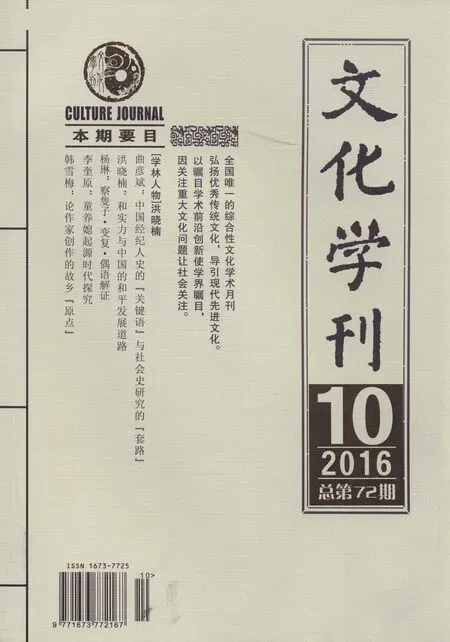當代誠信觀念的起源、特征及認知研究
張京玖
(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
【文化哲學】
當代誠信觀念的起源、特征及認知研究
張京玖
(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任何民族時代問題的解決都有賴于本民族的傳統文化與現時代狀況的結合。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當代中國,誠信缺失現象時有發生,說明以往注重依靠西方契約誠信及其衍生出的法律制度解決誠信問題的方式有其弊端。我國傳統誠信作為德性觀念和倫理原則在歷史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解決誠信問題必然要重新解讀當前誠信觀念,而這種重新解讀又必然要求重視并發展我國傳統誠信觀念。
誠信;當代定位;傳統道德誠信;契約誠信
一、誠信觀念的起源
“誠”“信”二字在我國現存最早的歷史典籍《尚書》中就已出現,而記錄“誠信”一詞的史書均晚于《尚書》,據此推斷,誠信一詞應是后人將誠與信組合構成的合成詞。“誠”源于人們對鬼神的敬畏,《尚書·太甲》講“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信最初就有相信之意,《尚書·湯誓》言“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隨著歷史發展,誠與信各自具有了更深層次的內涵。于誠,后人著重從內心德性和人性本真之實現處闡釋,將其提升到作為本體的天道的高度。《大學》中言:“所謂誠其義者,勿自欺也。”[1]此處,誠即為自我約束之意。《中庸》:“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2]此處的誠上升到了作為天道的本體層次,誠者與誠之者是天道與人道的統一,普通人通過“擇善而固執”的功夫逐步向誠者即圣人的境界邁進,這一修養過程是人內在道德心的自然展開,是人性的本真實現,誠由此具有了最深刻的本質釋義。于信,后人注重從外在人際關系和社會規范方面闡述。信是人際交往的人倫規范,《大學》中講“與國人交,止于信”[3]。信還逐步成為治國安民的社會規范,如《論語》中提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4]。可見,信在古代已成為百姓行事、君主治國的道德規范,對個人安身立命和國家安定均起到重要作用。
誠主內,信主外,但二者仍有內在的貫通之處:個體只有通過自律,做到誠,才會在人際交往中踐行信;信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誠的開展。誠與信是內外一體、相輔相成的。正是因為二者潛藏著的內在關聯,誠信一詞才必然產生。
“誠信”一詞最早出現于先秦時期,這與其時代背景密切相關。正值社會轉型期的春秋戰國,生產力的提高使經濟發展,逐利風氣興起,不斷出現見利忘義的事件;政治上諸侯爭霸,統治者為了利益背棄信義,擅自撕毀盟約互相討伐;社會動蕩使人倫盡失,人與人的信任也逐漸消失。基于社會動蕩、人倫道德盡失的現狀,“誠信”一詞應運而生。這一時期是誠信觀念的奠基時期,誠信綜合了誠、信二字的含義:于外在說,誠信既是言而有信的人際交往的道德原則,又應是取信于民的治國理政的準則;于內在講,誠信是人成就內在德性的基礎,即誠之者是趨向誠之天道必要的修養功夫。這一奠基時期形成的誠信觀念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由之發展而來的誠信觀念始終未超出此基本含義。
二、誠信觀念的特征
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誠信觀念以親人和熟人為紐帶,局限于小范圍的人際圈和地域,具有濃重的封閉性。處于幾千年封建專制主義統治下的中國,社會等級意識極為強烈,由此產生發展出的誠信不可避免地沾染了人倫等級的氣息,具有鮮明的階級性。[5]中國古代社會有重道德輕法制的傳統,注重由內在的德性修養達到生命的本真實現,因此誠信必然被定義為自律性的內在修養。也恰恰因為誠信講求“擇善而固執”的修養行為,才使古代誠信學說具有上達天道實現本真生命的意味。這也展現出中國傳統哲學中注重個體生命及其本然實現的人文關懷。
誠信是人類社會和歷史的必然產物,它在古希臘時期的西方世界亦已出現。西方誠信是為滿足人們利益最大化的功利需求應運而生的契約誠信。它植根于發達的商品經濟,萌發于人們廣泛的交易過程中,茁壯成長于利用契約相互約束的大樹的保護下,展現出強烈的開放性、平等性、他律性的特征。以上是中西方誠信的顯著差別。
三、我國誠信觀念現狀
改革開放初期,隨著提倡自由競爭、平等交易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逐利風氣興起,我國傳統誠信的約束力迅速減弱,損人利己、誠信缺失現象時有發生。這種逐利風氣如洪水猛獸般迅速彌漫到社會其他領域。誠信不再是人際交往的首要道德原則,出現信用誠信危機;報告中的虛假數據、學術論文中的屢次抄襲事件一再發生,政治誠信、學術誠信嚴重缺失。面對這一現狀,我們采取了西方誠信中強制性的法律約束機制,曾使誠信缺失現象有所緩和并一度好轉。
時隔近四十年,誠信缺失又一次成為亟須解決的時代問題。誠然,處于社會轉型期并且缺少法治傳統的當代中國,誠信的約束機制必然還不成熟,因此有學者提出“健全法制是解決誠信危機的根本途徑”。契約誠信精神理應作為現今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指導精神,但完善的法治并不能真正解決誠信問題。以美國為例,法律體系完備、法治設施健全,但也出現了次貸危機,進而演變為金融危機。由此可以看出,法制不是萬能的,正如著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指出的,“法律、契約、經濟理性只能為后工業化社會提供穩定與繁榮的必要卻非充分的基礎,唯有加上互惠、道德義務、社會責任感和信任,才能確保社會穩定繁榮”。
四、對當代誠信觀念的重新認知
解決誠信問題不能單純寄希望于法制,應采取多方面的綜合措施。這一盲目推崇法治約束誠信的錯誤觀念,根源于當代對誠信的定位出現偏差。誠信問題的解決必然以重新認知當代誠信觀念為前提,此是第一要務。任何民族的時代問題的解決都有賴于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和現時代狀況的結合,就當代的誠信含義而言,它絕不應是人們當前盲目崇拜西方契約誠信及其衍生出的法律制度,它應是道德誠信與利益誠信的結合,應以傳統誠信為根基的、以西方契約誠信為輔助。對當代誠信觀念重新定位,主要從當代誠信觀念的價值定位、適用范圍定位、約束機制定位三方面著手。
(一)誠信觀念的價值應定位于“義利并重”
誠信觀念的價值不應是傳統誠信觀念認為的信不及利,也不應是西方誠信觀念中的利益至上。[6]《論語》中講“信近于義,言可復也”。信的實踐行為是以合乎禮的規范和義的要求為標準,這顯露出建基于生產交換能力低下的熟人社會中的傳統誠信有著鮮明的重義輕利的價值取向,而以利益至上為原則的西方契約誠信亦面臨道德淪喪的困境,逐利忘義事件層出不窮。[7]因此,經濟高度發達的當代需要的是一種既能肯定利益的正當性,又能維護社會秩序的誠信觀念,即“義利并重”的誠信觀念。
(二)誠信觀念的應用范圍應定位于“社會誠信”
傳統誠信觀念講求“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局限于以血緣和地域為紐帶的狹小人際交往范圍內,一旦離開地緣和血緣的限制,“熟人誠信”就難以發揮作用。這種誠信觀不再適應以陌生人交易為特征的現代社會。傳統誠信觀念應將視域擴大,汲取西方契約誠信中的平等精神,突破自身的等級傳統,轉變為平等地約束個體、適用于整個社會各個領域內的普遍的“社會誠信”。[8]
(三)誠信觀念的約束機制應定位于外部法制與內在德性修養的結合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側重將法律作為誠信的約束機制,近些年的誠信缺失現象說明了道德培育的重要性。當代誠信應在堅持法律的制度保障下,追本溯源,注重傳統誠信中的反身自求的內在修養,構建外法內德的約束機制。
對當前誠信觀念的重新定位包含了轉變傳統誠信觀念和反思當前誠信觀念兩大過程,這一定位符合當下現實。正是通過上述重新定位,當代誠信觀念才能為人們廣為接受進而內化于人心,成為內在的德性觀念,推動人們感悟傳統文化中的誠的本體意味,繼而喚醒人們內在的良知。在誠信內化于心成為內在的德性觀念后,人們便會順從本心并自覺實踐,這一實踐過程既是主體作為生命存在本真呈現自身的過程,亦是人格完滿實現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吾心與他人、外物和社會融為一體,進入與萬物通達的和諧之境,亦使傳統誠信的本體意義得以彰顯。唯有通過上述重新定位,才能使誠信觀念發乎心踐乎行,真正重建誠信道德,為當代誠信缺失問題找到根治之方。
[1][3]王文錦.大學中庸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8.3.4.
[2]王治國.中庸譯評[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83.
[4]黃克劍.論語疏解[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5.
[5]張豈之.中國思想文化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77-78.
[6]夏偉東.重新認識中華民族傳統的誠信道德素質[J].鄭州大學學報,2003,36(2):5-7.
[7]樊浩.中國倫理精神歷史建構[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460-461.
[8]王進.中西方誠信觀比較[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08.
【責任編輯:王 崇】
D648
A
1673-7725(2016)10-0174-03
2016-08-05
張京玖(1996-),女,山東菏澤人,主要從事哲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