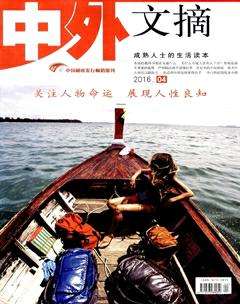一個人生活的苦楚與辛酸
□劉丹青
?
一個人生活的苦楚與辛酸
□劉丹青

焦 慮
王小西的單身生活就是從租房開始的。主動離開了上一段感情后,她住進了一個體面的公寓。
對比同齡人,她的家相當考究,貓也最貴:室內小吧臺、日式掛簾、無印良品全套被褥,一把椅子1500塊,上面躺著一只尊貴的折耳貓。
26歲的小西月入上萬元,但布置小家仍然刷爆了她的銀行卡。家里處處透著“一個人也要好好過”的決心。但這決心過大了,因此顯得有點焦慮。
作為文字記者,小西不坐班,工作無非采訪、寫稿,一個人走南闖北。獨居后,她徹底成了一座孤島。
以小西的年齡、條件,如果她想要,很容易就可以有一個伴侶。但她沒有這樣做。于她而言,親密關系里的消耗,有時比孤獨更難應付。
“你知道,如果一個女孩子自給自足,婚姻帶來的切實利益就會減少,吸引力也會降低”。小西觀念開放。單身前,她想,如果一個人過于孤獨,拿一段不認真的感情關系來消遣自己,只要拿得起放得下,去做也無妨。
單身后,她發現自己的生活自成系統,非常平靜,也很自由。
一開始她以看電視劇轉移注意力,不去想她為什么要這樣生活,但后來卻發現看電視劇只增加了沮喪與孤獨。
她知道自己應該離開房間到外面與人交際,卻缺乏動力。一切和大學時代已經完全不同,人們不會路過來敲門,而交朋友也越來越難,每個人都很忙,大家都沒什么時間。
于是,她將多數時間交給了那些雇傭和教導她的人,剩下的時間則用來自我提高:“你必須做一份占用你大量注意力的工作,這可以把你面對自己的時間壓到最少。”
她更加關注自己。每天吃飯,她會用近40分鐘的時間,從周圍50多家外賣里精挑細選。
一個人的生活里,悲傷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代價是:她也不再有強烈的快樂。小西說,之前兩個月里,只有兩件事讓她高興:一是去單位開了個會,見到同事;二是聽了一場樸樹演唱會。
松 弛
在小西的年紀上,蔡雅妮也有過一段焦慮期。可過了30歲之后,她反而松弛了。
蔡雅妮坦言,30歲之后,當她的經濟狀況變好,有了自主能力,獨立意識,相應的有了話語權,父母也變得像小孩子一樣聽話,小環境內,她不再面臨壓力。
現在的蔡雅妮是頗受歡迎的視頻節目《一人食》的制作人。這節目給了她不小的名氣和良好的經濟狀況,節目的靈感就來自于她的單身生活:一個人也要好好吃飯。
對蔡雅妮來說,一個人生活,技能不重要,燈壞了,有電工;鎖壞了,有鎖匠;難的是與自己相處。
變化是從3l歲開始的。這一年,她離開北京,回到上海,獨自生活。之前的兩年里,她的工作、感情一直不順利,一次連續48小時不眠不休的高強度工作后,她辭掉了某財經雜志圖片編輯的工作。
辭掉工作,換了城市,生活并沒有好起來。這一刻,她意識到,問題不在外部,而在于自己。
她開始整理身心,化妝、留心衣著、調控情緒,將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這需要極大的自我驅動力,但比跟另外一個人相處要輕松,“你可以控制自己,卻不能控制一段關系,因為對方是一個變量。”
一個人的生活里,她不再需要對另一個人的感受與狀態負責。
對經濟上有保障、繁忙而擁有豐富社交生活的蔡雅妮來說,獨居既保障了隱私,也提供了自我復原及個人發展的機會,《一人食》的成功驗證了這一點。有趣的是,當她關照自己的需要后,周圍的人際關系、異性緣反而好起來。她說,專注也是一種魅力:“你去喜歡一些事情,那種投入的美是會給你加分的。”
殘 酷
但對單身男人來說,過了35歲,聞天開始希望有一個伴侶。身邊的單身朋友紛紛進入婚姻,這使他們具備了良好的生活習慣、經濟能力,并過上了有保障的性生活。很多單身男性對這一點并不諱言:穩定的性生活,對男性而言非常重要。
35歲之前,聞天一直單身。他坦言,對一個年輕、健康、有體面收入及良好社會地位的男人來說,單身是一種上升空間最大、社交面最廣、感情關系最多的生活方式。
空窗期里,他有過多段戀愛。在隱秘、成人、自愿的原則下,過著性與情感完全開放的生活。
開放關系里,雙方都是不認真的。他靠降低期望值、減少投入來避免傷害。但幾年后他發現,長期在感情關系上有所保留的狀態,使他越來越難以對異性真正動心。
因此,當小他3歲、剛剛離婚的葉凌對他表現出好感時,他并沒有過于珍惜。
葉凌漂亮高挑,家教良好,惟一不符合世俗婚嫁標準的是她的離異經歷。這讓她在接近聞天時不免帶了一點謙卑。
聞天是喜歡葉凌的。她是他想要的女孩子,貼心、柔順、寵著他。兩人約會,葉凌開車來接他。
聞天感到男性的權威和絕對的控制力。他一面在與葉凌的關系里越陷越深,一面借著女孩的謙卑,暗暗抬高自己的位置。
他想把這種相處模式保持下去。這是第一次,聞天發現與一個人建立親密關系,比單身要更加愉快。
他已經做好了結婚的準備。可就在這時,葉凌提出分手。理由是,她無法接受兩人關系里的不對等。
第一次,他對自己在感情中的表現感到懊惱。單身生活中那些輕率的關系,讓他幾乎不會愛了。
現在,聞天又恢復了單身生活,一個人住三室一廳,吃著瓜子看《盜墓筆記》。他完全可以任性,不用擔心自己的趣味、習慣讓對方不適。
之前,聞天有個小圈子,周末跟高中同學、河南老鄉打打麻將。現在,這些人結婚生子,能約出來的朋友越來越少。他開始跟單位的實習生一起玩兒。有了電影票,分一張給這些小他七八歲的小伙子,但真玩兒到一起,又沒什么共同語言。
“你需要一個與你同齡、了解你、而又對你無害的親密關系。”聞天說,“幫你出謀劃策,跟你討論人生規劃。這種事上父母幫不上忙,又不適合去對領導同事講。”他處在體制內,人事復雜,利益相關。
早些年,聞天很享受單身,干什么都興致勃勃,覺得生活里多一個人都是阻礙。但年齡漸長,他感到那種活力在慢慢流失。
“我對很多東西都不那么感興趣了,惟一保留的愛好是看美劇。我挺珍惜。別有一天連這都不感興趣了——那挺可怕的。”
一輩子的孤獨
同樣處在三十出頭的年齡,李林林卻說,眼下的單身生活,是她刻意保持的。
身為大使館參贊秘書的李林林有過多段親密關系,但都以失敗告終。理由是,當一段關系進展到一定程度后,它就不再對李林林構成吸引,她發現自己很容易對人失去興趣。發現這一點后,她開始有意與親密關系保持距離。
“我不想再因為不感興趣而結束一段關系。這對別人傷害很大。”李林林說,“而且問題是,我不喜歡你,不是因為我喜歡上了別人,而是因為我對你沒感覺了,你講的笑話不再好笑。”她聳聳肩,“可我沒辦法改變這件事情。”
這情形在她身上屢次發生。最初,她并沒有意識到問題出在哪里。
李林林有過一次讓人艷羨的感情。二十歲出頭,留學土耳其時,一個羅馬尼亞的金發小伙子愛上了她,兩人一起讀書,錢放一起花。5年后,男孩念完醫科大學,買了鉆戒給她時,她卻慌了。
“我愛他,但害怕自己的未來跟這個人完全聯系在一起。”李林林說,“我愿意做你的生活伴侶,但不一定要簽字結婚,我對未來不確定。發現這一點后,我對自己很失望。”
她患上了抑郁癥,一個月瘦了20斤,服藥后手抖,情緒受到壓制,度過了一段非常艱難的時期。
如今,李林林每周健身兩次,周末陪父母,“我甚至懶得約會。時間都是我的,我不想分給別人。”對那些交往之初就懷有強烈結婚意愿的男人,“我根本不會去碰他。”
她有著開放的性生活,“我是個分得很清楚的人,可以有性,但不代表要與這個人建立親密關系,或有感情上的交流、糾葛。”
她滿意這種狀態,并且慶幸有讓自己開心起來的能力,從不介意一個人去吃飯、看電影、潛水、出國旅游。
惟一一次,在圣地亞哥的海洋館里,她看到幾只白鯨。它們大而美,卻被困在窄小的、不屬于它們的水域里。
她看了很久。竟然哭了。“她說她好像看到了自己一輩子的孤獨。”
(應采訪對象要求,王小西、聞天、李林林均為化名)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