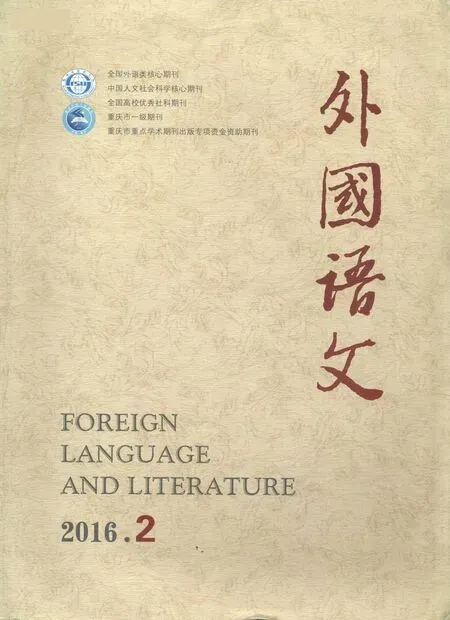救贖的力量
——論《大主教之死》的審美救贖
張健然
(南開大學 外國語學院,天津 300192)
?
救贖的力量
——論《大主教之死》的審美救贖
張健然
(南開大學 外國語學院,天津300192)
摘要:在地域小說《大主教之死》中,薇拉·凱瑟通過表現土著印第安人解放自然的觀念以及凸顯他們的“新感性”特質和印第安藝術的“光韻”,展現出印第安文化具有治愈現代文明痼疾和挽救現代性危機的救贖力量,詮釋了文學藝術擔綱的審美救贖之職。審美救贖是凱瑟打破資本主義社會“鐵籠”的策略,旨在糾正啟蒙現代性的過激發展帶給現代文明的負面影響,以期建立一種人與社會、自然與文明、感性與理性平衡發展的理想生存范式。這些藝術構想不僅與啟蒙現代性的價值觀相互抵牾和抗衡,還是凱瑟在想象世界中探求救贖現代性之策的最佳腳注,進而表明她的地域書寫以一種超越傳統與現代、地域與國家、本土與全球相互對峙的創作姿態,介入社會現實和反思人類文明的出路。
關鍵詞:薇拉·凱瑟;《大主教之死》;審美救贖
0引言
長期以來,評論家將薇拉·凱瑟(Willa Cather, 1873—1947)視為20世紀20年代美國地域文學的代言人,將她的作品等同于“懷舊”“保守”和“反現代”,并認為它們缺乏對資本主義社會和政治的關注,具有“逃避主義”之嫌(Reynolds, 1996:1)。誠然,在以內布拉斯加大草原為背景的地域小說中,凱瑟頌揚拓荒者純良、敦厚、實干的美德,描摹出富有鄉土色彩的美國西部圖景。但這并不說明作家刻意回避資本主義文明發展招致的社會弊端,亦非盲目地懷舊,更遑論逃避問題層出不窮的現代社會。凱瑟生活和創作的黃金時段見證了美國社會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從田園文明向機械文明轉型的過程。在社會轉型時期,城市化、工業化和標準化的社會大生產,合力將美國帶入快速的現代化進程。毋庸置疑,作為歷史現代性的基本維度,社會和經濟現代性奠定了現代美國文明的物質基礎,但與之相伴的是一系列的文明“綜合征”。資本主義的追本逐利和精于計算將現代文明推向異化的淵藪,現代人淪為機器大生產流水線上的齒輪,人際關系疏離,炫耀性消費盛行,社會物化,這些文明“綜合征”共筑成一道美國社會的病態景觀。正如邁克·斯賓德勒指出,隨著汽車、消費市場、超市、購物中心等現代性的標志遍及美國社會的角落,“美國中西部地區也正在步步逼近災難,淳樸粗獷的小鎮風貌日漸模糊,古道熱腸的‘西部精神’消失殆盡,人格淪喪和人性扭曲是人們對鄉村小鎮的普遍感受”(Spindler, 1983:98)。現代性以一種強大的吸附力,將“進步”“祛魅”等啟蒙的核心觀念附著于美國中西部的鄉村小鎮,使得該地域普遍受到文明“綜合征”的侵擾。面臨現代性痼疾向鄉村小鎮蔓延的現象,以薇拉·凱瑟為代表的地域作家在創作中是否僅僅傾向于詩意化的鄉村小鎮敘事?是否她的地域作品缺少對現代性問題的關注?答案是否定的。凱瑟不同于同時代的德萊塞、菲茨杰拉德、艾略特等現代主義作家,后者無情地撕下啟蒙現代性的光鮮面紗,揭示現代人的精神萎靡和幻滅,并在藝術殿堂開始奧德修斯式的求索,尋求拯救沒落的西方文明的方案。她的大多數地域小說以鄉村小鎮為敘事空間,將詩意化的鄉村小鎮敘事作為管窺現代性之隱憂的視角,并試圖從這些敘事空間表征的地域文化中覓得救贖現代性的精神支點。這些思想前瞻性地預示著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宗教衰落之后,用“審美救贖”的光亮燭照人類文明出路的理念。
作為現代性批判理論中的一個關鍵詞,“審美救贖”以批判工具理性為理論出發點,矛頭直指啟蒙運動以來理性的異化對人的主體性的消解,主張憑借審美或藝術的力量,對宗教淪落之后陷入社會“鐵籠”中的現代人和拙劣的現代文明提供一種世俗救贖。審美救贖的目標是抑制工具理性,克服異化力量,恢復人的完整性。面臨一個傳統崩塌、現代人精神式微的世界,馬克斯·韋伯、赫伯特·馬爾庫塞、西奧多·W.阿多諾等西馬批評家都肯定藝術具有的審美救贖功能,極大地豐富了審美現代性的內涵。韋伯明確指出,藝術具有將人從理性主義之重壓下解救出來的“世俗救贖”功能(Weber, 1946:342)。馬爾庫塞認為,審美通過某一種基本沖動(消遣沖動)而發生作用,能夠“消除強制,使人獲得身心自由”(馬爾庫賽,2008:119)。阿多諾堅稱,宗教衰落,傳統消逝,現代藝術和文學在提供價值判斷方面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他認為藝術能重新展現人們在現實中所異化的人性、理想和內心的烏托邦,因為“藝術是對被擠掉的幸福的展示”(Adorno, 1997:136)。實際上,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提出“審美判斷”的概念和“審美無利害”論,肯定審美帶來的愉快是“惟一無利害關系的和自由的愉快”(康德,1964:46)。謝林秉承康德的審美立場,提出“藝術哲學”的概念,并希望通過審美帶來的理性和感性的交融,實現拯救人類的宏大理想。可以說,審美的救贖功能是一個美學界長期關注的重大命題。席勒提出審美涉及的感性沖動能彌合人性的裂痕;尼采將酒神精神視為人走向自由的手段;海德格爾倡導人類在大地上“詩意的棲居”。這些哲學家的出發點是肯定藝術作品的審美救贖之職,借此,他們開啟了批判現代性的先河。
作為美國地域文學的典范,凱瑟的地域創作向讀者展示一個充滿“可能性救贖”的世界(Fisher-Worth, 1990:37)。本文以凱瑟的地域小說《大主教之死》(DeathComesfortheArchbishop, 1927)為例,將其放置在作品創作時代的社會、文化和歷史大背景下作考察,從審美現代性的維度,闡釋作品的審美救贖思想,認為凱瑟通過表現土著印第安人解放自然的觀念以及凸顯他們的“新感性”特質和印第安藝術的“光韻”,展現印第安文化具有治愈現代文明痼疾和挽救現代性危機的救贖力量。審美救贖是凱瑟打破資本主義社會“鐵籠”的策略,旨在糾正現代性的過激發展帶給現代文明的負面影響,以期建立一種人與社會、自然與文明、感性與理性平衡發展的理想生存范式。這些藝術構想不僅與啟蒙現代性的價值觀相互抵牾和抗衡,還是凱瑟在想象世界中探求救贖現代性之策的最佳腳注,進而表明她的地域書寫以一種超越傳統與現代、地域與國家、本土與全球相互對峙的創作姿態,介入社會現實和反思人類文明的出路。
1解放自然的審美救贖觀
羅伯特·多曼認為,20世紀20年代的文學地域主義和現代主義有著共通之處,二者都把握到啟蒙現代性的病灶在美國社會的反映,皆把美國表征為一個“非人的、動蕩不安的、頹廢的、自私的、物化的、空虛的、墮落的國度”(Dorman, 1993:2)。這些負面表征是啟蒙現代性將現代文明帶入危機狀況的有力舉證。以防美國繼續墮落,避免人的精神沙化愈發嚴重,以及規避傳統徹底崩塌,現代主義作家積極尋求解決啟蒙困境和救贖現代人的方案。埃斯特拉德·艾斯泰森精辟地指出,“現代主義可被視為美學英雄主義,面臨現代世界的混亂(一個‘墮落’的世界),它將藝術視為……是對現代現實中的混亂秩序的一種拯救”(Eysteinsson, 1990:9)。如果說具有世界主義視野的美國“垮掉一代”的作家紛紛走向巴黎左岸,向古老的歐洲文明汲取救國的養料,而哈雷姆文藝復興的黑人作家從黑人的文化傳統中找到對抗同質化社會的策略,那么,地域作家則從地域文化和社群意識中獲得療治現代性病癥的精神力量,體現出知識分子在現代文明陷入一元化危機的大背景下試圖緩解現代性危機的審美救贖思想。
同樣地,凱瑟的地域小說《大主教之死》是一部濃縮了作家審美救贖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被批評家稱為是凱瑟“最為精心構思的一部作品”(Woodress, 1987:406),小說以19世紀40年代拉都主教和助手維蘭在新成立的新墨西哥州傳教的經歷為線索,探討人與自然、社會、歷史和文化之間的多維關系。凱瑟從現代的視角重審歷史,引領現代人走進印第安人居住的美國西南部和體驗多元化的地域風情,凸顯印第安人的淳樸以及他們解放自然的天性。借此,凱瑟一方面影射她寫作時代的物化現實;另一方面,意在呼吁在異化社會傾軋下的現代人放棄矯揉造作的物化審美,走向自然審美,并在解放自然之中緩解現代生活帶來的精神焦慮和心理恐懼,使得處于均數狀態的人們在此岸獲得精神依托。
在《大主教之死》中,凱瑟給精神空虛的現代人開了一劑審美救贖的良藥:解放自然。依照馬爾庫賽的觀點,解放自然主要有兩個層面:一是解放人的自然,即人的原出沖動和感覺;二是解放外部的自然界,即人的實存的環境 (馬爾庫賽,2008:121)。就該小說而言,解放自然的審美救贖觀是指解放現代人的外部自然環境。凱瑟通過描繪印第安人天人合一的審美意象,引導現代人效仿印第安人的生存方式:崇尚自然,釋放自然中促成生命的原始力量,創造民胞物與的生活意境。印第安人解放自然的欲動促使他們尊崇大地,關愛棲居于大地之上的每一種生命體。透過拉都主教的視角,現代人管窺到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存之道。千百年來,這些納瓦霍人、阿孔瑪人、霍比人、普韋布洛人和佩科斯人是美洲大陸上最和善、最忠誠的居民。他們雖屬于不同的部落,但解放自然的理念將他們緊緊相連,共同譜寫出人在自然中“詩意棲居”的和諧樂章。凱瑟寫道,印第安人“是真正地生活在他們的巖石上:生于斯,死于斯”(Cather, 1931:99)。他們死后把能量還回大地,供養其他生物,以輪回的方式回報自然的恩澤。這種行為既體現一種關愛自然的倫理思想,又再現了解放自然的審美觀。印第安人僭越人與己、物與我的差異,遨游天地,以解放自然的精神騰飛在理性不能上升的精神高空,詮釋了一種和諧的、無功利性的審美理念。
解放自然,不干預自然的運作,是印第安人抵制大自然被啟蒙現代性的“祛魅”邏輯所統攝的方法。印第安人從不把自然當作實用對象,卻將自然看作美的發源地,尊重自然的原初價值,以素樸的生活方式在自足自為的自然本體中,參與宇宙的和諧運動。他們認為自然是萬物之母,因而,從不試圖改變大地的容貌,并在日常生活中踐行對大地的關愛。小說中,印第安人的住所完美地展示出他們與自然相融相契的生活狀態。“霍比人建在平頂山上的村莊,與腳下的巖石合為一體,從遠處看根本就察覺不到。”(Cather,1931:236)印第安人“無論到那里,從不驚擾任何東西,來去不留痕跡,像水中的游魚,天上的飛鳥”(Cather,1931:236)。他們的生活方式與科利考特對印第安文化的評價相吻合:“傳統的印第安文化象征著一種遺失但未曾忘記的人與自然的和諧。”(Collicot, 1998: 203)在此,凱瑟借印第安人簡樸的生活方式影射現代人生活的物化和非自然性。小說發表于1927年,此時的美國是一個物質文明發達和經濟高速增長的壟斷資本主義社會。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雖迎來經濟現代性的快速發展,卻招致社會異化、實用主義泛濫和工業主義甚囂塵上等現代性的拙劣后果。對此,凱瑟深感厭惡。在小說中,她雖未直接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發展將自然空間徹底地轉化為資本空間的做法,但她把前現代的自然空間視為尚未受商品經濟運作影響的審美對象,使之充滿不可言說的美感,并以此召喚現代人將解放自然看作現代主體通達精神樂園的一種救贖方式。
凱瑟倡導解放自然的審美救贖觀,并不體現為一種無目的懷舊,而是一種包含康德所說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凱瑟的懷舊不是呼喚現代人回到前現代的自然空間,而是將前現代作為反襯現代的一面鏡子,映照現代社會的弊病所在。她的懷舊是建立在對當下現實的否定之上,體現出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相互制衡的權力關系,即為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國家文化與地域文化、技術文化與自然文化甚至全球文化與本土文化之間壓制與反壓制的關系。可以說,凱瑟在《大主教之死》中對印第安人解放自然的審美觀的再現,意在突出現代性的歷史語境之中懷舊與現代、鄉村與城市、地域與國家之間相互博弈而形成的張力,而這種張力正是助推無精神寄托的現代人從孕育印第安文化的地域文明中尋找精神家園的原動力。凱瑟期望通過解放自然產生的審美體驗,修復工具化的文明常規加諸現代人之身的精神創傷,矯正理性主義鉗制現代人的情感表達而造成的人格扭曲,因為審美這一種表意實踐“在恢復被認知——工具理性和道德——實踐理性的表意實踐所‘異化’了的人的精神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潛能”(周憲, 2005:158)。《大主教之死》中解放自然的審美救贖觀是肇始于浪漫主義主張解放自然的理念在現代社會中的延續和升華,也是凱瑟對生活在千篇一律之中的現代人實施詩意救贖的藝術構想。
2恢復藝術“光韻”的審美救贖觀
不同于其他20年代的知識分子公開地對美國文化和社會展開“無情的”“全面的”批判(虞建華,2004:25),凱瑟以一種內省的姿態,撤回到一片安全的主觀文化島嶼,遠離瞬息萬變的客觀文化,辯證地考察現代社會的利弊,尋求對抗社會異化力量的策略。凱瑟和她同時代的作家面臨的現代世界是一個宗教衰落、信仰動搖、傳統凋敝、精神干癟的物化社會。宗教倫理無法指導人們的生活,傳統理念亦不能舒緩現代人焦慮、空虛和懷疑的情緒。那么,人如何在現世找到精神皈依?阿索希娜指出,凱瑟視“藝術為宗教”(Acocella, 2000:12)。在凱瑟看來,藝術能夠代替宗教,通過心無旁騖的審美體驗,輔助現代人重建心靈的烏托邦,兌現啟蒙規劃許諾人們的幸福生活。無獨有偶,在《大主教之死》中,凱瑟渴望用印第安人的藝術“光韻”,照亮異化生活中的灰暗場景,重振死氣沉沉的現代生活,以期解救困囿于社會“鐵籠”中的現代人。
小說中,印第安人的藝術“光韻”擁有田園藝術的和美與宗教藝術的凝重,它煥發出令人膜拜的氣息,不僅能抵制機械復制時代造成藝術的平庸化,還能整合碎片化的現代生活,以及免除現代人被機械化的體系肢解成碎片的危險。本雅明(1999:265)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將“光韻”定義為“一切距離外的獨一無二顯現——無論它有多近”。 作為“獨一無二顯現”,藝術“光韻”具有本真價值和膜拜價值,呈現為有一定距離的、安詳的審美景觀。如果說本雅明認為機械復制時代的來臨消弭了藝術“光韻”,而電影的“震驚”則充滿救贖的力量,那么,凱瑟則在印第安人的藝術中找回了缺失已久的“光韻”。在她的筆下,印第安人將澎湃的藝術激情融入宗教儀式和日常生活,對被文化工業祛魅的藝術進行復魅,使藝術作品散發出獨特的“光韻”。以印第安人的教堂為例,它雖外觀簡陋, 但內部裝飾充滿著色彩艷麗、質地特殊的宗教圣物。小小的祭壇供奉著印第安匠人手工制作的各種圣像,這些木雕圣像并不是機械大生產流水線上喪失個性的粗制濫造品,而是具有本雅明式的“此刻此在性”和“獨特性”的手工藝術品。它們“著色鮮艷,雖因年代久遠而褪色,但還穿著衣服,像玩偶似的。與俄亥俄州傳教教堂里那些工廠生產的石膏圣像相比,這些木圣像更符合神父的脾胃,……都是那么樸實無華”(Cather,1931:26)。這些承載著文化價值和個人情感的藝術品一方面說明印第安人有著虔誠和素樸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表明思想尚未被現代文明整合的族群持有超越世俗的藝術觀。
與印第安人的藝術觀相比,凱瑟所處時代的藝術創作受到市場經濟這只無形大手的操控,現代藝術缺少個性和靈魂,呈現出一片扁平、趨同和碎片化的跡象。凱瑟曾言:“在西部目前流行這樣一種觀念:我們必須和別人相同,好像我們都是同一個模子造出來的。我們穿同款衣服,開同樣品牌的車子,住在同一個街區的同樣風格的房子。這些都太讓人窒息。”(Bohlke,1986:46)凱瑟的言辭,以點帶面,以區域現象輻射國家狀況,不僅將批判的矛頭對準整個美國社會的趨同現象,甚至還前瞻性地預見到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這種趨同化的本土現象向全世界范圍蔓延的態勢。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從眾化傾向暗含著磨平個性、抹除差異的消極力量,助長現代人耽于平庸和狹隘的生活氣焰。凱瑟對機械大生產裹挾下的趨同社會深感痛心,令她更為痛心的是現代藝術被強制地納入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體系而失去自律性。在她看來,《大主教之死》中印第安人的藝術才是人類藝術的本質,更是現代人對抗異化的生存體驗、褪去機械枷鎖的力量之源。因此,凱瑟從遙遠的印第安藝術中重覓一種特有的“光韻”,以其莊重、圣潔、光亮和獨特的氣蘊,使得現代藝術相形見絀,進而彌補了現代藝術被粗糙廉價的機械復制品所過濾的詩意和情感。
印第安人的藝術“光韻”不僅在宗教器物上熠熠生輝,還匯聚在日常生活的物品之上。拉都主教在杰西教父家里看到一只在部落里代代相傳的木鸚鵡。“那是用一塊木料雕制而成的鸚鵡,大小和真鳥完全一樣……這東西非常輕,表面上有著古木那種潔白的天鵝絨似的光澤。雖然幾乎沒有經過雕刻, 而僅僅是磨光成形,卻活脫的像真鳥一樣,可以說是鸚鵡的一只木標本了。”(Cather,1931:86)這只木鸚鵡在印第安部落中世代受人膜拜,體現出印第安人將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觀念。這種觀念與現代人物化的審美體驗形成比對,兩者之間的反差不僅懸置甚至否定了現代人行合趨同的藝術觀,還激起現代人的集體無意識中對藝術“光韻”的再記憶,從而引導人們在日常生活的審美實踐中無功利地鑒賞藝術的顯性形式。小說中,凱瑟沒有直接揭露現代人和現代社會徹底向異化臣服的現象,而是采取懸置的手法,使現代性之隱憂退居幕后,取而代之的是詩意化的敘事以及它所表征的印第安藝術的“光韻”。對她而言,藝術“光韻”猶如耀眼奪目的陽光,穿透一切,照亮萬物,能使現代人忘卻日常生活的瑣碎和掙脫物質欲望的枷鎖,創造出充滿自由的審美情景,從而解決現實生活無法減緩人類精神疾苦的問題。
在《大主教之死》中,凱瑟通過虛擬的藝術世界,塑造了一個充盈著印第安藝術“光韻”的審美場,向現代人呈現了一個機械時代無法復制的藝術殿堂。她對印第安藝術“光韻”的描摹,把現代人帶回素樸的生活場景,使人們反觀物質富庶的現代生活之下隱匿的精神貧困與心理惰性,呼吁人們用藝術來舒展情感和獲得心靈的自由,進而將藝術審美轉化為協助人類擺脫刻板生活桎梏的力量。因此,恢復藝術“光韻”的審美救贖觀告訴我們:知識、進步和理性等啟蒙理念并不能完全祛除塵世的陰暗,而藝術“光韻”具有驅逐生活黑暗的力量,這種力量不僅能避免機械復制時代里藝術淪為商業附屬品的命運,還能助推著人類在幽暗的現代文明中覓得一塊光明的精神凈土。
3 張揚“新感性”的審美救贖觀
現代文明是理性強制管束感性而催生的畸形文明,而現代人的歷史是人存在于其文明中充滿張力的歷史。作為啟蒙現代性的核心價值,理性以效率最大化和計算精密化為最高原則,忽略考慮人性中的感性因素。原本為人所用的理性日趨工具化,演變成令人窒息的異己力量,剝奪人們表達感性情愫的權利,使得人成為理性與感性相互割裂、角色自我與真實自我相互脫離的“單面人”,飽受個性扭曲的痛楚。要修復扭曲的個性,大多數西馬批評家認為,唯有藝術,能勝此責。馬爾庫賽(2001:181)聲稱,“藝術,作為現存文化的一部分,它是肯定的,即依附于這種文化;藝術,作為現存現實的異在,它是一種否定的力量。藝術的歷史可以理解為這種對立的和諧化。”馬氏賦予藝術調和感性與理性相互對立、協調異己現實與理想圖式之間差距的功能,希冀通過藝術作品表達的“新感性”,刷新作為審美主體的人的認知意識,促使人們排遣被日益工具化的理性所鉗制的感性。個體在這種釋放真實情感的過程中,關照自身的本質自由,體味一種由于自我意識得以確證而產生的愉悅,使得愛欲備受壓抑的現代人在此岸找到心靈的棲居地。類似地,在《大主教之死》中,通過前景化印第安人的狂歡化舞蹈和關愛他人的倫理,凱瑟贊揚印第安人的“新感性”特質,鼓勵現代人效仿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表達愛欲的生存理念,恢復人的豐富性。
首先,印第安人狂歡化的宗教舞蹈既是他們表達愛欲的載體,也是管窺這些未沐浴啟蒙之光的人們具有“新感性”特質的窗口。在印第安人眼中,每一個節日都是放松身心、表達情感的世俗節日,也是“宗教激情的偉大復蘇”之時(Cather,1931:119)。每逢大小節氣,印第安人身著盛裝,載歌載舞,僵硬的身體頓時變得生龍活虎,展現出一幅狂歡化的圖景。集體性的狂歡活動是對理性長期壓抑感性的反撥。列斐伏爾提出,狂歡是“對被現代性壓迫得越來越深重的日常生活的解脫,狂歡和節慶突破常規,實現感性、審美和自由的存在,使人們體味非理性的文明和反抗工具理性”(Lefebvre, 1991:47)。小說中,印第安人狂歡化的宗教舞蹈完美地結合人的理性和感性,使人成為符合美的規律的人,這一點與“新感性”意味著“一種新型的人的誕生”遙相呼應(馬爾庫賽,2001:131)。上至耄耋老者,下至婦孺兒童,印第安人皆是“新型的人”的典范。拉都主教親眼看見兩個四五歲的印第安小男孩跳舞,“他們全神貫注地舞蹈,面容嚴肅,巧克力色的眼睛半閉著”(Cather,1931:233)。兩人跳舞的動作,嫻熟流暢,姿態柔美,使人陶醉其中,達到忘乎自我的境界。“他們那兩雙不比三角葉楊樹更大的、穿著鹿皮鞋的小腳,不需要任何口令便能附和著不規則的、古怪的音樂節奏,翩翩起舞”(Cather,1931:233)。他們的舞蹈把被放逐在理性之外的感性情愫和個體活力融為一體,豐富的肢體語言突破了身體的疆界,優美的舞姿成為他們傳遞美感、播撒愛意的方式。他們將這種愛欲散播到對族人、部落、宗教和自然的愛護,以游戲狂歡的姿態向現代人表明:感性領地是一片讓人身心愉悅的場域,是修復人性裂痕的黏合劑。
凱瑟對印第安人的宗教舞蹈的描寫,表達的不是她對孕育印第安文明的地域文化的盲目崇拜,而是呼吁現代人以本土為根基,從地域文化中汲取精神養料,對抗現代性招致的一元化危機。作為美洲大陸的最忠實、最古老的居民,印第安人用他們的智慧為多元化的美洲文明增色不少,他們懂得尊崇自然,順勢而為,善于表露感性。這些本能的天性少見于現代人之身,而他們所剩之物是揮之不盡的人性淡漠、歸屬感喪失和情感的機械化。凱瑟一針見血地指出機器的鐵齒利爪抓破甚至蠶食現代人的生活土壤,對美國人淪為機械奴隸的現象痛下針砭,疾言厲色地講道:“我們用機器聽音樂,我們依靠機器旅行,美國人已經完全被機器淹沒。有時候我甚至在思考,他們是不是借助機器才能哭和笑”(Randall III, 1973:156-157)。現代美國人和整個現代文明被機器合圍,情感表達被機械化,人的感性之維遭受重創。對此,凱瑟既給予批判,又表示擔憂,并發問:現代人應該如何修復感性之維的裂痕?作家通過精彩的地域創作,讓世人看到工具理性霸權和獨尊之外存在著感性和非理性的疆域,并以此敦促現代人像印第安人一樣張揚“新感性”,回歸淹沒于理性之中的感性,實現自我的精神救贖。凱瑟的救贖理念與阿諾德·豪賽爾(1992:55)對現代主義美學的評價一脈相承:現代主義美學“轉向過去和烏托邦,轉向兒童和自然,轉向夢幻和放肆,一言以蔽之,轉向能把他們從失敗中解脫出來的種種要求”。在此,“種種要求”便是重建價值理性、追捧感性生命。因此,在小說中,凱瑟對印第安人的“新感性”特質的描摹是她探索對現代人進行精神救贖的另一種藝術想象。這種藝術想象已經超越某一具體地域的限制,上升為人類追求“真善美”的共性,使得小說文本具有地域文學的“普世價值”(Wyatt, 1990:xviii)。在現代性乃至當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這些“普世價值”正是照亮人們固守精神世界、走向感性與理性和諧共存之路的燈塔。
其次,印第安人的“新感性”不只是在狂歡化的舞蹈中有跡可循,還在日常生活的人際關系中得以展示,體現為關愛倫理向日常生活普及的現象。關愛是憐愛和感動的情愫使然,是一種人的愛欲的體現,它使人克服因自戀而陷入孤獨的傾向,培育人們互愛的美德。小說中,出于憐憫和關愛,拉都主教毫不猶豫地救助瑪格達萊娜,使她擺脫丈夫的蹂躪。瑪格達萊娜從拉都主教和其助手的日常行為中,看到他們靈魂之中的善良和慈悲,因而,她不顧生命危險,在他們遇到困難之時,協助他們虎口脫困。同時,在拉都主教的協助下,瑪格達萊娜在修女院當廚師和管家,重獲新生,臉上露出安詳而美麗的笑容。“似乎在跨過苦難的青春之后,她在天主的家庭里,再次迎來綻放。”(Cather,1931:79)拉都主教和瑪格達萊娜互幫互助的行為是人處于本真狀態下的愛欲使然。人只有回歸本真狀態,才會不計利益得失,人的感性世界才能迸發出久違的愛欲,心靈的激流才能沖破物質枷鎖和逾越派別嫌隙,進而使人的存在符合美的規律。因此,在凱瑟筆下,印第安人身體力行,在日常生活中表達愛欲,他們的行為所詮釋的“新感性”具有振奮萎靡精神的救贖功效。
印第安人的“新感性”特質承載著凱瑟向往詩意生活、唾棄物化情感和修復人性異化的救贖情結,也傾注了她對人的愛欲的肯定。印第安人的愛欲,對于被啟蒙思想洗腦的大多數現代人而言,是原始的、未開化的,甚至是野蠻的。然而,凱瑟沒有附和,卻批駁現代人的感性被機械化、被物化的現象。她深知無法逃脫資本主義社會日趨物化的客觀事實,因而,她選擇回歸和堅守自己的主觀精神陣營,并與自身所處時代的社會保持一定距離,以藝術創作的方式緬懷印第安文明以及孕育它的地域文化。她通過新與舊、現代與前現代之間的比對,反觀和確診現代性的得失,并提供救贖現代人和解決文明病癥的良方。正如阿多諾所指,藝術,抑或文學藝術,只有站在社會的對立面,通過獲得自身的社會性偏離,方可表達對“特定社會的特定否定”(Adorno, 1997: 226)。顯而易見,以《大主教之死》為代表的地域書寫在背離、批判甚至否定主流社會意識形態的同時,還以“新感性”破舊立新的潛能垂范,以期解救社會“鐵籠”中的“單面人”和恢復他們的完整性,這一點無疑是凱瑟的審美救贖思想的人文意義所在。
4結語
凱瑟的地域創作常因采用寫實的敘事手法而被歸為現實主義作品,也因弘揚鄉土倫理和捍衛地域文化而被排斥在主張反叛、講究革新的現代主義文學的主流之外。但《大主教之死》中的審美救贖思想讓讀者看到凱瑟的地域書寫擺脫了“懷舊”“逃避”和“哀挽”等貶義之名,以關注現代性出路的姿態,在現代性危機的浪潮中探求緩解現代人的精神危機和挽救現代文明的方案。凱瑟以超人的姿態捍衛人的精神生活,并在《大主教之死》中勾勒出印第安人解放自然的審美意境,頌揚他們煥發“光韻”的藝術和“新感性”特質,重構了被現代文明壓抑甚至剝奪的感性世界。這些思想承載的審美救贖觀,正好與黑格爾倡導藝術的解放力量和韋伯堅持藝術的“世俗救贖”功能,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它們的共通之處在于:藝術帶來的審美體驗不僅能修葺被工業社會擠破的感性碎片,平衡理性與感性的天平,還能實現人與自然、社會的均衡發展,從而糾正啟蒙現代性一味追求理性而招致的文明“綜合征”。從這一意義上講,凱瑟的地域寫作從19世紀末期美國鄉土小說專注于表達傳統性、地方性和本土性的創作范式中脫穎而出,上升為兼具現代性、國家性和全球性的社會政治批判文本。正如評論家雷諾茲所言,凱瑟是一位“積極介入政治的作家,她的作品與自身所處時代的知識、政治和社會的各種辯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Reynolds, 1996: v)。直至今日,在消費主義盛行和同一性思維邏輯向全球蔓延的大背景之下,凱瑟在《大主教之死》中傳達的審美救贖思想無疑是給精神物化和缺乏歸宿感的人們指引了一條通往精神世界的康莊大道。
參考文獻:
Acocella, Joan.2000.WillaCatherandHerCritic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Adorno, Theodore W. 1997.AestheticTheory[M]. Trans. Robert Hullot-Kentor.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Ltd.
Bloom, Harold. 1985.ModernCriticalViews:WillaCather[G].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Bohlke, L. Brent.1986.WillaCatherinPerson:Interviews,Speeches,andLetters[G].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Callicot, J. Baird.1998. InDefenseoftheLandEthic[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Cather, Willa.1931.DeathComesfortheArchbishop, 2ndedition [M].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Dorman, Robert L. 1993.TheRevoltofProvinces:TheRegionalistMovementinAmerica, 1920-1945 [M].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Eysteinsson, Astradur.1990.TheConceptofModernism[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Fisher-Worth, Ann W.1990. Dispossession and Redemption in the Novels of Cather [G]. Susan J. Rosowski.CatherStudies,Vol. 1.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36-54.
Lefebvre, Henri.1991.CritiqueofEverydayLife,Volume.I[M] Trans. Michel Trebitsh. London: Verso.
Randall III, John H.1973.TheLandscapeandtheLookingClass:WillaCather’sSearchforValue[M].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Inc.
Reynolds, Guy.1996.WillaCatherinContext[M].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Spindler, Michael. 1983.AmericanLiteratureandSocialChange[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Weber, Max.1946.FromMaxWeber:EssaysinSociology[M]. Ed. and Trans.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odress, James Leslies.1987.WillaCather:ALiteraryLife[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Wyatt, David. 1990.TheFallintoEden:LandscapeandImaginationinCaliforni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瓦爾特·本雅明.1999. 經驗與貧乏[M].王炳軍,楊勁,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阿諾德·豪賽爾.1992.藝術史的哲學[M].陳超南,劉天華,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伊曼努爾·康德.1964.判斷力批判(上)[M].宗白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赫伯特·馬爾庫賽.2001.審美之維[M].李小兵,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赫伯特·馬爾庫賽.2008.愛欲與文明[M].黃勇,薛民,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虞建華.2004.美國文學的第二次繁榮——二三十年代的美國文化思潮和文學表達[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周憲.2005.審美現代性批判[M]. 北京:商務印書館.
責任編校:肖誼
The Power of Redemption: Aesthetic Redemption inDeathComesfortheArchbishop
ZHANGJianran
Abstract:In her regional novel Death Comes for the Archbishop, Willa Cather, by means of representing Native Indians’ concept of liberating nature and foregrounding their temperament of “new sensibility” and the “aura” of Indian art, showcases the redemptive power that can cure the malaises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save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and thus thoroughly gives explanatory notes to the function of aesthetic redemption shouldered by literary art. Aesthetic redemption, as Cather’s strategy to dismantle the “iron cage” of capitalist society, aims to redress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engendered by the radical development of Enlightenment modernity and to construct an ideal living mode in which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society, nature and civilization, and sensibility and sense can exist. These artistic conceptions not only offset and counteract the values of Enlightenment modernity, but also serve as the best notes to Cather’s pursuit for the plan to save modernity in the imaginary world. And they hereby attest that her regional writing, with a writing stance that transcends such binaries as the traditional/ the modern, the regional/the national, and the local/the global, engages with social realities and makes introspections on the outlet for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Willa Cather; Death Comes for Archbishop; aesthetic redemption
作者簡介:張健然,女,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外國語言文學博士后流動站在站博士后,主要從事美國文學研究。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國文學地域主義研究”( 10YJA75219) 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15-12-25
中圖分類號:I712.07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6414(2016)02-0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