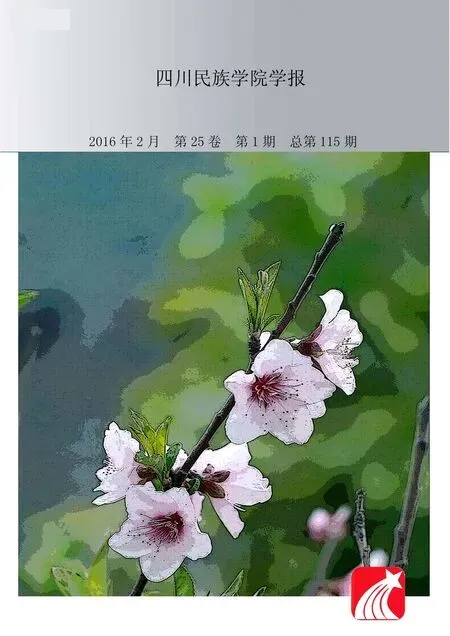19世紀下半葉康藏天主教士的天花接種與藏文編篡
趙艾東
?
★康藏研究★
19世紀下半葉康藏天主教士的天花接種與藏文編篡
趙艾東
【摘要】19世紀下半葉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天主教士出于宣教目的及對康藏自然與社會環(huán)境的適應,在康藏地區(qū)開展了天花人痘接種并邊學藏語邊編撰了《藏文-拉丁文-法文詞典》、藏文圣歌譜本等書籍。前者是對康藏地區(qū)衛(wèi)生防疫的最早貢獻,后者在客觀上促進了康藏地區(qū)的文化互動。這就為我們研究近代康藏史與康藏地區(qū)的文化互動提供了新的史料和視角。
【關鍵詞 】康藏;天主教士;天花;人痘;藏文
The Practice of Inoculation and the Compiling of Tibetan Books by the Catholic Missionaries in Eastern Tibet & Kham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Zhao Aidong
【Abstract】The M. E. P. Missionaries practiced the inoculation against smallpox and compiled Dictionnaire Tibétain-Latin-Fran?ais, Chants Religieux Tibétains and other Tibetan books while learning the Tibetan language in Kham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Although they did these for the purposes of evangelism and their adaptation to the local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they had made an early contribution to local sanitation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promoted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ern Tibet to a certain extent. Their activities offer us with fresh source materials and perspectives for the studies of modern Tibetan history of Khams and of local cultural interaction.
【Key words】Eastern Tibet & Khams; Catholic missionaries; smallpox; inoculation; the Tibetan language
近代最早進入康藏地區(qū)的西方人是法國天主教士,其活動始于1846年。至19世紀末,長期生活在康藏的西方人主要是巴黎外方傳教會(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 M. E. P., 1659年成立于巴黎)的天主教士。基督新教傳教士1897年始在康藏打箭爐設傳教點。因而,天主教士是該時期康藏百姓接觸的主要西方人。國內(nèi)有關康藏天主教士教案的史料和研究頗為豐富,而有關其醫(yī)療和編著等活動的研究甚少,主要有胡曉、[1]潘小松[2]、孫晨薈[3]等學者的論著。文章主要據(jù)檔案、論著等史料,探討19世紀下半葉在康藏處于困境中的天主教士為開拓其活動和適應康藏地區(qū),在天花接種與藏文編譯、編著等方面的活動及其與康藏社會的互動和影響。這一探討對全面、深入地研究近代西方人在康藏的活動和康藏史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一、19世紀下半葉天主教士在康藏地區(qū)的困境
19世紀下半葉,天主教士在康藏活動的范圍主要在云南茨菇、阿墩子(今德欽)、維西、察瓦博木噶、江卡和鹽井(今芒康)、察木多(今昌都)、巴塘、瀘定等地。天主教士在康藏面臨的極大困難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極為艱苦的生活和自然條件。1889-1890年英國博物學家普拉特(A. E. Pratt)兩次在打箭爐(康定)的考察,親眼目睹了主教畢天榮等四位神父的艱苦生活,指出所有天主教士“除住房比當?shù)厝苏麧嵑蜕院猛狻保罘绞脚c當?shù)貪h藏居民無差異。[4]他們也常常遭受疾病和時疫的困擾,部分人病死于康藏或因病離開康藏后身體逐漸衰弱而病逝。譬如,第一個進入康藏的巴黎外方會傳教士羅啟楨(Charles R. A. Renou)1863年病逝于江卡,是在康藏去世的第一個傳教士*20世紀初美國傳教士在江卡發(fā)現(xiàn)并拍攝下了羅啟楨的墳墓,照片參見:Aidong Zhao(趙艾東)and Xiaoling Zhu(朱曉陵), Far, 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 The Story of the American Doctor Albert Shelton and His Colleagues from the Disciples of Christ 1903-1950, St. Louis, USA: Lucas Park Books, 2014。。肖法日(Jean C. Fage)1854入藏,1888年死于云南。杜多明(Jacques Thomine-Desmazures)在康藏年邁多病,只得返回漢地,后于1869年去世。古特爾(Jean Baptiste Goutelle 于1895年病逝于維西。畢天祥(César Alexandre Biet) 在康藏患病后前往香港療養(yǎng),于1891年病逝。吳依容(Jean B. Houillon)1869年因病返法。丁碩臥(又名丁德安Joseph M. Chauveau)1865年底抵達打箭爐任主教,1877年底病逝于當?shù)亍:伟?Louis P. Carreau)1883年去世于打箭爐。白義思(Marie B. A. Couroux)1894年病死于鹽井。[5]
二是康藏部分人群的敵視。該時期天主教士與地方常有摩擦,其活動也常受社會各方監(jiān)視,*譬如,參見西藏自治區(qū)檔案館檔案“芒康頭人就一名外國人在巴塘地區(qū)定居并放債要百姓用小孩、土地、房屋抵債等情給三大寺的呈文(1件)”、“巴塘土司關于正在奏令繼續(xù)阻止外國人進藏,但因法國人持有皇帝的路照,故無法阻擋事給達賴的報告(1張)”。所發(fā)生的數(shù)次教案也集中針對天主教士。最為典型的是發(fā)生在巴塘的四次教案:1873年(同治12年)巴塘地區(qū)僧、眾驅(qū)逐全部教士,搗毀巴塘、鹽井、莽里三處教堂;1879年(光緒5年)奧地利攝政義伯爵等試圖入藏游歷,西藏官、民、僧俗等各方興兵入巴塘阻游,退兵途中損毀莽里教堂;1881年(光緒7年)巴塘城內(nèi)教堂司鐸梅玉林(Jean B. H. Brieux)押貨赴鹽井,在巴塘附近被劫匪殺害;1887年(光緒13年)發(fā)生的教案持續(xù)60余日,巴塘、鹽井、亞海貢三處教堂被搗毀,教士教民被逐盡,教方財物田土被分占,教墳被砸棺沉尸,教案波及云南茨中、阿墩子教堂*四次教案詳見劉傳英. 巴塘藏族反教衛(wèi)國斗爭史略[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劉傳英.巴塘反洋教斗爭論綱[J].康定民族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87年,00期。。[6]此外,1865年呂項(Pierre M. G. Durand)在秋那桶教案中逃往,途中受傷,隨后墜江而亡等。[7]
三是所處藏語困境。康藏腹地絕大部分居民為藏民,天主教士無論是要立足、開展宣教活動,還是要與地方官員、百姓打交道,都離不開藏語。因此,通曉藏語成為他們在康藏腹地活動的必要條件,而藏語學習又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
總之,在上述困境中,天主教士出于在開拓傳教事業(yè)的動機和目的,極力適應康藏的自然與社會環(huán)境。他們在天花接種與藏學學習、編譯方面尤為突出地體現(xiàn)了對康藏的適應及與地方社會的互動。
二、天花“人痘接種”法的引入和實施
天主教士是最早將天花“人痘接種”法引入康藏的外界人士。此法挽救了一些康藏百姓的生命。從中國的天花疫苗接種史看,19世紀初,西方人將牛痘接種傳入廣東,1828年將其帶往北方和北京。1861年上海引進了牛痘。19世紀后半葉,牛痘雖逐漸在中國各個階層和地區(qū)使用,但因西藏地理位置偏僻并抵制西方人進入,故19世紀牛痘對西藏產(chǎn)生的影響極少。在這一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天主教士將牛痘接種法出現(xiàn)之前東、西方都曾使用過的古老的“人痘接種法”或“天花接種法”引入了康藏。就中國言,相傳11世紀宋真宗時此法便傳于世,16世紀明朝時對此法有明確的記錄;而據(jù)清朝記錄,有四種不同形式的人痘法,其中有兩種易于實施的辦法是:“以痘痂屑乾吹入鼻中種之者,曰旱苗;以痘痂調(diào)濕,先蘸棉花納入鼻內(nèi)者,曰水苗。”[8](楊宜編著,《急性傳染病學》 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1955年,第258頁。) 據(jù)西方學者的研究,“人痘接種”(inoculation)或“天花人痘”法,作為一種經(jīng)驗性辦法,18世紀在土耳其也很普遍,即是在人體中“引入微量的天花病菌使其免于感染上自然界存在的可能致命或致殘的病菌”,“基本技術是從病人身上的天花膿包中提取膿液……再把膿液浸入線團,然后把線團插入淺表切”, 通過感染輕微的天花并康復來獲得終身免疫。18世紀的歐洲,天花取代了鼠疫成為當時“最普遍和最令人恐怖的致命疾病”, 1721年土耳其駐英國大使的夫人將人痘接種法引入英國,此法迅速流傳開來,隨后逐漸流傳到法國、荷蘭、德國和瑞典等西歐國家*參見耶魯大學公開課《1600年以來西方社會的流行病》 視頻,講師:Frank Snowden,“天花(二):接種與治療”, http://mov.bn.netease.com/movieMP4/2012/6/0/3/S831BR603.mp4。。歸結起來,“人痘接種法”即是把病癒者身上脫出的乾痂研成粉末,吹到接種者的鼻孔內(nèi)或進行皮膚下的接種。在疫苗昂貴且不易獲得、難以自制的19世紀下半葉康藏地區(qū),天主教士采用天花病毒接種的古法不僅挽救了一些百姓的生命,也為其傳教活動打開了一定的局面。
據(jù)載,1875年主教丁碩臥曾委派畢天祥(César Biet)到巴塘開展慈善活動,為藏民種人痘。[9]1880年鹽井和巴塘爆發(fā)天花瘟疫期間,倪德隆不僅救治了幾名天花患者并使其康復,還為當?shù)貎和M行了天花接種。同時期,在天花“極為猖獗”的茨菇一帶,天主教士在當?shù)孛癖娦哪恐兴粝碌摹白顬樯羁痰挠∠蟆奔词钱吿煜楹陀嗖稀皩嵤┎@得巨大成功”的人痘接種。天主教士給教徒們進行了“接種感染”后,并對其進行精心的醫(yī)治和護理,竟然無一人死亡。此事立即產(chǎn)生了轟動的社會效應,法國探險家巴達讓對此記述道:“這件事震動了附近的異教徒,他們跑來懇求給予同樣的恩典,并保證服從治療。將近800多項病例,沒有一個被接種的人死亡。事實證明,歐洲的這種醫(yī)療方法,大大優(yōu)勝于只能勉強拯救一半病人的漢族或藏族的醫(yī)療方法。”[10]其后,1906-1911年趙爾豐在川邊實施改土歸流時,從內(nèi)地引入中醫(yī)和牛痘接種。民國初期,川邊政局動蕩,時疫流行,政府無防疫措施。美國醫(yī)生史德文在巴塘面對天花的肆虐,發(fā)現(xiàn)從華東沿海購買疫苗不僅耗時長且昂貴。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經(jīng)反復試驗,最終于1915年成功地研制出了天花疫苗。[11]從康藏地區(qū)防治天花這一歷史過程可見,天主教士將“牛痘接種”(或疫苗接種)法產(chǎn)生之前的人痘法引入藏區(qū),它雖有一定局限性,如會將天花傳染給他人,大約有2%的死亡率等,但在天花盛行之時,天主教士用此法成功地挽救了數(shù)地康藏百姓的生命,是對康藏地區(qū)衛(wèi)生防疫的最早貢獻。
三、天主教士的藏語學習及對《藏文-拉丁文-法文詞典》的編撰
天主教士一邊學習藏語,一邊編撰詞典。據(jù)當代學者潘小松對其擁有的一本珍稀詞典的介紹并參考其它文獻,我們了解到:《藏文-拉丁文-法文詞典》(Dictionnaire Tibétain-Latin-Fran?ais)是19中后期康藏地區(qū)四位天主教士編纂的詞典,1899年由巴黎外方傳教會設在香港的拿撒肋會所(Hongkong: Imprimerie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Etrangères, 1883-1953)出版。編寫的初因是學習藏語所需。1852年學習藏文不足一年的羅啟楨開始編寫該詞典,邊學邊纂。[12]1856年肖法日與其曾入察木多。1859年兩人獲得匈牙利現(xiàn)代藏學創(chuàng)立者克勒希· 喬瑪· 山道爾(Koros Csoma Sandor)編纂的一本藏文詞典。[13]兩人將其與自己所編寫的字典對堪后,認為他們正在編寫的字典仍有價值,于是繼續(xù)編纂,直至1863年羅啟禎病故。1862-1863年肖法日繼承羅氏未竟之業(yè),將苦心搜羅來的藏文詞典的手稿合為一冊。1880年戴高丹(Auguste Desgodins)抵達印度,1883年到巴塘傳教點時,蕭法日的手稿便匯集在其手中了。戴高丹不斷增補、修訂內(nèi)容,并將手稿帶往香港。1894-1899年他在拿撒肋會所花了5年時間幫助排印了這部四位傳教士的心血結晶,詞典正文厚達1087頁。潘小松認為這部詞典是三位天主教士花費了10余年心血的結果。[2]據(jù)該書的出版信息,我們發(fā)現(xiàn)還有一名編者,排名第四位,即是主教倪德隆(Pierre Philippe Giraudeau)。
《藏文-拉丁文-法文詞典》的編篡和出版過程不僅是天主教士歷時數(shù)年、努力學習藏語和適應康藏文化與社會的過程,也是藏語、法語、拉丁語三種語言之間直接交流、溝通的過程。該詞典為后來的天主教士以及西方人學習藏語提供了極大幫助。
四、四線譜藏文圣歌譜本Chants Religieux Thibétains的出版
《雪域圣詠:滇藏川交界地區(qū)天主教禮儀音樂研究》[3]一書作者孫晨薈女士在滇藏川交界地區(qū)的調(diào)研中獲得一本四線譜藏文圣歌譜本Chants Religieux Thibétains原書。該譜本1894年出版于法國Oberthur-Rennes出版社,在藏區(qū)流傳至今。在其調(diào)查得來的信息與研究基礎上,我們對該普本有以下進一步的認識:
(一)對該藏文圣歌譜本的進一步考證
首先,我們進一步發(fā)現(xiàn),歌譜很可能原屬康定教堂。理由有二:
一是關于譜本是如何被保存下來的問題,孫氏在調(diào)研中聽到兩種說法。說法一:“鹽井(天主教會)會長說,文革時期剩余的譜本被康定教堂的負責人裝箱,埋入地下逃過一劫。待宗教政策落實后,被全數(shù)運送至西藏鹽井天主堂”。[3]說法二:“康定的神父卻說,文革期間被沒收的天主教物品堆在康定縣文化館內(nèi)。由于無人能懂,館負責人就將存下的部分送還康定天主堂。其中就有一批藏文圣歌譜本,80年代西藏鹽井教堂神父祝圣時,這批歌譜連同其他的藏文天主教資料,被送給鹽井教堂,供藏族教徒使用。”[3]我們發(fā)現(xiàn),在兩種說法中,關于這批歌譜之所以被送往鹽井天主堂的原因不一致,但都肯定了一個共同的事實,即在文革之前,這批歌譜是屬于康定教堂的物品。
二是其它史實可以印證。孫氏指出:“凡天主教出版之書籍,必須獲得該教區(qū)的主教準許印刷權。”歌譜封里的文字信息表明該譜本的出版“獲得了西藏宗座代牧區(qū)畢天榮主教的準印”。[3]據(jù)此信息和規(guī)定可以推斷:藏文圣歌譜本主要是因主教畢天榮所轄西藏宗座代牧區(qū)的教堂所需而出版的,因此畢主教所駐打箭爐(康定)必然是歌譜的主要存放地,這點也可與上述兩種說法中都認定的歌譜原屬康定教堂物品的事實互為印證。現(xiàn)存寥寥無幾的歌譜在不同教堂的分布也大致印證了這點:現(xiàn)存于世的歌譜中,“云南貢山縣天主教會有一本,丙中洛鄉(xiāng)各教堂的老教徒有數(shù)本,云南茨中教堂片區(qū)的老教徒有幾本。西藏鹽井教堂擁有的數(shù)量最多,但總共不過百本”。[3]孫氏在調(diào)研中還發(fā)現(xiàn)了該譜本的手抄體,所用字體是康定地區(qū)流傳的藏文小楷體。這一發(fā)現(xiàn)也為圣歌譜本主要在以歷史上康定為中心的康藏地區(qū)使用和流傳的推斷提供了佐證。[3]
其次,譜本與編寫上述《藏文-拉丁文-法文詞典》詞典的天主教士當有聯(lián)系。歌譜全書共22首藏文圣歌,100余頁,使用三種語言編寫。孫氏指出:“封皮封里標注法文,每首圣歌的標題為拉丁文和法文兩種,樂譜為四線紐姆譜,歌詞是拼音式藏文”。[3]其所說“歌詞是拼音式藏文”,實際上就是用拉丁文轉(zhuǎn)寫的藏文文字。據(jù)上述“歌譜原屬康定教堂”和畢主教準印兩個史實,以及1899年四位天主教士編寫的《藏文-拉丁文-法文詞典》在香港出版的史實,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1894年出版的匯集藏文、拉丁文、法文三種語言的圣歌譜本與編寫詞典的天主教士們當有聯(lián)系:首先,他們都必須通曉拉丁文;其次,要么是同一些天主教士翻譯了歌譜,要么歌譜是在通曉藏文、拉丁文、法文三種語言的天主教士的協(xié)助下完成的翻譯。此外,如果進一步將歌譜置于該時期天主教士在康藏地區(qū)的活動史中考察,就可發(fā)現(xiàn),這本歌譜的形成與《藏文-拉丁文-法文詞典》的完成是在同一時期,也就是說,它們都是康藏地區(qū)天主教士長期堅持學習藏文的成果,是邊學藏語邊翻譯的成果。這就共同反映了一個史實:19世紀下半葉,康藏地區(qū)的天主教士為了打開在藏民中傳教的局面,下了很大功夫?qū)W習藏語,且將學、用結合起來,邊學邊用,遂有上述詞典和歌譜的形成和出版。
最后,關于藏文圣歌譜本的作者。孫氏根據(jù)調(diào)研中當?shù)啬昀咸熘鹘掏降幕貞洠赋鲋饕髡呤俏樵S中神父(Jean Baptiste Ouvrard),另一作者是古純?nèi)?Francis Goré)。我們發(fā)現(xiàn),譜本于1894年在法國出版,而據(jù)巴黎外方傳教會檔案,伍許中 1906年從法國啟程赴藏,在打箭爐學習漢語后被派駐瀘定冷磧,后在打箭爐負責修建真元堂的主體建筑圣心堂,新教堂于1912年開放;[14]1908年升任西藏教區(qū)副主教兼云南鐸區(qū)總司鐸,曾駐沙壩、云南茨中等地。[15]而古純?nèi)视?907年才進入康藏。[16]二人的入藏時間比譜本的出版時間至少晚十二年。孫氏也指出無其它史料可同時證明歌譜為此二人所寫。因此,在上述三點考證的基礎上,又據(jù)伍許中、古純?nèi)嗜氩貢r間比歌譜出版的時間晚的史實,我們認為,孫氏稱伍、許二人是歌譜作者的論斷很難成立。[3]作者究竟是誰尚需進一步考證。
(二)從藏文圣歌譜本看天主教士與康藏文化的互動
經(jīng)孫女士考證,該圣歌普本中90%的內(nèi)容是傳統(tǒng)的拉丁素歌,即“格里高利圣詠”。它產(chǎn)生于羅馬,又稱羅馬教會圣詠。作為羅馬教會的宗教禮拜儀式音樂,它主要運用于彌撒和日課等禮拜活動,9世紀已在歐洲被廣泛吟唱,是“西歐中世紀重要精神文化財富之一”和“西方文化傳統(tǒng)的象征”;以其為代表的早期基督教音樂是西方音樂的主要源頭。[17]為展示譜本所反映的康藏地區(qū)天主教禮儀的施行情況,在此將孫氏整理和翻譯的22首圣歌的中文目錄列于下表:

1894年出版的藏文圣歌譜本22首圣歌的中文目錄 [3]
按用途分類,圣歌包括固定彌撒經(jīng)文、專用彌撒經(jīng)文(如葬禮)、圣體降福經(jīng)文及圣歌、節(jié)期歌曲。按內(nèi)容分類,圣歌包括耶穌圣誕、耶穌復活、耶穌圣體、耶穌圣心、耶穌圣名、圣母、圣若瑟、圣神、末日審判、悔罪與潔凈、贊美。從音樂風格看,其中有三首接近中國音樂風格。可見所收錄的圣歌涵蓋了天主教禮儀的基本層面和活動,并在所選圣歌的音樂風格上注意了文化的適應。總之,孫女士發(fā)掘的這本珍稀文獻和在藏民中的實地調(diào)研及相關研究,為我們見證了19世紀下半葉早期入藏的天主教士在康藏的文化適應。該歌譜從在康藏地區(qū)的形成到在法國的出版并被帶回藏區(qū),再到在康藏各教堂禮儀中的使用以及長時間、廣泛地流傳的史實同樣見證了該地區(qū)的文化互動。從學術研究來看,該藏文圣歌譜本因“使用拉丁文、法文、藏文三種文字與四線譜搭配,此類型的樂譜存世僅此一種”,故有很高的文化和史料價值。[3]
結語
19世紀下半葉,在英、法、美等西方列強在中國進行擴張的時代背景下,天主教士作為早期入藏的西方人和傳教士,在天花防疫、藏文編著等方面有一定貢獻,雖其活動是出于宣教與適應當?shù)氐哪康模诳陀^上促進了文化的互動與交流,并對當?shù)夭孛竦男l(wèi)生防疫有過積極的影響。除上述藏文編著、編譯外,19世紀后期康藏天主教士陸續(xù)編撰了其它一些藏文書籍,如將拉丁文天主教經(jīng)典翻譯成藏語,1897年由巴黎外方傳教會香港區(qū)(拿撒肋會所)出版了《十四處苦路經(jīng)》。[3]戴高丹還撰寫了一本《藏語文法論集:口語與字母及其發(fā)音》,1899年也由巴黎外方傳教會在香港出版。[18]因此該時期康藏天主教士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藏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橋梁、醫(yī)療技術的傳播者,這與以往我們在教案研究中所見天主教士的形象與角色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參考文獻
[1]胡曉. 法國傳教士倪德隆在四川藏區(qū)活動考述[J].宗教學研究,2011年第2期, p165-170
[2]潘小松. 1899年香港印<藏文拉丁文法文詞典>[J].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11年3月10日副刊“后海”
[3]孫晨薈. 雪域圣詠:滇藏川交界地區(qū)天主教禮儀音樂研究[M].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0年,p207、p210、p208、p289、p210-211、p223-224、p224-225、p216、p217
[4]Antwerp E. Pratt. To the Snows of Tibet through China,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2, p135
[5]趙艾東. 1919年前傳教士在中國康藏地區(qū)的活動[A].(香港浸會大學等聯(lián)辦第七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區(qū)域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區(qū)域景觀下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C].香港: 建道神學院出版部,2013年,p573-592
[6]劉傳英. 巴塘藏族反教衛(wèi)國斗爭史略[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7]巴黎外方傳教會檔案:http://archives.mepasie.org/notices/notices-biographiques/durand, http://archives.mepasie.org/annales-des-missions-etrangeres/la-mission-du-thibet
[8]楊宜編著. 急性傳染病學[M].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1955年,p258
[9]巴黎外方傳教會檔案:http://archives.mepasie.org/notices/notices-necrologiques/biet-1836-1891
[10]弗朗索瓦·巴達讓著(法),郭素芹著譯. 永不磨滅的風景: 香格里拉——百年前一個法囯探險家的回憶[M].昆明:云南出版社,2001年,p46
[11] 趙艾東、洪泉湖. 美國傳教士史德文在巴塘的活動及與康藏社會的互動[A].藏學學刊第7輯[C].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2年,p182
[12]Auguste Desgodins, Charles Renou, Jean-Charles Fage, P. Giraudeau. Dictionnaire Tibétain-Latin-Fran?ais: par les Missionaires du Thibet. Hong Kong: Imprimerie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1899
[13]Gabriel Bonvalot, Translated by C.R. Pitman, Across Thibet. New York: Cassell, 1892, p.393
[14]巴黎外方傳教會檔案:http://archives.mepasie.org/notices/notices-biographiques/ouvrard-1
[15]韓軍學、劉鼎寅.云南天主教史[M].p362
[16]巴黎外方傳教會檔案:http://archives.mepasie.org/notices/notices-biographiques/gore
[17] 劉紅梅.早期格里高利圣詠研究[D].濟南:山東師范大學,2005年,p7、p21、p69
[18] Auguste Desgodins, Essai de grammaire Thibétaine: pour le langage parlé avec alphabet et prononciation. Hongkong: Imprimerie de Nazareth, 1899
[責任編輯:林俊華]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大型藏區(qū)地方史《康藏史》編纂與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0&ZD110;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世紀上半葉中西文化互動下的川藏地區(qū)巴塘社會變遷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4BZS091。)
作者簡介:趙艾東,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碩導,歷史學博士,國際中國文化研究學會、東亞文化交涉學會會員。(四川成都,郵編:610064)
【中圖分類號】B97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8824(2016)01-0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