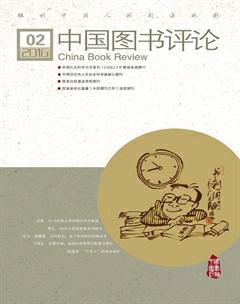2015年思想類圖書關鍵詞
傅正
資本的內部與外部:當代激進理論之爭
《正常與病態》,[法]喬治·康吉萊姆著,李春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
《斯賓諾莎與政治》,[法]艾蒂安·巴利巴爾著,趙文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
《例外狀態》,[意]吉奧喬·阿甘本著,薛熙平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
《大同世界》,[美]邁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里著,王行坤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
福柯在給法國哲學家喬治·康吉萊姆的著作《正常與病態》的英文版寫的導言中,曾指認了法國哲學的兩條脈絡。第一條是“經驗、感覺和主體的哲學”,另一條是“知識、理性和概念的哲學”。“一邊是薩特和梅洛-龐蒂的傳統;而另一邊是卡瓦耶斯(Cavailles)、巴什拉和康吉萊姆的傳統。”(第262頁)前者源自于亞歷山大·科耶夫,早為中國人所熟知;后者則一直在前者的光芒之下顯得門庭冷落。然而,正是后者誕生了阿爾都塞、福柯、布迪厄、巴里巴爾等一大批影響國際左翼理論界的重要思想家。不同于前者高舉主體性大旗,后者恰恰是去主體化的。這意味著這些思想家不僅排斥康德、費希特的啟蒙主義個體哲學,也排斥黑格爾意義上的實體主體,即歷史目的論。在他們看來,歷史并不是一個不斷實現自己目的的過程。它是概念更替的結果,沒有起點也沒有目的。康吉萊姆以這種思維解釋了生命科學的發展。對我們而言,更重要的是,這種思維方式實際上變革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
按照《共產黨宣言》的經典定義:“資產階級是自己的掘墓人。”資本主義創造自身的同時,也創造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后者完全是從前者那里內生出來的。資產階級也不過就是歷史實現自身目的,即共產主義的工具。可按照法國概念哲學的理解,反抗資本主義的力量顯然不能從資本內部自發地生成,新社會與舊社會是斷裂的關系,二者沒有內在的連續性。如果事情真是這樣,那么我們又該如何去重新解釋馬克思主義?
阿爾都塞提出“過度決定”(overdetermination,又譯“多元決定”)是要說明,馬克思的辯證法完全不同于黑格爾目的論式的辯證法。在他晚年劃定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義譜系中,絲毫看不見目的論的影子。為了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反目的論傾向,阿爾都塞繞過了德國觀念論哲學,直接把馬克思與斯賓諾莎勾連了起來。而新近翻譯出版的巴利巴爾的《斯賓諾莎與政治》,正是對其師阿爾都塞這一創見的發揮。
巴利巴爾指出:“在斯賓諾莎看來,自然也是歷史:一種沒有目的的歷史,實際上這種歷史只能是一個過程,一種變化的運動(也就是說,不存在什么被‘擔保的特定變化)。”(第198頁)我們要問,這種去主體化、去目的論的思想對于政治意味著什么?
很顯然,國家不是世界精神自我實現的工具(如黑格爾認為的那樣)。非要說國家具有什么目的性,那也只能說國家的目的只是它自身的公共安全。公共安全,這是霍布斯的核心命題。在霍布斯那里,國家是自然人通過契約締結而成的,主權者的權力來自于各個自然人讓渡出來的自然權利的總和。這就意味著各個公民的私人權利與公權力(法律)之間存在著一種二元對立的關系:公權力越大,私人權利越小。換言之,個人權利是法律不禁止的那種利益。
然而,霍布斯終究給人們留下了兩種看似相悖,實際互為表里的后果:一方面,他許諾了一種事實上并不存在的先驗的個體權利;另一方面,他又預設了一個超越于個人自由的抑制性的主權權力。主權權力是不可分割的,這一總體性的主權權力的實現,恰恰是排斥個人的結果。
在斯賓諾莎那里,這種公私之間的二元對立不復存在了,國家的整體性與個人自由具有同一性。巴利巴爾看到,斯賓諾莎很明確地拒斥了兩種古典權利觀:一種是像霍布斯那樣,把權利視為法律許可的那種自由,即“客觀權利”;另一種則是像后來的康德、費希特那樣,把權利視為普遍的自由意志,即“主觀權利”(第96頁)。此二者的共同之處在于,都對權利有種形而上學的想象。而在斯賓諾莎那里,權利就是一種政治事實,是個體的現實力量或政治實踐的表現。國家公權力能否實現,取決于各個個體的權利是否能在政治運動中形成合力。國家不是超越的形而上學預設,而是建基于現實的群眾運動之中。
巴利巴爾看到,在斯賓諾莎晚年的《政治論》中,存在著一條線索:“主權在物理上越少地被等同于社會中的某一部分(最為極端的情況是只等同于某個個人),越是與全體人民相一致,它就越加穩定和強大。”(第92頁)這豈不是在鼓吹君主專制?須知,在霍布斯那里,主權者的意志是排斥臣民的意志的,而在斯賓諾莎那里,主權者的整體性就意味著所有人都參與到主權權力當中去。所謂的專制,恰恰是對整體性的破壞。“某公民或某公民群體妄言自己比國家更好地知道公共福祉安全最急需者為何,此乃國家敗亡之源。與這一現象并行的是權力的獨斷運用,由此,權威向暴政退化。當君主有借口支配超出其實際力量的力量之時,或當貴族政體下權貴階層變為一個世襲階層之時,這種情況就會發生。”(第105頁)暴政的產生,并不像英美自由主義者認為的那樣,是由于無限的主權權力。恰恰相反,它是源于主權權力的解體。參與主權權力構成的各個公民越接近平等時,亦即一部分公民凌駕于其他公民之上的危險越小,主權權力才越穩固。盡管巴利巴爾沒有明言,但我們分明可以看到,斯賓諾莎的《政治論》與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之間存在著高度的相似性。換言之,巴利巴爾找到了一條貫穿于斯賓諾莎、盧梭和馬克思理論的線索,這就是政治唯物主義。
值得一提的是,斯賓諾莎在提到君主政體時,特意指出:“形形色色的‘絕對君主之下掩藏的是貴族政體,這類政體當中現實的權力歸于一個階層所有。可是,當這個階層(廷臣、貴族們構成的階層)因斗爭的野心而分裂。某個個人位居國家首腦之時,替換掉他也是可以想見的輕而易舉之事。”(第110頁)對君主最大的威脅永遠是貴族,而不是人民,“為了讓君主獲得他最大限度的力量,唯一合理的策略是:廢黜所有合作主義,把審議過程建立在群眾基礎之上,同時保證最終裁斷的完整性不受挑戰”(第111頁)。倘若我們把這里的“君主”替換成葛蘭西的“新君主”,斯賓諾莎豈不正為我們提供了一份左翼運動的策略和圖景嗎?
按照列寧的看法,經濟自發性最多只能產生工聯主義,只有通過先鋒隊組織從外部打斷舊的連續性,才能真正創造新的世界。不管先鋒隊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有何爭議,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都接受了類似的斷裂論。如本雅明就指出,卡爾·施米特的“例外狀態”仍不過是一種常態,真正的例外狀態并不是主權者的決斷,恰恰是對主權權力本身的否定,是對舊歷史的斷裂。
今年出版的阿甘本《例外狀態》一書,是《牲人》(HomoSacer)的姊妹篇。依據本雅明的洞見,阿甘本把“例外狀態”視作主權治理的一個有機部分。任何主權國家都在或多或少地通過宣布“例外狀態”,剝奪一部分人的公民權利,使其成為赤裸生命(bare life)。尤其在今天這個“全球內戰”的時代,例外狀態不僅可以被用于鎮壓反對派,更可以被用于國際反恐戰爭;赤裸生命不只是“猶太人”,更可能是一切被懷疑是“恐怖分子”的人。
然而,事實上真的存在一個超越于資本邏輯之上,僅憑借自己的自由意志就可以任意決斷例外狀態的主權者嗎?另一方面,被剝奪公民身份的“赤裸生命”只能是主權權力任意宰割的對象嗎?更重要的是,左翼學者對于資本主義的批判恰恰是把其看得無所不能。一切罪惡都源自于資本主義,那么解放的力量從何而來?存在超越于全球資本主義的解放力量嗎?
哈特、奈格里的《帝國》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大同世界》,于2015年7月在國內出版。書中,二位作者對各方批評做出了系統的回應。他們指出:“人類絕不是赤裸的,根本不能用赤裸生命(barelife)進行規定,而是有所遮蓋的。人類不僅擁有痛苦的歷史,而且擁有生產的能力和反叛的力量。”“人不可能被剝奪為‘赤裸生命,如果這個詞意味著沒有任何自由反抗的空間和力量的話。”(第42—43頁、第61頁)
在后福特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已經不局限于工廠的四道圍墻之內。遍布全社會的非物質勞動,已經成為了當下資本主義生產的主要方式。“在生命政治的語境下,可以說資本不僅吸納了勞動,而且吸納了作為整體的社會,或者說是社會生命本身,因為生命既是生命政治生產過程的要素,也是其產品。”(第113—114頁)資本主義生產創造了一種共同性(thecommon),如果說在馬克思和列寧的時代,共同性只局限于工廠內部,那么今天資本主義把全社會都凝結起來了。共同性正是諸眾的物質基礎,不是別人,正是資本主義本身創造了它的反對者諸眾。
我們看到,巴利巴爾、阿甘本與哈特、奈格里呈現給我們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思路。前者強調舊世界與新世界的斷裂,強調只有從舊世界外部才能顛覆它;后者則強調帝國與諸眾的連續性,只有在舊世界內部才能真正孕育新世界。應當說,哈特、奈格里與齊澤克、巴利巴爾、阿甘本等人的爭論,仍然是列寧與經濟自發性問題的當代回響。
嚴陣以待的自由主義:英美傳統與中國問題
《歷史的巨鏡》,金觀濤著,法律出版社,2015年
《自由的基因:我們現代世界的由來》,[英]丹尼爾·漢南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
《民主的歷史》,許良英、王來棣著,法律出版社,2015年
2015年7月,金觀濤先生《歷史的巨鏡》一書出版。所謂“歷史的巨鏡”,顧名思義,是要以西方現代化的歷史經驗為鏡,反照中國當下。本書分為“探索現代社會的起源”和“西方社會結構的演變”兩部分。
其中,第二部分“西方社會結構的演變”在1985年就以專著的形式出版過。通常認為,英國的現代化道路是生產力或其他經濟因素的結果。然而在該部分的“序言”中,作者反駁了這種觀點。例如把英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視為圈地運動的結果,但圈地面積只占總土地面積的2%—6%;又如17世紀以前,英國的商品經濟發展程度絲毫不比法、德兩國高,更遠遠低于中國。何以英國會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龍頭,而不是經濟發展程度最高的中國?
現代資本主義的因素孕育于城市,而非農村之中。作者通過對比西歐社會和中國社會的差異,指出西歐和日本的城市與其封建社會結構是相互排斥的,而中國城市則包容在其封建社會結構中。這意味著,在中國,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結果完全被用來壯大封建勢力;而西方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最終顛覆了封建勢力。然同屬西歐,何以英國,而不是法、德,引領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呢?
作者指出,在英國,國王和封建領主的力量達到了均衡的態勢。當封建領主強勢時,國王就與新興的市民階級聯合起來對抗領主;當國王強勢時,領主就與市民階級聯合起來對抗國王。國王和領主都需要拉攏市民階級,這為市民階級的發展壯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法、德兩國,前者國王勢力太強,后者領主勢力太強,都沒能像英國那樣出現國王—領主—市民階級的三角均衡。簡言之,正是英國的《大憲章》孕育了后來的現代社會。這個觀點在今天看來稀松平常,但在20世紀80年代不可不謂振聾發聵。當然,這一解釋框架也越來越顯露出其缺陷。
20世紀90年代以后,金觀濤先生更多地從文化、意識形態層面解釋其系統論。在金觀濤看來,中國傳統社會大概由天子、職業官僚和地方鄉紳三部分組成。乍看之下,天子的統治依據于卡里司瑪型權威,職業官僚則像法理型統治,地方鄉紳更依據于傳統型權威。而金觀濤則指出,這三部分實際上完全靠儒家大一統和天人感應聯結起來的。任何傳統結構的危機最終都會被歸結為統治者沒有遵循儒家道德或信仰,任何外來文化的沖擊(無論是佛教還是馬列主義)都會被儒家信仰同化。
反之,如金觀濤先生在該書第一部分“探索現代社會的起源”中所述的那樣,西方尤其是英美,在意識形態上與中國大異其趣。它一早就孕育了工具理性、個人權利和立足于個人的民族認同這現代性的三大要素,所以它沒能像中國那樣陷入“超穩定結構”。不用說,中國想要打破超穩定結構,只有掀起真正的啟蒙運動,在社會意識形態上樹立現代價值觀。這種現代價值觀只能來自于西方。對此,我們不禁好奇,西方自由主義者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傳統的呢?
毋庸置疑,1500年以后的世界歷史既是全球化的歷史,也是西方文明主導的歷史。然而,什么是西方文明?新近出版的丹尼爾·漢南《自由的基因》一書,質疑了“西方文明”這一觀念。作者出生于秘魯,成年后回到他的祖國英國并在那里開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拉美和不列顛,這種不同類型的生活經驗讓他深深地感到:“不用說,我喜愛西班牙文化。只是,待在那里越久,我就越難相信‘英語世界和‘西班牙語世界會共屬一個相同的西方文明。”(第5頁)不特“英語世界”和“西班牙語世界”截然不同,“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的所有政治領導人的童年都是在專制中度過的,雅克·希拉克和安格拉·默克爾也是如此。我們忘了,和平的憲法改革在這個世界上何其少,而發生在盎格魯圈以外的更是寥寥無幾。”(第11頁)
所謂的“西方文明”,毋寧說只是盎格魯圈。什么是“盎格魯圈”?說白了,其核心成員只有五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英國和美國。”以這五個國家為核心的盎格魯圈,皆以法治原則、個人自由和民主政府(代議制政府)為其最高的政治準則。盡管僵硬的歐洲大陸或許會在名義上認同這些準則,但是“當歐盟成員國采取集體行動時,這三個原則隨時都會被置于各國的政治需要之下”(第6頁)。作為保守黨黨員的漢南,堅定地反對英國融入歐盟,“當英國向歐盟交出主權的同時,也就相應地放棄了她的民族性中的若干元素”(第389頁)。相反,美國才是真正的兄弟,他甚至認為“美國獨立戰爭”具有“相當的誤導性”,這只不過是“盎格魯圈的第二次內戰”。漢南毫不掩飾:文明是分等級的,即便在西方文明內部,也存在著等級上的不同。盎格魯文明,應該是人類文明的頂端。
許多人認為,法治原則、個人自由和民主政府等原則源于《大憲章》,漢南卻認為,這些原則與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歷史一樣久遠。正如書名提示的那樣,自由民主就是撒克遜民族的DNA,它深深地根植于英國的普通法之中,并通過撒克遜民族的偉大勝利播撒到全世界。世界近現代史就是盎格魯圈的價值觀波及全世界的歷史,《自由的基因》正是在書寫這樣一部歷史。
遺憾的是,當盎格魯圈的準則成為世界的準則時,“英語國家卻正走向相反的方向,朝著大明王朝—蒙古—奧斯曼帝國的道路速奔:大一統,中央集權,高稅率,以及國家控制。毫無疑問,他們正在喪失他們的卓越”(第390頁)。漢南的著述反映了當下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的融合。新自由主義不再那么樂觀,他們開始擔憂傳統的失落,而迫切地要找回這個失落的傳統。不管作者愿不愿意承認,小布什才是自己學說的踐行者。但布什主義的實踐結果又是什么呢?
漢南并不了解“大明王朝”,它并不奉行什么“大一統,中央集權,高稅率,以及國家控制”。試問一個皇權不下縣,地方治理全部有賴于地方紳士的國家,一個于對外戰爭毫無興趣的國家,怎么可能是“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呢?試問一個連鑄造貨幣都不知道而任由墨西哥鷹洋任意流通的國家,一個連工商業稅和關稅都沒有的國家,怎么可能是“高稅率,以及國家控制”呢?小政府和放任主義,這分明是漢南眼中的理想國家才對。而這樣的國家為什么沒能自己走向現代?現代國家真的是靠漢南所說的這些原則實現的嗎?
對中國而言,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是:革命和激進的變革會剝奪個人自由,導致專制;中國卻“沒有自由主義的傳統”,這意味著中國必須激進地以外來的傳統代替自己的傳統,這二者豈不構成悖論?近代中國的問題是太過激進,乃至于剝奪了個人自由和社會秩序,還是太過保守,沒能真正引入英美自由主義傳統?
比如90年代后期列于“公共論叢”的《自由與社群》一書,就同時反映了這兩種聲音。該書以盧梭為箭垛,控訴革命造成專制;又以英美政治觀念為唯一正宗,欣賞伯克等人的保守主義傾向。可中國文化中豈有伯克所守護的那種傳統?這個悖論同樣反映在2015年5月出版的《民主的歷史》之中。
貢斯當曾區分“古代人的自由”和“現代人的自由”。古代人以政治生活為公民最高的生活狀態,自由意味著他們投身于政治生活當中;現代人則以私人空間為自由的原則,只有遠離政治才是自由的。在貢斯當看來,盧梭或雅各賓派的錯誤在于想在現代社會復制古代人的自由。與之相應,亨廷頓在《第三波》中引用了熊彼特的分類,區分了古典民主與程序民主。古典民主需要公民直接參與政治,而程序民主則需要人民把政治權力委托給一小部分人。用中國學者的習慣術語,古代人奉行直接民主,現代社會則需要間接民主。
《民主的歷史》分為兩編,第一編就寫西方“直接民主”向“間接民主”轉變的歷史。第二編寫的是“民主在中國的傳播”。作者許良英、王來棣劈頭就說“中國歷朝實行的是君主專制制度”“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三綱五常”,明言中國沒有自由主義傳統。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附錄專門論述“偽民主獨裁的政治哲學發明人盧梭”,大力反思法國大革命,似乎革命并不能真正帶來民主政治。
按照這個邏輯,中國欲實現現代民主,必須全盤學習英美政制,而學習英美政制只能走漸進式的改良主義道路。但問題是,改良主義的基礎是對于傳統資源的充分利用,一個以全盤英美化為目標的改良主義道路何以可能?又,作者在序言的結尾處指出:“要實現中國民主化,必須開展民主思想啟蒙運動,首先要有一批獨立知識分子,他們首先要啟自己的蒙。”這是否又會縱容少數人以啟蒙為名號進行新專制?這些對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而言,仍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傳統思想與現代中國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版)》,王?森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趙園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湖南人與現代中國》,[美]裴士鋒(StephenR.Platt)著,黃中憲譯,譚伯牛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2015年,王?森的又一本論文集《權力的毛細管作用》在大陸出版。他說自己受了柯林伍德“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極大影響。“思想史”一語當作何解?一千個讀者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如余英時便把這句話稱為“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王?森對于柯林伍德的推崇當是承接其師余緒。按照本書“緒論”所言,“我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歷史是由思想造成的,所以思想之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像是微血管般周流全身。試想如果不是政治思想一次又一次的改變,人類政治怎么可能從法國大革命一路演變到今天?”(第7頁)從這個意義上說,王先生對于清代(主要是清初)思想家的言行事跡的討論,也就是在討論他們的思想。
然而,明清之際士大夫的那些在今人看來十分怪誕的“正確思想”又是怎么產生的?何以本書不叫《思想的毛細管作用》,而要叫作《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明眼人一下就可以看出福柯的幽靈始終游蕩在該書的標題,乃至臺灣學術界上。本書的討論對象并不是普通民眾,而是士大夫階層。他們是國家治理的中介,是民眾的表率,因而在他們行為舉止間也無時無刻不折射出國家權力的光芒。這種權力往往不是懲戒式,而是規訓式的。這使得他們往往承受著遠遠超出普通民眾的道德約束,“不為圣賢,即為禽獸”的道德要求,竟造成了他們自虐性的修身方式。
比如王?森便提到清初士大夫的“省過會”與“日譜”。以顏李學派為例,袁枚在《小倉山房尺牘》中曾說:顏元的學生李?“自負不欺之學”,日記中有“昨夜與老妻敦倫一次”的記錄。此舉應是得自乃師,王?森就提到“顏元三十七歲時,他的夫人曾經向顏氏表示希望‘隱過不可記,這里的隱過可能包括閨房之事”。顏元卻訓斥道:“惡!是偽也,何如不為記?且卿欲諱吾過,不如輔吾無過。”(第263頁)
在我們今天看來,家庭是屬于私人空間的范圍,然而那時士大夫的日譜是要放到省過會討論用的。顏元、李?等人在日記中記了自己的私生活,是要將他們全部都公開化。趙園女士的新書《家人父子》就是從“父為子綱”和“夫為婦綱”兩個層面來考察明清之際士大夫家庭生活的公共道德意義,這也是權力在“家”這一層面的展現。
無論是王?森還是趙園,都將自己的著力點放在了明清之交。應當說,那時的士大夫對于異族入侵,衣冠文物敗滅而創巨痛深。他們更多地要從上古典章制度中尋求救世之道,這是清代禮學復興的思想源頭。時空更迭,到了清末這些復古思想家卻搖身一變為啟蒙家了。以王夫之為例,唐鑒、曾國藩等人發掘他的初衷,是要復興禮教,以“華夷之辨”為旗號抗擊崇信上帝的太平軍。可到了世紀之交,王船山卻抖然一變為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的先驅,被一再用于排滿革命。
王夫之思想在晚清民初的命運,正是裴士鋒《湖南人與現代中國》一書的主線。作者之所以選擇王夫之,更是因為他的湖南人身份。“現代湖南人”這一族群認同在晚清是一個“正在形成的”嶄新事物,卻要不斷訴諸于過去。王夫之正是作為湖南人“榮耀的過去”而被動員起來的。
裴士鋒指出:“傳統的中國近代史認識告訴我們,儒家忠君愛國的觀念自然而然轉化為對中國大一統的向往,于是順理成章的,中國知識分子無一不懷抱著中國一統的夢想。”(第3頁)而作者的研究恰恰是要打破這種成見,“把湖南視為本身自性具足的一個主體來看待”(第5頁)。對王夫之的想象便是近代湖南獨立的表征。遺憾的是,裴士鋒絲毫沒有舉例說明王夫之究竟有哪些主張可以被用于說明湖南脫離中國,“船山學”的興起與“湖南獨立”并不在一個論域之中。
中國晚清的現代化進程并沒有像歐洲或日本那樣,打破各級封建領主而建立起強有力的國家,反倒是部分省份的督撫走在了現代化的前列。比如裴士鋒就談到“湖南維新運動作為具有自我意識的省復興運動”(第82頁)。然而,他并沒有考慮到這種省籍認同或地域認同是要以京城的同鄉會館為紐帶的,這是把湖南命運與中國命運綁在一起的制度性紐帶。裴士鋒不知中國近代的鄉土教育,當然也就不會注意到“愛國之道,始自一鄉”,不會明白鄉土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同構性。
湖南人與中國人這兩種身份的形成,需要分別對應兩種不同的“他者”,即他省人和外國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起于其被迫融入世界民族國家競爭體系的那一刻,這需要中國最大限度地實現內部整合。正是在內部整合的前提下,湖南人與外省人的關系才會凸顯。這意味著,現代中國的國家理由只有在內部整合地方勢力和外部處理國際關系的雙重訴求下,才能得以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