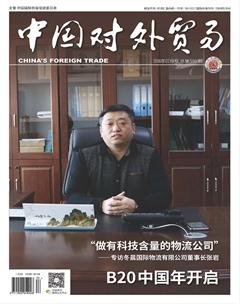劉勝平的白描藝術
胡祥
白描,源于古代的白畫,指以墨線勾勒表現物象,不著顏色的手法,也泛指略施淡墨渲染的線描畫格,其講究運用同一墨色與不同類的長短、粗細、輕重、轉折等線條變化來表現對象,并體現出其筆法本質,形態動態上的多樣性,達到簡潔,明快的特效,成為獨立的繪畫樣式。比如唐代東晉畫家顧愷之的《女史箴圖》,線條柔軟而纏綿,像蠶絲一樣細密流暢,就是典型的白描作品。白描繪畫藝術在中國繪畫的歷史發展中有著不可取代的地位,是中國歷史發展和人文精神的一個重要部分。
劉勝平是最具學術價值與市場潛力的花鳥畫家之一,現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工筆畫學會會員,河北美術學院陳子奮白描花卉研究中心主任。他是著名金石書畫家陳子奮先生入室弟子,與陳子奮一樣同為福州人,徐悲鴻這樣評價陳子奮:當代印人,精巧若收石工奇岸若齊白石、典麗則喬大壯、文秀若瘦鐵……而雄渾則無過于陳子奮者“接著又指出”“雙勾為中國畫之本源,足下可謂知所急務”,在近百年中國現代繪畫史上,陳子奮不僅工詩文、精纂刻、擅繪畫,精白描花卉,并以此奠定了他在中國近現代畫壇上不可動搖的學術地位。也就是說,在其生前與生后的二十多年,尚未有人在白描花卉創作上可以與之比肩者。而劉勝平在藝術上繼承并發揚了陳子奮的白描藝術,并在充分尊重這種傳統藝術的進行創新,取得如今大家公認的藝術成就。
線條是劉勝平作品中的一種標簽,他十分注意用筆過程中的斷與續、行與止。以《山情》為例,在花鳥形象、整體布局上皆與陳子奮的《白描花卉冊頁》非常相近,劉勝平在色彩上更加豐富,加入了彩色,描繪山石上的雙鳥與山下的花卉,而以墨竹作為背景,這幅畫中的線條非常復雜,有寫意的竹與石,又有寫實的白描的花卉,非常有陳子奮中期時的特色,筆法圓轉細勁,較為高古淵穆,行筆頓挫、轉折有力而富靈變。但是相比于陳子奮中期作品,劉勝平筆下的線條特色有很大的不同,最明顯的就是劉勝平的畫中線條的金石韻味不似陳子奮作品中那么濃厚,而是更為圓潤細綿,更講究濃淡對比,通過不同的線條營造出不同的層次感。

劉勝平的白描藝術,還體現在對物象的組織與藝術的概括,他十分講究利用線條的歸納與集中,比如《不借清風香自遠》,采用對比,襯托的手法,以線條的長短交替,敘事變化,粗細對比,使其線法隨意自然,而且極具法度。畫面中,近景處由亂石與花卉鋪滿,石頭的線條粗礦堅硬,色墨濃郁,花卉由亂石中挺拔而出,枝葉或整齊向上豎立或隨意曲卷舒展,花蕊嬌嫩,亂石由近及遠,很有層次感。而飛舞于花叢之中的蜜蜂是這幅作品的點睛之筆,蜜蜂的數量也非常講究,近處少而遠處多,精妙的頭部,撲扇的翅膀,搖動的身尾,栩栩如生,讓畫外人仿佛置身與春天的田野中,看見這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聞到了那似有似無的花香。這幅畫通過的題材內容的對比,筆墨的對比都表現出了藝術風格有時為了線法上的需求,對形象的構成作畫理上的調整,達到物理,物情,物態三者的和諧。
除了直接師承陳子奮之外,劉勝平的繪畫藝術還深受著名畫家潘天壽大師影響,他將山水畫與花鳥畫結合,于20世紀80年代,自創在生宣紙上“融工筆、寫意、花鳥、山水于一爐的四結合畫法”。如前分析,《山情》中就融合了這四中畫法,各種畫法的書法不一樣,墨韻的濃淡,線條的疏密,色彩的深淺,各自有自己明顯的特色,卻有顯得非常自然,相得益彰,共同襯托出一種和諧的精神追求境界。

在如何表現山水上,劉勝平傳承了潘天壽很多藝術特色。劉勝平不畫千巖萬壑,不畫本來就能夠喚起崇高感的高山大嶺,而以倚松傍花的小景為對象,但畫面效果卻雄大壯美,與明清山水花鳥畫率多優美、秀潤的特色大異其趣。如他的《陽春三月》,在布局上就很有潘氏美學特征,如要溯源,甚至可看到八大山人的身影。他筆下的山選用近景,選擇出奇制勝的視角,從右下角穿刺而出,與左下角的花卉,遠景的墨竹拉大距離,增強對比,如吳冠中所言,這種構圖能給人以“強烈、緊張、嚴肅、驚險及激動等等感覺”。所以,崇高的對象在某些人的筆下變為優美或者平淡、平易的景象在另外的人手下卻變為雄壯而奇崛,源自審美主體的能動作用。劉勝平繪畫不入巧媚、靈動、優美而呈雄怪、靜穆、博大,即源自他的氣質、個性和學養的審美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