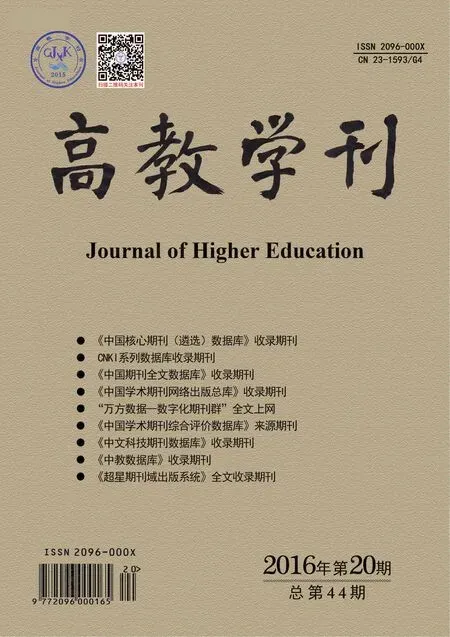后殖民主義視閾下《混血兒》作品中的文化身份的解讀*
馬小驥 黃思楠 張學金
(黑龍江科技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0)
后殖民主義視閾下《混血兒》作品中的文化身份的解讀*
馬小驥 黃思楠 張學金
(黑龍江科技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0)
文章通過分析土著女作家坎貝爾的自傳體小說《混血兒》中坎貝爾在后殖民主義的社會中對自己文化身份的向往、彷徨、墮落、悔恨最后覺醒的心理變化,揭示后殖民主義對土著人民為了追求自身文化身份產生的巨大影響。
后殖民主義;文化身份;身份解讀;身份建構
一、《混血兒》中的后殖民主義的視閾下文化身份的解讀
后殖民主義是世紀之交學術研究中最受人關注、擴展最迅速的文學和文化批評流派之一。瑪利亞·坎貝爾是加拿大當代頗具影響力的梅蒂斯女作家。她以女性和土著人的雙重身份和視角創作的自傳體小說《混血兒》,一經問世就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這部自傳不僅在顛覆加拿大白人所述歷史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而且彰顯了土著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蘊,因此被譽為加拿大土著文學復興的一座里程碑。作為加拿大土著女性作家少有的自傳體小說,《混血兒》展現了20世紀70年代梅蒂斯民族的生活圖景及梅蒂斯女性的生存狀況。
《混血兒》作為加拿大后殖民時期土著文學最具代表作品之一,她探討了加拿大土著民族如何面對由加拿大殖民主義及其法制所造成的歷史創傷和種族創傷。在經過長期的困惑和掙扎,瑪利亞·坎貝爾最終從創傷經歷中恢復。在經歷了艱難的探索后,坎貝爾通過文學創作,以土著女性的視角,發出自己的聲音努力建構民族文化身份。最終坎貝爾在民族文化的呼喚中覺醒。
二、《混血兒》作品中土著群體文化身份
文化是一個民族存在與發展的根基。“文化殖民”無疑在一步步地消除土著民族的文化個性特點,甚至是吞噬者土著民族的文化,而處于這種狀態下的土著居民失去了自身民族文化的支持,就好像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根基,內心充滿的恐懼感和自卑感。
《混血兒》中文化和身份上的不認同使得土著居民,特別是梅蒂斯人的社會地位極端低下,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生活極為貧困——這是梅蒂斯人一直面臨的困境。白人移民對這塊殖民地進行土地和資源的控制開發,不斷從政治、經濟和精神方面對殖民地進行霸權式的控制,并不斷毀壞其本土所存在的社會關系,使土著居民靈魂深處產生一種無可排解的自卑情結和劣等民族的心理定位,給扭曲的土著居民的心靈疊加上更大災難的是使他們沒有文化地位,沒有社會地位,也沒有自主和民族自尊的所謂“邊緣人”。
自傳體《混血兒》表面上是敘述作者自己的成長經歷,但是實際上作者在作品中一直用“my people”“our men”“our people”來講述她的混血人民族在糅雜的文化身份中如何掙扎如何在混雜的社會中確定自己的身份并得到社會認同。小說開始講述混血人1860年由于逃避歧視來到一片新的土地。在作者童年時,當她看到白人因勝利而驕傲,歡呼跳舞時,她心理感到受傷害而自卑并且知道白人不認同她的民族。
當她注意到她爸爸除了喝酒以外從不和白人說話時,坎貝爾從小就意識到她與白人有不同的身份。
I never saw my father talk back to a white man unless he was drunk。
但是從小說開始我們能充分意識到梅蒂斯人內心里具有一種強烈的反抗精神。(However they were drunk they became aggressive and belligerent,and for a little while the whites would be afraid of them.)這種思想源于殖民者長期灌輸的白人文化至上,挖走了土著居民靈魂深處對自我民族身份的認可。
《混血兒》小說中的主人公坎貝爾開始將自身社會地位的低下歸罪于自身所處民族的文化劣根性。當坎貝爾9歲時,她在學校被白人同學嘲笑并發現她與白人學生有完全不同的待遇開始憎恨她的混血身份進而憎恨她的父母。她的言行被曾祖母Cheechum看到后,對坎貝爾進行嚴厲的批評并且遭到曾祖母的痛打。通過Cheechum與坎貝爾的對話,我們知道Cheeechum對梅蒂斯人受白人壓迫的痛恨,更讓Cheeechum痛恨的是坎貝爾由于對自己身份的厭惡而痛恨她的父母。這件事使得坎貝爾覺醒,她開始在白人面前抬頭走路,保護自己的朋友和學會控制自己的情緒。其實,種族歧視不僅來自學校并且來自歐洲人統治社會的每個角落。
當坎貝爾成人時,她努力擺脫自己的身份,渴望融入白人主流社會中并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她雖遭到家人尤其是曾祖母Cheechem的強烈反對,但她最終還是嫁給白人Darrel。
“One night he was staying with us when Darrel came home drunk and in an ugly mood.He slapped me and I fell down the stairs.I was taken to the hospital because the doctor was afraid I would lose my baby.However,I was okay except for a sprained ankle and a broken wrist.”[1]
坎貝爾認為自己的身份通過嫁給白人就可以改變并且最終改變家人的生活狀態和自己的身份,但是Darrel掌控家里的一切并對她進行家暴。她在家里沒有一點地位和尊嚴。她在婚姻中徹底地迷失了自我。
坎貝爾的雙重身份與后殖民主義時期的社會環境中形成了鮮明的不對等。坎貝爾的土著身份與白人社會充滿了矛盾和沖突。她最終無法根本改變的身份,最后她在婚姻中徹底地迷失了自我。
由于坎貝爾被丈夫Darrel無情的拋棄,她和女兒Lisa因沒有經濟來源而無法生存。坎貝爾從期望丈夫的回歸到失望最后絕望。她最終吸毒并淪落成妓女。她曾經想和孩子一起同歸于盡。正如霍米巴巴所說身份的“選擇”及其心理表述和意識形態表述是一場你爭我奪的痛苦斗爭。
三、坎貝爾土著文化身份建構的反思
加拿大歐洲殖民化給土著民族文化帶來了巨大的創傷,但是土著人們從來沒有放棄建立他們文化身份的追求。她們通過文學寫作構建文化身份。處在歐洲文化同化和本土文化的兩難境地中,坎貝爾曾一度向往、彷徨、墮落、悔恨最后覺醒。她當過妓女吸過毒甚至兩次自殺想徹底地喪失自己的身份,但對家族尤其是外祖母Cheechem的教誨和童年快樂的記憶使她決定想通過文學創作吐露自己的心聲。她的文學創作最終使她重構文化身份。
《混血兒》中坎貝爾的曾祖母Cheechem對坎貝爾及其家族的文化身份的建構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同時Cheechem也是坎貝爾整個人生的精神支柱。在坎貝爾小時候給她講述土著傳奇、土著民族的價值觀、土著人們的信仰和土著文化。Cheechem支持并鼓勵坎貝爾為土著人們的權利而奮斗。盡管反抗沒有成功,但她從來沒有接受失敗。她始終相信總會有一天梅蒂斯人能在這場種族之戰取得勝利。Cheechem的勇氣和強烈的民族自尊感給坎貝爾留下深刻印象。曾祖母Cheechem幫坎貝爾度過了一道道生活的難關并告誡她無論其他人怎么看待土著人,土著人要有自尊,土著文化都應代代相傳。
盡管坎貝爾和她的民族在爭取民族自尊、民族權利和民族文化身份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在后殖民主義影響下,她們仍然面臨著多方面的挑戰,坎貝爾的個人成長經歷折射出整個加拿大土著民族從生存到康復再到面臨的挑戰的奮斗歷程。《混血兒》不僅展示了加拿大土著女性建構自身文化身份的艱辛歷程,客觀揭示了加拿大土著民族的歷史、文化及生存狀況而且對保護和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也有一定借鑒作用。
[1]Maria Campbell Halfbreed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Lincoln and London:123-124.
[2]繩立平.無聲的吶喊:《潛鳥》的后殖民主義思想[J].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9).
[3]鄒威華.族裔散居語境中的“文化身份與文化認同”——以斯圖亞特霍爾為研究對象[J].文化研究,2007(2).
[4]呂紅.海外新移民女作家的邊緣寫作及文化身份透視[J].華文文學,2007(1).
[5]生安鋒.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論研究[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The paper analyzed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 of Cambia's worship,dilemma,depravation,regret and realization of her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from the autobiography"Halfbreed"written by aboriginal female writer Cambia. This paper revealed the great impact o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aboriginal people under the post colonial environment.
post colonialism;cultural identification;understanding of identification;structure of identification
I106
A
2096-000X(2016)20-0259-02
省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年度項目,項目題目“后殖民語境下的加拿大土著文學研究”(編號:13C050)。
馬小驥(1973,10-),回族,專業: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學位:碩士,職稱:講師,工作單位:黑龍江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畢業學校:黑龍江大學西語學院。黃思楠(1975,10-),專業:英語語言文學,學位:碩士,職稱:副教授,工作單位:黑龍江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張學金(1982,05-),專業:英語語言文學,學位:碩士,職稱:講師,工作單位:黑龍江科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