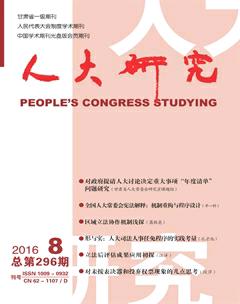地方立法重復的反思
孫述洲
地方立法應在法律和行政法規“照顧不到的地方”,適應本地實際需要、解決本地實際問題,這才符合授予地方立法權的本意。
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以下簡稱《立法法》)賦予設區的市立法權,進一步擴大了地方立法主體范圍。賦予地方立法權,是為了規范地方特殊問題,發揮地方管理當地經濟社會的積極性。“正因為單有中央立法不足以解決地方的特殊問題,不足以反映各地不平衡的狀況……才在中央立法之外,再辟地方立法的蹊徑。”[1]因此,地方立法應在法律和行政法規“照顧不到的地方”,適應本地實際需要、解決本地實際問題,這才符合授予地方立法權的本意。然而,一些地方立法中出現的大量照抄照搬上位法的現象,使得這種本意大打折扣。
一、對4省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的文本統計分析
筆者以近兩年4省市人大同一部法規為例,通過法條文字比對,統計分析了照抄上位法的立法重復現象。值得說明的是,盡管統計只涉及部分地方人大的同一部法規,但毋庸諱言,地方立法重復現象絕非個例。
2013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作了修訂。隨后,甘肅省、江西省、湖南省、上海市分別根據修訂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地方法規進行了修訂。以下是4省市法規與上位法的重復統計:
從以上統計結果來看,4省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與上位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文字重復50%以上的法條數占各自總條款數的比例,均達到三分之一左右。
例一:《甘肅省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第九條,消費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權利。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或者接受服務時,有權獲得享有[2]質量保障、價格合理、計量正確等公平交易條件,有權拒絕經營者的強制交易行為(刪除線部分表示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相關文字的刪除,下劃線部分是地方法規增加的內容,其余為重復上位法,下同)。

該條完全照抄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十條。既然《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已經明確規定了消費者所享有的公平交易權利,對全國普遍適用,對甘肅當然也適用。地方立法再照抄一遍,并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消費者相關權利,完全沒有必要。
例二:《江西省實施〈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辦法》第六十一條,消費者和經營者發生消費者權益爭議的,可以通過下列途徑解決:(一)與經營者協商和解;(二)請求消費者協會權益保護委員會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調解消費者組織調解;(三)向有關行政主管部門投訴;(四)根據與經營者達成的仲裁協議提請仲裁機構仲裁;(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該條照抄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三十九條。從法的適用角度,當發生消費糾紛時,消費者或其聘請的律師一般會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途徑去解決,道理很簡單:既然是重復規定,而上位法更權威,在全國普遍適用(當然適用于江西),避開下位法、選擇上位法順理成章。可以想見,該條款將成為“僵尸條款”。
例三:《湖南省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第十五條第一款,經營者應當保證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務、設備設施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的要求;對可能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商品和服務,應當向消費者作出真實的說明和明確,設置醒目的警示標志,并說明和標明告知正確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方法以及和防止危害發生的方法。
該條款從《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十八、十九條而來,從文字比對來看,屬于部分重復(50%以上)。該條款第一句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商品或者服務”后增加了“設備設施”。經營者提供服務當然需要場地、設備設施,即“服務”已經涵蓋了“設備設施”,沒必要再增加。接著,該條款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作出真實的說明和明確的標志”修改為“設置醒目的警示標志”。從表意上,“作出……明確的標志”與“設置醒目的警示標志”并沒有區別,前者表意也是清晰的,而且更簡潔。接下來,該條款將“說明和標明”修改為“告知”,而“告知”的方式正是“說明”和“標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表意并無不妥。因此,該條款對上位法的修改并未起到補充或細化上位法的作用,實質上仍然屬于重復。
上述統計[3]和分析可以表明,地方法規中大量存在完全沒有必要的重復[4],相當部分屬于無用條款。更嚴重的是,這種重復性規定不僅“無用”,而且“有害”。
二、地方立法重復的弊端
(一)增加立法成本
大量重復上位法的條文,給在起草、審議、立法后評估、修改方面都人為增加了工作量。
從起草來看,盡管文本照抄本身不會耗費多少精力,但為保持條文的邏輯統一和表述規范,抄哪些、不抄哪些,卻要花許多時間去選擇、論證。從審議來看,在目前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會期短、審議時間本來就短的情況下,大量重復條款的存在,無疑增加了不必要的工作量,拉長了審議周期。在審議實踐中,對部分條款意見不一而又必須作出結論時,往往最終選擇直接照抄上位法,因為這樣最容易取得共識。如此,立法審議過程進一步導致重復條款增加,這又增加了后續的立法后評估等工作量[5]。
當上位法修改時,大量重復上位法的地方法規還會面臨被動修改的尷尬。重復條文越多,修改的工作量越大。在地方立法距上位法實施有較長時間間隔的情況下,甚至會面臨“前腳剛立、后腳修改”的窘境[6]。
(二)喪失法條的嚴謹
法律的表述本身是十分嚴謹的。地方立法重復作為上位法的法律時,一般并非全盤照抄,而是有照抄有修改。這種有選擇的重復,恰恰容易造成法條的不嚴謹。仍以《湖南省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第十五條第一款為例。該條款增加了“設備設施”,形成與“商品”“服務”并列意義的表達,形成邏輯矛盾。因為“設備設施”本身是“服務”的一部分,二者是從屬關系,而不是并列關系。如果立法的目的是突出“設備設施”,那“場地”為什么不突出?按照常識,“場地”同樣是服務中造成消費者人身財產損害的重要因素。該條款還刪除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方法”,形成“正確使用商品、服務、設備設施的方法”的表述。從語法上來看,“商品”“設備設施”可以“使用”,而“服務”一般不說“使用”,只與“接受”(買方)或“提供”(賣方)等詞語相搭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接受服務”的表述是恰當的,該條款刪除后反倒形成語病,使法條失去應有的嚴謹。
(三)形成法理悖論
從法理上講,地方立法者僅對自行起草的“地方性”條款有審議和表決權,對已經通過的上位法條款并無審議表決權,只有執行義務。如果法規草案大量重復上位法,由于審議表決是針對所有條款(包括重復上位法的條款)“打包”進行的,這就意味著地方立法者“一并”審議和表決了已經通過的上位法條款,因而難以避免越權嫌疑,形成法理悖論。
此外,地方立法重復,還會造成法制宣傳和適用困難[7]、“污染法律”[8]、喪失“地方性”[9]等問題。
三、地方立法重復的原因
(一)制度層面
地方立法重復并非新近出現的現象,而是由來已久。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存在這個問題,為此,九屆全國人大提出,“地方性法規要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突出地方特色,注意簡明宜行,力戒照抄照搬,減少立法重復。”[10]但由于沒有相應的制度約束,地方立法重復并未得到有效遏制。2015年修訂的《立法法》也注意到了地方立法重復的問題,于是增加規定:“制定地方性法規,對上位法已經明確規定的內容,一般不作重復性規定。”但是,其一,何謂“一般”,何謂“特殊”(“必要”)?如何區分與界定?何謂“重復性規定”?是以文字重復比例,還是以行為模式、法律后果的重復為認定標準?對此,《立法法》均未明確,全國人大常委會也未出臺相應的立法解釋。其二,更重要的,地方立法重復的后果是什么,《立法法》也未規定,從而使上述規定缺乏起碼的可操作性,難免淪為具文。在實際的備案審查中,對于地方立法重復,全國人大常委會也并未予以撤銷或要求修改。原則性規定的巨大解釋空間,加上實際行為的默許(變相鼓勵),為地方立法重復敞開了大門。
在地方立法重復自我審查方面,盡管部分地方人大根據《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對立法重復也作了相應規定,如2015年修訂的《上海市制定地方性法規條例》規定,“地方性法規規定的內容,應當明確、具體,具有針對性和可執行性,對上位法已經明確規定的內容一般不做重復性規定。”但是,與《立法法》一樣,該條例也未明確“重復性規定”的認定標準與后果,同樣不具有可操作性。在實際立法審查中,地方人大也并未將重復上位法作為否定的標準加以制止。
(二)立法心理層面
剛性制度闕如固然是一方面原因,但立法重復這種表面上沒有益處的事盛行不衰,必然有更深層的原因。
1.起草、審議者的“避風港”。與上位法不抵觸是地方立法的首要原則。在該原則的指導下,地方立法者“往往采取保守主義態度:寧可相同或相似,也不搞差異……寧可照搬照抄,也不立足于提高而搞創新”[11]。對法規草案的起草者來說,創新(自制條文)不僅需要大量的時間開展調研論證,而且還存在違反上位法的風險。因為,起草者既要遵守所有相關上位法的明文規定,還要遵守相關的法律原則和精神。而對于法律原則和精神,往往難以準確界定。因此地方法規起草者如果創新,將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會陷入違法的境地而得不償失。于是,為安全起見,創新能少則少,條文能抄則抄,躲進上位法這個“避風港”方為上策。一些由政府相關部門起草的地方法規草案,起草者照抄上位法既為安全,也“為起草部門隱藏部門利益提供掩護載體”[12]。在審議和表決過程中,當對有關條款爭論不下時,照抄上位法同樣是最安全、最簡便、最容易達成共識的選擇。起草和審議中的這種心理,其實質是立法“惰性思維”的表現:不求有功(創新),但求無過(不違反上位法)。
2.追求政績的心理。地方立法中一個普遍現象是“貪大求全”[13]。地方法規大多體例完整、法條數量多,一般都是洋洋灑灑幾十條甚至上百條。在體例上,一般選擇“條例”,因為在地方立法者看來,“條例”要比“實施辦法”“規定”顯得更為系統,更“像法”,也更有“面子”[14]。2014年,甘肅省、江西省通過的地方法規均為7部,采用的體例全是“條例”,上海市通過的11部中有9部采用了“條例”的體例[15]。即使采用“實施辦法”的體例,也往往追求“大而全”。以上述4省市的消費者權益保護地方立法為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共8章,分別是:總則、消費者的權利、經營者的義務、國家對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保護、消費者組織、爭議的解決、法律責任、附則,而4省市的法規全都是8章,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完全一致[16]。在“大而全”心理的驅使下,“自制條文不夠、上位法來湊”,便成為順理成章之事。在推進依法治國、擴大地方立法權主體的新形勢下,立法顯然已被地方人民代表大會當作政績去追求。對有立法權的地方人民代表大會來說,立法好比“立言”,是看得見的政績。從單部法規來說,一部只有幾個條文的“若干規定”,“面子”上并不好看,“政績”也不明顯,而一部“大而全”“像法”的地方法規,顯然更符合地方立法者的胃口。
在制度與實際行為的默許甚至變相鼓勵下,在立法“惰性思維”和追求政績等心理的驅使下,地方立法者制定一部真正具有地方特色的法規的意愿和動力都不強,照抄上位法才是更好的選擇。
四、出路及其他
理清了地方立法重復的原因,解決問題的出路似乎就比較清楚了:認識上,強調地方立法重復的危害,對其實行“一票否決”;摒棄“貪大求全”和“政績”的心理,有幾條立幾條,務求立法實效。制度上,對地方立法重復的認定標準予以明確和細化[17],同時明確立法重復的后果(撤銷或修改),并嚴格實施。
按照行文邏輯,本文本該可以結束了。然而,并非與本文無關——如果我們不是故意 “裝鴕鳥”,或者過于理想和樂觀,就應該心存疑問:即使通過“堵”遏制了重復上位法的問題,地方立法者從此就能制定出好的地方法規嗎?
應該看到,制定一部真正具有“地方性”、經得住實踐檢驗的地方法規極為不易。地方立法者“必須正確地把握并表達社會生活的客觀需要……正確認識各種利益及復雜的利益關系”[18],深刻洞察和把握地方的特殊性,同時熟練掌握立法技術,才有可能制定出一部真正好的“地方性”法規。以消費者權益保護地方立法為例,在全國統一大市場的背景下,甘肅、湖南、江西、上海的消費者、消費市場與全國相比有何特殊性?如果有,這種特殊性是否具有相當的普遍性,是否一定要通過地方人大立法來解決[19]?如果沒有特殊性,立法的必要性何在?在上位法已經對經營者、消費者權利義務作出平衡的情況下,地方立法如果增加經營者的義務,是否會導致權利義務失衡[20]?對這些問題,如果不能作出科學、準確的回答,必將“為立法而立法”,要么簡單重復上位法,要么違反上位法。201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對有關計劃生育管理等6方面390件地方性法規進行調查研究后發現,95件存在與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等問題,比例高達24.4%[21]。
另一方面,從立法力量(立法人才)分布來看,“上(中央)強下弱”是不爭的事實。立法要求高而能力弱,地方立法中的這種反差,是地方立法質量普遍不高的重要原因[22]。
看到這種反差,地方立法者在不斷提高立法能力的同時,還需要摒棄“法治就是立法”“立法萬能”[23]的幻象,克制立法沖動[24]。“節制是立法者的美德”(孟德斯鳩語),對立法的必要性,要進行非常深入、科學的論證[25]。當不能得出顯而易見的結論時,謹慎立法或許是更明智的選擇[26]。在新《立法法》進一步擴大地方立法主體范圍的情況下,筆者的呼吁似乎不太合時宜[27],但是,面對普遍的地方立法重復等低質量立法,我們有理由多一份冷靜和謹慎。
注釋:
[1]周旺生主編:《立法學》,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76頁。
[2]該條僅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獲得”改為“享有”,從文字表達角度,“獲得……條件”比“享有……條件”更為準確。
[3]需要說明的是,以上統計,不包括大量文字重復在50%以下、涉及行為模式或法律后果的條款照抄上位法的情況,例如4省市都照抄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關于“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也不包括文字上未重復,但實質上重復(或不必要)的條款,如《上海市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款:“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的標識,應當符合法律、法規的規定。”該條款并無實質性內容,如果法律法規已對標識作出明確規定,地方法規完全沒有必要“重申”。
[4]有學者將地方立法重復分為“必要的重復”和“不必要的重復”,“必要的重復”包括對上位法立法目的、法律原則、法律規則中的前提條件的重復。參見湯善鵬、嚴海良:《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復的認定與應對——以七個地方固廢法規文本為例》,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4年第4期。以此而論,本文統計除“立法目的”(法規第一條)外,均屬于“不必要重復”。但在筆者看來,對立法目的、法律原則等的重復,仍然屬于不必要重復。對這個問題,限于篇幅,本文不予探討。
[5]如果地方立法的原則是,上位法已經有明確規定就不再重復,那么地方立法過程將變得十分單純:集中精力在那些上位法沒有明確規定的條款中,不必糾纏于抄哪些,不抄哪些,也不必在沒有意義的重復條款上耗費精力。
[6]如果地方法規不重復上位法規定,那么被動修改的機率將大大降低。因為,上位法的修改如果吸收了地方法規的相應規定,則地方法規無需修改;如果沒有涉及地方法規相應條款內容,則地方法規也無需修改。
[7]王宗炎:《地方立法不應重復照抄上位法條文》,載《上海人大月刊》2004年第12期。
[8]周永坤教授指出,“一個全國性的大法,31個省、區、市大家都來抄(重復)一遍,無疑是法律的污染”“本來是統一的法律,地方在抄的過程中水平不一,加上‘創新’,法律反而不統一了”。參見周永坤:《地方立法可以休矣》,http://guyan.fyfz.cn/b/585698,2015年12月15日最后上網。
[9]大量重復上位法,無疑會“淹沒”“地方性”條款,使地方法規喪失“地方性”。
[10]時任委員長李鵬在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轉引自上海市行政法制研究所:《我國地方立法的流變與展望——以上海市地方性法規的分析為例》,載《政府法制研究》2005年第4期。
[11]孫波:《試論立法“抄襲”》,載《法商研究》2007年第5期。
[12]有學者認為,執法主體作為起草主體在利益上很難中立,其關注的重點幾乎不可避免地都放在維護、擴大自身部門利益上。在一部篇幅短、架構簡單的法規中,這些部門利益條款顯得太醒目,于是起草一部結構完整、內容“豐富”的法規草案方便隱藏這些條款。參見林琳:《對實施性地方立法重復上位法現狀的原因分析和改善設想》,載《人大研究》2011年第1期。
[13]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國家法室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39頁。
[14]林琳:《對實施性地方立法重復上位法現狀的原因分析和改善設想》,載《人大研究》2011年第1期。
[15]另外2部分別是《上海市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上海市查處車輛非法客運若干規定》,由于未采用“條例”的體例,條款數均較少。前者因涉及選舉組織等事項較多,但也只有34條;后者更只有7條,兩部法規基本都是具有針對性的“干貨”,沒有重復上位法的情況。
[16]除江西省采用“實施辦法”的體例外,其余三省市均采用“條例”。章名上,僅有個別表述有細微差別,如甘肅省的第四章為“消費者權益保護”,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為“國家對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保護”。
[17]或以文字重復(率)為標準,或以行為模式、法律后果的重復為標準等,當然,對該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
[18]朱立宇、張曙光主編:《立法學》(第三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頁。
[19]在我國還處于社會轉型期的背景下,一些現象和行為變化十分快,有些法規剛出臺就不適應新的形勢了。因此,考慮到規范治理的需要,通過政府制定規章或者規范性文件的方式可能更靈活,也更能及時適應新情況。
[20]如《甘肅省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第四十條規定,“餐飲業的經營者,應免費為消費者提供符合衛生條件的餐具。”實際上,對消毒餐具另外收費是普遍現實,盡管消協一再認為該收費不合法(實際上并無法律依據)。本質上,餐具收費是經營者與消費者的約定,并非強制。如果消費者認為不合理,大可以不去該店消費。餐具收費問題需要通過市場競爭去解決(實質上降低餐飲價格、提高服務質量),地方法規強行增加經營者義務,有政府干預市場的嫌疑,也導致權利義務失衡。
[21]李高協:《再議地方立法的不抵觸、有特色、可操作原則》,載《人大研究》2015年第9期。如果再去掉這些地方法規中重復上位法的部分,真正體現地方特色、管用的條款可能并不剩多少。這也從側面證明了制定一部好的地方法規的困難。
[22]從經驗來看,公民、法律工作者普遍忽視地方法規,法院適用頻率并不高,地方法規的質量由此可見一斑。或許有人會說這正是立法發揮了指引作用的結果。但是,一部地方法規立法的必要性,一定是某類行為在當地具有普遍性和經常性,立法者才認為有必要通過立法予以調整。如果適用頻率非常低,立法的必要性和質量就值得懷疑。
[23]有關這方面的論述,20 世紀利益法學派代表赫克最早打破“制定法萬能”的神話,認為即使最好的法律也存在漏洞,原因是:其一,立法者的觀察能力有限,不可能預見將來的一切問題;其二,立法者的表現手段有限,即使預見到將來的一切問題,也不可能在立法上完全表現。參見梁慧星:《民法解釋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頁。列寧指出:“假使我們指望寫上100 個法令就可以改變農村的全部生活,那我們就是十足的傻瓜。”參見《列寧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8頁。當代學者也指出,法律的功能是有限的、相對的,同時又是滯后的。法律與無限、多變、超前的社會之間始終處于矛盾狀態。立法不是根除一切社會瘤疾的靈丹妙藥,理性的法制建設只能是一個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漸進過程。參見丁偉:《“激情立法”當忌》,載《上海人大月刊》2005年第9期。
[24]根據學者統計,目前我國有效的法律及有關問題的決定722件,國務院法規及文件676件,司法解釋及文件3218件,部門規章及文件3803件,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有效地方性法規20071件,合計28490件。參見王春業、聶佳龍:《論立法的節制性美德——從立法禁止“啃老”談起》。從數量上看,我們已過了“無法可依”的階段,當務之急是謹防地方人大立法重復等低質量立法和“立法泡沫”。
[25]如北京等部分地區在立法項目論證時,通過對預立法規的必要性及“是否窮盡其他調整手段”等量化標準的分析,將一些不具備啟動條件的法規攔在門外。
[26]針對地方立法,周永坤教授認為應該消極,理由是:中國是單一制國家,地方不是主權者;中國的地方立法是特殊情況(1949年以后法律缺位)下的產物,而這一特殊時期已經過去;地方立法造成法律的歧義與不統一等。參見周永坤:《地方立法可以休矣》,http://guyan.fyfz.cn/b/585698,2015年12月15日最后上網。
[27]筆者無意質疑《立法法》的規定,這也不是本文的目的。
(作者單位:上海市人大常委會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