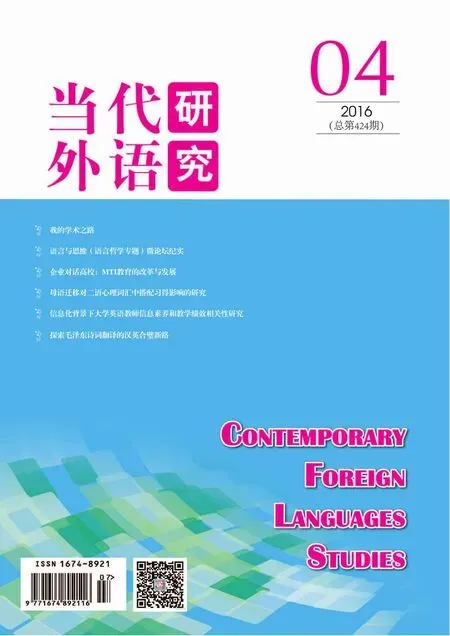我的學術之路
曹順慶
?
我的學術之路
曹順慶
1.
我6歲時,就讀于貴陽市貴溪路小學,“文化大革命”剛開始那一年,我就讀于位于解放橋的貴陽第十四中學初中,記得我的班主任老師是李正祥;由于我會拉二胡,進了學校宣傳隊,當時的宣傳隊隊長是鄒培賢,手風琴拉得很好,后來到香港去了。帶隊老師與鄒培賢帶著我們四處去演出,當時大家興奮得很,干勁十足,我的二胡技巧也大有長進,還學會拉京胡,拉小提琴;后來還擔任學校宣傳隊長。初中畢業,上高中,進了當時最好的中學貴陽一中。一中也有校宣傳隊,領隊老師是鼎鼎大名的胡啟文,我當然就進入了學校宣傳隊,結果在高中僅僅一年,我考上貴州省軍區宣傳隊文藝兵,1970年11月進入貴州省軍區宣傳隊,正式軍齡從1971年1月1日算起。當上文藝兵,在當時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情,自己很自豪,拉琴更加刻苦用功,擔任了第一小提琴手。部隊文藝兵不僅僅要演出,而且也要下連隊訓練,長途拉練,還要搞生產,挖地挑糞,栽秧打谷子,我還放過牛。1976年退伍進入貴州省黔劇團,在樂隊工作。1977年3月,我作為最后一屆工農兵學員進入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文學評論專業學習。當時復旦大學的校長是陳望道,中文系系主任是朱東潤,都是鼎鼎大名的學者。中文系有許多名師,例如郭紹虞、劉大杰;直接給我們授課的老師有:蔣孔陽、王運熙、顧易生、王水照、李慶甲、章培恒、陳允潔等老師。“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大學的記憶是美好的,老師們的課程精彩紛呈,我聽了王水照老師的課,悄悄寫了一篇稱贊王老師授課的文章,交給了校報,署名“小草”,居然被刊登出來了!多年以后,我與王水照老師在北京西郊賓館評審國家社科基金,晚飯后一起散步聊天時,我提起此事,王水照老師才知道原來那個“小草”就是我“小曹”,十分感慨。我記得同學們學習起來跟瘋了似的,復旦大學圖書館的大門常常被我們擠破。當時我真的覺得復旦太好了,圖書館的開架書庫竟然可以隨便進入,我常常在里面一泡就是一天。看了很多書:西方的、中國的、理科的、文科的、現代的、古代的,我都如饑似渴地讀;或許我的學術根底,就是在復旦大學打下的。在復旦,我還寫了一篇學術論文《略論孔子的美學思想》,我主動將這篇稚嫩的習作交給蔣孔陽教授和王運熙教授,請他們批評指教,這兩位恩師非常認真,給我仔細修改,直到現在我還珍藏著老師的修改稿。最后這篇論文發表在《復旦大學學生學術論文集》中,這是我的處女作,對我鼓舞極大。1980年3月畢業,工農兵學員必須哪來哪去,畢業之際,我報考了研究生。隨后我被分配到貴州省電影公司宣傳科工作,編輯《電影評價》,結果才工作幾個月,就接到了四川大學研究生錄取通知書。9月初,我背上小提琴,來到成都望江公園旁的四川大學,成為了著名《文心雕龍》專家楊明照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碩士研究生。師從楊明照教授攻讀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的碩士學位。在四川大學,我深受恩師明照先生的影響,楊先生上《文心雕龍》課,首先給同學們背一遍原文,然后再逐句講解;楊先生的書桌上,永遠放著《十三經注疏》,先生博大精深的學識、爐火純青的研究,深深激勵了我。
在楊先生言傳身教下,我發奮努力,一方面浸漬于中國古代文論,另一方面探索比較詩學路徑。在讀研究生期間,我一年級就在《江漢論壇》發表習作《亞里士多德的“Katharsis”與孔子的“發和說”》,該文一發表就被《新華文摘》摘登,令我興奮異常。以后又陸續發表《“風骨”與“崇高”》、《“移情說”、“距離說”與“出入說”》等多篇論文①,我將碩士學位論文的選題確定為《〈文心雕龍〉中的靈感論》,這是一個當時沒有人寫過的創新性問題。該文在郭紹虞主編的《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叢刊》第6輯上發表后,引起了古典文論研究界的普遍關注與好評,而且還得到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的肯定。錢學森來信如下:
“四川省成都市四川大學中文系研究生曹順慶同志:
去年十二月二日來信及大作《‘文心雕龍’中的靈感論》均收到。我把論文立即送給哈爾濱科學技術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的劉奎林同志看,因他在研究“靈感學”,現得他回信說:‘很受啟發。’
我們這些搞科學技術的,有個毛病,不滿足于論述一番,而要刨根問底、探索機制。因此想把研究靈感搞成一門科學,叫靈感學。我們當然歡迎文藝界同志給我們幫助和啟發。所以我對您表示感謝。
此致敬禮!
錢學森 1983.1.20”
大科學家的鼓勵,更堅定了我從事比較詩學研究的決心。碩士研究生畢業,本想赴北京工作,已經聯系好北京的工作單位,但是四川大學讓我留校任教,我服從組織安排,繼續師從楊明照教授,在職攻讀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的博士學位,成為四川大學中文系第一個博士生。1987年上半年,我應邀赴香港中文大學比較文學研究中心訪學,與李達三、袁鶴翔、周英雄、黃維梁諸位教授相處甚歡。1987年9月進行博士論文答辯,楊師明照先生親自主持,當時的答辯委員會有徐中玉、王運熙、張文勛以及本院張永言、項楚等著名教授,評審專家有季羨林、楊周翰、張松如、錢仲聯、周來祥等著名學者,他們對我的博士論文給予高度評價,我至今仍然珍藏著這些評審表格。季羨林先生的博士論文評審意見如下:
“我個人認為,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論文。中西文論的比較研究之重要性,現在幾乎盡人皆知。全面認真而系統地鉆研探討的文章或專著還很少見到。原因是,這種比較研究工作難度極大。倘若對中西兩方面的文論沒有比較扎實、比較系統的理解,實在難以完成這一件工作。中西文論(詩學)都有極長的歷史,著作之多汗牛充棟,鉆研起來,十分吃力。其次,想進行中西文論的比較研究,必須宏觀與微觀相結合,沒有宏觀,則易為中西兩方面的繁瑣的文筆現象而束縛,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沒有微觀,則又容易流于空泛,不能真正談到點子上,不能真正搔到癢處。這樣就只見森林,不見樹木。曹順慶同志的論文既有宏觀的觀察,又有微觀的探討。中西兩方面的文論中都有不少的專門術語,比如‘典型形象’、‘意境’、‘氣象’、‘神韻’、‘性靈’等等,都是很難理解,難以捉摸的。曹順慶都用簡短扼要的語言,說明了這些術語的涵義。他對中西兩方面的主要的文藝理論流派都能了若指掌,論述起來,有極大的概括性,頗有高屋建瓴之勢。他的論述確持之有據,言之成理,有極大的說服力。我常常感覺到,世界上文學理論能獨立成為體系的不外三家:中國、印度、希臘(包括近代西方各國)。此文只對比了中國和西方的文論。倘若將來能擴而大之,把印度古代文論也包括起來,把三者進行對比。其成就必將有更大的意義。總之,我認為,曹順慶同志的論文已經完全達到博士論文的水平。”
楊周翰先生的評審意見是:
“曹順慶同志所占有的中西文論材料極為豐富,難能可貴,足見其用功之勤。在大量占有材料之后,抽繹其關鍵概念,作中外比較,列論詳盡。在國內對中西文論作如此系統的比較,有首創精神。”
山東大學周來祥教授評審意見:
“曹順慶同志的論文,對于掌握中國古代詩學的民族特色,對于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對于促進中外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中西比較詩學,在我國還是一門新興的學科,當前學術界雖已有不少有價值的探索,但還缺乏系統性和完整性。作者在概括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本質論、起源論、思維論、風格論、鑒賞論等五個方面,比較全面系統地對中西詩學作了總體的比較研究,論文具有開拓性,也表現了作者理論上的勇氣和創新精神。通觀全文,新見迭出,美不勝收。作者在意境論與典型論的比較中,揭示了中西方對學術本質的不同理解。由物感論和模仿論,提出了中西方兩種不同的藝術起源論,過去很少有人提到這個問題,文中的論述既新穎,又有力。”
這篇博士學位論文1988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被公認為我國第一部中西比較詩學專著,是中西文論比較領域“開風氣之先”和“填補空白”的著作。《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二十年》一書指出:“比較詩學是近20年來我國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最大熱點,曹順慶的《中西比較詩學》和黃約眠、童慶炳主編的《中西比較詩學體系》、錢念孫的《文學橫向發展論》等是公認的學術精品……《中西比較詩學》是我國第一部中西詩學比較研究的專門著作……可以說是開辟了中西比較詩學的一個新階段。”(王向遠2003:248-251)此書獲1990年全國首屆比較文學圖書專著一等獎。這本書,可以說成為我學術生涯的第一個里程碑。
1990年,我被破格晉升為教授,30多歲當上正教授,成為四川大學最年輕的教授,在當時是罕見的。從此,我更是意氣風發,一門心思做學問,決心將自己獻給學術創新事業。
自出版《中西比較詩學》后,我學術信心大增,便下決心開始著手寫一部大書《中外比較文論史》,初步預計幾百萬字,現在回想起來真的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為寫此書,我吃盡了苦頭!為什么要寫這樣一本書,一方面是受季羨林先生鼓勵,季先生在我的博士論文評語中說“我常常感覺到,世界上文學理論能獨立成為體系的不外三家:中國、印度、希臘(包括近代西方各國)。此文只對比了中國和西方的文論。倘若將來能擴而大之,把印度古代文論也包括起來,把三者進行對比。其成就必將有更大的意義。”我非常渴望踐行季先生的期望,當時更進一步的想法是準備探索另一條創新之路,即從總體文學的角度來研究比較詩學。為什么要探索這樣一條路呢?1989年《文學評論》第2期發表了我的《從總體文學角度認識〈文心雕龍〉的民族特色和理論價值》一文,我在文中指出:僅僅以西方文論為參照系,從中西文論的比較中來確定《文心雕龍》的歷史地位,尚缺乏一種真正世界性的宏觀眼光。西方人視西方文學為世界文學固然不對,中國人以中西兩極文學為世界文學亦不恰當。因為世界文學理論并不僅僅為西方與中國所具有。用中西對比的方法,固然也能說明一定問題,但最終不能真正確定中國文論在世界文論史上的地位。這是因為:第一,超過西方并不等于走在世界前列,尤其是在古代文學及其理論方面。第二,中西的對比研究,在很多情況下是不對等的:要么缺乏縱向的時間一致性,要么缺乏理論內涵的類同性。這種不對等性的比較,很難確定孰高孰低,孰優孰劣,“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要真正確定《文心雕龍》在世界文論史上的地位,或者說確定中國古代文論在世界文論史上的地位,不能夠僅僅以中西兩極比較或中西二元對比來加以確定,而必須以世界批評史的宏觀眼界,對世界各國、各文化/文明圈的文論一視同仁地予以重視。即:不但重視以古希臘、羅馬為源頭的西方文學理論批評,也要重視以《舞論》為代表的印度古代文論;既要充分肯定中國古代文論的理論成就,也不能忽略阿拉伯、波斯、日本、朝鮮、越南等國(文明圈)的古代文學理論與批評。只有在充分考慮了世界各國(各文明圈)的文學理論批評的基礎上,才可能真正確定《文心雕龍》(或中國古代文論)在世界文論史上所應有的歷史地位和理論價值。我的這一看法,得到了學界同仁的支持,《文學評論》1989年第2期《編后》指出:“曹順慶談《文心雕龍》的文章,為國內‘龍學’研究的沉悶局面開出了一條新門徑,作者推導的結論意見及其論述的示范作用,也是值得注目的。”香港《星島日報》(1989年1月17日)發表黃維梁教授的文章指出:“國內一位青年學者曹順慶教授,在其論文中談到《文心雕龍》的世界性地位和價值,頗能高瞻遠矚,言而中節。”我感謝學界同仁的鼓勵,同時也更加堅定了我從總體文學角度深化比較文學研究,撰寫《中外比較文論史》的信念。
為了做好前期材料準備,我先清理中外文學史。1989年,我擬出了《比較文學史》寫作大綱,試圖以總體文學的方法,融全世界文學為一體。我的設想很快得到全國各地學者的熱情支持,參加《比較文學史》撰寫者有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廈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華東師大、天津師大、陜西師大、湖南師大、西南師大、上海外國語大學、四川外語學院、深圳大學、四川大學等全國20多所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學者,其中有老一輩知名學者茅于美、豐華瞻,也有中青年著名學者如王寧、錢林森、葉舒憲、楊武能、謝天振、劉象愚、郁龍余、王曉平、何乃英等。著名比較文學家李達三(John J. Deeney)親自寫序指出:這是一部“內容深廣,人們十分需要的著作”。該書于1991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從總體文學的角度來撰寫這部《比較文學史》,克服了以往世界文學史(外國文學史)大談西方而忽視東方,或只談外國而不論中國的“西方中心”的偏向,將縱向的文學發展與橫向的交流和相互影響聯系起來,并將中國文學發展史納入其中,用縱向發展的經與橫向比較的緯,將全世界文學織成一個完滿的整體,讓讀者從縱橫兩個不同角度,更好地認識全世界文學這張完整的“網”,認識文學交流與影響在文學發展中不可忽略的巨大作用,并在比較之中更鮮明地認識各國文學的不同特征及其對世界文學的獨特貢獻,認識全世界文學的基本走向和總體特征。因而這部《比較文學史》,可以說是我用總體文學的方法來撰寫中外文學史的一次大膽嘗試,也可以說是為我撰寫《中外比較文論史》打下的一個文學史的基礎;而我打下的另外一個基礎,則是《東方文論選》的編寫工作。
因為要撰寫《中外文論史》,必須要清理東方各國文學理論,大約從1990年開始,我即開始著手編寫《東方文論選》的準備工作,當時發現國內有關東方文論的資料少得可憐。除中國文論外,情況最好的是印度文論:金克木先生曾選譯過五部印度文論資料,1980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全書僅八萬字(北京大學出版社于1993年又出版了黃寶生的《印度古典詩學》);其次為日本文論;而豐富多彩的阿拉伯文論在我國竟沒有任何一篇(部)譯文!1990年,牛枝慧同志收集了一些材料,選編了一本《東方藝術美學》,由于資料的缺乏,只能選一篇美國人撰寫的《阿拉伯文學的美學原則》。金克木先生在此書的《序》中坦率地指出:“你(指牛枝慧)選一些資料,編出這一本關于東方美學的書,顯得很單薄,恐怕也是顯示了今天我們研究的單薄。”(牛枝慧1990:8-9)面對這種狀況,我在感慨之余,決心盡快編出一本較為全面而翔實的《東方文論選》來。1991年春擬好編寫大綱之后,我專程赴京,拜訪了我仰慕的著名東方文學專家季羨林先生,季先生與我交談后非常支持,并推薦我去約請著名梵語文學家金克木先生。我與金先生長談了幾次,受益匪淺。金克木先生不但答應參加編寫,還推薦了中國社科院黃寶生研究員、伊宏研究員參加印度文論與阿拉伯文論的編寫工作。季羨林先生親自約請了北大波斯文學專家負責波斯文論的編譯。以后,我又約請了韓國高麗大學許世旭教授和正在日本作客座教授的王曉平教授以及湖南師大蔡鎮楚教授、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馬瑞瑜教授等人負責朝鮮文論、日本文論和阿拉伯文論的編選。該書幾經磨難,換了三家出版社,終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正式出版。這部70萬字的《東方文論選》,絕大部分材料是第一次譯成中文,被學界認為是第一部較全面地反映了東方各國文論概況的文論選,填補了學術界一個重要空白。季羨林先生親自擔任名譽主編,并揮筆作序,認為“讀此一書,東西兼通。有識之士定能‘沉浸濃郁,含英咀華’,融會東西,以東為主,創建出新的文藝理論體系,把中國文藝理論的研究水平,東方的文藝理論的研究水平和世界的文藝理論研究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高度和水平上”。《東方文論選》被評為“填補了我國東方文論譯介與研究的一個空白”(王向遠2003:253)。劉介民教授發表了《東方古代文論的開拓性著作》,認為“曹順慶主編的《東方文論選》,是一部東方文藝的‘開山綱領’性的著作”(劉介民2002)。郁龍余教授發表專文評介認為,該書“像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一樣,曹順慶主編的《東方文論選》在中國文論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郁龍余1998)。
在主編《東方文論選》的過程中,我本人也大大地開闊了眼界,學到了許多新東西,獲得許多學術上的啟迪。在《東方文論選·緒論》中,我曾寫下這樣一段話:美國斯坦福大學已故著名學者劉若愚(James J.Y. Liu)在《中國的文學理論》(ChineseTheoriesofLiterature)一書中指出:“我希望西方的比較文學家注意到本書提出的中國文學理論,而不再僅僅以西方的文學經驗為基礎去建構一般的文學理論(General Literary Theory)。”劉若愚教授所提出的這一看法,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但我想在此基礎上做一點修正和補充,即:西方學者與中國學者不但應當注意到中國文學理論,而且應當注意包括中國、印度、阿拉伯、日本、波斯、朝鮮、越南等東方各國的文學理論,并與西方文論相互參照比較,融會貫通,在此基礎上建構所謂一般的文學理論(或曰總體文學理論)。而不再僅僅以西方文論,或僅僅以中西文論為基礎來建構新的文論體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強調東方文論,并非是要與西方文論爭強賭勝,而是從文學理論發展的角度思考人類文學理論發展的規律,實事求是地、全面地總結人類各民族文學理論的成就,并在此基礎上,重新建構總體文學理論,這是世界各民族文學和文論發展的基本的和必然的趨向。明智地認識到這一趨向,自覺地把握、順應這一趨向,我們就能高瞻遠矚,從根本上認識人類文學理論發展的基本規律。《東方文論選·緒論》的這一段話,也正是我本人所追求的目標。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我還有一個短板需要補上,即我還沒有在西方生活過,沒有西學根底與研究實踐,我必須去歐美訪問游學,親身體會一下西方社會文化氛圍,深入理解西方文學與文論。很幸運,我獲得了霍英東教育基金會的資助,并受到美國哈佛大學、康乃爾大學等校的邀請。1992年初春,我告別妻子及幼女,飛到了大洋彼岸,先后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比較文學系、哈佛大學東亞系、比較文學系做訪問學者。在康乃爾大學,我與著名文論家艾布拉姆斯(M.H. Abrams)常常往來,受益良多,還拜訪了著名文論家喬納森·卡勒(Jonathen Culler);在哈佛大學時,我的導師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當時他既是哈佛大學東亞系系主任,同時也是比較文學系教授。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宇文教授抽煙,是用煙斗抽煙絲,他的辦公室安了一個排風扇,我去拜訪他時,一定要先看看排風扇轉不轉,如果轉,他肯定在。在哥倫比亞大學,我拜訪了著名學者夏志清,在交談中,夏教授告訴我,他對中國文學史的重要貢獻之一,是將當時大陸學者不重視的張愛玲、錢錘書寫進了現代文學史。多年以后,歷史證明了夏志清先生的遠見卓識。兩年多的異域生活與訪學,使我對西方文化與文學有了更深入的體會與理解。在哈佛大學圖書館、康乃爾大學圖書館,我查閱到許多寶貴的資料,汲取了大量學術信息。1993年,我人還在美國時,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為博士生導師,當時叫作“國批博導”,四川大學非常重視此事,因為當時中文系僅有楊師明照先生、張永言教授、趙振鐸教授和項楚教授是博士生導師,加上我才五位,恩師楊先生不斷地催促我回國,希望我能為四川大學多做貢獻。1994年暮春,我與妻子蔣曉麗(她于次年到美國康奈爾大學做訪問學者)一起,從紐約肯尼迪機場乘飛機,經香港回到成都,回到了培育我的四川大學,回到了我熟悉的書齋。
2.
回到國內后,由于我在國外的經歷,我回過頭來反思國內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研究問題,提出了兩個轟動全國學界的學術觀點,其一是“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另一個是中國文論的“失語癥”。
1995年,我在《中國比較文學》(1995年第1期)上發表了長篇論文——《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基本理論特征及其方法論體系初探》,引起了學界的關注。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比較文學在大陸剛剛復興之際,季羨林、楊周翰、賈植芳、朱維之等老一輩著名學者就多次大聲疾呼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比較文學學派,表達了中國比較文學學者共同的熱望和心聲;但另一方面,相關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建設卻相對貧弱與滯后;一些臺灣著名學者也公開批評大陸比較文學界對“中國學派”的學科理論建設“只是流于抽象的一般性的陳述”而“沒有什么建樹”。正是在這樣一種學術背景下,這篇論文引起了比較文學界的高度關注。該文一發表即在“國內外比較文學界引起極大反響,被多處引證,反復評說”(吳興明1999)。南京大學錢林森教授撰文認為“它確實是迄今為止這一話題表述得最為完整、系統、最為深刻的一次”,“令人耳目一新”(錢林森1996);劉獻彪教授認為,曹文的發表“無疑宣告了比較文學中國學派走向成熟。……不僅對中國比較文學建設和走向有現實意義,而且對比較文學跨世紀發展也將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劉獻彪1996)。該文的發表還令臺港學界對大陸比較文學界刮目相看。如臺灣師范大學著名比較文學專家古添洪稱贊該文“最為體大思精,可謂已綜合了臺灣與大陸兩地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策略與指歸,實可作為‘中國學派’在大陸再出發與實踐的藍圖”(古添洪1998)。
然而,就在“中國學派”的討論在比較文學界逐步深入的同時,我又提出了中國文論的“失語癥”問題②。1996年,我在《文藝爭鳴》發表《文論失語癥和文化病態》一文,引起學界高度關注。論文的基本觀點是:長期以來,中國現當代文藝理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話語,處于文論表達、溝通和解讀的“失語”狀態;中國文論患上了嚴重的“失語癥”,沒有一套自己的文論話語,一套自己特有的表達、溝通、解讀的學術規則,我們一旦離開了西方文論話語,就幾乎沒辦法說話;這種“失語癥”是一種嚴重的、隱而難見并將遺患深遠的文化病態;是中西文化劇烈沖撞(甚至可能是極為劇烈沖撞)的結果,是“五四”以來文化大破壞的后果之一;在世紀之交,認識到這種文化病態,能夠引起學界的警醒,促使他們真正理解“重建中國文論話語”是一項跨世紀的重大命題,并著手尋求具體的重建路徑與方法,以及通過文論話語的批評實踐來證實其方法的可操作性;認識并重視“中國文論失語癥”,具有巨大而深遠的現實意義與歷史意義(曹順慶1995,1996)。很快“失語癥”的呼聲在中國古代文論、文藝理論以及中外文論研究界引起巨大反響,眾多專家學者都認為這是一個關系到中國文化發展戰略以及中國文學批評理論之命運的重大問題。在世紀交替之際,《文學評論》、《文藝研究》、《文學遺產》、《外國文學評論》、《文藝理論研究》、《文史哲》、《文藝評論》、《人文雜志》、《東方叢刊》、《中國比較文學》、《中外文化與文論》、《河北學刊》、《社會科學研究》等眾多刊物以及一大批高校文科學報,發表了有關失語癥、古代文論現代轉換以及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等方面的大量文章,形成一道頗為壯觀、亮麗的學術景觀,以至于有學者將我提出的“‘失語’問題”視為1996年10月中國中外文化文藝理論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等單位在陜西師大召開“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學術研討會的“導線”,由此“拉開了古代文論現代轉換討論的帷幕”(蔣述卓、閆月珍2002;程勇2001)。提出的關于中國文化與文論的“失語癥”及重建中國文論話語問題,是一個具有重要學術原創性的、在全國產生了廣泛而深遠影響的重大理論問題。我先后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文藝爭鳴》、《文化中國》(加拿大)等重要刊物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在學術界引起極大反響與熱烈討論。中國文論“失語癥”問題,獲得季羨林、敏澤、錢中文、張少康、羅宗強、蔡鐘翔、黃維樑等諸多著名學者不同程度的呼應;也有許多反對的意見。羅宗強教授(南開大學)在《文藝研究》1999年第3期發表的《古文論研究雜談》中指出:“三年前,曹順慶先生提出文學理論研究最嚴峻的問題是‘失語癥’,同一時期他又提出醫治此種‘失語癥’的辦法是重建中國文論話語。而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途徑,主要是借助于古文論的現代轉換。對于文學理論界來說,這個問題的提出確實反映了面對現狀尋求出路的一個很好愿望。因為他接觸到當前文學理論界的要害,因此引起了熱烈的響應,一時間成了熱門話題。”“失語癥”一石激起千層浪,贊成者有之,反對者有之,其引起的學術論爭已經遠遠超出了這個口號本身。支持者認為,失語癥的提出接觸到當前文學理論界的要害并有利于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探討。我在《文藝爭鳴》發表《文論失語癥和文化病態》一文,也成為高引用論文,被引量為286。
在學術界的熱烈論戰中,我更加感受到必須加快我構思多年的《中外比較文論史》的撰寫。因為很多的論戰,其實是不了解世界文論全貌造成的。不言而喻,這部《中外比較文論史》是一項難度極大的大型學術工程,寫這種文論史,需要花費比專題研究或國別文論史大得多的心血和精力,而且很容易吃力不討好。連羅素(Bertrand Russell)這樣的大學者,其名著《西方哲學史》亦難免于此,所以羅素在《西方哲學史》美國版序言中辯解道:“關于任何一個哲學家,我的知識顯然不可能和一個研究范圍不太廣泛的人所能知道的相比。我毫不懷疑,很多人對于我所述及的任何一個哲學家都比我知道得多。然而,如果這就成為應該謹守緘默的充分理由,那么結果就會沒有人可以論述某一狹隘的歷史片斷范圍以外的東西了。”(羅素1963:1)中國古代著名文論家劉勰,在其“體大而慮周”的《文心雕龍》中,也深有感觸地說:“夫銓序一文為易,彌綸群言為難,雖復輕采毛發,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可勝數矣。”羅素與劉勰所慨嘆的“彌綸群言”之難,還僅僅是指同一文化圈內的哲學史或文論研究而言;要想撰寫跨越幾大文化/文明圈的文論史,那就更是難上加難了,這簡直就是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課題。因為這里面涉及一系列的文化差異與異質文化的可比性問題。因此,這部《中外比較文論史》,特別注重了文化探源性的跨文化比較研究,這是我在比較文學方法論上的又一著力的方面。一般而言,文論史大多論述“是什么”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文論史,只要將“是什么”說清楚,把各家文論思想觀點交代明白,也就達到目的了。但作為跨文化研究的《中外比較文論史》,如果僅僅論述“是什么”,總讓人覺得不愜于心。在最初的撰寫中,我尤為強烈地感受到了這一點。于是,我調整了撰寫大綱,將文化探源式的跨文化比較研究,作為本書一項重要內容;在論述“是什么”的同時,進一步探索“為什么”。我力圖從“意義的產生方式”與“話語解讀方式”和“話語表述方式”等方面,尋求東西方各異質文化所賴以形成、發展的基本生成機制和學術規則,并從意義的生成來源、生成方式、解讀方式和話語言說方式的探索之中,進一步清理文論范疇群及其文化架構、文化運作機制和文化發展規律。由于這種文化探源式的研究,是從文化基本生成規律和學術運作規則入手,因而不但具有探本求源的意義,而且具有明顯的可操作性,是一條追尋東西方文化生成運作機制和規律的切實可行的路徑。從這條路徑,我們不但可以比較東西方各異質文化圈的不同文化精神,而且可以總結出各類文化生成與運作規律。這種規律,不僅可以加深我們對東西方文論特征的認識,而且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可以給當今的文學理論建設提供一種“活的”文化運作機制和規則。只要我們能真正認識到這種文化運作機制與規則,那么不但可以回答“為什么”的問題,而且還可以為建構新的文論體系,或者說建構一般的(或總體的General)文論體系提供若干“活生生的”學術規則和運作方式,而不僅僅是提供一堆“死的”材料和人物。作為文論史固然要借鑒古人,要研究“秦磚漢瓦”、“古希臘、羅馬”、“吠陀、奧義書”等等“死的”材料,但我們更需要從生生不已的文化傳統中尋求其文化生成方式與運作規則,發現其“活的”文化生成方式與運作機制。同時,也只有在探索其文化生成方式與運作機制的同時,才可能真正進行深入的跨文化的比較研究,真正回答清楚東西方文化為什么會“分道揚鑣”的基本原因;也才可能真正認識東西方各異質文化的不同路徑、文論特色及其互識的必要性和互補的巨大價值。
因為當前中西文論對比研究不對稱的,這種尷尬狀況主要原因是缺乏差異比較的學理基礎,比較的結果當然也就是可疑的,比較的意義也就是有限的,這就從根本上背離了比較文學“可比性”的學術規范。如果單單從理論內涵的類同性對中外文論進行比較的話,在漫長的人類文論的發展史上就會出現極大的跳躍性,打亂時間的一致性,可比性原則同樣會遭到破壞,因此,我選擇了以時間的縱向一致性來對東西方文論進行比較分析,這樣,至少在比較文學的可比性這一點上取得了相對的合理性。近年來,盡管我的學術思路有所調整,但關于這個課題的研究我卻是一直堅持差異性也應當可以比較的觀念,唯有如此,中外文論的比較研究才有可操作性。于是乎,我又開始了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研究,提出了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比較文學變異學理論研究兩個重要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問題。
3.
在堅持多年的《中外文論史》編寫過程中,我發現不研究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不行了,因為中外文論研究中的許多問題都與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密切相關,不搞清楚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比較詩學研究也無法真正深入展開。在研究中,我逐漸發現,我國當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一個嚴峻問題是缺乏自己的、切合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與教學實踐的學科理論。正是這種理論的缺乏,導致了中國當代比較文學研究中出現的許許多多問題以及學科發展上的徘徊與茫然,甚至導致學科發展的危機,如淺層次的比較和“X+Y”的比較。因此,我決心下一番功夫研究比較文學的學科理論,希望能夠解決比較文學研究中的一些問題。我發現,一些問題的出現并不是因為原有的學科理論(或者說是西方引進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發生了錯誤,而是原有的學科理論不能適應中國現狀了。以前的法、美學派都是在同屬古希臘羅馬文化的歐洲文化圈內的比較,在跨越了中西方文明之后已經變得有些水土不服。也就是說,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必須有自己的學科理論才能解決中國自己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我曾在《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發展的三個階段》中講比較文學第三階段的特點進行了概括,其中一條就是跨異質文化。比較文學的前兩個發展階段是在同一文明圈內進行的,而一旦突破這個文明圈,西方原有的學科理論就不行了,如美國著名的比較文學學者韋斯坦因堅決反對將文學的比較擴展到兩種不同的文明。而中國學者一開始面對的就是不同文明,所以,我提出了跨文明比較文學研究,沒有這個意識,真正的全球化的比較文學研究是不可能的。
比較文學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差異性問題。如果我們只是一味地求同,顯然是不行的,還必須求異。以前是求不同中的“同”,而現在是要求不同中的“不同”,而且應當將差異放在最為重要的位置。但這并不代表我們不要向西方學習了,因為,前兩個階段的學科理論,如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形象學研究等等,還是可取的,并不是一無是處。這些理論可以拿過來作為我們的學科理論的一部分。因此,學習西方一是可以積累我們自己的知識,二是可以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實現我們自己的創新。
異質性的強調已經成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一個突出特征,中國人文學術的創新也需要在異質性的基礎上進行。對于異質性的討論也成為近年來學術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影響研究與平行研究共同的缺憾,都在于只重視求同性,而忽視了不同文明間的差異性、異質性。“首先,影響研究與平行研究都是建立在‘求同’的基礎之上,他們是求不同中的同:求不同國家中的類同、不同學科中的共同。影響研究的可比性建立在‘同源性’基礎之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建立在‘類同性’基礎之上。這種‘求同’的理論模式,并不完全符合比較文學的基本事實和客觀規律。因為法國學派所強調的以‘國際文學關系’為核心的‘影響研究’,其變異性要大于類同性。即便是在美國學派強調的以‘類同性’為共同規律的‘平行研究’與‘跨學科研究’中,也存在著大量的變異現象。”(曹順慶2008)正因為影響研究與平行研究有著共同的求同性局限,所以當影響研究與平行研究的方法論實踐不久之后,就會出現學科危機,使比較文學學科的發展陷入難以避免的窘境。由于缺乏變異研究的理論認知、理論總結和方法論探討,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和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不是限制了自身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成果,就是導致由局限而陷入無邊論的泥潭。經過長期的思索,我正式提出了比較文學變異學理論,并于2006年在《復旦學報》2006年第2期發表《比較文學學科中的文學變異研究》,指出:“變異學是指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的文學現象在影響交流中呈現出的變異狀態的研究,以及對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的文學相互闡發中呈現的變異,探究比較文學變異的規律。變異學研究的重點在求‘異’的可比性,研究范圍包括跨國變異研究、跨語際變異研究、跨文化變異研究、跨文明變異研究、文學的他國化研究等方面。”幾個方面共同構筑起變異學的理論體系。2014年,我的比較文學英文專著TheVariationTheoryofComparativeLiterature(《比較文學變異學》)由國際著名出版社Springer在海德堡、倫敦、紐約同時出版,受到國際學界廣泛關注。歐洲科學院院士多明哥(Cesar Dominguez、美國科學院院士蘇源熙(Haun Saussy)等著名學者合著的比較文學專著(Dominguez & Saussy 2015)高度評價了曹順慶提出的比較文學變異學,美國普渡大學A&HIS期刊《比較文學與文化》(ComparativeLiteratureandCulture)專門刊發了專家書評(Wang 2013)對該書給以好評。變異學為比較文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可行的新方向,它既保證了學科邊界的科學性、合法性,又大大拓展了研究方法與研究視角;既打破了求同性思維模式和研究模式的局限,將差異性作為比較文學可比性的重要研究內容,既能集中體現比較文學中國學派治學的方法論特點,又為世界比較文學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拓展了國際比較文學新的空間,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學科理論奠定了學理基礎。2005年,我獲得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外比較文論史》又成為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項目,促使我進一步加快了寫作進度。2012年,該書終于出版,共計260萬字,分為四卷。澳門大學黃維梁(2014)教授為此書寫了長篇書評,指出:《中外文論史》耗時 20 多年,凡四卷共八篇,連目錄、前言、參考書目、后記,共約 4180 頁,是皇皇巨著,是中外迄今唯一一本涵蓋中外文學理論的史書。主編者曹順慶把世界的文學理論史以古希臘、中國、印度作為第一個階段開始,共劃分為七個階段,每個階段占一編的篇幅,一個階段為時三數百年。”“此書涵蓋的國家有中國、希臘、印度、羅馬、埃及、阿拉伯、波斯、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朝鮮、越南、泰國、美國,跨越歐亞非美四洲,跨越不同的文明。在視野、規模方面,遠非William Wimsatt和Cleanth Brooks的AShortHistoryofLiteraryCriticism,以及René Wellek的AHistoryofModernCriticism所能企及。此書的總體性、全面性、宏觀性厘然可見。”“如果目前漢語的國際性地位可與英語看齊,或者如果此書有英語等外文譯本,那么,這部宏微并觀、縱橫比較、內容富贍、析評精彩、彰顯中國文論價值的《中外文論史》,就是在國際文論學術界響亮‘發聲’了。”
如果從1990年算起,我寫此書共計用了22年,人們常常說十年磨一劍,我這部書磨了22年!人生易老,我從一個36歲的年輕人,已經磨成了60多歲的老年人!然而,我并不后悔,因為本書的撰寫,踏踏實實地強化了我的學術根底,實實在在地推進了我的學術研究,磨礪了我的學術人生,尤其重要的是,撰寫這樣一部大書,讓我在全世界文論資料探幽覽勝的同時,發現了許多學術創新問題,我本意僅僅是為了編寫《中外比較文論史》,結果派生出一部又一部的學術專著,生發出如此多的學術創新問題,這些創新問題成了我在比較文學研究道路上一個又一個學術創新的起點,成了我學術生涯一個又一個里程碑。四川大學將我評為“杰出教授”,與院士同等待遇,我還獲得國家級教學名師獎等等各種獎勵和榮譽。2014年,我擔任了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我感到光榮的同時,更加感到責任重大:“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遠!”
附注
① 分別刊載于《江漢論壇》1981年第6期、1982年第5期、第11期以及《文藝研究》1983年第4期和《中國比較文學》創刊號。
② 據羅宗強先生考證,雖然王一川、張新穎分別于1991年和1993年在文學研究中涉及“失語癥”問題,但“他們都不是直接談論文學理論國際對話中的失語問題”,是“曹順慶先生正式談論此一問題”。參見羅宗強《古代文論研究雜識》注釋①,載于1999年《文藝研究》第3期。
參考文獻
Wang, N.2013.Variation theory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book review article about Cao’s work [J].ComparativeLiteratureandCulture15(6): 18-7.
Dominguez, C. & H. Saussy.2015.IntroducingComparativeliterature:NewTrendsandApplication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曹順慶.1995.21世紀中國文化發展戰略與重建中國文論話語[J].東方叢刊(3):21-31.
曹順慶.1996.文論失語癥和文化病態[J].文藝爭鳴(2):50-58.
曹順慶.2008.變異學: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重大突破[J].中山大學學報(4): 34-40.
程勇.2001.對九十年代古文論研究反思的檢視[J].江淮論壇(3): 86-93.
古添洪.1998.中國學派與臺灣比較文學的當前走向[A].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墾拓(黃維梁編)[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63-177.
蔣述卓、閆月珍.2002.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古代文論學術活動述評[J].福州大學學報(1):34-38.
劉介民.2002.東方文論的開拓性著作——讀曹順慶主編的《東方文論選》[A].中外文化與文論(錢中文主編,第9輯)[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366-375.
劉獻彪.1996.比較文學中國學派與比較文學跨世紀發展[J].中外文化與文論(2):137-138.
羅素.1963.西方哲學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
牛枝慧.1990.東方藝術美學[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錢林森.1996.比較文學中國學派與跨文化研究[J].中外文化與文論(2):139-142.
王向遠.2003.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二十年[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吳興明.1999.理路探微:詩學如何從“比較”走向世界性——對曹順慶比較詩學研究的一種解讀[J].中國比較文學(3):78-88.
郁龍余.1998.舊紅新裁熠熠生輝——簡評《東方文論選》[J].外國文學研究(1):48-50.黃維梁.2014.宏微并觀縱橫比較彰顯中國——曹順慶主編《中外文論史》評介[J].中國比較文學(1):199-203。
(責任編輯管新潮)
主持人語:
兩年前,楊楓主編創建了一個“外語朋友圈”的微信群(目前已有500個成員)。群內成員都是外語界的學者,以中國大陸為主,遍布世界各地。群中常有學術討論,但是限于微信形式和成員學術方向不同,討論難以集中和深入。鑒于此,楊楓教授提議擬定一些議題,開幾場更有重點和針對性的專題討論會。美國馬里蘭大學的蔣楠教授提議“語言和思維關系”這個題目,并得到一些成員的首肯。于是,楊楓主編另建了一個“《當代外語研究》語言與思維微論壇”的微信群。恰逢在“六一兒童節”這天迎來了我們的首場專題討論。這種形式在國內外語學界尚屬首創——通過微信朋友圈成立由學者們自愿組成學術共同體,以平等對話的方式交流學術思想,碰撞靈感的火花、更新知識、拓展視野。
在開始討論問題之前,我想引用著名哲學家江怡的話簡要闡明我們微論壇的特點和意義。
江怡教授曾經在他的《對話和交流是學術的生命》一文中指出:無論古今中外,對話始終是思想產生的一個重要法寶……蘇格拉底通過對話的方式,與對話者進行互相質問,由此尋求暴露對話者各種觀點中的沖突,并在反思這些沖突以及關于它們的可能答案的基礎上重建這些信念……對話的前提在于平等,這不僅是學術地位上的平等,更是思想上的平等。真理并不取決于地位權勢的高低,也不取決于接受人數的多少,真理存在于交流和對話的過程之中。這就意味著,對話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對話的一方最終說服對方,而是在于對話各方的互相理解,因而寬容的精神和虛心的態度始終是對話的基本原則。
江怡先生還說:學術作為天下的公器,總是以追求真理為己任。但真理并不在學術之外,而正是在學術的對話和交流之中。由此,對話和交流就構成了學術的生命:沒有對話和交流,學術就成了學者們玩于股掌的游戲;沒有對話和交流,學術就成了學者們孤芳自賞的戀癖。只有在對話和交流中,學術才能真正成為天下之公器。道理不說不透,真理不辯不明。
因此,希望微論壇能為外語學界吹進一股清風,為學者開展平等對話和交流提供一個和諧、共享、開放的平臺。
作者簡介:曹順慶,四川大學文科杰出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電子郵箱:shunqingcao@163.com 周頻,英語語言學博士(后),上海海事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認知神經語言學、語言哲學、語言科學研究方法論。電子郵箱:pinzhou@shmt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