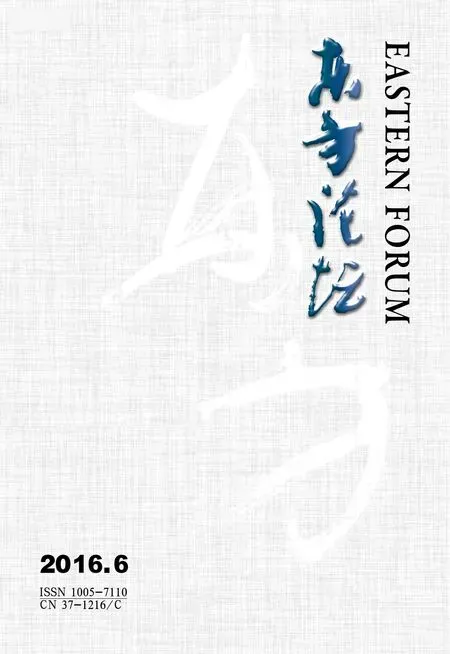戰國秦代“西—雍”交通
王 子 今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北京 100872)
戰國秦代“西—雍”交通
王 子 今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北京 100872)
編者按:
這組論文是2014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秦統一及其歷史意義再研究”(14ZDB028)的階段性成果,作者試圖從行政史、交通史等不同視角考察秦統一問題,分別有所收獲。秦統一的重要主題是度量衡的統一,相關論文考察了若干具體問題。漢代人對秦史記憶猶新,他們以親身感受獲得的知識,描繪了當時人的秦史認識。后人的秦史記憶以及秦史判斷,也是我們研究秦史不可以忽略的重要的歷史文化信息。
“西”與“雍”之間的交通聯系,在秦交通史進程中具有至為重要的地位。這條交通線路對于秦的立國、崛起以及后來實現統一,意義重大。秦始皇兼并天下后第一次出巡,應當經行這條交通線的部分路段。“西—雍”交通在漢代依然受到重視。“西—雍”道路,其實也是自關中平原中部向西實現與西域聯系的“絲綢之路”交通系統的構成內容之一。
西;雍;交通;秦統一;秦始皇;馳道
“西”與“雍”都曾經是秦國崛起時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兩地之間的交通聯系,在秦交通史進程中具有至為重要的地位。這一交通道路對于秦的立國、崛起以及后來實現統一,表現出極其重要的意義。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出巡,應當經行這條交通線的部分路段。秦實現統一后,“西”“雍”共同的神學影響,使得執政者頻繁往來“西—雍”恭敬禮祀,促成這條交通線路的建設和養護,應達到帝王乘輿順利通行的水準。西漢時期,這一情形依然繼續。受到高度重視的“西—雍”交通線,其實也是自關中平原中部向西實現與西域聯系的“絲綢之路”交通系統的構成內容之一。
一、“西—雍”早期交通
秦人有重視交通的悠久傳統。[1]據《史記·秦本紀》,“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關于“汧渭之間”,張守節《正義》:“言于二水之間,在隴州以東。”[2](P177)秦人的產業經營,發展空間已經由長江流域的西漢水上游轉移至黃河流域的“汧渭之間”。這一變化應當與聯系“犬丘”與“汧渭之間”兩地的交通道路開拓有關。從“好馬”“主馬”及“馬大蕃息”等記載看,這一交通線路的使用,或許已經以“馬”作為主要運輸動力。
秦襄公時代,秦人向東進取的交通行為又明確見于《秦本紀》的記載:“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這成為秦立國的重要契機。秦襄公“始國”后,“祠上帝西畤。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秦襄公東行“救周”之后,又回到“西”“祠上帝”。隨后又東進“伐戎”。從“至岐,卒”的文字,可知秦襄公大概在“岐”去世。《秦本紀》又記載:“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十年,初為鄜畤,用三牢。……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2](P179)看來秦人當時往來“西—岐”之間,似乎并不需要克服很嚴重的交通困難。
還應當注意,導致“秦襄公將兵救周”的“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這一民族史與戰爭史事件[2](P179),其實也可以看作交通史信息。也就是說,“西戎犬戎”“伐周”的軍事行為,也曲折體現出秦人之外的西北少數民族對這一交通線路建設的歷史貢獻。
二、“西”與“雍”的畤
秦人對于“畤”的設置和經營,表現出與東方諸國神學信仰有所不同的極具個性的文化精神。司馬遷記述相關歷史事實時所謂“僭端見矣”的評論,透露出人們對于秦人作“畤”行為其背后的文化意義的重視。關于秦諸畤的陸續設立,《史記·封禪書》中可以看到這樣的記錄: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暤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駵駒黃牛羝羊各一云。[2](P1358)
這是史籍記載最早的白帝紀念的記錄。裘錫圭研究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子羔》篇有關商得金德傳說的內容引錄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事,指出:“《封禪書》記秦人祀神之事頗詳,當有秦人記載為據。如此處所記無誤,則早在東西周之交,以少皡為白帝的說法即已存在。”[3]秦人的“西畤”經營與“始國”的歷史變化直接相關。《史記·秦本紀》:“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駵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司馬貞《索隱》:“襄公始列為諸侯,自以居西,西,縣名,故作西畤,祠白帝。畤,止也,言神靈之所依止也。亦音市,謂為壇以祭天也。”[2](P179)秦襄公雖然已經得到“岐以西之地”,卻仍然“自以居西”,“故作西畤”。《史記·封禪書》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事之后緊接著又記載:
其后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縉紳者不道。
此后有“陳寶”之祠的設立,“作鄜畤后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封禪書》又記載:
作鄜畤后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后子孫飲馬于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于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御蠱菑。①關于“磔狗邑四門,以御蠱菑”的理解,參看王子今:《秦德公“磔狗邑四門”宗教文化意義試說》,《中國文化》總12期,又《周秦文化研究》,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德公立二年卒。其后四年,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2](P1358-1360)
畤,作為秦人基于自己神學理念的文化發明,在上古信仰史上有重要的地位。隨著秦人東進的足跡,神祠建設的新格局又在東方得以開創。于是出現了“西”“雍”禮祀共同對象的畤。[4]畤由“西”而“雍”的營造,一方面體現了進取精神,一方面體現了對傳統的堅持。從交通史的視角觀察相關現象,也是有意義的。
三、《史記》“西雍”辨正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為郎中令,任用事。”隨即有關于“始皇廟”的討論:
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群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
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群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
所謂“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之“西雍”,張守節《正義》:“西雍在咸陽西,今岐州雍縣故城是也。又一云西雍,雍西縣也。”[2](P266)
張守節《正義》提出了兩種解說:第一:“西雍在咸陽西,今岐州雍縣故城是也。”第二:“又一云西雍,雍西縣也。”其實,“西雍”應斷讀為“西、雍”。是說“西”和“雍”。
“西”,在天水禮縣。這里發現了秦早期遺跡,其中包括祭祀建筑基址。《漢書·地理志下》:
隴西郡,秦置。莽曰厭戎。戶五萬三千九百六十四,口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二十四。有鐵官、鹽官。縣十一:狄道,白石山在東。莽曰操虜。上邽,安故,氐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為漢。莽曰亭道。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浸。予道,莽曰德道。大夏,莽曰順夏。羌道,羌水出塞外,南至陰平入白水,過郡三,行六百里。襄武,莽曰相桓。臨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禹貢》西頃山在縣西,南部都尉治也。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莽曰西治。[5](P1610)
其中有關“西”的內容值得重視:“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莽曰西治。”
《史記·秦本紀》:“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復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張守節《正義》:“《水經》云:‘秦莊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與大駱犬丘之地,為西垂大夫。’《括地志》云:‘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漢隴西西縣是也。’”[2](P178)明確指出其地在“漢隴西西縣”。
所謂“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應當讀作“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理解此說,應關注“先王廟”分置于“西”“雍”“咸陽”的事實。
四、“西”“雍”神祀中心
自春秋時期起,中原以外地方政治勢力崛起,即《史記·周本紀》所謂“齊、楚、秦、晉始大”[2](P149),《史記·秦本紀》 所謂“齊、晉為強”[2](P183),《史記·齊太公世家》所謂“唯齊、楚、秦、晉為強”[2](P1491),《史記·匈奴列傳》 所謂“當是之時,秦晉為強國”。[2](P2883)
這些原先處于邊緣地位的政治實體迅速強盛,出現了《荀子·王霸》所謂“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的局面。[6](P205)
戰國七雄的遷都方向則多顯示向中原靠攏的趨勢,說明中原在統一進程中的文化重心地位重新受到重視。秦由西而東的遷都方向尤其典型。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秦人的神祀重心實現了由西向雍繼而向咸陽的轉移。
這與秦向東發展的戰略方向是一致的。“西—雍—咸陽”神祀重心的變化,也符合秦“公—霸—王—帝”的政治影響力上升的歷史進程。
據前引《史記·秦始皇本紀》,在“始皇廟”營造之前,“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而位于“西”“雍”的其他諸神祠,如《史記·封禪書》記載:
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余廟。①《漢書·郊祀志上》顏師古注:“風伯,飛廉也。雨師,屏翳也,一曰屏號。而說者乃謂風伯箕星也,雨師畢星也。此《志》既言二十八宿,又有風伯、雨師,則知非箕、畢也。九臣、十四臣,不見名數所出。諸布、諸嚴、諸逐,未聞其義。逐字或作逑。”(《漢書》卷二五上《郊祀志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207頁)西亦有數十祠。
所謂“西亦有數十祠”,司馬貞《索隱》:“西即隴西之西縣,秦之舊都,故有祠焉。”這些“廟”“祠”,“各以歲時奉祠”。《封禪書》還寫道:“雍菅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2](P1375)②《漢書·郊祀志上》顏師古注:“其鬼雖小而有神靈也。”(《漢書》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1207頁)“雍……百有余廟。西亦有數十祠。”形成了兩個神祀重心。這一情形在西漢時依然得以繼承。《漢書·郊祀志上》說,漢興,“(高祖)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5](P1210)
“各以歲時奉祠”的制度,要求“西—雍”之間必須有高等級的交通道路。這一道路的建造和養護,應保證良好的通行條件。
五、“西—雍”“通權火”的可能
《史記·封禪書》記載,秦漢諸畤間禮祀活動曾經采用“通權火”的信息發布形式,在“上不親往”的情況下傳遞敬意:
唯雍四畤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畤,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塞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月祠,若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骍,秋冬用駵。畤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于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親往。
“通權火”,裴骃《集解》:“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絜皋矣。其法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漢祠五畤于雍,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司馬貞《索隱》:“權,如字,解如張晏。一音爟,《周禮》有‘司爟’。爟,火官,非也。”[2](P1377)
以“烽火”“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是利用光的傳遞速度的一種特殊的信息交通方式。這種形式秦時已經采用①詳見王子今:《秦“封”試探》,《秦陵秦俑研究動態》1997年第2期;王子今:《試說秦烽燧——以直道軍事通信系統為中心》,《文博》2004年第2期。,漢世仍然繼承,“漢祠五畤于雍,五里一烽火”。“雍”與“咸陽”之間的這種信息傳遞形式,由下文“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親往”推想,“西”與“雍”之間,也很有可能采用。
六、秦始皇二十七年出巡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述秦實現統一之后秦始皇第一次出巡: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2](P241)
按照《史記·貨殖列傳》表達的經濟地理學理念,“隴西、北地”與關中同屬于一個經濟區:
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2](P3262)
《貨殖列傳》的文字強調了三點:1.“與關中同俗”;2.“畜牧為天下饒”;3.“地亦窮險”。這樣,從三個方面分析了這一地區的文化、經濟、交通地位:“與關中同俗”,指出與“關中”區域文化的類同;“畜牧為天下饒”,指出曾經成為秦富國強兵的重要條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指出這里與東方聯系必須經由“京師”,然而另一方面,東方包括“京師”與西方的聯系,也必須利用這里“窮險”的交通條件。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相關內容顯示的“大關中”的區域觀念,也是將“隴西、北地”看作“關中”的共同經濟地理與文化地理構成的。[7]
近年考古學者發現秦比較集中的早期遺跡的甘肅甘谷、清水、天水地方,就在隴西郡。甘肅禮縣發掘的祀所遺址,有的至西漢初期仍然進行祭祀活動。②參看梁云:《對鸞亭山祭祀遺址的初步認識》,《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5期;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國家博物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學文博學院編著:《西漢水上游考古調查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90—291頁。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西巡,應當視察了“秦之舊都”與故祠。
《史記·秦始皇本紀》關于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政事的記述僅僅只有88字: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③裴骃《集解》:“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漢書·賈山傳》曰:‘秦為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筑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41—242頁)
最后說到“治馳道”。而“治馳道”,是非常重要的行政舉措。馳道的修筑,是秦漢交通建設事業中最具時代特色的成就。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巡隴西、北地”后即宣布“治馳道”,因而開啟了在中國古代交通史進程中意義重要的全國交通建設的宏大工程。“治馳道”的設計,應當最初與“隴西、北地”交通規劃有關。現在看來,秦始皇此次出巡中經歷“窮險”交通條件的切身體驗,很可能即這一決策的形成緣由。④參看王子今:《秦始皇二十七年西巡考議》,《文化學刊》2014年第6期,后收入《秦文化探研:甘肅秦文化研究會第二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5年。
值得注意的是,與秦始皇實現統一后第一次出巡相對應,漢武帝“始巡郡國”,也來到隴西北地。《史記·平準書》記載:
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于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于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2](P1438)⑤《漢書·食貨志下》:“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辯,自殺。行西踰隴,卒,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于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于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漢書》卷二四下《食貨志下》,第1172頁)
而《漢書·武帝紀》的記載是:“(元鼎四年冬十月)行自夏陽,東幸汾陰。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5](P183、185)《資治通鑒》卷二〇的處理方式,則將“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與“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以及“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于是誅北地太守以下”分隸元鼎四年(前113)和元鼎五年(前112):“(元鼎四年)冬,十月,……是時,天子始巡郡國;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元鼎五年)冬,十月,上祠五畤于雍,遂逾隴,西登崆峒。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惶恐,自殺。于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于是誅北地太守以下。”[8](P660、665)可以看到,漢武帝元鼎五年(前112)的這次出巡,幾乎完全遵行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西巡舊跡。值得注意的是,河東太守和隴西太守均因交通服務條件“自殺”,北地太守也因為軍事交通系統建設未能達到要求被“誅”。盡管漢武帝西巡的目的應當與秦始皇有所不同,但是兩者路線相當接近,值得交通史和區域文化史研究者深思。①參看王子今:《秦始皇二十七年西巡考議》,《文化學刊》2014年第6期,后收入《秦文化探研:甘肅秦文化研究會第二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5年。
考察秦交通史,必須重視秦始皇“治馳道”的歷史作用。而“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的交通實踐的意義,自然應當有所肯定。“西—雍”道路的交通條件中不能使得新的統一帝國的最高執政者滿意之處,可能也會激怒秦始皇,使得責任者“惶恐”不安;但是其優越之處,則亦有可能成為全國“治馳道”重要交通建設規劃的藍本。
[1] 王子今.秦國交通的發展與秦的統一[J].史林,1989,(4).
[2] 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3] 裘錫圭.釋《子羔》篇“銫”字并論商得金德之說[Z].武漢:“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2006”論文,2006.
[4] 王子今.秦人的三處白帝之祠[A].早期秦文化研究[C].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5] 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6]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8.
[7] 王子今.秦漢區域地理學的“大關中”概念[J].人文雜志,2003,(1).
[8] 司馬光.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6.
責任編輯:侯德彤
The Xi-Yong Transportation in the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and the Qin Dynasty
WANG Zi-jin
( The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Research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Unearthed Documents and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Beijing 100872, China )
The traffic link between "Xi" and "Yong"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transportation history of the Qin Dynasty. This transport line is of great signifi cance for the founding, rise and unifi cation of Qin. First Emperor of Qin had the fi rst inspection tour after absorbing the other kingdoms, and should have followed this section of the line. The Xi-Yong route was still highly valued in the Han Dynasty. This road, in fact, was also part of the Silk Road connecting Guanzhong Plain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Xi, Yong; transformation; unifi cation of Qin; First Emperor of Qin; ancient driveway
K231
A
1005-7110(2016)06-0001-05
2016-10-08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秦統一及其歷史意義再研究”(14ZDB028);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中國古代交通史研究”(10XNL001)
王子今(1950-),男,河北武安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教授,陜西理工大學漢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