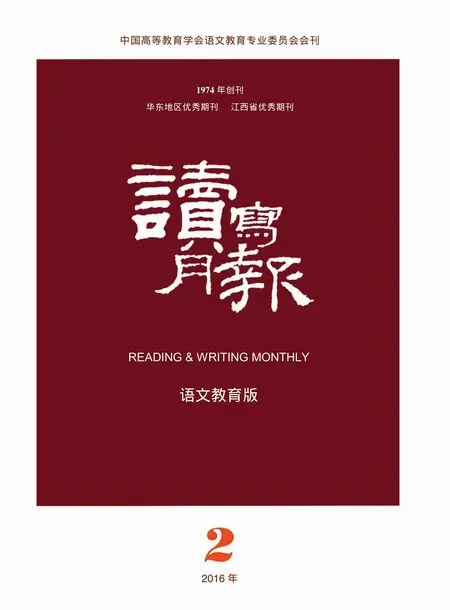和諧生態的呼喚,綠色未來的守望
——論胡冬林的生態散文集《狐貍的微笑》
符鵬
和諧生態的呼喚,綠色未來的守望
——論胡冬林的生態散文集《狐貍的微笑》
符鵬
滿族作家胡冬林的生態散文集《狐貍的微笑》是新世紀生態散文的一部力作。這部生態散文集以樸素的生態智慧和先進的現代生態理論為思想基礎,以吉林長白山原始森林中的各種動植物為表現重心,運用平視的眼光和清新自然的語言,逼真地把生機盎然的原始森林的現場展現給讀者;同時,又以高度的生態責任感和生態使命感為引領,探尋原始森林的野生生命的存在意義和價值,批判人類對原始森林動植物的破壞,呼喚對待動物的倫理,探索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可能途徑,守望綠色未來。
生態散文;生態倫理;和諧生態;綠色未來
新世紀以來,我國的生態環境惡化問題進入高頻高發階段,人們的生態意識日益提高,生態文明建設為生態文學的創作提供了豐富而深厚的土壤,越來越多的作家積極投身于生態散文的創作,其中的代表作家有:徐剛、李存葆、韓少功、周曉楓、詹克明、白忠德和胡冬林等;同時,也誕生了一批優秀的生態散文集,如《山南水北》《大自然從未離開》《空釣寒江》《誰為人類懺悔》《獸部落》《我的秦嶺鄰居》和《狐貍的微笑》等。這些生態散文作家和生態散文作品共同推動著新世紀生態散文進入到深化發展階段。其中,滿族作家胡冬林的生態散文集《狐貍的微笑》發揮了其自身獨特的作用。
胡冬林(1955-),滿族扈什哈里氏,吉林長春人,當代散文家。受喜愛森林的父母潛移默化的影響及受自然書籍的熏陶,他自小熱愛自然、憧憬山林生活。1995年起,胡冬林每年都會抽出兩三個月的時間走進東北的“白山黑水”進行文學采風。其中,長白山原始森林保護區是他采風的主要區域。為了實現自身能夠每天與森林、溪水、動物為伴的愿望,以及開拓自身新的文學創作生活的愿景,胡冬林從2007年5月初至今長期租住在長白山腳下的二道白河鎮體驗生活,過著半個森林人半個寫作者的生活。只要天氣允許,他幾乎“每天進入原始森林,認花識鳥記樹辨蘑菇;尋訪獵手、挖參人、采藥人、伐木者,聽他們講述放山打獵和野生動物的故事;感受自然四季美景和動植物生活,了解森林生態系統奇妙而復雜的關系……”[1]充分運用自身所有的感官在原始森林保護區中找尋、迎接、遭遇和思索原始森林中時時處處出現的各種驚喜。而且,在行走于原始森林的過程中,胡冬林還與長白山原始森林中的一切生靈平等、和睦地相處,積極地以實際行動守護原始森林保護區,探索野生世界生靈的生存真諦。因而,胡冬林被譽為“中國離野生動植物最近的作家”。
十二年深入東北白山黑水間進行文學采風及近十年深入林區體驗生活的經歷,為胡冬林的生態文學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原始森林的各種動植物為他提供了豐富的創作材料和不竭的創作源泉,如森林中的狐貍、星鴉、黃金鼬、山貓、水獺、松鼠和熊等各種動物,以及香菇、羊肚菌、灰樹花、紅蛤蟆菌、亞側耳、平蓋靈芝、紅松等各種植物都是胡冬林生態散文的主人公。正如胡冬林在散文集“后記”中所言:“這座森林于我是創作源泉,心靈寄托,神圣之地。”[2]在長白山的原始森林體驗生活期間,胡冬林的生態散文創作結出了較為豐碩的果實。其中,生態散文集《狐貍的微笑》就是其代表成果之一。這部森林生態散文集按照創作時間排序,共收集了《青羊消息》《拍濺》《原始森林手記》《約會星鴉》《蘑菇課》《黃金鼬》《山貓河谷》和《狐貍的微笑》等八篇精品長篇生態散文,這些生態散文運用審美的語言和藝術化的形象為長白山原始森林的動植物深情畫像,多維度闡釋了長白山原始森林保護區的生態文化。并且,這部散文集配有約百張長白山原始森林動植物、自然風光精美圖片,集精美散文、生態科普、攝影作品、戶外經驗等于一身,作品內涵較為豐厚。其中,尤以蘊含的生態意蘊最為突出。這部生態散文集以樸素的生態智慧和先進的現代生態理論為思想基礎,以吉林長白山原始森林中的各種動植物為表現重心,在歷史和現實的對照中,運用平視的眼光和清新自然的語言,逼真地把生機盎然的長白山原始森林的現場展現給讀者,探尋原始森林生靈的存在意義和價值,揭示野生世界與人類共生共榮的生態關聯。同時,面對成片的原始森林被砍伐、野生動物被殘忍獵殺和原始森林保護區污染日趨嚴重的現實,作者又以高度的生態責任感和生態使命感為引領,將其氣憤和悲痛之情刻畫紙上,生態批判、預警和呼喚之聲顯現于散文之中,充分地展現了作者自覺的生態意識、深沉的生態正義感和深廣的生態情懷。
首先,生態散文集《狐貍的微笑》蘊含著深沉的批判精神和反思精神,強烈批判了人類對原始森林動植物的破壞。
胡冬林在長白山原始森林體驗生活的過程,也是發現問題的過程。面對人類反生態的行為和思想文化,作者既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積極保護原始森林,又以散文創作形式批判和反思人類對野生世界的破壞。生態散文集《狐貍的微笑》在歷史和現實的對照中,多層面揭露了人類對原始森林的侵擾,批判了人類的急功近利對原始森林造成的無法估量的破壞,表達了對野生世界動植物未來的憂慮,充滿了強烈的反思精神和批判精神。“僅僅不到200年的捕獵,長白山的野生動物已到了滅絕的邊緣。從冰河期以來東北地區隨處可見的東北虎、禿鷲和青羊等當地動物物種正變成明天的古生物。”[3]“在長白山的這兩年,我耳聞目睹很多人把長白山保護區當成搖錢樹,大搞所謂的旅游開發,在保護區砍倒1400棵大樹蓋五星級別墅;鏟光珍稀的溫泉瓶兒小草建溫泉廣場;在小天池放魚苗,想把小天池變成養魚池。這些魚苗大吃珍稀的兩棲動物極北小鯢的卵,竟長到2-4斤重;砍光500畝人工林,興建占用1500畝以上林地的國家早已明令禁止興建的高爾夫球場。 ”[4]
散文不僅批判了人類為了一己私欲破壞自然生態的行為,還深刻地剖析了反生態的思想文化。生態散文集《狐貍的微笑》著重批判了唯發展主義和消費主義等反生態的思想文化對原始森林保護區的破壞。散文中指出,一些人在唯發展主義觀指導下,為發展而發展,一味追求自身經濟效益,不顧原始森林保護地區的生態效益,進而導致中國現在唯一一片寒溫帶原始森林不斷遭受到原始漂流、林下參養殖、打松子、采蘑菇、養林蛙創收、抓蛤蟆等人類活動的侵擾,野生動植物賴以生存的環境不斷被侵占,原始森林中的動物也遭受持續獵殺,如當地每年被吃掉的和被販賣的熊掌,數目實在讓人觸目驚心。胡冬林指出,消費主義文化對野生動物的傷害尤為巨大,一些人為了滿足自身奢侈性的消費,間接使得原始森林的野生動物不斷受到獵殺。“無論獵狐養狐,都是為了取皮,給人類做衣裳。一張狐裘大衣需用狐皮7-14張,一張狐皮外套需用狐皮4-8張。”[5]“街里的許多飯店可以點清燉榛雞,180元一大盤。我親眼見過,盤中盛放著兩只國家二級保護動物。”[6]面對人類為了滿足自身不合理消費使得野生動物慘遭殺害的現實,作者悲憤而痛苦地寫道:“當最后一棵樹被砍倒,最后一只動物被殺,最后一條魚被捕,最后一道河中毒,人們啊,你們吃錢嗎?”[7]面對野生動物不斷遭到獵殺的客觀事實,面對野生動物種類和種群不斷縮小甚至徹底消失的現狀,作者高瞻遠矚地針對長白山原始森林的一些動植物發出生態預警,科學地預見一些動植物可能面對的災難:“野生棕熊在東北乃至在我國滅絕,只是個時間問題。主要原因有兩個:一個是獵殺屢禁不止;另一個是持續不斷地開發,人為干擾日益加重,導致它們的棲息地大面積消失。更何況棕熊數量太少,它們找不到配偶或已經開始近親交配,棕熊正一步步走向末路”。[8]而人類長期對長白山原始森林地區的嚴重破壞,更使熱愛自然的胡冬林深受震撼,面對人類對原始森林的暴行,作者決絕而憤怒地聲明:“當人類與野生世界發生沖突時,我永遠站在野生世界這一邊。”[9]這展現了胡冬林作為一位生態散文作家身上具有的生態正義感和生態責任感。
其次,散文集《狐貍的微笑》秉承著眾生平等的理念,呼喚倫理地對待動物。
作者堅持敬畏生命的理念,認為應將倫理學范疇延伸到動物身上,人與動物應該和睦平等地相處。生態散文集《狐貍的微笑》以生態倫理關照原始森林中的動物,不僅詳細描寫了棕熊、兀鷲、水獺、山貓、黃金鼬、狐貍等幾十種動物的生存環境、生活習性、生存智慧和生存行為,例如捕獵、交配、分娩、哺乳、爭斗和領地之爭等等;還多維度闡釋了動物與森林生態系統、人類之間的共生共榮的生態關聯,指出任何動物都應有平等的存在價值,具有自身固有的內在價值和對自然生態的外在價值,而不是僅僅具有所謂的工具價值,更不能以人類對動物的價值觀作為衡量標準。“生物的存在即合理,況且以人類的庸俗價值觀衡量,狐除了消滅大量危害林木的智齒動物外,采食的大量漿果種子隨糞便排出,成為一個漫游四方的播種機。可見狐貍是森林健康的守護者。一座森林若沒有狐貍,這座森林將逐漸顯露出生態失衡所帶來的影響。”[10]由此可見,每個野生動物不僅具有其自身存在的價值,對于森林生態系統它也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同時,散文中指出,每個野生動物也具有自身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人類不要打擾和干涉野生動物的生活,人類應該給予野生動物基本的尊重。“從大道理講,整個保護區的原始森林乃至整個長白山,全部屬于世世代代在此居住的各種野生動物。人類——不管你是誰,在這里都只是一個令森林原住民十分討厭的匆匆過客。 ”[11]
當然,倫理地對待動物不能僅僅局限于野生動物,即使是非野生的動物也依然具有自身尊嚴和內在價值。正如美國著名動物倫理學家湯姆·雷根所言:“那些與我們有關的動物(如,我們要捕獵的、食用的那些動物)與此情況一模一樣,它們也必須看做是生命體驗主體,具有它們自己的固有價值。”[12]針對膽熊吃人事件,散文中寫道:“不要說動物兇殘,在對動物的虐待和獵殺方面,人往往比動物更無情也更兇殘。膽熊被囚禁終生,取膽汁受苦終生,人靠它們發財,最后竟不給它們喂食,連懷孕的母熊也不給吃的。”[13]呼吁人們不要虐待動物,認為每個動物也有作為生命本身的尊嚴,倫理的范疇不應只適用于人類,而應該擴展到一切生靈。最后,散文中指出理想型的人與動物的關系應該是“兄弟”般的親密。“我與山上的狐貍是兄弟,人類與四海之內的野生動物也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兄弟——親兄弟。”[14]人類與生俱來就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動物在很久以前就是人類的鄰居,作為大自然進化最為完美的人類應該給予動物充分的尊重,人與動物的關系可以是兄弟般的關系;而且,這種良好的關系不但有利于動物的保護,而且對人類自身也大有益處。正如史懷澤所言:“我們越是觀察自然,就越是清楚地意識到,自然中充滿了生命,每個生命都是一個秘密,我們與自然中的生命密切相關。人不能再僅僅只為自己活著。我們認識到,任何生命都有價值,我們和它不可分割。出于這種認識,產生了我們與宇宙的親和關系。”[15]散文集《狐貍的微笑》體現出了一位有擔當的知識分子寬廣的生態視野和深沉的生態責任感,也體現了一位生態散文作家對動物博大而無私的愛。
最后,散文集《狐貍的微笑》還探索了人與自然生態和諧相處的可能途徑。
作者面對原始森林不斷遭受侵占、污染和破壞的現實,以高度的生態使命意識為引領,同時基于自身近20年的原始森林采風經歷、經驗以及自身具備的深厚鳥類學、植物學、動物學、魚類學、昆蟲學、氣候學等相關知識,嘗試指出人與自然生態和諧相處的可能途徑、守望綠色未來。首先,胡冬林指出人類應該停止獵殺和虐待動物。“只要人類停止殺戮和虐待動物,讓它們自由自在生活,它們將很快忘記人類對它們犯下的血腥暴行,重新與我們和諧相處。”[16]因為“人類是野生動物的最終消滅者和奴役者。只要人類導致一個動物物種在自然界中的對手或天敵滅絕,自己取而代之,或者在自覺不自覺中成為一個頂級動物物種如熊、虎、豹、鷹等物種的捕殺者,那么,人類會被這一物種認定為最大的敵人。這個結論將被印刻在動物的遺傳密碼中被一代一代傳下去”。[17]只有停止殺戮和虐待才能消除動物對人類的恐懼和仇恨,人與動物和諧相處才有基本可能。同時,這也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最基本的起點。
散文指出,人類不應干涉野生世界動物的生活。“自然界發生的任何死亡與新生、繁盛與衰落、枯萎與萌發、傷病與健康、悲痛與狂歡都是進化的一部分,只要人類不加干涉,萬物各有其生存之道與生死定規。”[18]互不干涉的原則不僅適用于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處,也可以適用于人類與野生世界之間的相處。當人類把動物也視為一個個獨立的生命主體時,人與動物之間的對立沖突才能被瓦解,人與動物才能真正和諧相處。因而,人類不去干涉野生世界動植物的生活看似無所作為,其實對于野生世界的動植物而言卻是“大為”,這其中蘊涵著深邃的生態智慧,不失為一條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可能途徑。散文中也列舉了客觀事實予以證明這一途徑的現實可能性及其有效性,“自2006年在保護區采松子的禁令實施后,第三年迎來松子大收年,星鴉種群隨之迅速壯大,黑熊、野豬、狍、松鼠等動物數量明顯增多。事實證明,只要人類不去破壞和干擾這片中國唯一的溫帶原始森林,自然萬物在數億年進化史形成的自我修復與再生的神奇活力將重新煥發出來,再過二十年、三十年,必將出現點石成金般的奇跡”。[19]
散文同時指出,人類應該幫助自然界的動植物守護它們的領地。“五年了,母山貓和我做了五年鄰居。這五年我不曾動搖,你也仍在固守。那就讓我們繼續下去,我和你,守護這條山谷,守護我們共同的領地。”[20]事實上,人類本來就屬于大自然的一部分,人類也需要依存大自然,守護野生動植物的領地,也是在守護人類賴以生存和生活的環境,守望人和動物共同的綠色未來。
總的來說,作者在生態散文集《狐貍的微笑》中指出的人與自然生態和諧相處的可能途徑具有一定的建設性和科學性,對于當前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也有一定的啟發和借鑒價值。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在行走于原始森林的過程中,時時處處通過自身的實際行動為保護野生世界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胡冬林既是大自然的觀察者、生態文學的寫作者,又是保護自然生態的行動者。如,多次發現原始森林保護區周圍的火情,并及時報案,看守火場直至滅火隊趕到;多次向國家有關部門實名舉報偷獵者和當地環境破壞者;還有,2012年6月24日,胡冬林通過微博實名舉報長白山發生連殺五熊的慘案,并接待各路采訪這一事件的記者,協同有關部門調查長白山原始森林保護區熊的分布情況,向當地政府提出防范偷獵者的相關建議,最終使得原始森林保護區的生態保護工作也出現了全新局面。綜合而言,胡冬林不但通過生態散文創作守望綠色未來,而且以自身的實際行動捍衛人與自然生態和諧相處,充分體現了一位“森林之子”的生態正義感和生態使命感。他是無愧于現代生態文明的推動者,無愧于我們這個時代的守望者。
胡冬林多年長期深入原始森林保護區體驗生活、醉心于生態文學創作,生態文學的寫作也與他的生活方式以及個體生命的存在形態逐漸融為一體。他的生態散文寫作不是從原始森林外來者的視角表現自然生態,也不是簡單從原始森林外部觀察和描寫野生世界,而是自覺以森林大家族中一員的視角來表現生機盎然的野生世界,自發以生態倫理觀照原始森林的動植物。正如文學評論家雷達所言:“我覺得胡冬林寫作的意義不僅僅是外來者的深入生活,他把自己作為一個森林人,在探尋生命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我覺得這與那種常見的來自文明社會的綠色保護者,或探險者,或拯救者是不同的。后者總帶著啟蒙或教化的企圖,而胡冬林完全沒有,他幾乎與山里人無區別。”[21]在此視角下,作家運用充滿靈性的文筆多角度呈現原始森林的原生態面貌,詳實描繪多種動植物細節的同時,還以體驗原始森林現場為基礎,用“在場主義”和“非虛構”的寫作方式真實描寫長白山野生世界的動植物,引領讀者與他一起進入神秘、野性的原始森林現場,行走于那混亂而有序、豐富多彩的“原生態生活”,因而他的生態散文極具真實性。
不僅如此,胡冬林的生態散文寫作還以先進的生態理念為指導。他認為“生存環境關乎生存與毀滅,當下的動物寫作不同以往,必須揭示動物主人公的生存之道與森林外物互惠互利、共生共榮的進化奧秘,使讀者去了解、尊重、呵護它們,進而思考如何珍惜我們身邊的環境”。[22]作者在樸素的生態智慧和先進的現代生態理論的指導下,創作了一系列純正而又極具自身特色的精美生態散文,進而使得這些生態散文具有生態意義。總之,胡冬林的生態散文寫作方式和寫作理念是較為具有新意的,也是值得借鑒的。他的生態散文在一定程度上不僅體現了新世紀生態散文寫作的新境界,還豐富了生態文學的創作理念和寫作方式。并且,他的生態散文寫作不但對長白山原始森林的生態保護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于整體意義上的生態文明建設也具有一定的價值。
注釋:
[1][2][3][4][5][6][7][8][9][10][11][13][14][16][17] [18][19][20][22]胡冬林:《狐貍的微笑》,重慶出版社,2012年,第 112頁,第 330頁,第 3頁,第 76頁,第318頁,第 76頁,第 18頁,第 79頁,第 332頁,第307頁,第162頁,第116頁,第325頁,第322頁,第118頁,第260頁,第153頁,第286頁,第284頁。
[12][美]彼得·辛格、湯姆·雷根:《動物權利與人類義務》,曾建平、代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22頁。
[15]陳懷環、朱林:《天才博士與非洲叢林——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阿爾貝特·史懷澤傳》,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6頁。
[21]雷達:《他發出真正的天籟之音——談胡冬林的生態散文》,《作家》,2013年第15期,第5頁。
(作者單位:江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編輯:李運 隨喜
責任編輯: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