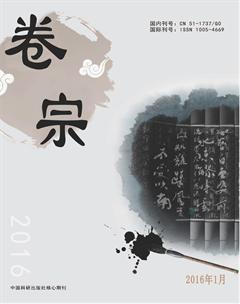檢察機關訊問錄音錄像的錄制規(guī)制研究
劉文娟
摘 要:作為我國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新刑事訴訟法正式確立了訊問錄音錄像制度,這有利于規(guī)范偵查訊問和遏制刑訊逼供等取證行為,保障公民個人的合法權益。但該制度在立法上只是原則性規(guī)定,操作性較弱,證據(jù)規(guī)則內(nèi)容缺失。結合我國司法實際和借鑒國外立法經(jīng)驗,有必要從訊問和錄制規(guī)則等方面進行補充完善。
關鍵詞:檢察機關;訊問錄音錄像;錄制規(guī)則;完善對策
科學的制作程序和要求,有助于訊問錄音錄像全面客觀固定證據(jù),增強其可采性。我國新刑事訴訟法僅規(guī)定了偵查訊問錄音錄像應全程進行,保持完整性,但對具體的制作主體、監(jiān)督機制和方式等要求均未涉及,有必要加以完善。
1 訊問錄音錄像的訊問與錄制主體
從證據(jù)材料的一般制作過程來看,偵查人員既是訊問行為的實施主體,也是該證據(jù)材料的制作主體。而訊問錄音錄像的主要功能在于規(guī)范偵查機關的取證行為,加上其又容易被通過剪接、復制等手段加以篡改,決定了其訊問主體應與制作主體之間相分離,否則難以保障該證據(jù)材料的客觀真實性。目前,我國公安機關在偵查訊問過程中并未普遍采取錄音錄像,對自身錄音錄像的訊問與制作主體相分離工作進行的并不多。新刑事訴訟法頒布施行后,公安機關在對于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偵查中,應當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當下,建議公安機關借鑒檢察機關工作經(jīng)驗,建立偵查訊問錄音錄像訊問與制作相分離的機制: 訊問由偵查人員負責,不得少于二人,錄音錄像由專門人員負責; 偵查、錄制人員應當適用刑事訴訟法有關回避的規(guī)定。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的人員,不得參與錄制工作。從長遠看,為保障立法中所確立的訊問錄音錄像制度目的能夠落到實處,改革偵查機關在內(nèi)部所建立的訊問與制作主體分離模式,將錄制主體由羈押犯罪嫌疑人的看守所等部門實施,待經(jīng)驗成熟時,將看守所等羈押部門劃歸司法行政部門管轄,以實現(xiàn)訊問與錄制主體的真正分離。
2 訊問錄音錄像的監(jiān)督機制
將訊問錄音錄像的訊問主體與制作主體相分離,是為了通過內(nèi)部監(jiān)督機制,防止偵查訊問人員濫用權力。但從監(jiān)督的效果來看,適當?shù)耐獠勘O(jiān)督,尤其是來自當事人、辯護人和律師的監(jiān)督不僅有助于保證訊問錄音錄像的真實性,而且有利于實現(xiàn)當事人對案件的知情權,在更大意義上推進刑事訴訟過程的公開化和民主化。新刑事訴訟法既然已明確將律師介入偵查階段的身份定義為辯護人,雖在立法上沒有建立訊問時的律師在場制度,但可在實踐中實驗建立訊問錄音錄像在場制度。在訊問結束后,偵查人員對訊問錄音錄像的封存不僅要由偵查人員、制作人員、犯罪嫌疑人進行親自簽封,而且辯護律師也應簽封。當然,這種監(jiān)督方式在立法和實踐中存在兩個障礙: 第一,偵查機關在對犯罪嫌疑人訊問之前必須告知其有權聘請律師,請求訊問錄音錄像時的在場權; 第二,在偵查訊問錄音錄像時,若犯罪嫌疑人無力聘請辯護律師時,司法機關要及時為其指定免費援助律師。結合我國立法和司法資源實際,建議對于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實行律師訊問錄音錄像在場制度,若當事人無力聘請律師時,偵查機關應為其指定援助律師; 若其能夠支付起在場律師的費用,但不愿聘請,可視為放棄該項權利。
3 訊問錄音錄像的進行方式
新刑事訴訟法雖規(guī)定錄音或者錄像應當全程進行,保持完整性,但對訊問過程的起止如何界定、誰有權界定等問題沒有明確規(guī)定。目前,我國偵查機關在訊問錄音錄像實際操作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xiàn)為:把當事人打服了再帶入訊問室錄音錄像;利用當事人上廁所的時間對其進行刑訊逼供;在錄音前先對當事人進行“預訊問”,待事實交代清楚后再進行錄音錄像;利用當事人在看守所被羈押期間,通過看守所的工作人員對其刑訊逼供;在訊問之前先跟嫌疑人對好口供,把訊問全程先過一遍,然后再打開鏡“演戲”,進行錄制。因此,為保證訊問錄音錄像資料的完整性和客觀真實性,建議采取下述措施。一是訊問錄音錄像要以能夠反映偵查訊問過程的全貌和全景為原則,在錄音錄像設備可全程監(jiān)控的范圍內(nèi),不僅要包括犯罪嫌疑人,還要有偵查訊問人員及訊問時的重要場景。在錄音還是錄像方式的采用上,應以錄像為原則,錄音為例外;二是偵查機關的錄音錄像內(nèi)容不僅包括訊問過程,還應包含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強制措施后直至訊問前的全過程,在有關的警車上也應安裝錄像設備,確保犯罪嫌疑人不在錄像的盲區(qū);三是訊問過程中如果發(fā)生停電、機器故障等特殊情形,影響訊問錄音錄像的完整性,應當中止訊問,并在訊問記錄中作出說明和解釋;四是在有合理理由時,被告人可以該證據(jù)材料未能反映訊問全部場景,缺乏客觀性為由,申請鑒定人鑒定和法庭予以排除的權利。偵查機關對被告人的該主張承擔舉證責任,否則訊問筆錄不具有可采性。
4 訊問錄音錄像適用的案件范圍
新刑事訴訟法采取了選擇性的規(guī)定,把訊問錄音錄像強制實施的案件范圍確定為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以及其他重大犯罪案件。這其中既考慮到錄音錄像的技術和設備要求以及經(jīng)濟成本,又考慮到這些案件的疑難復雜性、犯罪嫌疑人權利保障的重要性及案件本身的社會影響度。但在實踐操作中會出現(xiàn)以下問題:一是在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之前,如何判斷一個案件為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以及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如現(xiàn)場抓獲的搶劫犯、恐怖犯罪等,但有些案件沒有經(jīng)過偵查訊問,無法判定其案件的復雜程度和所涉犯罪可能判處的刑罰。二是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以及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是個不確定的概念。三是刑事訴訟是個動態(tài)過程,偵查、檢察、審判人員對案件事實的認識是個漸進的過程,對犯罪嫌疑人將會判處的刑罰和案件的復雜程度的認識同樣是個漸進的過程。在訊問過程中采取了錄音錄像,即使是法院宣判其無罪或所處以的刑罰輕于死刑、無期徒刑,這與立法上的要求沒有沖突之處,但偵查人員若一開始在訊問過程中沒有進行錄音錄像,而犯罪嫌疑人卻被判處無期徒刑或死刑,那么之前所制作的訊問筆錄是否應具有法律效力、偵查行為是否有效等一系列問題就值得思考。為彌補立法上的缺陷,建議:一是在新刑事訴訟法實施的前五年,將我國刑事實體法中規(guī)定有可能判處死刑、無期徒刑的罪名加以羅列,用列舉的方式確定偵查訊問應采取錄音錄像的案件范圍;對重大犯罪案件的判定標準進行細化。二是新刑事訴訟法實施五年后,制約我國偵查機關偵查訊問錄音錄像技術和經(jīng)濟成本的因素應當說在全國范圍內(nèi)已不存在,雖然立法上并沒有要求偵查機關對所有刑事案件的偵查訊問采取錄音錄像方式,但司法解釋部門可通過證據(jù)制度立法的完善,將更多關于偵查訊問行為合法性的舉證責任分配給偵查機關,加大該取證方式的適用,最終實現(xiàn)偵查訊問以全程錄音錄像為原則,不適用為例外。
參考文獻
[1] 蘇奕帆.偵查訊問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制度的現(xiàn)狀分析及完善建議[J]. 法制與社會. 2015(33).
[2] 閔春雷.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適用問題研究[J].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14(02).
[3] 王秋杰.偵查訊問同步錄音錄像制度的細化完善[J]. 遼寧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 201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