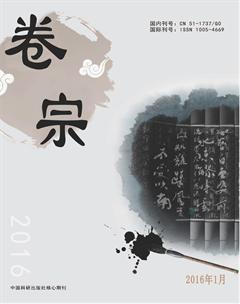從改寫理論視角分析《野騾子》的翻譯策略
摘 要:二十世紀中期以來,翻譯理論的研究開始逐漸將視角從語言學層面轉向文化層面。在此期間產生的操控學派,其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爾,提出翻譯不僅是語言層面上的轉換,更是譯者對原作進行的文化層面上的改寫。本文通過改寫理論對美國漢學家葛浩文對莫言的小說《野騾子》翻譯的探討,得出結論:英譯本在某種程度上說是譯者對源文本的一種改寫。在本論文中改寫體受到了兩個方面的影響:意識形態和詩學。
關鍵詞:操縱理論;葛浩文;野騾子
對翻譯作品介紹:莫言,是中國最著名的當代作家之一。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他創作了一系列關于鄉土生活的作品并且迅速地獲得了國際知名度。《野騾子》就是莫言的一篇中篇小說,它收錄于中篇小說集《師傅越來越幽默》中。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同年《紐約客》雜志刊載了由美國漢學家葛浩文翻譯的Bull 一文。葛浩文是莫言作品在英語世界的主要譯者,由他翻譯的莫言的作品在英語世界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但他的翻譯并非完全忠實于原作。在翻譯的過程中,考慮到讀者的接受力等因素,葛浩文對原作進行了大量的改寫,這些改寫即包括了情節的刪減和增加,也包括了敘述順序的改變。本篇論文將利用這一理論來進行分析。
理論基礎:本篇論文所采用的理論基礎是安德烈·勒菲弗爾所提出的改寫理論。安德烈·勒菲弗爾提出的改寫理論創新性地對翻譯活動中意識形態、詩學與贊助人等因素進行了分析。在他的著作《翻譯﹑改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控制》中,勒菲弗爾提出了改寫這一概念。根據他的理論,文學作品的翻譯,改寫,文學批評,編訂選集等一系列的活動都屬于改寫,所以,采用他的理論來研究翻譯中的改寫是合理的。
就他提及的三個方面而言,首先,關于意識形態指的是“社會應該是(被允許是)的形式”,更具體的定義在他的著作中這樣寫道“意識形態是形式,習俗,信仰的綜合,它對人的行為產生影響。”;其次,關于詩學,詩學指的是“文學應該是(被允許是)的形式” ;最后,關于贊助人,贊助人是指“能促進或抑制讀,寫及文學作品改寫的權力擁有者”。比起詩學來,“贊助人關注的常常是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方面的改寫:人作為社會動物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會環境當中,總是受一定的意識形態的影響。而根據勒菲弗爾的理論,文學作品的改寫主要由兩個基本因素決定,其中之一就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可能是源自于譯者本身,也可能是源自于贊助人。而意識形態具體是指對人的行為產生影響的信仰,習俗等綜合因素。
由于意識形態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文學翻譯。在葛浩文的翻譯中,許多的例子都說明了意識形態是怎樣影響和操控他進行翻譯的。在接下來的部分當中,就將進行例證分析。
例1: 村里人有罵他的,有貼小字報攻擊他的,也有寫人民來信控告他的,但擁護他的人遠比反對他的人多。(莫言, 2012:205)
Some villagers spoke out angrily and some attacked him on wall posters, calling him a member of the retaliatory landlord class, which was intent on overthrowing the rule of the village proletariat. But talk like that was out of fashion. Over the village P.A. system, Lao Lan announced, “Dragons beget dragons, phoenixes beget phoenixes, and a mouse is born only to dig holes.” (Goldblatt, 2012:67)
在莫言的原作中的一句話被葛浩文增補了很多原文沒有的信息而成為了一段話。加入的內容是階級斗爭色彩非常濃厚的一段話“叫他(老蘭)是地主階級中的報復份子,妄圖推翻村民的無產階級統治”。結合原文與譯者的翻譯,我們可以看出故事顯然發生在文革結束不久的一段時間里。村民們不滿老蘭往豬肉牛肉里注射福爾馬林賺了大錢,于是采取了“小字報”這種階級斗爭的方法發些情緒。在翻譯中,葛浩文卻增補了“推翻無產階級統治”,把村民們的言行明顯放大了。從某種程度上這是為了迎合西方讀者的需求。葛浩文知道西方讀者對于這段歷史懷有一種隔岸觀火的好奇感,于是他夸大了村民的行為,使譯文呈現出這樣的安排。
詩學方面的改寫:根據勒菲弗爾的理論,詩學“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各種文學手法、題材中心思想人物原型和場景,以及象征等;二是文學在整個社會體制中的作用。后一方面在決定選擇何種與社會體制相關的文學作品的主題才能使作品引起注意時特別具有影響力。”
例2:我仔細地打量過那兩頭小豬,它們身上可吃的肉實在是有限,但它們那四只呼呼喀喀的大耳朵還能拌出兩盤子好菜…(莫言, 2012:208)
I took a long look at the pigs—it was true that there wasnt much meat on either of them, but those four fleshy ears would have made for good snacking. (Goldblatt, 2012:68)
同樣,在此處,“我”為豬耳朵著迷,認為它們的大耳朵能拌出兩盤“好菜”,在葛浩文的翻譯中變成了“點心”。這也很顯然是因為西方人沒有食用豬耳朵的習慣,所以為了照顧英語讀者的閱讀習慣,譯者并沒有把豬耳朵當成是一種正式的菜來翻譯。
結論:本文采用安德烈·勒菲弗爾的改寫理論,分析了莫言中篇小說《野騾子》的英譯本,得出了《野騾子》在被翻譯成為英語的過程中,受到意識形態和詩學的影響。受意識形態影響表現在翻譯者極力發掘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對中國思維和言行的改變,強化這些情節,從而迎合西方讀者的閱讀興趣。受詩學影響則表現在翻譯者把很多帶有中國文化特色而英語世界并不強調的事務和詞匯弱化或者改變,使其在西方讀者看來可以接受。
參考文獻
[1]譚載喜.中西現代翻譯學概評[J].外國語,1995(3).
[2]季進.我譯故我在—葛浩文訪談錄[J].當代作家評論,2009(06).
[3]胡安江.中國文學“走出去”之譯者模式及翻譯策略研究—以美國漢學家葛浩文為例[J].中國翻譯,2010(6).
[4]莫言.野騾子[A].師傅越來越幽默[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
[5]Lefevere, André.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4.
[6]Goldblatt, Howard. Bull[J]. The New Yorker, 2012 (11).
作者簡介
朱未弟(1991-),男,湖南,碩士,翻譯理論及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