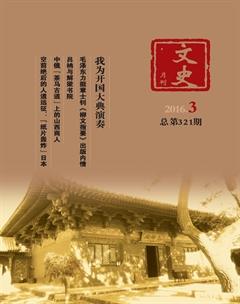中晚唐進士的“入幕”風氣
王洋
在科舉制已大體確立,并成為選拔官吏主要途徑的唐代,進士及第是當時士人們投入畢生心血所追求的目標,并成為選拔高級官吏時考量其出身的最主要標準。唐人有“進士初擢第,頭上七尺焰光”之說,可見進士登科在士人心中乃至整個唐代社會中都具有“登龍門”般的效應。京師應舉的舉子人數眾多,韓愈稱“以千數”,但每年實際錄取的人數只有幾十人,可見進士考試的高淘汰率。值得關注的是,正是在對進士出身推崇備至的中晚唐時期,卻有許多進士及第的文人進入各地的藩鎮“幕府”擔任幕僚。相對于中央朝廷,分布于各地的藩鎮具有濃重的軍事色彩,“基層”的軍事政務也無疑是繁重而瑣碎的。唐代士人素來有著“重京官而輕外官”的觀念,緣何幕府對于這些飽讀詩書的才子們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天之驕子” 爭相入幕
唐代時,科舉考試成為中央和地方選拔人才的主要手段。早在隋代,“其法既極弊而不可挽救”的九品中正制便已逐漸被統治者擯棄,隋煬帝“始建進士科”,但僅限于“試策”方面。唐代的進士科顯然更為重要,已成為中下層文人得以仕宦的主要途徑,同時也是中晚唐時期選拔高級官員最主要的來源。據統計,進士在宰相人數中的比重,從安史之亂后肅宗時的三分之一左右,至貞元、元和年間進士出身者在宰相中完全“占據絕對優勢”,懿宗時21名宰相中有20人俱是進士出身。相較于中晚唐時備受推崇的進士一科,明經科與門蔭入仕等途徑則在高級官員的選拔方式中被逐漸排擠和淡化。明經科依舊開設,但影響和社會評價已遠遠不能與進士科抗衡。《劇談錄》中載李賀以“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譏諷上門結交的元稹,可見時人對“明經擢第”者甚至有輕視之意。與明經等科黯然失色相比,“進士及第”的身份在唐人心目中可謂是至高無上的榮耀。中晚唐時期的進士一朝及第,社會地位將會迅速攀升。中晚唐時期的社會各階層對于進士的重視和推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所謂“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許多文人為考取進士焚膏繼晷,殫精竭慮,更有年逾七十依舊熱衷科舉者。天復元年,曹松等五人及第,“皆年逾耳順矣,時謂‘五老榜’。”總之,作為舉子中選拔出的精英人才,在進入仕途時較之明經和其他“雜科”出身者,從資歷、地位以及社會聲望等方面看,都更具有優勢。
恰恰在中晚唐時期,不僅是掌握科舉選拔權力的中央,日漸崛起的藩鎮也在不遺余力地招攬精英人才。安史之亂后,藩鎮的數目和規模迅速擴大,至唐亡時約有四五十個。藩鎮幕主開設的幕府中不僅有為數眾多的武官,更需要有文官來從事案牘工作,輔佐藩帥。對于考中進士的士子來說,唐代的銓選制度規定了進士及第后并不能直接授官,絕大多數新晉進士的文人必須在相當長的守選期內等待,吏部銓選是他們最為普遍的入仕之路,但官闕數量有限,相形之下,以藩鎮之多,幕府之廣,需求的人才數量自然也是巨大的。一些進士會在幕府的熱情招攬下選擇離開京師,進入幕府供職。杜牧出身京兆杜氏,祖父杜佑是三朝宰相,可謂門第顯赫。大和二年(828年)杜牧進士及第,同年便入江西觀察使沈傳師幕。“沈傳師廉察江西宣州,辟牧為從事,試大理評事”,杜牧自述“我烈祖司徒岐公與公先少保友善,一見公喜曰‘沈氏有子,吾無恨矣’”。可見其之所以成為藩鎮僚佐,與幕主的招攬有很大關系。對一些社會公認的才子,藩鎮幕主甚至會采取強硬手段“搶奪”人才。令狐楚弱冠及第,才名遠播,藩鎮幕主多有禮聘之意,“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才,欲以禮辟召,懼楚不從,乃先聞奏而后致聘。”藩鎮幕主“求才若渴”的急迫心態可見一斑。
進士們投入藩鎮的另一現實誘因是藩鎮豐厚的俸祿待遇。中唐曾有多道詔令規定進士可以蠲免賦稅和徭役,姚合感嘆“闕下科名出,鄉中賦籍除”,唐代進士雖享有一些政策上的優待和特權,但是一些家庭貧寒的進士仍舊難以擺脫入不敷出的困境。王泠然描述自己進士及第后的狀況,“兄弟未有官資,嗷嗷環堵,菜色相看,貧而賣漿”,雖有促狹之意,但仍從側面說明了家貧進士的經濟狀況未能因及第而迅速改變。進士及第也意味著巨大的開銷,慶賀及第的宴請繁多,“一春之宴”往往耗費萬錢,一些進士由于貧寒而“苦于成名”。進士需要解決及第后尚未任官時的生計問題,因此進入幕府的情況十分常見。大中五年(851年),李商隱受劍南東川節度使柳仲郢禮聘任節度判官。幕主“賜錢三十五萬以備行李”,詩人自謙“尚遙玉帳,已賚金錢。”“古求良材,必有禮幣。”一方面幕主對進士們不惜重金相邀,另一方面,進士們雖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然而匱乏的經濟狀況和無法馬上獲得官職和俸祿導致的現實困境令他們暫時放下為朝廷供職的訴求。且從財力來看,藩鎮幕僚在俸祿上往往比同級別朝官具有優勢,這些都是促使守選進士和郁不得志、無法升遷的任滿進士遠赴藩鎮的重要原因。
還有一些進士是迫于時勢,不得不離開朝廷而避入幕府。《容齋續筆》中載“劉蕡對策,極言宦官之禍……考官見蕡策,皆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劉蕡落選,皆因對策矛頭直指宦官。甘露之變后,宦官大權獨攬,劉蕡處境兇險,在朝廷無立錐之地,所幸藩鎮幕主及時給予庇護。“令狐楚在興元,牛僧孺鎮襄陽,辟為從事,待如師友。”可見藩鎮相對于中央權力中樞的相對獨立性,可以不畏宦官威權,任用劉蕡這樣仗義執言的文人。
“入幕”風潮 事出有因
風行于中晚唐時期的進士入幕現象,究其根源來看,最重要的原因無疑是安史之亂后大批藩鎮的崛起與中央實力的逐漸衰落。朝廷將辟署幕僚的權力放寬正是在安史之亂時期的從權之計,玄宗下詔“其諸路本節度使、采訪、支度、防御等使……其署官屬及本路郡縣官,并各任便自簡擇。”辟署權一經下放便開啟了藩鎮自行任命僚屬,各藩鎮間爭相聚攏人才,乃至與中央爭奪人才的序幕。
藩鎮辟署權的放寬,為無法入仕的人才打開了新的通道,但中央并未將任官的權力全部委任給幕府,進士出身高級佐僚的辟署有一套必須遵守的正式而相對完善的程序。進士擔任的多是中高層文官,于幕府所署憲銜外,須藩鎮為其奏請,由朝廷賜予“朝銜”。另外,對比安史之亂前從軍幕僚的出身不難發現,唐前期的進士幕僚不僅人數上較少,擔任幕職的時間較短,地域也局限在一些戎馬倥傯的邊鎮中,且幕職遷轉的流程并未像中晚唐時期那樣完善,入幕不能有效地讓進士們的仕途通向更加顯要的職位。“進士及第后辟入藩府,入朝為清官,這在憲宗特別是文宗以后,成為士大夫迅速升遷、致位顯要的捷徑”。中晚唐時期進士通過入幕途徑捷轉朝廷,繼而晉身顯位,這一方式已成為被越來越多人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捷徑”。而且“唐代士人不可能一生只任京官,必須常在仕宦中途普遍出任外官”,辟署權的放寬和藩鎮的人才需求,銓選制的弊病以及進士自身對“顯達”的渴求,令“入幕”成為進士們在必須出任外官時優先考慮的“捷徑”,也導致“入幕”成為一種社會風氣。
從朝廷一方的角度來看,首先,中央掌握著科舉考試和銓選的權力,但政治風氣和制度上的弊端使一些進士不得不先入幕而后入朝。中晚唐進士參加銓選前的守選期比明經等科短一些,如進士及第守選三年,明經及第守選七年,童子科及第守選十一年等。總體來看,進士的守選期都具有一定優勢,這體現了朝廷希望進士科人才能夠盡可能多為朝廷所用的態度,但仍然不足以抑制進士們走入幕的捷徑。韓愈貞元八年(792年)中進士后,參加吏部博學宏詞試卻屢屢折戟,所謂“三選于吏部而卒無成”,以至于處境十分落魄,“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不得不入宣武軍董晉幕府任掌書記。即使進士獲得了官職,朝廷官吏四考一任,任滿須繼續參加銓選才能重新獲得官職的規定,進士們需再次行卷。從大量進士入幕時間都發生在守選期的事例,可以發現正是唐代銓選制度的特點給藩鎮引進人才創造了可乘之機。銓選制的弊病和守選期過長的局限導致進士們必須繼續通過考試的方式求得一官,也導致漫長的守選或應試過程中人才的必然流失。不甘等待或回鄉、隱逸的進士們通過入幕解決生計問題和謀求仕途上的出路,是基于當時現狀而做出的選擇。藩鎮待遇之隆,倚仗之重,也是這些在朝暫時無法大展才干的“白衣公卿”們投效的重要原因。
筆者認為,進士與藩鎮之所以“一拍即合”,正是建立在藩鎮自身是一級擁有對其下州縣的管理權的行政建置的基礎之上,正如《劍橋中國隋唐史》中所提到的,“大的方鎮衙門有時很像具體而微的朝廷”。基于中晚唐藩鎮自身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以及朝廷需要其對下面的州縣進行管理這一特殊性,其對文職幕僚的選擇范圍必定不可能只滿足于有才名的“布衣”或初唐時常見的武人幕僚。幕主身為藩鎮的管理者,同時也是隸屬于朝廷的將領或朝臣。因此在對幕僚的選拔方面,幕府與朝廷的標準也極為相似。進士既是中晚唐時期朝廷高級官員的主要來源,同時也是中高級文職官員的主要來源。進士作為時人青睞的精英,雖及第但因為銓選制存在弊病,求官之路漫漫,以“入幕”作為對策,也就可以理解了。
入幕歷練 經世致用
對于進士來說,入幕最明顯的作用是能使他們的政務能力得到提高。唐代士人赴州縣、藩鎮等地方鍛煉能力,積累經驗的做法,并非安史之亂后才提出。所謂“宰相起于州部,猛將發于卒伍”,早在玄宗時張九齡便建言“凡官,不歷州縣不擬臺省”,即高官只從有過基層工作經歷的官員中選拔。元和二年(807年)憲宗又詔令“臺省官及刺史,赤令有闕,先從縣令中揀擇。”朝廷要求士人任州縣官也從另一側面體現了朝廷對官員鍛煉實際政務能力的重視。進士出身的幕僚在藩鎮受到更多禮遇,與幕主的關系也更為親厚。但藩鎮的事務也是十分繁重的,幕僚在幕府不僅要承擔案牘工作,輔佐幕主,熟悉藩鎮政務、軍務,也要主持所屬州縣考試。一些文采出眾的幕僚需作文為幕主宣揚政績,高級佐僚還需要充任與其他藩鎮交往的“使節”,或代表幕主入京,進行“朝正”等任務。一旦遇到兵亂甚至是所在藩鎮幕主叛亂等情況,幕僚實際處理事務的能力和隨機應變的能力就成為備受考驗的必要條件。許多藩鎮中的突發事件因幕僚的出色表現而得以消弭,尤以藩鎮最常見的兵亂為甚,高級幕僚的處置方法往往直接決定事態發展的輕重緩急。令狐楚在太原鄭儋幕中任節度判官時,“鄭儋在鎮暴卒,不及處分后事,軍中喧嘩,將有急變。中夜十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從中可以看到,在突發狀況頻出的藩鎮,幕僚的個人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朝廷的吏部銓選在“身言書判”四項上對進士的實際能力作出了要求,而幕府的日常事務更磨礪了進士們的能力。進士們在幕府對軍事政務耳濡目染,經受多番歷練,彌補了文學取士的不足,在思想上擺脫了“迂夫子”或“官僚”的窠臼。這種入世經歷也正好暗合了進士時務考試中“或用古事,或取今事,亦無定程”,要求進士們“閎辨通敏”,從而經世致用的風格。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晚唐的大多數時期,進士們無論在幕府的仕途多么順利,他們的主觀上還是傾向于將幕府當做“跳板”,最終的目的依舊是回到朝廷。“從士人的立場看,入幕只是為幕主個人服務,好比是幕主的‘私人助理’而已,格局似乎小了些……如果出任正式的職事官卻是為天子服務,那則是為整個國家、朝廷做事,是傳統士人‘學而優則仕’的‘正途’,似乎更清高一些。”
幕僚們渴望得到幕主舉薦,必然需要表現出實際才干和政績,這也令藩鎮的政務能夠有條不紊地維持日常運作。文人以朝廷為“正途”的態度決定了大多數幕僚在藩鎮發生兵亂或幕主叛亂時,能夠堅決地擁護唐朝廷政權。這些“小人物的忠誠”很大程度上在基層維持了唐政權的穩定。另外,有過入幕經歷的進士對驕橫的藩鎮態度反而更加強硬。董晉去世后,韓愈目睹汴州軍亂,作《汴州亂》指出兵亂的根源是“廟堂不肯用干戈”,即統治者姑息縱容。杜牧在牛僧孺幕日久,作《罪言》建議朝廷“先取魏,后圖河北。”作《守論》斥朝廷“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終唱災禍”,鋒芒直指河朔三鎮及驕橫的其他藩鎮。“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可見杜牧的軍事思想不僅有理有據,而且極為實用,這與他多年幕府生活的歷練有極大關系。這些現象折射出進士們深受儒家思想浸潤,當他們親身經歷了藩鎮割據之亂,目睹了大眾飽受流離之苦的慘象后,往往會產生盼望中央能夠積極作為,懲治藩鎮的思想。
“進士入幕”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唐代制度的不完善,令這些人才找到了施展抱負的天地,有利于社會的穩定。由于多數進士抱有以朝廷為“正統”的心態,身處藩鎮而積極擁護中央政權。唐政權能夠避免分崩離析,入幕的進士們所起的作用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有才學、有抱負的人才先進入地方和“基層”歷練一番,積累經驗,增長見識。這種經歷客觀上對人才培養所起到的積極作用,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