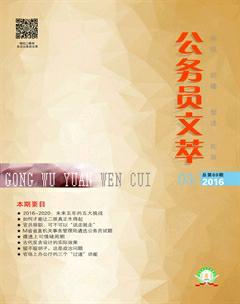學者俞可平
蔡如鵬
去年12月3日,剛剛辭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出任北大講席教授的俞可平,正在這里給學生們作公開講座,他演講的題目是《政治學的公理》。
作為中國最知名的學者之一,俞可平因2006年發表《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而蜚聲海內外。在擔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的14年中,他積極倡導國家的民主自由,追求國家和社會層面的善治,屢次發聲褒贊民主,亦被視為體制內民主的思想推手。
2008年,他因此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評選為“改革開放30年30名社會人物”。
而就在這次演講的前一天,俞可平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表示,作為一名政治學者,除了推動中國現實政治的進步之外,他還有種強烈的責任,“希望推動中國政治學的發展。”
對一名中管干部而言,這樣的轉型卻并非易事。
辭 職
自1988年從北大畢業后,在短暫的留校后,俞可平很快就調到中央編譯局工作,并且一干就是27年,從一名普通的助理研究員成長為局領導。其間,創造了多項局里的記錄:最年輕的研究員、最年輕的所長、最年輕的副局長……
但熱衷學術的他越來越意識到,自己內心更希望做一個純粹的教授。這種意識在過去四五年變得愈發強烈。
“這些年,我多次申請辭去行政職務,回到大學做學問。但一直沒有得到批準。”俞可平說,“我很高興這次中央領導同意我回北大,這表示他們尊重我的興趣,畢竟大學有更廣闊的學術空間。”
盡管從政多年,俞可平至今仍保持著一個學者的習慣和作息:喜歡爬山、游泳、射擊,不跳舞、不去卡拉OK、很少應酬,每天晚上只睡6個小時,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讀書、做學問。
結果是,其學術影響力不但一直在政治學和國際政治研究領域中保持領先地位,而且據不久前上海交通大學發布的一項統計顯示:過去十年中,在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俞可平發表論文的引用率也高居榜首。
俞可平重回北大雖然只是一次人事調動,但消息一經媒體披露,還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動。有人猜測,他肯定是鼓吹民主,犯了錯誤,被邊緣化,不得不離開;也有人懷疑,俞可平是不是對改革失去信心,心灰意冷,提前隱退。
“這些猜測都是捕風捉影。”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我只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時間做學問,實現一個學者推動學術進步的愿望。”
在俞可平看來,做學問有兩種:一種是“塵世的學問”,一種是“天國的學問”。“這兩種學問的性質不一樣,前者是對策研究,為現實服務,后者是純學問,屬于基礎性的理論研究。”他說。
重回校園的俞可平,希望能做自己的“天國的學問”。
俞可平也希望用自己的行動實踐中央提出的干部能上能下的用人原則。“我做了14年的副局長了,我自己研究的就是政治體制改革,了解一般一個干部在一個崗位上不得超過8年,我已經超過任期6年了,我應當帶頭能上能下。”
從一名中管干部到大學教授,變化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沒有了司機,坐了14年專車的俞可平,現在需要自己開車上下班。其次,沒有了辦公廳、秘書處,以前打個電話就可以辦好的事情,如今得靠自己。
有一次,俞可平在浙江大學與學生座談時說,“如果你覺得自己非常優秀,非常聰明,那么我提一個小小的建議:你最好去做一名學者。為什么呢?你想想,現在是民主政治,你官再大,再聰明,你的權力也是受到制約的。但是如果你成為一位學者,你的潛力就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
沒想到幾年后,他以自己的親身行動實踐了當年的建議。
探 路
上世紀80年代末的中央編譯局正面臨一場轉型,從單一的翻譯機構向兼顧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智庫轉變。這給年輕的俞可平提供了施展抱負的舞臺。
初到編譯局的俞可平“很安靜”,沒有人估量到這個助理研究員的潛力和膽量,但很快他就顯示出了不同。
1990年,剛入職兩年的俞可平發表了一篇談論人權的文章《馬克思主義人權觀》。他在文中說,人權是人類的基本價值,而在一些國家人們對人權則一直緘口不語。
這是一個大膽的舉動。“過去談論人權是禁區。”據俞可平當時所在的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原所長詹汝琮回憶,文章將人權和馬克思主義聯系起來,“大膽而有分寸” 。
多年后的今天,俞可平回想當年的情景仍頗有感觸。“我研究現實政治和意識形態,當然知道它很敏感,但我是初生牛犢不怕虎。”
不出意料,文章發表后引起了很大反響,也招致了很多批評。中央很重要一個部委的司長,拿著文章說,俞可平鼓吹人權,是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宣揚資產階級的觀點。還有一些人直接給中央編譯局局長打電話施壓。
不過,局領導很支持這個大膽的年輕人,都給頂了回去。“我非常感激他們,沒有他們的寬容和理解,不可能有今天的我。”俞可平說。
作為中共中央直屬機構,中央編譯局負責編譯和研究馬克思主義著作,翻譯中共中央重要文獻和領導人著作,是典型的中共意識形態機構。
但由于編譯的需要,這里的工作人員能夠接觸到很多普通學者接觸不到的國外文獻,包括一些敏感材料。所以中央編譯局盡管在關注的內容上頗有意識形態特征,但他們反而思想更開放,更具國際眼光,學術環境也比較自由。
“我們既不是大學,也不是政府機構,介于中間。”俞可平說。
正是這種相當自由、寬松的小環境,使得屢觸敏感話題的俞可平,不僅沒有受到批判,反而獲得了破格提拔。這個執著于學術研究的年輕人,很快就成了單位最年輕的研究員。
此時的俞可平在中國年輕的政治學者中已開始嶄露頭角,他甚至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組織發起了“全國中青年政治學論壇”,而參加者大多是年歲大他一輪的學者。他在1994年應邀去美國杜克大學任訪問教授,1995年又赴德國柏林自由大學任客座教授。
2000年前后,俞可平已經成為國內舉足輕重的政治學者。他和中央編譯局團隊開始大量接受官方委托的課題研究,為高層決策提供政情信息和理論支持。
除了在理論上為中央提供決策服務外,俞可平逐漸意識到實踐的重要。他開始為中國的政治改革尋找現實路徑,希望找準突破口,用最小的社會和政治成本,推動實質性的社會政治進步。
作為體制內的高級別官員,俞可平倡導民主,積極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認為“政改不是一件‘應當做的事,而是一件‘必須做的事”。但同時,他又從現實出發,不脫離實際,強調改革路徑的可行性和政治成本。
一些西方媒體和學者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充滿爭議,認為中國三十多年的改革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
對此,俞可平并不認同。他認為,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是雙向互促、不可分離的。正是基于這種考慮,俞可平創造性地提出了“增量民主”的概念。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簡單地說,增量民主就是中國增量改革在政治領域的體現。”
在俞可平看來,增量民主是在中國目前特定的條件下,以現實的政治手段達到理想之政治目標的一種政治選擇,其目標是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創新來持續地推進中國的民主進程,最終實現善治的政治理想。
盛 名
作為一名學者型官員,俞可平盡管理論成果豐碩,但讓他進入公眾視野的,卻是9年前他那篇不足2000字、近似白話的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
由于話題敏感,再加上作者的特殊身份,文章很快引起了各方的注意。一些境外媒體將它解讀為中國最新政治風向標,認為這是對傳統意識形態的重大突破。
不久后的12月27日,這篇文章又被人民網、新華網和《學習時報》文摘版同時全文轉載。“官網”“官報”這一不尋常的舉動,讓此文顯得更加高深莫測。一時“解套說”“投石問路說”等揣測紛紛出籠,而俞可平本人也被貼上了中共“文膽”“智囊”的標簽。
事實上,《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只是俞可平一本同名訪談集的自序,并且在此之前已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公開出版。
隨著《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在各界持續發酵并最終擴散于公眾,俞可平也在一夜之間成了公眾人物,近乎家喻戶曉。
而第二年中共十七大召開帶來的政治話題升溫,讓他的聲譽再次達到新的高度,使他成為當時中國最耀眼的政治學者。
當時很多猜測,俞可平拋出《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是中共高層的授意,旨在為十七大推進政治改革預熱和探路。
9年后的今天,已經退出官場的俞可平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對此做出回應。
他告訴記者,當年他撰寫、發表《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與高層沒有任何直接的關系,完全是出于一個政治學者對中國政治的直覺判斷和社會責任。
“就像一個大夫,行醫久了,他能夠憑經驗、憑感覺,做出診斷。我研究中國政治也有這種感覺,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民生的改善,老百姓一定會有政治的需求。這個時候,民主的要求一定會提出來,這是社會政治發展的必然邏輯。其實,治理與善治的情況也是這樣,我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倡導治理與善治時,很多人也不以為然,但現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已經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善治的理念也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上正式提出。我的許多觀點和理論順應了中國現實政治的邏輯,這一點我很自豪。”俞可平說。
《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在受到追捧的同時,也引發了巨大爭議。
在俞可平看來,這正是他所期望的——既有來自極右的批判,也有來自極左的批判,“缺少一個,我都感到很遺憾。這說明了我的文章避免了這兩種極端。”他的名言是:“不左不右,走人間正道!”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