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上的春節
文/本刊記者 王璐
?
指尖上的春節
文/本刊記者 王璐

剛剛過去的猴年春節,搶紅包成為了節日期間最大的“主角”,搶紅包活動的范圍之廣、參與度之高、形式之繁多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們咻一咻、刷一刷、搖一搖,將局部肢體的靈活協調性以及速度體能發揮到了極致,在頻繁的切換和熱情的期盼中,興致勃勃地玩起了紅包大戰。
“互聯網+紅包”正成為新的春節符號,難怪有人說,這是一個指尖上的春節。
“集五福”大戰
眾多紅包大戰中,又以支付寶集五福活動引發的全民參與熱潮最為熱烈。支付寶用戶通過“咻一咻”的功能不僅可以直接“咻”出現金紅包,還能“咻”出五種不同內容的“福卡”,各集齊五張便可參與共分超兩億現金紅包!如此誘人的一個大紅包,自然帶動了很多人的參與熱情。集五福的第一階段,企圖在支付業務基礎上搶占社交功能的支付寶推出:添加10個支付寶好友可隨機領取3張福卡。瞬時讓勤勞智慧的用戶們不僅寄希望于“手機掉餡餅”,更下定決心將命運牢牢把握在自己手(手機)中。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人們見面的第一句問候變成了“你有幾個福了?”、“打開支付寶,輸入口令,就能加我為好友,快幫幫忙吧!”這樣一條信息頻繁出現在各種朋友群里。一時間,平日里含蓄內斂的人敢于大膽地告白加對方為好友,彼此間不熟悉的人變得情同手足,大有“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勢頭。

支付寶推出的集五福活動讓很多人對“福”字充滿從未有過的熱情,馬云棋高一招的營銷策略在于對“敬業”的崇尚,最令人百爪撓心的不是一個福都沒有,而是集齊了四個福以后,尋找那第五張神一樣存在的令人魂牽夢縈的“敬業福”。有網友打趣,江湖戲言6種東西找不到:長生丹,后悔藥,鐵老大的火車票;絕情丹,情花毒,支付寶的敬業福。大家身體力行地展現對“敬業”的深切渴望和心悅誠服。朋友圈、微信群、貼吧,到處都是換卡、賣卡的信息。有傳聞稱,一張“敬業福”甚至能在黑市炒出上千元的高價。
隨著大年三十兒晚上的傳統節目春節聯歡晚會的臨近,全民搶紅包熱潮行至巔峰。有道是態度決定一切,運氣暫且可以先放一邊,但先要從思想上重視起來。有網友為了避免疏漏,提前將BTA公布的紅包方案整理出時間表,執行力強大的網友按搶紅包時段提前上好鬧鐘,同時備注好搶紅包口令,按部就班地執行沖刺計劃。
根據支付寶提供的數據顯示,大年三十兒晚上20點多的時候,參與“集五福”活動的全體用戶中只有8000多人集齊了五福,這意味著平均每人可分得2.6萬元。然而22點40隨著春晚又一輪咻一咻結束后,五福集齊者就漲到了68萬人,支付寶最終揭曉,79萬人平分2.15億現金,每人分得271.66元。“搶紅包”游戲結束后,大家又恢復了本來的矜持。商家飽賺人氣,策劃實施了一出穩賺不賠的大戲,絕大部分人在與紅包擦肩而過之后只剩下悵然若失。
首次與央視春晚聯手的阿里給出的數據顯示,在春晚進行中,支付寶“咻一咻”互動平臺總參與次數達到了3245億次,是去年春晚互動次數的29.5倍,并且有11億對好友成為支付寶好友,有30%的用戶選擇將福卡送給了家人。
搶并快樂著
搶紅包的隊伍中有很多人并沒有將目光鎖定在支付寶2.15億紅包上,而是更樂于選擇通過互動的方式參與其中,因此微信朋友圈成為了春節紅包的又一大陣營。用戶們看重與熟悉的親朋同事之間聯絡感情,同時為節日增添一些娛樂的氣氛。在記者發起的對身邊親朋的一項調查中,31.4%人表示自己“搶并快樂著”,而并沒有在意和統計春節期間搶紅包的盈虧情況,甚至有37%的人表示“虧并快樂著”。
騰訊數據顯示,全球共有4.2億人次收發微信紅包,除夕當天微信紅包收發總量達到80.8億個,參與“刷一刷”QQ紅包的總用戶數為3.08億,共刷1894億次,QQ除夕當天的紅包收發總量達到42億。微信峰值每秒40.9萬個。

江湖戲言六種東西找不到
長生丹,后悔藥,鐵老大的火車票
絕情丹,情花毒,支付寶的敬業福
今年的搶紅包壯觀景象中,搶紅包不僅僅是年輕人的專屬了,這場全民狂歡的游戲開始向中老年人擴張——“全家老少齊上陣”。由企鵝智酷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紅包”大數據報告》顯示,小于19歲、20-29歲、30-39歲3個年齡段的網民中,約有90%的人開啟過紅包服務;40-49歲網民中收發過紅包的人有83.7%;50歲及以上的網民中,也有64.6%的人喜歡參與紅包“角逐”。
紅包雖小,卻折射出互聯網技術與文化對人們生活的深層次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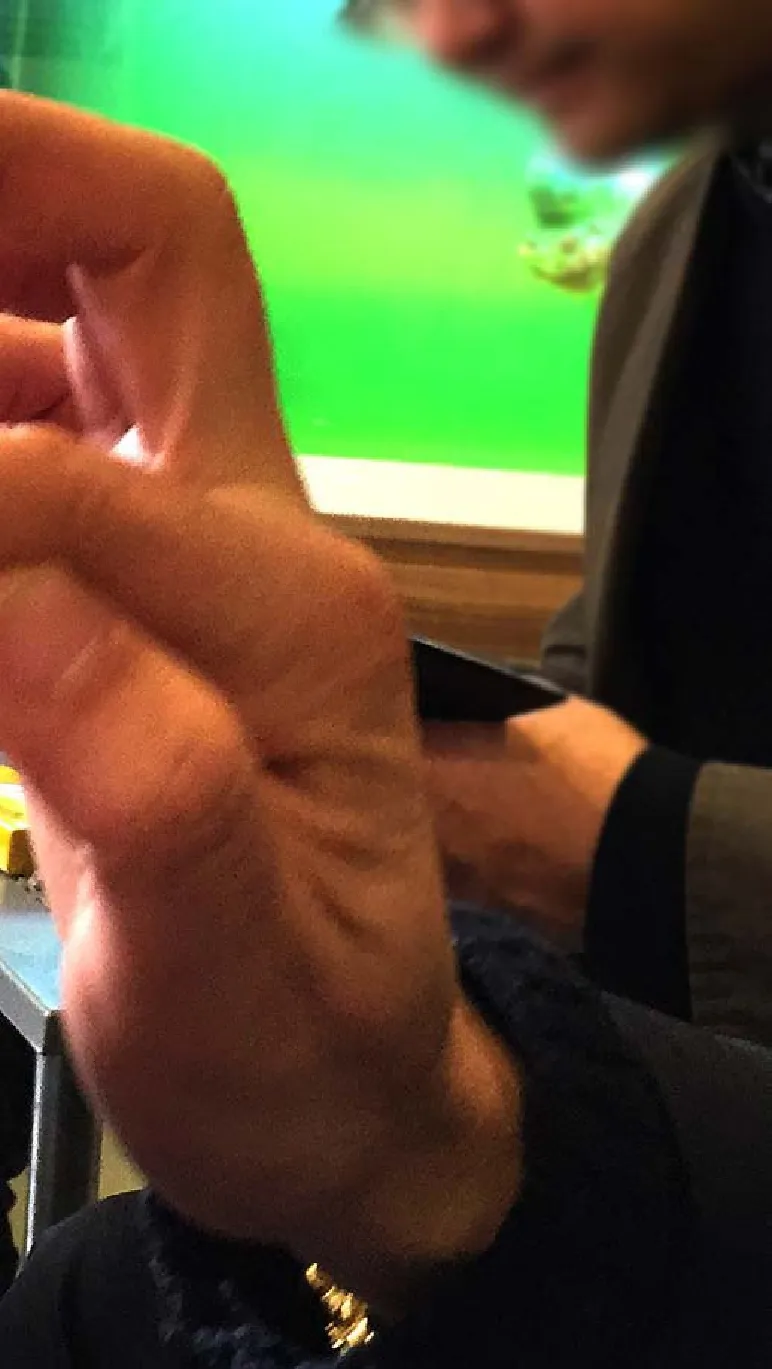
都是“紅包”惹的禍
“搶紅包”的“搶”字其基本解釋:奪,硬拿。“搶”字當頭,似乎迎合了許多人力爭上游的積極人生態度,也暗含著對巨大人生財富的欲求不滿。
小劉是一名小學老師,因為春節正值寒假,她有更多的時間來搶紅包。“我們是1月下旬放的寒假,當時搶紅包的熱潮已經來臨了,我還在朋友圈里開玩笑說,今年要靠搶紅包發財呢。”整個假期,小劉對搶紅包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白天,媽媽叫她去買對聯,被她給推了,因為要搶紅包;晚上,朋友喊她聚會,她也不去,理由還是要搶紅包;除夕夜,爸爸給她遞來一個紅包,她倒是不客氣地收下了,可話還沒說上幾句,鬧鐘響了起來,她立即抱著手機搶紅包去了。她自己略為夸張地總結:整個假期除了吃和睡,就是搶紅包了。像小劉這樣原本與家人團聚、共敘親情的美好時刻還沒來得及迎來更好的表達方式,就被“搶紅包”無情地朝攀暮折。如此這般舍本逐末地方式顯然不是我們所追求的,親情需要有感情有溫度的表達和傳遞,一個大大的擁抱抵得過一切紅包。
不僅如此,互聯網紅包引發的諸多不和諧,也成為了節日之中的遺憾,甚至在歡樂祥和的節日期間以健康、財產和生命安全作為代價換取紅包。
春節期間,江蘇揚州張女士為了搶紅包,忙得不可開交。從除夕到正月初二,張女士連搶3天紅包,玩得不亦樂乎。初二晚上張女士給孩子洗澡時,突然發現她的右手腕處竟然鼓起一個拇指大小的包,兩天后不見好轉,張女士便去醫院。據接診醫生介紹,經診斷,張女士手上長出的包是腱鞘炎,也就是大家熟悉的“鼠標手”。
節后各大醫院的眼科也異常火爆,據同仁醫院眼科劉衛華大夫介紹,人們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容易造成視疲勞、干眼癥、視力下降等眼部疾病,出現眼睛干燥、酸澀、有異物感,或者怕光、流淚、視物不清等現象,到醫院進行擴瞳驗光等檢查發現,散光、近視度數增高。由于長時間盯著手機、電腦造成睫狀肌長期處于高度緊張狀態,而眨眼次數由每分鐘20~25次減少到5~10次,從而減少了淚液的分泌,造成眼睛干澀不適,國外將這些現象統稱為“顯示器癥候群”。這樣的病例在春節后較為多見。
春節前,正在駕駛轎車的男青年胡某被微信朋友圈里紅包誘惑,一邊開車一邊玩弄手機,一心二用地看著熱火朝天的朋友圈紅包大戰。還為搶得幾個幾毛錢的紅包沾沾自喜。當轎車行至一個交叉路口時,由于注意力不集中與一輛紅色的轎車發生碰撞,導致雙方車輛近萬元的經濟損失。

科技往往是一把“雙刃劍”。不法分子也瞄準了網絡詐騙的“新領地”。沈陽一派出所接到報警,市民張女士為了在春節期間不錯過大家發的紅包,下了一個名叫“搶包神器”的軟件,卻不想使用之后不但紅包沒搶到,就連自己的微信余額也被洗劫一空。回過勁兒的張女士恍然大悟,原來正是這紅包神器在作怪,搶紅包是假,竊取錢財才是真,其實質屬于網絡詐騙。
互聯網時代的新饋贈
隨著時代的變遷及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互聯網紅包成為人們新的慶祝新年的方式,它讓親人朋友間溫潤的情感在紅包的收發間得以傳遞。微信等移動社交軟件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高滲透,讓之前以電話拜年的方式慢慢被取代,不同的拜年方式呈現著不同的時代烙印。記者的調查中顯示,超過85%的參與調查對象參與春節期間搶紅包的活動,而幾乎所有參與了者最終都以娛樂及親朋好友及同事同學之間聯絡感情為目的。超過85.6%的參與者表示,搶紅包并不會疏離親情和沖淡年味,不同時期應有不同的年味兒,互聯網紅包是一種過年的新方式,是時代發展留下的印跡。
企業以不同形式派發紅包能夠推廣品牌、提升形象,也烘托了春節的節日氣氛,表達了對當下乃至未來的良好期待。多年來,港澳地區經常向永久及非永久居民派發紅包,旨在進一步與市民分享經濟成果,新加坡也有類似行動。無論向全民發紅包,還是“送溫暖”,都體現了還利于民、還富于民的優良傳統。
互聯網紅包為人們的節日時光帶來了無可比擬的樂趣與放松,同時也是一種極具形式感并且有分量的社交行為,將歡樂吉祥拓展到了更為廣闊的互聯網空間。
有人認為紅包是體現誠意的表達,因為是真金白銀,送出的祝福不會顯得虛弱無力。在群里點開一個紅包,能夠感受到久違的節日喜慶感,更重要的是因為它激起了潛藏于我們心底對情感聯結的渴望。無論如何比點贊和群發誠懇多了。
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寧家駿認為,微信紅包拜年融合了網絡新技術和中國傳統民俗,豐富了人們的社交空間,緊密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傳達友情、親情的同時,給民俗文化增添了現代、娛樂的新氣質。
事實上發展到今天,“互聯網+紅包”恰好成為了互聯網技術與傳統習俗巧妙結合的重要體現,使中國的傳統紅包習俗進入“數字化時代”,它強化了網絡空間的交往,增進了感情交流的互動方式,其本質上是年俗的體現,也是傳遞祝福的一種方式,讓人際交流更頻繁、更密切、更平等。從某種意義上說,互聯網紅包開始形成一種新民俗。
許多人認為,2016年,互聯網紅包將帶動商業模式的升級,并帶動互聯網特色向更深遠的維度邁進。沒有哪一項娛樂傳播活動能像互聯網紅包那樣達到如此大規模的影響,同時集趣味性和美好寓意于一身。互聯網紅包體現了中國民俗與現代科技巧妙融合的中國式過年方式,并留下鮮明的中國印記,春節已經迎來了互聯網時代的新饋贈。
“搶紅包”搶走了什么
當然,我們在點贊互聯網紅包的同時,也不可忽視它的弊端。凡事過猶不及,手機“搶紅包”也要把握好分寸和熱度,不能讓搶紅包變了味兒。
第三方消息推送技術服務商“個推”基于6.5億日活躍用戶提供的數據顯示:除夕和初一,平均每個用戶每天花在手機上的時間是3.91個小時,比過去一年每天的平均值多了1個小時。其中,春節期間從一線城市返鄉的人群,“低頭”時間尤長。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楊建華表示,“指尖社交”占據了太多的時間,讓假期變成了手機上的忙碌,真正陪伴家人的時間明顯偏少,方式也比較單一。大家應適當節制對手機的依賴,在現實的交流中提高團聚的幸福感。”
無論家遠在何方,過年的時候都要回家團聚,在春節這個意味著團圓的特殊時期,全家人的相聚似乎為奮斗了一年的人們找到了一年中短暫卻最溫暖的歸宿,珍惜親人相聚時的美好時光,用親切的交談和笑容維系美好的親情,當真誠交流和微信紅包相輔相成時,親情才能日漸緊密,從而感受新春的溫暖和力量。但回家與家人說不上幾句話就只顧著以社交網絡屏蔽與家人的溝通,顯然與春節歸家的意義背道而馳。
中國人向來注重禮節,在人情往來、待人接物中增進感情,如果一門心思專注于搶紅包,與別人交談時心不在焉,由此怠慢了別人,也顯得不夠禮貌。公司的年會、好友的聚會,原本是應該面對面增進交流感情的時刻,卻經常上演著“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莫過于我們坐在一起,你卻在看手機”的尷尬。
另一個使人無法忽視的群體就是老年人。作為堅守傳統文化的重要人群,多數老年人都對互聯網紅包不為所動,一方面緣于對新生事物接受的能力較之年輕人弱,一方面他們扮演著家家戶戶傳統過節方式中的主角,打掃房屋、張羅年夜飯使得他們大多數人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過年的瑣碎中,沒有過多的精力去關注互聯網紅包。盡管并不輕松甚至比平時更為操勞,但期盼團圓、享受團聚才是他們最大的心愿。在接受記者調查的參與者中,表示搶紅包并不會疏離親情和沖淡年味的85.6%的參與者,按年齡劃分絕大部分屬于25-40歲之間的中青年人,而問及家人對自己搶紅包的態度,83%的人表示家里人并不覺得困擾甚至采取支持的態度。老人對孩子的愛永遠是無私且寬容,甚至是毫無原則的。在父母心中,對春節的美好沒有過多苛求,僅僅是全家人聚在一起已是最大的幸福,哪怕面對著子女們忙碌奮戰的背影。寬容的愛更應該喚醒親情,因此手機紅包,適當玩玩未嘗不可,但是實在不該占用太多團聚時光,沖淡了團圓的本意。
作為中華民族傳統節日的開篇之作,春節是全世界華人心中最重要、最隆重的節日,也是中國傳統節日中持續最長、內容和儀式最多、節奏感最強的一個節日。讓我們帶著回憶穿越到兒時的畫面,沒有互聯網、沒有手機,但全家人在“守歲”的時刻,祭祖、吃年夜飯、包餃子、壓歲錢、放花炮……,莊重又充滿激情,深情又富有浪漫。魯迅在《朝花夕拾·阿長與〈山海經〉》中曾描寫道:“一年中最高興的時節,自然要數除夕了。辭歲之后,從長輩得到壓歲錢,紅紙包著,放到枕邊,只要過一宵,便可隨意使用。睡在枕上,看著紅包,想到明天買來的小鼓,刀槍,泥人,糖菩薩……”
春節的文化符號是維系春節傳統的重要紐帶,也是民族情感與心理的凝結,將這些文化符號傳承下去是保護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在如今互聯網科技多元化發展的環境中,我們一方面需要認真思考傳統文化如何找到創新發展的途徑,所謂的創新離不開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進行正確釋讀和深刻領悟。但另一方面,要認識到無論怎樣創新,我們應該始終懷揣敬畏之心,對傳統文化的情感真核堅守不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