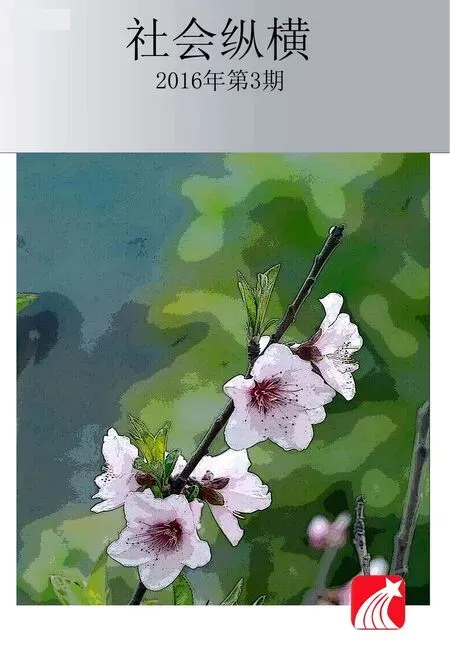甘肅出土文獻統計與分析
高國祥
(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 甘肅 蘭州 730000)
?
甘肅出土文獻統計與分析
高國祥[1]
(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甘肅蘭州730000)
【內容摘要】甘肅出土文獻是全國最為豐富的地區,其中簡牘文獻、敦煌文獻和黑水城文獻孕育了簡牘學、敦煌學和西夏學三個國際性顯學的誕生。本文通過統計整理和提要分析,對上世紀甘肅出土文獻的基本情況進行了較為清晰的梳理,認為甘肅出土文獻具有十分鮮明的地域和時代特征,是全國唯一較為完整的鏈接秦漢至宋元1800余年地下文獻發展史的省份,從而為文化資源大省的地位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甘肅出土文獻統計分析
*本文為甘肅省社科規劃項目“甘肅省歷代文獻提要整理與研究”(批準號:13YD119)。
甘肅區域概念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指當代行政區劃;廣義指歷史概念,即甘肅全境及寧夏、青海及部分內蒙古地區。本文兼取歷史廣義,部分時期涉及周邊省區,統計與分析范圍包括出土紙質文獻與非紙質文獻兩個方面。其中簡牘文獻、敦煌文獻和黑水城文獻最具特色,在全國出土文獻中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產生了重大的國際學術影響,孕育了簡牘學、敦煌學和西夏學三個國際性顯學的誕生。
一、甘肅出土簡牘文獻
甘肅出土簡牘上自戰國秦下迄魏晉南北朝時期,時間跨度約800年,其中以漢代為主。出土或采集總量約6萬枚,主要分布于疏勒河流域的敦煌、居延、玉門,河西張掖、武威、高臺等地以及天水和武都地區。
1.甘肅迄今發現最早的完整文獻
天水放馬灘秦簡[1]。竹制,461枚,1986年天水市北道區黨川鄉放馬灘1號秦墓出土。內容分甲種《日書》、乙種《日書》和《志怪故事》三種。其中甲種《日書》73枚,乙種《日書》381枚,《志怪故事》7枚。放馬灘1號秦墓屬戰國晚期,是甘肅迄今發現最早的完整文獻。現藏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20世紀東方文明“四大發現”之一
居延漢簡[2]。木、竹質,以木質居多。形制主要有簡、牘、觚、楬、封檢等,總數約3萬余枚。主要分兩次在古居延地區發掘和采集。第一次為1930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采獲約1.1萬枚,分別出土于破城子、金關、地灣、大灣等30個地點。紀年為西漢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至東漢建武六年(公元30年),現藏臺北“中央研究院”,統稱“居延漢簡”。第二次為1972至1976年間,甘肅省居延考古隊考古發掘近2萬枚,其中破城子出土7865枚,甲渠第四燧出土195枚,金關出土11577枚,其他地點采集164枚。紀年為西漢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至建武七年(公元31年)。現藏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統稱“居延新簡”。兩次發掘出土的主要內容包括大量官、私文書和少量典籍、歷譜等。居延漢簡大多出自掾史之手,系統地反映了漢代邊塞的屯戍生活,涉及當時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是研究漢史的第一手資料,具極高的史料價值。
3.甘肅出土簡牘統計[3]
20世紀甘肅出土簡牘的次數和數量,除已知正式發掘外,早期盜掘數量和中后期采集、征集次數無準確統計,大致按時間順序排列如下。
1907年敦煌出土漢簡。木質,發表705枚。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敦煌玉門關發現第三座烽火臺并獲取漢代木簡近千枚。其中有紀年166枚,紀年為西漢武帝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至東漢順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4]。
1908年居延出土漢簡。木質,2枚。俄國人科茲洛夫考察黑水城遺址時獲取[5]。
1913至1915年敦煌、酒泉出土漢簡。木質,189枚。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第三次進入敦煌,在漢代烽燧遺址獲得木簡84枚,安西、酒泉獲得木簡105枚[6]。
1920年敦煌出土漢簡。木質,17枚。周炳南在敦煌西北小方盤城玉門關外沙灘中掘得,內容為屯戍記事[7]。
1927年居延地區出土漢簡。木質,8l枚[7]。
1930至1931年居延出土漢簡。木質,11000余枚。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于博羅松治漢代烽燧遺址以及額濟納河流域黑水城附近的30多個地點掘得,統稱“居延漢簡”[7]。
1944年敦煌出土漢簡。木質,49枚。西北科學考察團團員夏鼐、閻文儒在敦煌玉門關以東烽燧遺址獲得[8]。
1945年武威南山刺麻灣出土漢簡。木質,7枚。
1959年武威磨咀子6號墓出土漢簡。竹木質,610枚。內容為《儀禮》、《服傳》和《喪服》[9]。
1959年武威磨咀子18號墓出土漢簡。木質,10枚。內容為詔令,即“王杖十簡”[10]。
1971年甘谷牛家山坪東漢墓出土漢簡。木質,23枚[7]。
1972年居延地區采集簡牘。木質,21枚。出土地點不明,分別為14和7枚[7]。
1972年武威旱灘坡東漢墓出土簡牘。木質,簡78枚、牘14枚。內容以本草為主,載藥物約100種,其中20余種為古籍中所無,是目前發現最早的醫學文獻[11]。
1972至1974年居延出土漢代簡牘。竹木質,約2萬余枚。1972年11月甘肅省居延考古隊第二次考察居延遺址50余處,發掘木簡近800枚。1973年9至11月,1974年6至11月,甘肅省居延考古隊兩次發掘額濟納河居延漢簡出土遺址,在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隧和肩水金關遺址出土簡牘19400余枚,多為木牘,少為竹簡。統稱“居延新簡”[12]。
1976、1982年居延采集漢簡。木質,283枚。甘肅省居延考古隊在漢居延都尉三十井塞次東隧地區采集173枚,又甲渠候官遺址采集22枚,又甲渠塞第四隧地區采集67枚,又居延地區采集散簡兩批計21枚[7]。
1977年玉門花海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簡牘。木質,簡91枚、七面觚1枚。甘肅省居延考古隊在玉門花海以北30公里處長城烽燧遺址發掘出土。屬漢代酒泉郡北部都尉文書檔案,其中“武帝遺詔”觚與《倉頡篇》的發現,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獻地位[13]。
1979年居延采集漢簡。木質,100余枚。甘肅省居延考古隊再次對額濟納河下游80余處遺址展開普查,采集漢簡100余枚[7]。
1979年馬圈灣出土漢代簡牘。木質,1217枚。甘肅省博物館發掘玉門關以西馬圈灣西漢后期烽燧遺址獲得,形制為木簡、兩行牘和木觚[14]。
1979至1989年敦煌采集漢簡。木質,147枚。敦煌市博物館在歷次文物普查中,于鹽池灣、后坑、小方盤城南第一隧、馬圈灣、小方盤城、臭墩子、蘆草井溝、小月牙湖、后坑墩、人頭瘡瘩、條湖坡懸泉置等12個遺址中采集[14]。
1981年武威磨咀子漢墓出土漢簡。木質,26枚。后稱“王杖26簡”[7]。
1984年武威市五壩山3號漢墓出土木牘。木質,1枚。
1985年武威旱灘坡19號晉墓出土木牘。木質,5枚。
1986年天水放馬灘1號秦墓出土簡牘。竹制,461枚[1]。
1986年張掖高臺晉墓出土木牘。木質,l枚。
1986年居延肩水金關出土漢簡。木質,1000余枚。1986年6至8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金塔縣大灣城(A35)發掘獲得[7]。
1986至1988年敦煌市博物館采集漢簡。木質,137枚。
1989年武威旱灘坡東漢墓出土漢簡。木質,16枚。內容有兩類,一為養老受王杖之制書和王杖受令之律令,二為坐贓為盜、蟲害、水災的刑律。
1990年清水溝漢代烽燧遺址出土漢簡。木質,1冊27枚、散簡14枚、素簡21枚。內容為歷譜、符、爰書、品約、簿籍等。其中歷譜為宣帝地節元年(公元前69年)歷書,是迄今發現最早最完整的歷譜,為認識太初改正后的標準歷譜格式提供了實物資料。
1990至1992年敦煌懸泉驛出土漢簡。木質,字簡23000余枚、素簡12000余枚。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在敦煌與安西交界處漢代懸泉驛遺址發掘出土。包括詔書、律令、科品、檄記、簿籍、爰書、劾狀、符傳、歷譜、術數、醫方等方面。內容完整和基本完整的簡冊40多部[15]。
1990至1998年安西采集漢簡。木質,約100枚。安西縣文物部門在長城烽燧遺址普查中采集。
1999年敦煌采集漢簡。木質,300余枚。敦煌市博物館在玉門關外小方盤城遺址中采集。
2000年武都縣琵琶鄉趙坪村出土漢簡。木質,12枚。雙面書寫。
敦煌研究院建國初期購藏漢代簡牘。木質,16枚。
二、敦煌出土文獻
敦煌莫高窟第17窟(敦煌研究院編號,俗稱“藏經洞”)出土的文獻,統稱“敦煌遺書”或“敦煌文書”,是迄今發現一次性出土量和影響力最大的古代文獻。清光緒26年5月26日(公元1900年6 月22日),莫高窟守寺道士王圓箓在清理第16窟流沙時,17窟始現于世。敦煌遺書的發現,引發國際學術界巨大震撼,被譽為“20世紀東方文明四大發現”之一。
莫高窟出土文獻為古寫本和印本,總量約5萬件。材質以紙質為主,部分為絹質。時代跨度為4至11世紀約800余年。內容可分宗教文獻和世俗文獻兩大類,其中宗教文獻約占80%。宗教文獻以佛教典籍居多,包括經律、論、疏釋、贊文、陀羅尼、發愿文、祈請文、懺悔文、祭文、僧傳、經藏目錄等,以及部分佚經和偽經等。此外尚有道教典籍500余件和三階教、摩尼教、景教等其他宗教典籍。世俗文獻包括天文、歷法、歷史、地理、方志、圖經、醫書、民俗、名籍、賬冊、詩文、辭曲、方言、游記、雜寫、習書等,內容多為傳統文獻中不可多見的資料。形制以卷軸裝為主,間有梵篋裝、經折裝、旋風裝、蝴蝶裝、冊子裝和單頁等多種形式,以及部分拓本、印刷本和刺繡本。文字以漢文俱多,另有吐蕃文、回鶻文、西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闐文、梵文、吐火羅文、希伯來文等多種古代民族文字。
敦煌文獻現存情況,據相關數據概略統計如下:[16]

敦煌文獻發現后劫難頻仍,自1907至1914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俄國人奧布魯切夫、鄂登堡,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美國人華爾納等人,先后從莫高窟掠走約3.5萬件,約占出土總量三分之二。
除上表外,海內外尚有私人和部分圖書館、藝術館院、研究院所藏有數目不詳的敦煌文獻。
三、黑水城出土文獻
額濟納旗黑水城遺址出土的西夏文等少數民族文字文書及宋遼夏金元漢文文書統稱“黑水城文獻”。
黑水城位于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達賴庫布鎮(原屬甘肅省)東南約25公里的荒漠中,歷史上曾是一片綠洲。西夏設黑水監軍司,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設亦集乃路總管府。“亦集乃”為“黑水”西夏語稱,后世異稱“額濟納”。元亡,黑水改道,植被沙化,城郭廢棄。
500余年后,1908年4月和1909年5月俄國人科茲洛夫率探險隊兩次進入黑水城掠走大量文獻與文物。1914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涉足黑水城得到不少西夏遺物。1927年中瑞(瑞典)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中方團員黃文弼在黑水城及附近遺址采集數百件文書。1962年和1963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調查古居延時,在黑水城采集少量文書。1976年和1979年甘肅省文物工作隊兩次調查黑水城,分別采集少量文書。1983年和1984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對黑水城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出土各類文獻4000余件。
黑水城出土文獻總量約3萬件,橫跨宋、遼、金、夏、元約400余年,包括西夏文、漢文、古藏文、畏兀爾蒙古文、八思巴蒙古文、回鶻文、亦思替非字、古阿拉伯文等多種民族文字類型。其中西夏文獻數量約占90%,漢文次之。形制有卷軸裝、經折裝、蝴蝶裝、縫繢裝、包背裝、線裝及單頁等多種形式。
內容上西夏文可分為語言文字、歷史法律、文學、古籍譯文、佛教經典5類。其中《番漢合時掌中珠》、《文海》、《音同》、《天盛律令》、《孟子》、《孫子兵法》、《孝經》、《類林》等較完整典籍對研究西夏語言文字、政治結構、法律典章、社會生活、民族習俗、宗教信仰以及補遺、正誤漢文傳統文獻具有十分珍貴的資料價值。漢文文獻可分為農政文書、錢糧文書、俸祿與分例文書、律令與詞訟文書、軍政與站赤文書、卷宗(含票據、契約、書信)、儒學(禮儀、文史)、宗教、醫算(含歷學、符占秘術、堪輿地理及其它)10類[18]。
黑水城及疏勒河流域出土西夏文和宋遼金夏元漢文文獻現存情況綜合統計如下[19]:
1.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文獻,131種,8286面,形式有寫本、刻本、活字本等。內容以佛經為主,兼有《瓜州審案記錄》、《軍抄文書殘頁》等部分世俗文獻。館藏以1947年寧夏靈武出土文獻為主,后收入俄藏佛經21卷。部分有“天賜禮盛國慶元年”、“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皇慶元年”等紀年。史金波1973年、1982年重新整理,在其《西夏佛教史略》[20]附錄中列目。
2.中國國家博物館藏西夏文獻,殘葉1紙兩面,寫本。正面“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背面“瓜州審案記錄”。
3.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西夏文獻,殘葉4紙。《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寫本3紙,背面《瓜州審案記錄》寫本3紙;西夏文經咒殘葉1紙,刻本。
4.敦煌研究院藏西夏文獻,共23種類。1958年莫高窟附近佛塔內出土3種175面;上世紀90年代敦煌研究院對莫高窟北區進行系統考察時出土,20種類81紙。
5.甘肅省博物館藏西夏文獻,22種類。1952年天梯山出土5種22面;1972年武威張義下西溝峴出土17種類97面。
6.定西市安定區文化館藏西夏文獻,泥金寫本,經折裝,8頁,內容為《大方廣佛華嚴經》。1972年武威張義下西溝峴出土。
7.武威市博物館藏西夏文獻,14種類100面,1987年武威纏山鄉亥母洞遺址出土。
8.張思溫先生藏西夏文獻,內容為《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十一至第十五,活字本,經折裝。1917年寧夏靈武出土,現藏寧夏回族自治區檔案館。
9.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藏西夏文獻,內容為《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十六、五十七、七十六,活字本,經折裝。1917年寧夏靈武出土。
10.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藏西夏文獻,23種類,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為賀蘭山方塔出土,16種類310面,另計長卷4種及多紙殘葉。另一部分為賀蘭縣宏佛塔出土,3種類2殘紙及長225厘米《發愿幡帶》1件。
11.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藏西夏文獻,佛經5 種32面,刻本,蝴蝶裝、經折裝,1991年中央電視臺拍攝記錄片《望長城》時在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綠城遺址發現。
12.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黑水城文獻,由三部分組成,主要是1983、1984年對黑水城進行系統清理發掘的成果。一是西夏文文獻,30種類81面及殘葉100余紙,刻本、寫本,蝴蝶裝、經折裝及單散葉,內容為佛經和各類社會文書。二是漢文文獻,共4213件,以元代文獻為主。其中社會文獻占絕大多數,有公文、民間文書、票據、印本等等,內容涉及農政、錢糧、俸祿與分例、律令詞訟、軍政站赤、契約、卷宗、書信、禮儀、儒學、文史、醫算、歷學、符占秘術、堪輿地理以及佛教文獻等。三是少數民族文字文獻,除西夏文外,尚有畏兀爾蒙古文、八思巴蒙古文、古藏文、亦思替非文字、古阿拉伯文等多種民族文字文獻。
13.西安市所藏西夏文獻,佛經5種130面。西安市文物局藏4種,泥金寫本、墨書寫本,刻本;陜西省圖書館藏1種,刻本。
14.故宮博物院藏西夏文獻,佛經1件,長卷式刻本,高17厘米、長260厘米,后有施經發愿文34行,刊記為“大明朝壬子”“五年正月十五日”。
15.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西夏文獻,佛經2種。《圣妙吉祥真實名經》刻本,經折裝,共16面,面6行。《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刻本,經折裝,殘葉。1930年貝格曼在黑水城附近掘得,后自香港轉至美國,1965年入藏臺灣[21]。
16.俄羅斯藏黑水城文獻[22],主要是1909年前后俄國人在黑水城先后掘獲,現藏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與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即冬宮博物館)。共有8000多個編號,內容涉及政治、法律、經濟、軍事、文化、社會和語言文字等方面,時代包括宋、西夏和元。其中西夏文占絕大部分,兼有部分漢文及其它少數民族文字。上世紀初大量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獻的發現,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震撼,西夏學便應運而生。
17.日本藏西夏文獻[23],分藏于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圖書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亞人文情報學研究中心、龍谷大學圖書館、大阪大學外國學圖書館、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7家單位,共532面。內容涉及《大方廣佛華嚴經》、《圣勝慧彼岸到功德寶集頌》、《白傘蓋陀羅尼經》、《種咒王蔭大孔雀經》、《現在賢劫千佛名經》、《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佛頂心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圣摩利天母總持經》、《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等諸多佛經,以及“瓜州監軍司審判案”和少量谷物借貸等社會文書。除紙本文書外,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尚藏有西夏文佛經斷簡和西夏文、回鶻文文書斷簡。
18.英國藏黑水城文獻[24]主要是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在黑水城遺址掘獲品,現藏英國國家博物館(又名不列顛博物館),共7000多編號。除西夏文外,波斯文、藏文、回鶻體蒙文、巴利文、梵文和漢文文種數量也十分可觀。內容涉及官府文書、軍法兵書、典當契約、韻類辭書、詩歌藝文、醫學藥方、星歷占卜、佛經等。
19.法國藏西夏文文獻[25],分藏于法國國家圖書館和法國集美亞洲藝術國家博物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著錄246件,內容包括《華嚴經》、《二十一種行》、《瑜伽師地本母》、《正法念處經契》等。其中經折裝《華嚴經》1件、木板寫本1件和部分殘葉是1938年伯希和在中國購得。法國集美亞洲藝術國家博物館藏為六卷本西夏文泥金寫本《妙法蓮華經》中的三卷。1900年八國聯軍攻進北京后,法國使館毛利瑟、費爾南·貝爾多和伯希和在北京白塔下掠取。此經紺紙金書,絹面被覆,里紉黃絹,外紉藍絹,經首有佛像一頁,外有漢字題簽。裝幀精美,保存完好,系存世最完整的西夏文泥金寫經卷冊,具有重要學術、文物和藝術價值。
20.德國藏西夏文文獻與法國集美亞洲藝術國家博物館藏同品,為六卷本西夏文泥金寫《妙法蓮華經》的另三卷。原存法國,后輾轉被德國博物館收藏。
21.瑞典藏西夏文文獻指瑞典斯德哥爾摩民族學博物館藏品。內容為《大白高國新譯三藏圣教序》、《佛說月光菩薩經》、《佛說了義般若波羅密多經》、《圣無能勝金剛火陀羅尼經》、《毘俱胝菩薩一百八名經》、《佛說菩薩修行經》、《大方等無想經》等西夏文佛經以及部分殘葉。時代多為元代刻經,其部分題有“元世祖及皇太后、皇后印經”等重要款識至為珍貴,尤其《大白高國新譯三藏圣教序》為西夏文文獻遺存孤品,是研究西夏早期譯經史的重要資料。
上述各地收藏的西夏文文獻與黑水城出土漢文及其他少數民族文字文獻,近20年來大部分已經整理出版。2005年出版的《中國藏西夏文文獻》由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學研究中心和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中心(現西夏學研究院)整理完成,匯集了國內各家庋藏的西夏文文獻。2008年出版的《中國藏黑水城出土漢文文獻》和2013年出版的《中國藏黑水城出土民族文字文獻》由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和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所共同對上世紀80年初期黑水城清理發掘成果進行的全面整理與研究。俄、英、法、日藏西夏文獻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學研究中心、北方民族大學等單位陸續整理出版。瑞典、德國及法國集美亞洲藝術國家博物館等藏西夏文獻,目前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學研究中心和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正在積極整理當中,不日將公諸于世。
甘肅是出土文獻最為豐富的地區之一,在全國具有重要的地位。巨大的原始文獻出土量不僅有力地補證了傳世文獻的闕誤,反映了秦漢至宋元各個時期政治軍事和社會生活的真實面貌,極具歷史研究價值。同時還全面揭示了甘肅乃至西北地區秦漢至宋元地下早期文獻的發展。甘肅出土文獻從文獻反映的時代上可以劃分為三個不同階段,第一階段簡牘文獻,上自戰國晚期天水放馬灘出土的秦簡,下至張掖高臺晉墓出土的木牘,歷經戰國、秦漢、魏晉時期約800年。第二階段敦煌文獻,其最早記年為日本中村不折所藏前秦苻堅甘露元年(公元359年)《佛譬喻經》,晚至北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歷經東晉十六國、南北朝、隋唐、北宋約600余年。第三階段黑水城文獻,跨越唐、五代、遼、宋、西夏、金、偽齊、元(北元)近800年。各階段在時代上首尾交錯相接,較為完整地鏈接起甘肅乃至西北地區先秦至宋元約1800余年地下早期文獻的基本發展脈絡,這在全國絕無僅有。
參考文獻:
[1]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放馬灘秦簡[M].中華書局,2009.
[2]甘肅省文物考古隊,甘肅省博物館.漢簡研究文集[M].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
[3]孛鵬旭.百年來簡牘出土數量新統計[J].絲綢之路,2009 (10).
[4]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M].商務印書館,2013.
[5]黃文弼.羅布卓爾考古記[M].線裝書局,2009.
[6]斯坦因著,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M].中華書局,1987.
[7]何雙全.簡牘[M].敦煌文藝出版社;2004.趙超.簡牘帛書發現與研究[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8]閻文儒.河西考古雜記[J].社會科學戰線,1986(4).
[9]甘肅省博物館.甘肅武威磨咀子6號漢墓[J].考古,1960 (9);甘肅省博物館.甘肅武威磨咀子漢墓發掘[J].考古,1960(9).
[10]甘肅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漢簡[M].中華書局,2005.
[11]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武威漢代醫簡[M].文物出版社,1975.
[12]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冊文書[J].文物,1974(7).
[13]嘉峪關市文物保管所.玉門花海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簡牘[Z].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合編.漢簡研究文集[M].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吳仍禳,李永良,馬建華釋校.敦煌漢簡疑文[M].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
[14]吳礽驤,李永良,馬建華釋校.敦煌漢簡釋文[M].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
[15]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發掘簡報[J].文物,2000(5).
[16]郭峰.敦煌西域出土文獻的一個綜合統計[J].敦煌學輯刊,1991(1).
[17]中國書店藏敦煌文獻編輯委員會.中國書店藏敦煌文獻[M].中國書店,2007.
[18]塔拉,杜建錄,高國祥.中國藏黑水城出土漢文文獻[M].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19]史金波,王菡,全桂花,林世田.國內現存出土西夏文獻簡明目錄[J].國家圖書館學刊(西夏研究專號),2002年增刊;史金波,陳育寧.中國藏西夏文獻[M].甘肅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藝出版社,2008.
[20]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M].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21]林英津(臺灣).史語所藏西夏文佛經殘本初探[J].古今論衡,2001(6).
[22]史金波等主編.俄藏黑水城文獻[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至2000.
[23][日]荒川慎太郎主編.日本藏西夏文文獻[M].中華書局,2010.
[24]西北第二民族學院,英國國家圖書館等編.英藏黑水城文獻[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5]西北第二民族學院,英國國家圖書館等編.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獻[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作者簡介:高國祥,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主任、總編輯。
中圖分類號:G25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9106(2016)03-013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