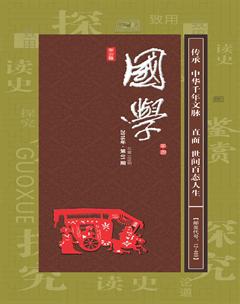士人的風骨
易中天
士與知識分子
認真說來,士或士人,作為概念或稱呼,已經是歷史了。今天沒有“士”,只有“知識分子”。所謂“知識分子”,又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指“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狹義的特指“社會的良心與良知”。這兩種,都與“士”有關。
廣義的知識分子,是士人身份的現代化。古代的士,原本就是一種“社會分工”和“職業身份”。所謂“士農工商”,即意味著農是莊稼人,工是手藝人,商是生意人,士是讀書人。要求最嚴的時候,士人除了讀書,以及因為讀書而做官,不能從事別的行業。當然,躬耕于垅畝,是可以的。但,耕是副業,讀是主業。耕讀為本,是因為國家重農;詩書傳家,才是命脈所系。親自到地里干活,帶有“體驗生活”的性質。
所以,士人可以不耕,不能不讀。開作坊,做生意,就更不行。劉備賣履,嵇康打鐵,當時便都算“出格”。讀書做官,則理所當然。做官以后,也還要讀書,有的還寫寫詩,做做學問。這就叫“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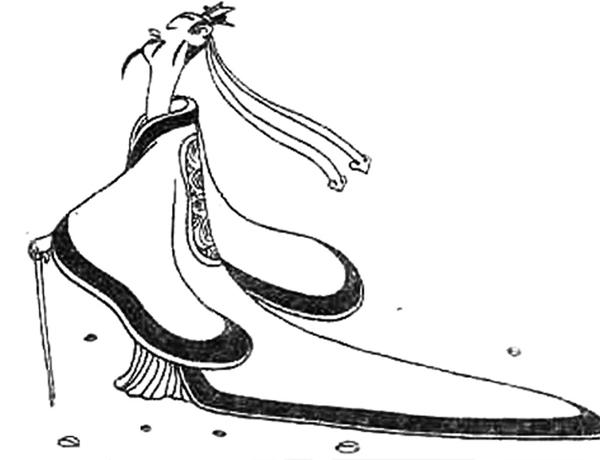
可見,古代的士,就是讀書人,而且是“職業讀書人”。或者說,是在讀書與做官之間游刃有余的人。因為“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的“優”,是優裕的意思。也就是說,做官輕松自如,就做點學問;治學精力過剩,就當當官員。這是古代士人的最佳狀態。能做到這一點的,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這樣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今天受過高等教育的,即廣義的知識分子,其實未必都讀書。教科書當然是要讀的,但那叫“學習”或“上課”,不叫“讀書”。畢業以后,也未必都要做官,更很少有人再去務農。他們可以當白領,做律師,辦企業,搞藝術,成為科學家,都正大光明,自由平等。讀書,則只是業余愛好。因此,我們很難從職業身份,來認定誰是士,誰不是。甚至讀不讀書,也不足為憑。要知道,就連文人,也讀書的。
不看職業,也不看讀書,那看什么?看精神。實際上,士或士人在古代,既是一種“職業身份”,又是一種“文化精神”。狹義的知識分子,則是士人精神的再傳承。因此,本文所說的士人,也包括其他,都是指某種精神類型、氣質類型或人格類型,甚至只是一種“文化符號”。比如梅蘭芳,職業雖是藝人,卻不但成就極高,更在抗戰時期,表現出傳統士大夫的精神氣質。因此,文化界普遍視他為士人,要尊稱“梅先生”的。
那么,士人的精神、氣質和人格特征是什么?
擔當與擔待
我認為,就是有風骨、有氣節、有擔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是有風骨;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孟子·盡心上》),可殺不可辱(《孔子家語·儒行解》),是有氣節;仁以為己任,死而后已(《論語·泰伯》),是有擔當。
擔當是廣義的,包括“好漢做事好漢當”,自己的事情自己負責。有此一條,即可無愧為“士”。但嚴格意義上的“士”,還得有“天下之擔當”。這種擔當,古之士人,一般都有。后之士人,也“可以有”。但如果是“國士”,則“必須有”。劉備寄居劉表時,就曾當面痛斥一個名叫許汜的人,說他明知天下大亂國難當頭,卻居然“求田問舍,言無可采”,真是徒有國士之名,當為士林不齒(《三國志·陳登傳》)。
可見古人心目中的國士,必須像《畢業歌》所云,能夠“擔負起天下的興亡”。至于“無雙國士”,則恐怕只有像諸葛亮那樣才行。可惜這樣一位難得的士人,卻被《三國演義》歪曲為自命清高忸怩作態的酸腐文人,作夠了秀才出山,實在讓人忍無可忍。
詩人和學人,則可以不必有此擔當。真正的詩人,當然也都是與國家民族同呼吸共命運的。他們的作品,也一定是人民的心聲。但這是“反映”,不是“擔當”。同樣,學人也可以撰寫時評,發表政見,以天下為己任。但這時,他已經是士人了。或者說,是具有士人精神的學人。純粹的學人,完全可以“兩耳不聞天下事”。正如純粹的詩人,完全可以“每有閑情娛小我”。天下和國家,是可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為社會和人類,提供了高質量的學術成果和藝術作品,就是真正的學人和詩人。
至于文人,則是沒有擔當的,也別指望他們有。幫閑和幫腔,要什么擔當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點兒“擔待”。比方說,皇帝或上級犯了錯誤,便挖空心思替他們擦屁股,打補丁。2007年,陳水扁夸人時誤用“罄竹難書”一詞,輿論嘩然。歷史學家出身的“教育部長”杜正勝,便硬說這成語沒有貶義,用在哪兒都行。看來,替主子文過飾非,也是古今如一,兩岸皆同,而且“駕輕就熟”的。
如果實在打不了圓場,主子又不想認賬,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當替罪羊。還有,揣摩失誤,站錯了隊,表錯了情,得自認倒霉。賴得一干二凈的也有。哪怕白紙黑字寫著,眾目睽睽看著,當事人都還活著,也不承認。但,你可以不認錯,不能不認賬。賬都不認,哪有擔當?連擔待都沒有!
這就是士人與文人的區別之一。士人有擔當,文人得擔待。擔當是對天下的,擔待是對領導的;擔當是自覺的,擔待是無奈的;擔當是對自己負責,擔待是幫別人賴賬。所以,士人,也包括詩人和學人,都能文責自負。文人,則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別人頭上。而且那“別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級。除非那上級,是上上級正好要收拾的人。
傲骨與傲氣
沒有擔當,也不會有氣節。何況幫腔與幫閑者,原本就沒有什么需要堅守。因此,文人不講“氣節”,只講“節氣”。到什么季節,就開什么花;刮什么風,就使什么舵。名為“與時俱進”,實為“與勢俱進”。哪邊得勢,或可能得勢,就往哪邊靠。
所以,文人的“風骨”,極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來,不是“長”出來的。就連他們的“反骨”,也不過“另一副嘴臉”。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徹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這是“返祖現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風骨”。
風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個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子·盡心下》)。哪怕“千首詩傲萬戶侯”,或者“天子呼來不上船”,也算詩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風骨。這仍然與職業身份無關。比方說,某些教授、博導、學術帶頭人,見了當官的,就點頭哈腰,滿臉諂媚;或者領導放個屁,就馬上提供“數據支持”,還說得頭頭是道。請問,這還能算是學人嗎?
真正的學人,一定有士人的風骨。其表現,就是堅持學術的標準,堅守學者的良知與良心。這就像真正的詩人,面對災民和冤魂,絕不會說什么“縱做鬼,也幸福”。寫這種狗屁玩意的,一準是文人,還是不入流的。
或許有人會問:文人,就不傲嗎?呵呵,傲,而且傲氣十足。他們往往目空一切,誰都不放在眼里,還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輕”。但這是傲氣,不是傲骨。有人一見文人的傲,就覺得他牛,欽佩不已,這其實是腦子進了水,還一輩子沒甩干。
傲氣與傲骨,有什么區別?傲骨是因為自己,傲氣是因為別人。堅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趨炎附勢、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別人看不起,又要出人頭地、體面風光,所以有傲氣。傲氣,也是秀出來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無傲氣;地道的文人,則有傲氣無傲骨。傲骨還是傲氣,是區分士人與文人的緊要之處。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漢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貴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諸侯、大夫);秦漢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農、工、商)。但無論哪種,士都是最有知識、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貴感。這種高貴,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貴族”。他們也許在經濟上一貧如洗,在事業上一事無成;但在精神上,卻富有得像個國王,可以把一切權貴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風骨。
俠義與清高
士人不但有傲骨,還往往有俠骨。傲骨是對權貴的,俠骨是對朋友的。所謂“士為知己者死”,即此之謂。至于是“紅顏知己”,還是“知遇之恩”,則無所謂。但可以肯定,成為士人的知己,極難。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
這同樣不奇怪。因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來,文士變成了儒,武士變成了俠,都為專制不喜。韓非就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韓非子·五蠹》),統統應該消滅。只不過漢武以后,統治者的辦法,是恩威并重,軟硬兼施,兩手都用。對儒,主要是“撫”(封官許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對俠,則主要是“剿”(武力鎮壓),兼之以“撫”(誘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但,統治者能夠消滅俠,卻消滅不了俠義。形式上或職業的俠沒了,俠就會變成精神和風氣,滲透于骨血,彌漫于天下。它在民間,為“義氣”;在士人,為“肝膽”。不過,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常是讀書人。畢竟,文士是統治者收買拉攏的重點,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賢有云:與有肝膽人共事,于無字句處讀書。
但真正的士人,總歸是有肝膽的。肝膽相照,則意氣相投;同聲相應,則同氣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們的聲譽,則叫“清譽”;他們的品性,則叫“清高”。總之,士人最為看重的,是“清”。不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純、清淡、清靜、清朗、清明、清雅、清正。為此,他們甚至甘于清貧。故士人發表的時評,就叫“清議”。他們的圈子,也當然“清一色”。閑雜人等,根本別想混入。
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點:愛惜羽毛。表現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連一般的世俗也會拒絕。比方說,反對白話文,拒絕上電視。前者是極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別的謹慎。因為一怕做“規定動作”,被“喉舌化”;二怕為了收視率,被“娛樂化”;三怕主持人問一堆愚蠢問題,被“弱智化”。這可有礙清譽,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總之,士人的特點,就是有風骨、有氣節、有擔當、有肝膽,再加“愛羽毛”。
然而眾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這話又怎么講?也只能說,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為清高只能來自風骨。風骨靠不住,清高又豈能是真?就連他們的“俠義”,當然也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