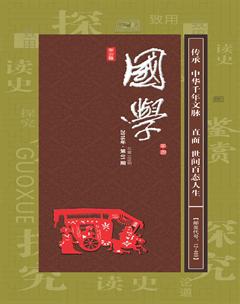1883年: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金融危機
近現(xiàn)代商業(yè)史上,第一場中外大商戰(zhàn)發(fā)生在1884年。但是倘若沒有1883年的那場金融危機,歷史也許將被改寫。
清光緒年間,湖州南潯民間及江浙一帶曾出現(xiàn)以湖絲發(fā)家的所謂“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的巨商。財產(chǎn)達百萬以上者稱之曰“象”。五十萬以上不過百萬者,稱之曰“牛”,其在二十萬以上不達五十萬者則曰“狗”。南潯“四象八牛”之說,屬于民間說法,并無正規(guī)的統(tǒng)計和詳細記載,七十二墩狗僅僅是泛指。
19世紀60年代之后,江南絲商面臨重大危機。洋商壟斷蠶絲出口市場,拼命壓低生絲價格,抬高廠絲價格,從中攫取暴利。江南紡織業(yè)迅速沒落,昔日富可敵國的絲商們頓時都成了“病象瘦牛喪家狗”。
概況:第一場中外商戰(zhàn)
1882年5月,后世被譽為商圣的紅頂商人、當時的中國首富胡雪巖出手,高調(diào)坐莊,第一場中外大商戰(zhàn)爆發(fā)了。
胡雪巖大量購進生絲,見絲就收。新絲一出,胡雪巖即派人大量收購。外商想買一斤一兩而莫得,無可奈何,向胡說愿加利1000萬兩,如數(shù)轉(zhuǎn)買此絲,胡非要1200萬兩不可。外商不買,過了數(shù)日,再托人向胡申買,胡堅持咬定此價。外商決心不買胡之生絲,等待次年新絲出來再說。胡雪巖則邀請絲業(yè)同行合議,共同收盡各地生絲,不要給外商,迫外商出高價收購,這樣我們必獲厚利。商戰(zhàn)進入決戰(zhàn)時刻,胡雪巖前后已投入資金超過1500萬兩,繼續(xù)堅壁清野,囤貨堅挺,大部分上海絲商停止營業(yè),屏氣而作壁上觀。華洋雙方都已到忍耐極限,眼見勝負當判,誰知“天象”忽然大變。
變數(shù)之一,歐洲意大利生絲突告豐收,歐洲期貨市場的緊張頓時緩解,消息傳回中國,商心開始動搖。更大的變數(shù)是,中法爆發(fā)戰(zhàn)爭。市民提款遷避,市面驟變,金融危機突然爆發(fā)。11月,江浙絲商的價格同盟瓦解,生絲易爛,不能久儲,胡雪巖不得不開始拋售,價格一路狂泄,損失以千萬兩計。
另一變數(shù)是中法戰(zhàn)爭中國失敗后,第二年9月,胡雪巖的依恃左宗棠病逝于福州。
慘烈的商戰(zhàn)中,民族資本倒下
1883年,這一年中國發(fā)生了史上第一次金融風(fēng)暴,“我國第一代民族資本家”胡雪巖與洋商對抗失敗,晚清民族產(chǎn)業(yè)被扼殺了,傳統(tǒng)商人階層集體隕落。“三大商幫”中的兩枝,徽商和江浙商人在此役中損失慘重,從此一蹶不振,萌芽于晚明的紡織業(yè)徹底崩盤。不僅如此,胡雪巖的破產(chǎn)同時也是脆弱的中國新興經(jīng)濟體系的一次災(zāi)難。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金融危機。
胡雪巖雖然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倒下,但卻為后人留下很多寶貴遺產(chǎn),他精心創(chuàng)下的胡慶馀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價”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今天的我們,都應(yīng)該向胡雪巖學(xué)習(xí),讓我們知道是什么讓我們的先輩倒下,耽擱了發(fā)展的道路。
金庸先生曾為胡雪巖題詞:
富國裕民,東南阜康,
振興經(jīng)濟,昌盛吾杭。
商機還是危機
1850年左右,中國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股市,最早是一些在華的外國人從事外企的股票投機,后來一些中方買辦看到有利可圖,也加入進來。洋務(wù)運動興起后,很多近代意義的中國企業(yè)開始出現(xiàn),為了融資的需要,這些企業(yè)也開始發(fā)行股票,進入股票市場。經(jīng)過20多年的培育,中國股市迎來了一個黃金時期,從1870年代開始,上海股市開始瘋漲。許多商人和投機者大肆追捧新上市的中方企業(yè)股票。因為在他們眼中,這些企業(yè)多半是官督商辦,有著很強的官方背景,經(jīng)營上也少有競爭對手。在投機者的追捧下,這些企業(yè)的股票開始瘋漲,當時輪船招商局的股票一開始一股只有幾十兩,短短幾個月便上漲到近300兩,而開平礦務(wù)局的股票也在短時間內(nèi)從不足十兩漲到百余兩。
受股市瘋漲的刺激,不僅普通投機者開始大量涌入,一些錢莊也不甘人后,開始將錢莊資金投入股市。錢莊逐漸成為股市中的主力軍,其用于拉升股價的資金幾乎全為錢莊的流通資金,而在這些資金大量進入股市后,由流通資金變成企業(yè)的生產(chǎn)資金,也就意味著市場流通貨幣開始減少,這離股災(zāi)的爆發(fā)就不遠了。
事情是這樣發(fā)生的:1882年前后,當時中國興起了一股造鐵路、開煤礦、興輪船的熱潮,相關(guān)的股份公司紛紛建立。大量資金從錢莊、商號流向股市。更要命的是:許多人都把買賣股票當作了賺錢的正當生意,所以向錢莊貸款用于炒賣股票的現(xiàn)象也很普遍。
惡果隨之而來,《申報》說:從1882年開始,“買賣股份之旺,幾于舉國若狂,不及一年,而情弊顯露,股票萬千直如廢紙。”(見1884年1月23日《申報》)從錢莊、商號流出的大量資金就此在股市中蒸發(fā)。壞賬、呆賬由此而大量出現(xiàn),經(jīng)濟形勢就此惡化。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胡雪巖將一筆數(shù)額不小的資金用在了囤積物資(生絲)上,應(yīng)該說在當時是明智之舉。畢竟在面臨資金困難時,生絲還能夠及時變成現(xiàn)銀的。但是,胡雪巖錢莊的資金遠不止這囤積生絲的480萬兩白銀,更多的資金當時都放貸在外。當猛烈的金融風(fēng)暴降臨后,這些放貸在外的大量資金往往就成了無法收回的壞賬、呆賬。一旦遭遇擠兌風(fēng)潮,自然就難以招架。
胡雪巖是一個傳奇。他是安徽績溪人,幼年喪父,家境貧寒,徒步百里到杭州,進了一家錢肆當學(xué)徒。他頭腦活絡(luò),善于經(jīng)營,很得于姓主人的信賴,主人竟在臨終前將錢肆都贈給了胡雪巖。不過,胡雪巖真正發(fā)跡卻是從結(jié)識了左宗棠才開始的。
1862年,胡雪巖因機緣結(jié)識了任浙江巡撫、正在跟太平軍作戰(zhàn)的左宗棠,此后20年里一直當他的采運官,為之籌措錢糧、軍餉,成了后者的“錢袋子”。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胡雪巖的財富驚人地暴增。他依仗左帥權(quán)勢,在各省設(shè)立阜康銀號20余處,成為信用最好、實力最強的徽商錢莊,并經(jīng)營中藥、絲茶業(yè)務(wù),操縱江浙商業(yè),資金最高達2000萬兩以上,擁有土地萬畝,在短短20年內(nèi)一躍成為全國首富。他深得朝廷信賴,被授布政使銜江西候補道,從二品頂戴,還是清朝300年唯一一個被賜穿黃馬褂的商人。
在1882年,早已名滿天下的胡雪巖面臨著事業(yè)上的一次重大抉擇。他手握1000萬兩以上的巨額現(xiàn)銀,是去辦洋務(wù),還是倒賣生絲,竟一時躊躇。胡雪巖對洋務(wù)并不陌生。可是,左宗棠與李鴻章是政治上的死對頭。當時主管洋務(wù)的卻是李鴻章,這讓深諳官場門道的胡雪巖十分遲疑。第二條路就是倒賣生絲。
19世紀60年代之后,江南絲商面臨重大危機。當時,英美各國開始在上海創(chuàng)設(shè)機械繅絲廠。西方“工業(yè)革命”的技術(shù)創(chuàng)新就是從紡織業(yè)開始的,所以,中國傳統(tǒng)手工繅絲的生產(chǎn)效率和質(zhì)量根本無法與機械繅絲競爭。洋商為了進一步掠奪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原料,壟斷蠶絲出口市場,拼命壓低生絲價格,抬高廠絲價格,從中攫取暴利。1868年,生絲每擔(dān)市值白銀517兩,到1875年,每擔(dān)價格已下跌至285兩,再過8年,更暴跌至200兩。興旺百年的江南紡織業(yè)迅速沒落。
目睹此景,胡雪巖認為商機浮現(xiàn)。繅絲產(chǎn)業(yè)蒸蒸日上,而作為原材料的生絲卻價格日跌,這是一種極其不正常的現(xiàn)象。據(jù)他觀察,主要原因是華商各自為戰(zhàn),被洋人控制了價格權(quán)。因此,他決定靠自己的財力,與之一搏。另外,還有消息顯示,在過去的兩年里,歐洲農(nóng)業(yè)遭受天旱,生絲減產(chǎn)。
正是基于這些判斷,首富胡雪巖出手了。
胡雪巖因放貸無力收回而破產(chǎn)
1882年5月,胡雪巖大量購進生絲8000包,到10月達1.4萬包,見絲就收,近乎瘋狂。與胡雪巖同時代的晚清學(xué)者歐陽昱在《見聞瑣錄》中詳細記錄了這場商戰(zhàn)的慘烈景象:其年新絲一出,胡即派人大量收購,無一漏脫。外商想買一斤一兩而莫得,無可奈何,向胡說愿加利1000萬兩,如數(shù)轉(zhuǎn)買此絲,胡非要1200萬兩不可。外商不買,過了數(shù)日,再托人向胡申買,胡堅持咬定此價。外商認為生絲原料僅操縱在胡雪巖一人之手,將來交易,唯其所命,從何獲利?決心不買胡之生絲,等待次年新絲出來再說。胡雪巖則邀請絲業(yè)同行合議,共同收盡各地生絲,不要給外商,迫外商出高價收購,這樣我們必獲厚利。商戰(zhàn)進入決戰(zhàn)時刻,胡雪巖前后已投入資金超過1500萬兩,繼續(xù)堅壁清野,囤貨堅挺,大部分上海絲商停止營業(yè),屏氣而作壁上觀。華洋雙方都已到忍耐極限,眼見勝負當判,誰知“天象”忽然大變。
變數(shù)之一,歐洲意大利生絲突告豐收,歐洲期貨市場的緊張頓時緩解,消息傳回中國,商心開始動搖。更大的變數(shù)是,中法因越南問題交惡,爆發(fā)戰(zhàn)爭。市民提款遷避,市面驟變,金融危機突然爆發(fā)。外國銀行和山西票號紛紛收回短期貸款,個人儲戶也緊急提現(xiàn)。一般商品無不跌價30%至50%,所有的房地產(chǎn)都難以脫手,貿(mào)易全面停頓。
世事如此,胡雪巖已無力回天。11月,江浙絲商的價格同盟瓦解,生絲易爛,不能久儲,胡雪巖不得不開始拋售,價格一路狂泄,損失以千萬兩計。生絲對搏失利,很快影響到“堅如磐石”的錢莊生意。民眾排隊提款,一些與胡雪巖不和的官員乘機逼催官餉,可怕的擠兌風(fēng)潮出現(xiàn)了。先是杭州總舵關(guān)門,繼而波及北京、福州、鎮(zhèn)江以及湖北、湖南等地的20多個字號,到12月5日,阜康錢莊宣告破產(chǎn)。中法戰(zhàn)爭中國失敗后,第二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11月,朝廷下令對胡雪巖革職查抄,嚴加治罪。他遣散姬妾仆從,在圣旨到來之前,就非常“及時”地郁郁而死了。他的棺木被一老仆埋于杭州西郊鸕鶿嶺下的亂石堆中,一直到整整100年后,才被人偶然發(fā)現(xiàn)。
因中法戰(zhàn)爭而誘發(fā)的上海金融危機,不僅是胡雪巖失利的直接原因,更是脆弱的中國新興經(jīng)濟體系的一次災(zāi)難。
胡雪巖在短短幾十年間,依靠靈活的手腕在官場和商場長袖善舞,很快建立起自己的商業(yè)帝國。他所掌握的阜康錢莊營業(yè)區(qū)域遍布大江南北。在這次股市繁榮之中,阜康將掌握的大量流通資金投入股市。正當阜康大肆牟利時,作為阜康的老板胡雪巖突然垮臺,這使得阜康發(fā)生擠兌風(fēng)潮,由于無力應(yīng)對,阜康只得宣布倒閉。阜康的倒閉令早就岌岌可危的股市終于崩盤,股價一瀉千里。開平礦務(wù)局的股票1883年5月還是每股210兩以上,并且很難買到,到了8月,其股價已跌至120兩,而有人則“愿意以115兩或更低的價格隨意出讓”。到了10月,開平股票每股只值70兩,到1884年則跌落到29兩。輪船招商局的股票也從1882年9月的253兩跌至1884年的34兩。與1882年9月的股價相比,這兩種股票平均下跌了87%。其余公司的股票亦莫不如是,從高價位跌到“簡直一文不值。”這場股災(zāi)是中國股市第一次大災(zāi)難,股災(zāi)之后,投機者的信心10年都沒有恢復(fù)。
正當胡雪巖因囤積生絲占用了大筆資金,而顯得捉襟見肘的時候,阜康號遭到了擠兌。擠兌首先發(fā)生在杭州,雖經(jīng)浙江布政使德馨協(xié)助料理,暫時無事,但上海阜康則因存戶聞訊爭來提款,一時無法應(yīng)對,而于1883年12月1日閉歇,上海關(guān)道立即派謝湛卿去封閉胡雪巖在浙江的四個當鋪。同一天,杭州分號也關(guān)閉了。
官府行為加重擠兌風(fēng)潮
本來杭州平日交易使用銀錢票居多,但由于“各行棧店鋪往來皆須現(xiàn)銀,概不用票,致各行業(yè)交易大受影響”。12月3日,京師阜康分號關(guān)閉。接著,鎮(zhèn)江、寧波、杭州、福州、南京、漢口、長沙等分號亦相繼閉歇,市面大為恐慌。此時官府若能出面維持金融市場穩(wěn)定,或者給予阜康票號以信用支持,危機或許可以避免,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反腐調(diào)查卻最終將阜康票號及胡雪巖推上了敗落之路。
光緒九年十一月,有人舉報刑部尚書文煜在阜康號中所存銀兩來歷不明。后經(jīng)查實其中有十萬兩是為前江西布政使文輝代存的,文煜也辯稱其“由道員升至督撫,屢管稅務(wù),所得廉俸歷年積至三十六萬兩,陸續(xù)交阜康號存放”,最后朝廷下令“即由順天府向該號商按照定款如數(shù)追出,以充公用”,責(zé)成文煜捐銀十萬兩了事。除了這十萬兩充公銀外,遭擠兌后,阜康號倒欠的官私款項約1200萬兩,其中尤以官款為重。比如,阜康及其分號裕成倒閉時,福建“省司道府庫及稅、厘、善后局匯兌京、協(xié)各餉,或購軍火,或地方善舉,由該商經(jīng)手共計存銀二十三萬一千兩”。由浙江著追的有1613900余兩,另有虧欠江海關(guān)、江漢關(guān)及兩江采辦軍火、電線等銀786800余兩,兩項共2400700余兩,占倒欠官私各款的20%。阜康倒閉后,朝廷發(fā)布上諭,稱:
現(xiàn)在阜康商號閉歇,虧欠公項及各處存款為數(shù)甚巨,該號商江西候補道胡光墉著先革職,即著左宗棠飭提該員嚴行追究,勒令將虧欠各處公私等款趕緊逐一清理,倘敢延不完繳,即行從重治罪。并聞胡光墉有典當二十余處分設(shè)各省,買絲若干包,值銀數(shù)百萬兩,存置浙省。著該督咨行各該省督撫,查明辦理,將此諭令知之。
次年閏五月初五的上諭中再次提到阜康銀號:“現(xiàn)在順天(府)辦理賑務(wù)。所有阜康銀號應(yīng)交充公銀十萬兩,著撥給順天(府)以充賑需,即由劉秉璋嚴行催追,如數(shù)解交順天府,毋稍遲延。”
轉(zhuǎn)瞬之間,官員個人的債權(quán)就變成了官府的債權(quán),阜康票號必須立即清償。至1885年12月17日,除繳還者外,尚欠公款208000余兩。胡雪巖名下的當鋪、藥店等財產(chǎn)亦被拿來充抵債務(wù)。
可以設(shè)想,如果在阜康號面臨擠兌風(fēng)潮時,政府不是急于主張自己的債權(quán)“優(yōu)先受償權(quán)”,不是忙著催逼官款,而是設(shè)法維系金融市場的信用基礎(chǔ),提供信貸支持的話,或許阜康票號就不會倒閉,胡雪巖就不會一敗涂地,其他票號也不會受到殃及。
然而,如同希冀19世紀的中國法律能為商人提供有限責(zé)任是種奢望一樣,要當時的官府出面挽救瀕臨破產(chǎn)的商人也無異于一種苛求。試想,若官府能積極制定法律保護本國商人的利益,那么它也就能夠?qū)M出口貿(mào)易施加有效的影響,抑制外商的傾銷與過度壓價。如是,胡雪巖也就不必憑個人的力量去同整個西方絲繭行業(yè)斗法了。
票號廣受官款逼提而倒閉
光緒十年冬戶部的一份奏議生動地勾畫出倒閉了的阜康號、胡雪巖們在當時官府心目中的形象:“上年胡光墉所開阜康及胡通裕票號,倒欠公私款項極多,尤為可惡!”———在官府看來,他們無異于討厭的多事之徒和麻煩制造者,應(yīng)受到反復(fù)的詛咒。除了關(guān)注自己的債權(quán)之外,官府很少考慮其維護市場秩序的職責(zé),也不理會由擠兌引發(fā)的信用危機和金融動蕩,至多只是防止那些錢鋪卷款逃跑。
耐人尋味的是,后來很多南幫票號都重蹈阜康的覆轍:源豐潤票號因經(jīng)營源通官銀號而與上海江海關(guān)歷任觀察過往較多,在橡皮風(fēng)潮中靠江海關(guān)借款維持了3個月,最后因江海關(guān)觀察蔡乃煌被革職催要借款而倒閉;李鴻章之侄李經(jīng)楚開辦義善源票號,同時還出任交通銀行總辦,遂從銀行借入大量款項,后因不能及時償還而破產(chǎn)。究其原因,在于南幫票號與政府官員過從緊密、過多地利用官款,因而一旦遭遇官款逼提就難逃倒閉的命運。
在前現(xiàn)代的法律框架中,原本就缺乏公域和私域、(公共)權(quán)力與(私人)權(quán)利的法律界分,因而作為公權(quán)代表的官府可以很輕松、毫無顧忌地跨入當下人們認為屬于私法的領(lǐng)域。在金融機構(gòu)破產(chǎn)倒閉時,政府(官府)總是傾向于積極主張自己的債權(quán)優(yōu)先于私人債權(quán)人受償,甚至還將債務(wù)人名下的全部財產(chǎn)都延攬來擔(dān)保自己債權(quán)的實現(xiàn)。至于股東有限責(zé)任,在公權(quán)力毫無限制的情況下,完全不存在由當事人通過契約方式約定設(shè)立的可能。再退一步,即使當事人真這樣做了,在官府處于強勢地位、公權(quán)力無限擴張的背景下,面對政府的債權(quán)優(yōu)先權(quán),該制度也未必能發(fā)揮什么作用。
——《財經(jīng)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