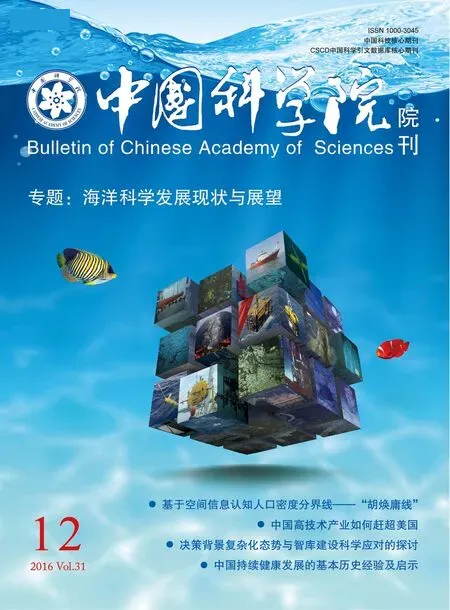深海極端環境與生命過程研究現狀與對策*
李超倫 李富超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 青島 266071
深海極端環境與生命過程研究現狀與對策*
李超倫 李富超
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 青島 266071

深海作為海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涉及到國家戰略和疆域拓展,一直是海洋強國爭奪的戰略重點。深海極端環境塑造了特殊的生命過程,資源潛力巨大,對其探測與研究是國際地球科學前沿。對水深 1 000 m 以下的海山、熱液、冷泉等海洋極端環境與生活在這些環境中的特殊生命進行綜合探測,涉及到深海地質環境、化學環境、物理環境和特殊生態系統,涉及到深海極端環境特殊裝備的研發以及深海探測與研究綜合平臺建設,涉及到考察船、深潛器、特殊裝備、方法體系的建立和技術體系的建立,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體現。文章總結了國際上深海極端環境和生命過程研究進展,在分析我國深海研究現狀基礎上,提出未來我國深海極端環境和生命過程研究對策。
深海,極端環境,生命過程,研究現狀與對策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16.12.003
一個國家的海洋權益,涉及到該國的核心利益。在全球陸地被瓜分之后,陸地周邊12海里領海、200 海里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也先后有了歸屬。現在人們的目光投向了屬于公海的深海和大洋。全球海洋的平均深度超過 3 500 m,水深大于 1 000 m 的深海區域超過 90%,其中絕大部分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的不屬于任何國家管轄的國際海域,約占地球表面積 49%。國際海域因其在海洋中所處的獨特的政治、法律地位,更因其擁有多樣性的資源,成為各國延展可控制疆界、爭取海洋權益的新空間。
深海作為海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擁有深海平原、海山、熱液、冷泉等特殊環境,導致海底地形、理化因子的劇烈變化,從而影響深層海洋動力、熱力等環境,進而孕育了獨特的生態系統和生命過程,還可能對上層海洋熱量耗散產生影響,直接關系到全球氣候變化,因此深海研究在整個地球科學和全球變化研究中都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迄今為止,人類對于深海的認識還知之甚少,對深海基本地形的實際測量甚至不如人類對火星以及月球背面的探測。因此,對于深海環境和生態系統的探索與認知是當前地球科學的前沿領域。
另外,深海蘊藏著豐富的礦產和生物資源。從 20 世紀 60—70 年代太平洋的多金屬錳結核,到海山上的富鈷結殼和洋中脊熱液口的金屬硫化物,以及最近發現的太平洋深海底的稀土資源,都將逐步成為今后各國深海資源開發的重點。同時,深海海底生物物種豐富,據估計生活在深海的未知生命類群超過 1 000 萬種。由于處于極端的物理、化學和生態環境中,深海生物形成了極為獨特的生理結構和代謝機制,產生包括各種極端酶在內的特殊生物活性物質,對生物資源的開發利用、新能源的探索乃至新型生物材料的研發都具有重大的理論和應用價值,展示了極大的資源潛力。
本文圍繞深海極端環境與生命過程研究這一當前深海研究熱點領域,總結了國內外研究進展和發展趨勢,提出我國深海極端環境和生命過程研究對策。
1 國際研究進展
從 19 世紀末英國“挑戰者號”第一次實現環球海洋科學考察以來,深海一直是國際海洋科學研究的前沿和孕育重大科學發現的搖籃。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以美國為代表的世界強國高度重視“藍海戰略”,極大增加了對深海研究的投入,催生了一系列突破性科學進展。例如,20 世紀 60 年代末發現洋底擴張,證實了“板塊學說”,并創立了“古海洋學”新學科;20 世紀 70 年代末發現深海熱液和“暗能量生物圈”,證明地殼深處有物質和能量向上輸運,并能維持龐大的不依賴于光合作用的生物群落,從而為海洋科學發展開拓了全新的領域。進入新千年后,相關國家加快向深海進軍步伐,紛紛建造用于深海研究的新型科學考察船和探測裝備,啟動了一系列深海大洋探測計劃,例如“國際海洋生物普查計劃(CoML,2001—2010)”“綜合大洋鉆探計劃(IODP,2003—2013)”“歐盟深海計劃(INDEEP)”“國際洋中脊計劃(InterRidge)”等,圍繞海山、熱液、冷泉等深海環境和生態系統熱點區域開展了一系列綜合探測和研究工作,取得了許多新的認知。
海山的形成過程與物質組成反映了地球內部物質和能量轉移的結果,海山巖石蝕變過程也是重要的能量交換過程,塑造了不同的地質環境。另外,海山可通過激發內波,促進深層海水的混合,驅動深層環流[1]。海山的阻擋形成了上升流,驅動底層水與中上層水間的垂向交換。在南大西洋巴西海盆的觀測顯示,距離海洋表面 4 000 m 海山觸發的深層湍流混合可影響到 400 m 水深的上層海洋區域[2]。另外底層流受到海山地形阻擋形成渦狀結構——Taylor-Hogg 地形旋渦[3],促使最低含氧帶水體與中深層水交換,導致海洋環境要素的變異,進而形成遠洋漁場,還觸發了一系列重要的氧化-還原反應,多種金屬元素和磷元素凝聚沉淀。海山生態系統研究計劃(CenSeam)曾在多個海區開展了綜合研究,結果顯示海山生態系統是復雜和多變的,與我們通常所認為的海山生態系統是高生產力、高生物現存量的認識不同,一些海山的生物量較低,其在水動力學、生物地球化學和生物學方面與周圍的大洋相比具有清晰的海山效應[4]。例如單個海山上的生物多樣性通常很高,但是海山之間的變化很大,物種局地化的速率在不同海山間也有很大差別,因此海山生態系統可能受流型、顆粒物通量、地貌、底質類型與分布、水深及含氧量等因素影響,但這些方面還缺乏清晰的系統研究資料。
深海熱液活動則持續向周邊深層海洋環境中輸送著物質和能量。以西太平洋馬努斯弧后盆地為例,巖漿作用產生高溫(〉1 100 °C)、富含揮發份與金屬的流體注入海底熱液循環系統噴出,導致熱液柱及彌散區范圍內的深層水體出現明顯的濁度、酸堿度、化學組成異常[5]。弧后盆地熱液可形成上升到離海底 300 m 的熱液羽狀流和周圍數百公里的彌散流區域,不僅形成獨特的生化環境和生態系統,也深刻地改變了周邊深層環流和水團[6]。因此,推測熱液羽狀體的運移可能推動了大洋中層水的循環,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影響著海洋環境和全球氣候變化。
海底熱液獨特生物群落的發現是 20 世紀后期最顯著的科學發現之一,與其相關的資源、環境問題和“黑暗食物鏈”生命過程是當前深海研究的焦點[7]。從海底熱液樣品中分離到一種嗜熱菌,其生長溫度達到 121°C,是現有生命所能耐受的最高溫度[8]。熱液生物群落是深海化能合成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生物多樣性和生產力完全可與陸地熱帶雨林相媲美。以化能自養細菌為基礎的管狀蠕蟲、貝類、甲殼類生物生活在不同類型的熱液區,通過化能營養繁衍[9],與陸地和淺海生命形式迥然不同,并且熱液噴口化學成分對其生物群落的分布影響顯著[10]。深海化能合成生態系統生物地理計劃(ChEss)從熱液系統中發現大量新的物種,初步劃分了深海化能合成生態系統全球生物地理格局,發展了新的生態學分支[11],并且在基因組水平上認識到生物對缺氧、富硫和金屬等特殊環境新的適應策略。在時間和空間分布上,熱液活動是動態的、不連續的,不同類型或者不同發育階段的熱液噴口,其生物群落和生態系統特征差異顯著[12,13],但是造成這種差異的關鍵因素不清楚。
冷泉是海底物質和能量向上輸送的又一重要“窗口”。冷泉區天然氣水合物的分解支撐了化能合成為主的冷泉生物群落,并且甲烷氣的羽狀流可以升的很高,對周邊環境產生重要影響。雖然冷泉在深海廣泛分布,大洋板塊俯沖帶和海底的烴類溢出口都有存在,但人類對其認識才剛剛開始。
深海是構成深部生物圈巨大微生物群落的聚居地,是地球表面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地區,地球上高達 2/3 的微生物可能深埋在海底下的地殼和沉積物中[14,15]。深海及熱液、冷泉等極端環境造就了其具有陸生生物無法比擬的細胞結構、基因功能、生理功能及特性。對深海極端海洋生態系統中的微生物資源及其多樣性進行系統的調查和比較分析,對揭示生命的起源、進化以及研究生物對特殊環境的適應能力有著極為重要的科學意義。而且,海洋微生物多樣性的調查有利于探討海洋環境中微生物的生態功能,揭示海洋環境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的原理和規律,同時也可發現更多新的微生物資源及相關新的功能基因和復雜多樣的代謝產物和機制。海洋微生物資源的開發將為生物醫藥、工業酶等提供寶貴材料,具有重要的開發利用價值。聯合國海底管理局已將深海海底生物基因資源納入管理議事日程,海洋微生物資源特別是深海微生物資源已經成為國際海洋科學研究和科技戰略規劃的熱點。
當然,上述科學研究的進展離不開深海技術裝備的支持,正是基于“阿爾文”號潛器的深海探測,才發現海底熱液,推動深海環境和生命過程研究的跨越發展。目前基于船基的電視抓斗等可視化采樣設備,載有各種傳感器、聲學和光學設備的水下拖體,載人深潛器(HOV)、無人纜控潛器(ROV)和自主式水下潛器(AUV) 等水下觀測平臺,以及海底固定觀測系統等已經成為開展深海極端環境和生命過程研究的主流技術手段,對深海認知的不斷深入正是深海技術進步的具體體現。同時,科學研究的迫切需求推動深海技術裝備的迅猛發展,構建“船基-潛器-原位-長期”一體化綜合深海探測技術體系成為深海極端環境與生命過程研究的重要內容。
2 國內研究現狀
受制于深海探測裝備的落后,我國在深海探索與研究中長期處于“望洋興嘆”地步,與海洋大國地位不符。2 000 年以前主要是圍繞地質構造和海底礦產資源開展了部分勘查工作。進入 21 世紀以來,隨著我國國力的增強,深海研究也逐步實現由單一資源調查(多金屬結核)向探測與科學研究相結合的綜合科學考察的戰略性轉變。2005 年我國首次在西南印度洋發現熱液噴口,2007 年證實了天然氣水合物在南海的大量存在并進而啟動“南海深部過程演變計劃”,以及后續啟動的“973”計劃“西南印度洋洋中脊熱液成礦過程與硫化物礦區預測”“典型弧后盆地熱液活動及其成礦機理”等,推動了我國深海研究的發展。而“蛟龍”號 7 000 m 載人深潛器的研制成功,標志著我國在深海研究方面的實力提升。特別是,隨著“科學”號海洋綜合考察船的投入使用和中科院 A 類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熱帶西太平洋海洋系統物質能量交換及其影響”的實施,實現了我國深海大洋科考能力跨越式發展。這主要表現在:通過自主探索與實踐,在國內首次建立了宏觀與微觀、走航與定點、梯度與原位相結合的深遠海環境探測技術體系,突破了 10 000 m 深海定點探測、7 000 m 深海探測與采樣、4 500 m 深海精準探測與取樣、1 000 m 水體剖面走航探測、深海 30 m 長沉積物取芯和 20 m 長巖石取芯等關鍵技術,具備立體同步精準開展深海地形地貌、海底環境、水體環境的綜合探測和樣品采集的能力。迄今,完成國內首個沖繩海槽熱液區 50 km×50 km 船載全海深多波束地形探測(圖1—圖3),首次獲得馬努斯海盆熱液區域 1 m 分辨率的高精度深海地形圖;新發現 4 個深海熱液噴口,國際上首次獲得了熱液噴口周圍的溫度梯度分布;在南海冷泉、沖繩海槽熱液區、馬努斯海盆熱液區、雅浦海山區獲得 3 600 余號、220 余種大型生物樣品,包括 1 新科、3 新屬、23 個新種,實現了深海環境和資源新認知。
3 我國深海極端環境與生命過程研究對策
深海探測與研究區域廣闊、過程復雜,涉及到地質環境、化學環境和特殊生態系統,涉及到深海極端環境特殊裝備的研發、技術體系的建立、深海探測與研究綜合平臺的建設,涉及到科學與技術的有機結合。國際上深海極端環境和生命過程研究的發展趨勢可歸納為:(1)研究重點趨向于全球深海大洋中的不同生境,包括海山生態系統、深海化能合成生態系統、深淵生態系統、洋中脊生態系統等;(2)研究內容和方法趨向多學科交叉、滲透和綜合;(3)研究方式趨向國際合作和平臺數據共享;(4)研究手段不斷采用高新技術,并向全覆蓋、立體化、自動化和信息化方向發展。
目前,雖然我國已經擁有國際一流的深海綜合探測平臺,已經具備開展深海綜合探測與研究的基礎條件,但是深海科學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因此,針對當前國際深海領域的研究現狀與發展趨勢,圍繞深海研究的特點,突出特色、重點突破,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國際深海科學領域占得一席之地,滿足國家海洋戰略的重大需求。

圖1 中科院海洋所使用“發現”號ROV上配備的超高清攝像機原位觀測沖繩海槽Lion熱液噴口(黑煙囪)

圖2 中科院海洋所使用“發現”號ROV上配備的超高清攝像機原位觀測沖繩海槽JADE熱液噴口附近的化能生物群落

圖3 中科院海洋所使用自主研發的深海激光拉曼光譜探測系統(RiP)在沖繩海槽熱液區Dragon噴口進行熱液流體的原位探測,溫度顯示290℃,并獲得流體中溶解甲烷、硫化氫、二氧化碳和硫酸根離子等成分的原位濃度
(1)突出區域特色。當前深海探測與研究雖然呈現全球化趨勢,但是研究區域大多集中在大西洋和東太平洋,西太平洋相對薄弱,缺乏系統研究。然而,西太平洋海底地質過程非常活躍,發育了全球 70% 以上的弧后盆地,也是全球海山系統分布最為集中的海域,使該區域海洋物質和能量交換更加復雜;同時蘊藏巨量的多金屬硫化物和富鈷鐵錳結殼資源,并且孕育了全球海洋生物多樣性中心。因此西太平洋構成了我國科學家躋身國際深海科學前沿得天獨厚的地理區位優勢。通過探測該區域海山、熱液、冷泉、深淵系統,在其與水體的物質能量交換過程、深海生命過程等方面取得新發現和新認知,將填補該區域深海海洋科學的研究空白,使我國成為該區域深海資料掌握最全的國家,提升我國在深海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
(2)聚焦科學問題。圍繞當前深海研究的前沿課題和西太平洋的區域特色,重點關注板塊俯沖過程及資源環境效應;熱液/冷泉區/海山/海溝等海底地形地貌及構造結構,及其形成的地質條件、地質過程、分布格局和探測技術;極端環境下的化能生態系統中生物群落特征及起源演化,剖析深海生物對極端環境的適應性機制;熱液和冷泉系統的物質能量輸運動力學過程及其對海底生態系統的支持與相互作用;極端環境地層微生物的生命過程、影響因素和在礦物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深淵專屬性物理海洋與地球化學現象,闡釋深淵環境與極端生命的耦合演變機制等。
(3)強調學科交叉。深海特殊的地質、物理、化學環境塑造了特殊的生態系統和特殊的生命過程,是物理、化學、地質和生物過程綜合作用的結果。開展深海極端環境與生命過程研究需要從海洋系統的角度綜合考慮分析,通過多學科交叉推動系統性、集成性成果的產出,提升我國在深海領域的學術地位。
(4)強調科學與技術融合。深海研究的瓶頸主要在于探測技術。深海研究的每一次突破都是得益于新技術、新設備的應用。因此,加強科學目標引領下的深海技術裝備研發,重點提升 ROV、AUV 等深海自主觀測平臺技術能力,加強深海精準定位與信息通訊、原位探測、原位實驗等技術裝備研發,構建深海環境與生態系統長期觀測體系,發展深海資源勘測與利用技術,提升我國深海研究的自主創新能力。
(5)加強國際合作。積極開展國際合作,參與并引領國際大型深海計劃,開闊研究視野,拓展研究領域;開放深海觀測與研究平臺,推動技術體系和研究團隊的國際化,提升我國深海研究的國際知名度、貢獻性和影響力。
1 Lavelle J W, Lozovasky I D, Smith IV D C. Tidally induced turbulent mixing at Irving seamounts-Modeling and measurement.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04, (31)∶ 308-318.
2 Polzin K L, Toole J M, Ledwell J R, et al. Spatial variability of turbulent mixing in the abyssal ocean. Science, 1997, (276)∶ 93-96.
3 Mikhailik A. Cobalt-manganese crusts on guyots of the Magellan seamounts of Tatler-Hogg eddies through Cenozoic. Abstract for Conference∶ Minerals of the Ocean-Integrated Strategies. St. Petersburg, 2004, 25-30.
4 Christiansen B, Wolff G. The oceanography, biogeochemistry and ecology of two NE Atlantic seamounts∶ the OASIS project. Deep-Sea Research II∶ Topical Studies in Oceanography, 2009, 56 (25)∶2579-2581.
5 Reeves E P, Seewald J S, Saccocia P, et al. Geochemistry of hydrothermal fluids from the PACMANUS, Northeast Pual and Vienna Woods hydrothermal fields, Manus Basin, Papua New Guinea.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11, 75∶ 1088-1123.
6 Gurvich E G. Metalliferous Sediments of the World Ocean∶Fundamental Theory of Deep-Sea Hydrothermal Sedimentation. Berlin∶ Springer Verlag, 2006, 416.
7 Reysenbach A L, Shock E. Merging genomes with geochemistry in hydrothermal ecosystems. Science, 2002, 296∶1077-1082.
8 Kashefi K, Lovley D R. Extending the upper temperature limit for life. Science, 2003, 301∶ 934.
9 Jollivet D. Specific and genetic diversity at deep-sea hydrothermal vents∶ an overview.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1996, 5(12)∶1619-1653.
10 Luther G W, Rozan T F, Taillefert M, et al. Chemical speciation drives hydrothermal vent ecology. Nature, 2001, 410∶813-816.
11 Baker M, Ramirez-Llodra E, Tyler P, et al. Biogeography, ecology, and vulnerability of chemosynthetic ecosystems in the deep sea. In, McIntyre A. (ed.) Life in the World’s Oceans∶Diversity, Distribution and Abundance. Chichester, GB, 2010, Wiley-Blackwell, 161-182.
12 Tunnicliffe V, Fowler M R. Influence of sea-floor spreading on the global hydrothermal vent fauna. Nature, 1996, 379∶531-533. 13 Huber J A, Mark Welch D B, Morrison H G, et al. Microbial population structures in the deep marine biosphere. Science, 2007, 318∶97-100.
14 Arrigo K R. Marine microorganisms and global nutrient cycles. Nature, 2005, 437∶ 349-355.
15 Lipp J S, Morono Y, Inagaki F, et al.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of Archaea to extant biomass in marine subsurface sediments. Nature, 2008, 454(7207)∶ 991-994.
李超倫 中科院海洋所所長助理,深海極端環境與生命過程中心主任,研究員,博士。1991 年本科畢業于青島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系,1997 年和 2002 年在中科院海洋所先后獲得海洋生物學碩士和博士學位。2004—2005 年挪威特拉姆瑟大學訪問學者,2007 在美國康涅狄格大學開展合作研究。主要從事海洋生態學研究工作。目前擔任國際南極研究科學委員會(SCAR)生命科學工作組委員,北太平洋海洋科學組織(PICES)28 工作組成員。E-mail∶ lcl@qdio.ac.cn
Li Chaolun Professor, Director of Deep-sea Extreme Environment and Life Processes Center, Assistant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OCAS). He obtained his Ph.D. degree from IOCAS in 2002. Since then, He has been worked in the zooplankton team of IOCAS. As a visiting scientist, He worked in the University of Troms?, Norway during 2004–2005, and in the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USA in 2007.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zooplankton feeding ecology, zooplankton population dynamics, pelagic ecosystem in the polar sea, and deep-sea ecosystem maintenance mechanism and biological adaptability. Now he is the member of PICES 28WG and Standing Scientific Group on Life Sciences of SCAR. Email∶ lcl@qdio.ac.cn
Extreme Environment and Life Process in Deep-sea: Research Status and Strategies
Li Chaolun Li Fuchao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China)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rine system, the deep ocean relates to the national strategy and territory expansion, which is always the key point of contention for the maritime power. The extreme environment of the deep-sea has created a special life process, which is great potential resource. To comprehensively detect marine extreme environment to a depth of 1000 meters below and life in these environments, such as the seamounts, hydrothermal vents, and cold seeps, it needs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of geology, chemistry, physical oceanography, and ecology. It needs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equipment for deep-sea extreme environment and the integrated platform of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It depends on research vessels, submersibles, special equipments, and technology system. It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trength.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extreme environments and life processes in the world, and puts forwar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deep-sea extreme environment and life process in China.
deep-sea, extreme environment, life process, research status and strategies
*資助項目:中科院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XD A110 30000)
修改稿收到日期:2016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