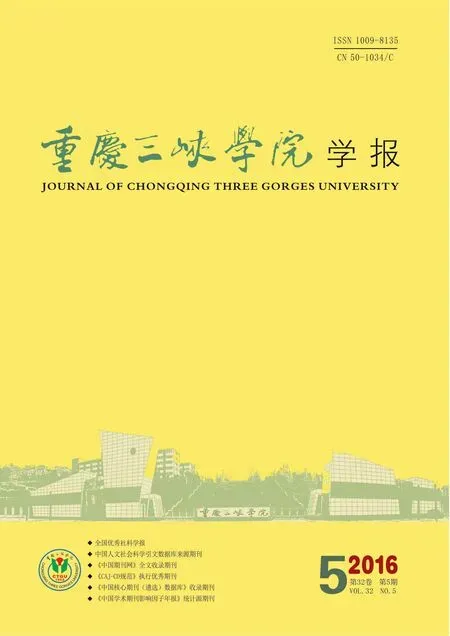隱逸風景中
——徐訏創作心態考察
陳廣通 趙憲花
?
隱逸風景中
——徐訏創作心態考察
陳廣通 趙憲花
(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遼寧大連 116081)
關于徐訏的文學精神、思想來源,以往人們關注較多的是他的創作與宗教,特別是與西方宗教的關系,與宗教精神相關的隱逸思想卻少有涉及。徐訏的一生都在孤獨寂寞里度過,這些孤獨寂寞來自于自身的經歷與現實的重壓,這些經歷與重壓有時候甚至會把他的孤獨寂寞化為一種恐懼,于是形成了他具有時代性的“逃避”心態。“逃避”與自然風景緊密相關。深受西方哲學影響的徐訏同時也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思想。
徐訏;創作心態;風景;隱逸
關于徐訏的精神、思想來源,以往人們關注較多的是他的創作與宗教,特別是與西方宗教的關系,與宗教精神相關的隱逸思想卻少有涉及。隱逸有兩個意思,一個是看破世事變幻后的皈依,另一個是逃避現實中的壓力,只要是從精神向往出發,教、派、宗都是一樣的。到目前為止,對于徐訏隱逸思想的理解,筆者認為他直到生命最后也仍然是一種“逃避”而不是“看空”。隱逸、逃避與自然相關,當我們面對巨大壓力無處排遣的時候,總會從室內出去散散步,徜徉在大自然里,呼吸呼吸新鮮空氣、感受一下鳥語花香、觀覽一下高山流水……這些都是風景。隱逸于風景中也許會讓徐訏“生命的偶然性”在“不斷逃離的必然性里獲得永生”,但是“巔峰”與“低谷”的人生起浮必然會使他明白事實上“他無法逃脫那個早已套在其腳上不斷催促他的命運之匙”[1]153。
比起郁達夫、廢名、沈從文、張愛玲等現代文學史上的寫景高手,徐訏作品中的風景描繪并不算多。作為一位以離奇曲折的情節、豐富的哲理思考名世的作家,他小說里的風景描寫當然要少一些,但是只要寫到風景就必定沒有無用的筆墨。戲劇就更不說了,但也有不少以自然風物為題的劇目,比如《月亮》、《野花》、《北平風光》、《荒場》、《心底的一星》、《水中的人們》等。散文也多是敘事、說理型的,但是那些短小精悍的小品中也不乏對于自然的懷想,如《魯文之秋》等。詩歌比較例外,其中自然景物相當多,而且是根據自己心理情緒的需要來組織想象中的風、花、雪、月……翻翻徐訏的傳記,我們發現他的一生都在孤獨寂寞里度過,這些孤獨寂寞來自于他本人的經歷與現實的重壓,這些經歷與重壓有時候甚至會把他的孤獨寂寞化為一種恐懼,于是形成了他具有時代性的“逃避”心態。“逃避”與自然風景緊密相關。對于徐訏而言這一關系是如何表現的?徐訏在表現“逃避”與自然風景的關系時與他同時代的作家有什么不同?徐訏是如何應驗了隱逸精神的“逃避”一面?徐訏的隱逸思想來源于哪里?深受西方哲學、心理思想影響的徐訏是否也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思想?這是些不大但也不小的問題,理解之后我們有可能在徐訏的精神世界中找到某些共鳴,也可能是對徐訏宗教精神研究的小小填補,也可能把居于現代文學史邊緣地位的徐訏融入二十世紀前中期的中國文學大環境中。
一、寂寞山水中的“執”與“懼”
徐訏在《江湖行》的開頭寫道:“我們無法設想沒有故事的人間,沒有故事的人間是沒有大氣的空間,這該是多么空虛與寂寞。”一直以來我們總認為徐訏可能是新文學以來最會編故事的作家。善于編故事本來無關對錯,可總是有些人把他看成是媚于流俗的小說家。如果我們把上面的引文用心感受,我們將會明白徐訏之講故事其實是因為內心的“空虛與寂寞”。“沒有故事的人間是沒有大氣的空間”,沒有大氣我們該怎么活下去呢?這種情形徐訏無法想象,事實上也正是如此。人們免不了對道聽途說感興趣,正如魯迅筆下的“看客”們,我們沒有必要責備他們對于他人苦難的麻木,無聊當中尋求樂趣本來是人類的天性,沒有新奇事物供之觀瞻,人生確也有些枯燥寂寞。徐訏不是一個把別人的苦難當笑料的人,所以當內心的孤獨無法忍受時也就只有編織自己的故事,故事的精彩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稍解他的寂寞。可是讓人咀嚼寂寞滋味的并不是只有故事的情節,還有穿插于故事里的風景。善于講故事的人也一定是個精于描畫風景的人,徐訏當然不會例外,他不僅把寂寞編進故事,更把寂寞嵌于風景。
在徐訏的一生里,寂寞總是他最忠實的伴侶。即使在他傾心為國為民用文學抗戰的“孤島”時期里,那些讓人熱血沸騰的日子也并沒有把寂寞從他的內心中趕開。“此時期徐訏小說對環境的描寫充滿了濃厚的異國情調和強烈的地方色彩”,風、霧、云、月“既迷茫,又莊嚴,既壯麗,又氣勢磅礴,徜徉于悠悠的天地和茫茫的宇宙間,并與主人公孤寂的心態融匯在一起。”[1]142-143《吉卜賽的誘惑》之獻辭:“我暫想低訴我在黑夜的山上,怎么樣撫摸我周圍的云霧。”山上當然只有詩人自己,他“撫摸”的動作是尋找,可是“黑夜的山上”他什么也看不見,也沒有任何人看見他,云霧里的孤獨寂寞有誰會與他一起體味呢?最后“我”是有了潘蕊的陪伴,可是“簡單而諧和的生活”建立在“我們生活在游戲之中”的基礎上,當“那悠遠悠遠的海天”邊只有孤單一個人的時候,孤寂的內心還會覺得那些“游戲”值得回味嗎?如果說《吉卜賽的誘惑》中的風景描畫很少而且故事結局比較完滿,不足以見出作者的孤獨寂寞,那么寫于同一時期的詩歌《溪聲》則為我們的觀點提供了不容置喙的實例,這首詩好就好在表達孤寂的過程中“不著一字”,需要的是讀者的品味功夫。
在茫茫的原野中,/竟無人遙望,/那潺潺的溪水,/在村頭苦吟。//靠那藍黑的天際,/是幾顆殘星,/夜色在此刻,/還有誰肯相信?//三更四更的月色,/來投下一絲聲音,/那么難道到五更時分,/荒野中會有一聲雞啼?//多少人間的甜語與愛,/一夜中被溪水流盡,/那么我今宵溪歌的秋夢,/將流入誰家蘇醒?
詩人把原野、溪水、殘星、月色等自然事物變成了想象中的風景,其實他是把自然風景“抽象”化了。在寫詩的同時他并不一定實實在在見到了這些自然景觀,而是出于心態的寂寞,在幻想中把它們融合到了一起。充滿動感的“無人遙望”的“茫茫的原野”、“潺潺的溪水”是遠逝的象征,剩下詩人自己還在祈望著“月色,來投下一絲聲音”,可是永駐內心的寂寞使他懷疑“難道到五更時分,荒野中會有一聲雞啼?”當一個人只有把雞一樣的禽畜當成陪伴自己的唯一可能,可見他的內心該有多么孤單無依。人的宿命是孤寂,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那么也就只有一個人“苦吟”在“村頭”,把“我今宵溪歌的秋夢”珍藏為“流入誰家”都不會“蘇醒”的“殘星”。問題是那“幾顆殘星”也一樣讓人難以“相信”,所以那些“甜語與愛”在“一夜中被溪水流盡”,也就讓它流盡吧,剩下我苦吟的聲音在黑夜……
可是,黑夜讓人恐懼。
恐懼是徐訏創作心態的另一個方面,當然也表現在他對于自然風景的描畫中。在《魯文之秋》里他寫到“第二年秋風起時”的情景,“實在太殘酷了,像是冥頑的暴力姿意殘殺無抵抗的婦孺,像是人間的地震,監獄的火災,沒有幸免,沒有逃避,一陣風聲一次崩裂,于是滿地都是瓦礫了”。這篇著名的文章寫于1936年,那時作者雖然沒有親身經歷上海“孤島”時期的日軍燒殺搶掠的恐懼,但是“人間的地震,監獄的火災”似的“殘酷”、“暴力”也一樣燒殺了一切,這是自然災害帶給人類的恐懼。這“蕭殺而陰森的魯文的秋”,讓“我”感覺到“當時的無聊與痛苦以及時時想出逃與自殺的情緒”。人只有在對痛苦感到無法忍受時的恐懼心態下才會想到自殺,可是生的執念又使人不想真的死去,于是只有回到大自然,和它一起同生共滅吧。在這同一篇文章里,魯文的鐘聲讓作者“驟然會感月兒也瘦了一暈似的。但是誰有法子禁止它,避開它呢,它是幽靈,也是鬼,跟著你,釘著你,一步不放松你。這實在可怕!”恐懼使他“只好逃避”,于是他來到了巴黎。但是《漫話巴黎》中寫到的這個城市“那繁華之中隱藏著的凄涼”仍讓他感到惆悵與寂寞。上面說的是大自然帶給徐訏的恐懼,社會時代環境也一樣讓他恐懼,當日本人侵入租界時,面對日偽漢奸的勸誘、威脅,徐訏的心里又怎能沒有恐懼呢?于是他再次出逃,目的地是陪都重慶,路上他仍然沒有忘記大自然這個可以讓他逃離社會恐懼的安樂所在。這里就出現了一個問題,社會時代的戰亂使徐訏感到恐懼,自然萬物的凋落也讓徐訏感到恐懼,那么他為什么還是在社會恐懼無法忍受的情況下尋求大自然的庇護?對此徐訏說:“因為在世俗的人世間勞碌一生,偶爾到山水間宿一宵,鐘聲佛號,泉鳴樹香之間,會使我們對于名利世事的爭執發生可笑的念頭,而徹悟到無常與永生,一切欲念因而完全消凈,覺得心輕如燕,對于生不執迷,對于死不畏懼了。”[2]32
二、隱逸——解脫與救贖之道
徐訏作品中的風景描寫與新文學以來的其他作家不同,他往往能在自然風景的展現里融入哲學思索。散文《夜》的寂靜與漆黑使作者體會到了生命的真諦;小說《鳥語》中,在“映照著斜陽”的蕓芊那“蓮花瓣一般的臉頰”上“我”看到的是“有因本無因,無因皆有因,世上衣錦客,莫進紫云洞。”他的哲學思索是伴隨于寂寞、恐懼心態而來的皈依自然的隱逸思想。
隱逸其實是一種逃避,對于少年時在上海初等小學求學的那段生活,徐訏說:“房間對我來說,就好像是一所監獄”,這種“囚獄體驗曾淋漓盡致地體現在他晚年的小說創作中,如在《江湖行》中他就把這種經驗擴大化了,他說人生像個監獄,出了小監獄,仍要進入一個大監獄。人生就是如此不斷反復地忍受折磨,忍受痛苦。”[1]15少年時期隨父親四處漂泊也“并沒有給年幼的徐訏帶來多少興奮感,相反,那段遠離家鄉的日子,留在徐訏心里的是接連不斷的遷居與一如既往的寂寞”[1]14。所以他想逃,這種逃逸當然不止是肉身的逃逸,更是精神的解脫。從寂寞里逃脫是徐訏《遁詞》的主題:
我寂寞,/在靜悄悄的夜里,/我像是殘落了的花瓣,/在黑泥的冰凍中抖索,/我像是水蛇所遺棄的殘衣,/在荊棘叢中寥落。//我要飛,/要跑,/要走,/我要拋棄我的家,/拋棄我塵世的衣履……
落寞中詩人“要飛,/要跑,/要走,/我要拋棄我的家”,像是有點一語成讖。徐訏的一生一直在逃亡的路上,浙江、上海、北京、美國、法國、桂林、重慶,到了香港總算是停下了。且不說作為文學家的天性,就拿普通人來說,旅途中的寂寞誰又能忍受得了呢?在徐訏的一生里孤獨感始終伴隨著他。兒童時期父母離異,少年時期獨自求學,中年時期顛沛流離,老年時期妻女遠隔重洋……這些孤獨寂寞去到哪里才會擺脫得了呢?只有人類來時的源頭和歸去的終點——大自然。逃難途中的寂寞讓他無以排遣,所以在日軍侵入上海租界后南遁的路上他也沒有忘記到南岳衡山上游覽一番,為了忘卻戰亂和煩惱他很想在此山隱居。生命本身的沖動讓徐訏把大自然當作他的伴侶,《虛無》表達了他的回歸悵惘:
我來自偶然,成長于偶然,/看時間飛逝,如白云流水,/從渺茫到渺茫,/從無常到無常。/從愛到愛,夢到夢。/我本是塵土,歸于塵土,/我本是虛無,歸于虛無。
徐訏明白,人來于虛無,隱于虛無。《風蕭蕭》里海倫的生命變化讓他感到了“一種美麗的隱士的心境”,海倫“把生活交給了自然,像落花交給了流水,星球交給了太空”。《彼岸》把“與宇宙終極的諧和貫通”看作生命“至高的境界”。徹底放棄生命的《時與光》中“我的存在只是遺留在云層中的我用宇窗光芒所寫的淡淡的發亮的紋痕”。信奉過馬克思主義、柏格森到自由民主主義的徐訏到了晚年受盡了“現實的殘酷”,從而“對人世間的所有‘思想’都產生了懷疑,他只能尋找一種終極的、與人世無關的思想,以求最后的解脫與救贖”[1]310。“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思想的結果是自己和自己過不去,所以他只有歸去到大自然中尋求解救。徐訏對于各種思想的懷疑類似于原甸,他的“精神探索并沒有因為皈依宗教而止步,還仍然保留著強勁的懷疑精神”[3]127。徐訏在晚年皈依了宗教。
三、溯 源
以往我們一般把徐訏的隱逸、逃離心態與西方宗教思想相聯系,其實其中也不乏對于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的繼承與發展。對于自然山水的宗教式情懷,把徐訏與西方宗教的功利訴求區別開來。無欲無求的追求使徐訏在生命最后時刻皈依基督看起來順理成章,其實里面只是隱藏著整個人類對于生命將盡的恐懼心理,這與是否信仰某一特定的宗教派別無關。他在“孤島”時期的作品,都是描寫人生價值的失落,明顯地有某種佛、道的痕跡,“他還常常從理念本身去看不同的事物,令人感到‘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出世味道”[2]32。所謂的隱逸、逃離、自我流放,目的地都是那個無人尋到的超脫塵世的所在。深受馬克思主義、柏格森、盧梭、弗洛伊德影響的徐訏并沒有忘卻中國傳統文化,佛道思想與古代詩文的轉用是其文學造詣的體現(歐陽修的《秋風賦》是其從童年到老年一直記憶猶新的繁華凋落之夢)。無論是基督教還是天主教,它們向往的雖是“彼岸”,但對于“彼岸”的指向更可以被看成一種策略,它的目的其實只是以心理安慰的形式讓塵世中人的日子能好過一些。而且宗教一度被西方國家當權者作為政治統治的工具,這一工具性運用就更與中國宗教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出世”追求無關了。關于宗教,中國與西方不一樣,佛、道從來就沒有被封建帝王作為實行國家管理的指導思想。徐訏的隱逸與逃離,事實上更符合中國道家的人與自然渾然一體的出世追求,不同之處在于因為時代社會的發展造就人類視野的開闊,徐訏把那個超脫塵世的所在搬到了異域,把隱逸思想表現在那些極度富有“異域情調”的作品中。《吉卜賽的誘惑》、《阿刺伯海的女神》、《荒謬的英法海峽》……這些作品的名字已經昭示了徐訏對于海外那方天地的神往,更不用說故事的發生地了。《阿刺伯海的女神》的故事發生在黑夜大海上的一只船上,《荒謬的英法海峽》的故事發生在一個美麗的小島上,《吉卜賽的誘惑》最后“我”與潘蕊“在各大都市的旅館、飯館里出入”,“在各處看相與算命”,這是“大隱隱于市”了。吉卜賽、阿拉伯海和英法海峽的異域風景使徐訏遠離鬧市,這是徐訏對于“異域”概念的借用。
單純從風景觀念方面說,中國與西洋也有很大的不同。徐訏認為“風景這個東西……在中國是出世的,在西洋則是入世的;中國人對于風景愛想到無常,是逃避現實;西洋人對于風景聯想到淫樂,是享受現實”[1]139。徐訏隱逸于風景是“逃避現實”,西方人欣賞風景是享樂,如果說大自然被西方人用來滿足自己的原始欲望,那么徐訏就等于是把大自然當成自己僅堪信仰的“宗教”。
隱逸也是一種“閑適”,徐訏有很多小品、雜感之類的文章,比如《魯文之秋》、《談美麗病》、《等待》、《夜》、《論煙》等。“閑適”文章體現出徐訏隱逸思想的另一個重要來源——現代中國文學史上的幽默大家林語堂。他編輯過林語堂創辦的《人間世》,又在《論語》、《宇宙風》上頻頻發表作品,還與林語堂、陶亢德等人共同創辦《西風》,再加上和林語堂在日常生活中的書信往來,如此過密的交往不可能不使徐訏受到“閑適”大師的影響。
四、造就于出世與入世之間的文學史地位
我們說徐訏“逃避”現實,一心把大自然當成心中的歸宿,但是他也如中國古代的陶淵明、王維、孟浩然等山水田園詩人一樣并沒有缺失對于蒼生、庶民的仁愛之心。徐訏的隱逸不是因為厭倦俗世,也不是因為對現實社會悲觀失望,而是因為不滿現實才會在他的“諸多小說創作中表現出對鬼魅世界、烏托邦世界”等脫離世俗的空間的深厚興趣[3]19。《鬼戀》中的“鬼”早先傾其所有投入革命斗爭,她不是不想對人生社會有所貢獻,可是當這個“最入世的人”亡命國外回來,發現曾經的伙伴“賣友的賣友,告密的告密,做官的做官,捕的捕,死的死,”同儕中只剩自己“孤苦的一身”之后,她已經無處可去。曾經意氣風發、誓死與共的同路人成為賣友求榮、告密升官的小人,她該如何面對?她是不滿于“人”還是不滿于時代、社會環境?還是對整個世界充滿憤激?那“我要做鬼,做鬼”的歇斯底里又低沉沙啞的哀嘶里的壓抑情緒,只有做了鬼之后的自己才能深深體會。當年有不少學者從社會、時代、革命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出發,認為《鬼戀》是對世事的諷喻,現在看來這種觀點也無可厚非。說徐訏“借‘鬼故事’的敘說否定了現實世界,他意圖有所超越,希望能有一個更理想的‘桃花源’世界和美好的生活方式,可以說他是借‘鬼’之酒杯來澆心中塊壘”,也并不是毫無根據[3]63。即使在最具抒情性的詩歌體裁上,也仍然表現出徐訏對于人民大眾的人道關懷,《錢塘江畔的挑夫》、《老漁夫》、《賣硬米餑餑的》、《早》等詩作是其“革命人道主義”的代表性作品。“身上壓著百斤重擔”的挑夫、只靠“一張網來養活他早寡的兒婦,以及他五個幼齡的孫屬”的漁夫、年景使他無法過活的小販、賣不出瓜的瓜農,這些小人物的現實命運怎么能讓人道情懷極其強烈的徐訏對現實滿意呢?徐訏認為“藝術的欣賞必是由娛樂出發,當藝術無可娛之處,這藝術是不會存在的”[4]416,可是徐訏又認為,如果中國作家的作品“沒有中國民族的特色,那么這作品不會是成功的作品”[5]151。徐訏說的“中國民族的特色”固然是從藝術的角度出發,但是從另一方面看,按照王德威、李歐梵等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的說法,中國文學的民族特色(特別是晚清以來的現代文學)之一就是始終脫離不了對于社會現實批判、民族家國構建的無法抑制的介入此說見于王德威《想像中國的方法》、李歐梵《未完成的現代性》以及李揚《現代性視野中的曹禺》等有關中國文學“現代性”的論著。。徐訏也沒能例外,早年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他為國家民族大義投入身心的最初嘗試,抗日烽火燃起后他又毅然離法回國,旅美之后對賽珍珠對于中國偏見的輕蔑不屑……凡此種種,有鑒于此,我們不可以說徐訏不負責任地把自己逍遙在“隱逸”天地里。
當年,幾乎所有的“革命作家”都把徐訏看成是色情小說家,譏諷其為娛樂大眾的能手(對此,徐訏回應道:“藝術不注意娛樂的成分,這藝術不是變成說教,就成為小圈子的統治階級所娛樂的藝術。”[4]413這不能不算是徐訏對于革命“君子”針鋒相對的反擊。),這是對徐訏極不公平的誤解。當年,魯迅把林語堂的“閑適”小品批得一塌糊涂,徐訏并沒有聲援自己的摯友,這是因為他理解魯迅。雖然他與魯迅并沒有什么過深的交往,但是同樣作為藝術家的他們在某次偶然的相遇中已經了然彼此。徐訏可以把魯迅看作知音,[②]徐訏與魯迅的交往參見:吳義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傳[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魯迅又被革命諸君當成導師、舵手,這就完全有可能把徐訏與時代主流話語試為溝通。徐訏以自己獨有的方式投入到壓倒“啟蒙”的“救亡”的時代洪流中,這是我們把居于現代文學史邊緣地位的徐訏融于二十世紀前中期的中國文學大環境中的最可靠的依據。
但,徐訏有自己的與“革命君子”判然有別的超拔精神。即使在上述那些稍帶憤懣的詩作中,他仍然沒有忘記對于自然的懷想,“錢塘江畔”、種瓜的農民、打漁的老翁……讓我們看到了生命勞作間隙的自然風景,這說明“回到現實軌道”中的徐訏仍有超越性的一面。無法忘懷大自然其實是一種無奈,現實的境遇讓作家感到無所適從,他的“逃避”就成了一種被動的隱逸。在“孤島”時期的徐訏進行著與倭寇的周旋,卻飽受同胞的誤解,兩難的“橫站”姿勢怎能不讓他感到力不從心?(這一現實說明這樣一個道理:“中國的自然主義……主要因為政治”[6]272)被動的隱逸心態浮出水面。這時,他給遠在美國的諍友林語堂寫去一首頗有歌行風范的舊體詩《寄友》:
月如畫中舟,夢偕君子游。游于山之東,游于海之南,游于云之西,游于星之北。山東多宿獸,宿獸呼寂寞,春來無新花,秋盡皆枯木;海南有沉魚,沉魚嘆海闊,白晝萬里浪,夜來一片黑;云西多飛鳥,飛鳥歌寂寥,歌中皆怨聲,聲聲嘆無聊;星北無人跡,但見霧飄渺,霧中有故事,故事皆荒謬。
愛游人間世,人間正囂囂,強者喝人血,弱者賣苦笑,有男皆如鬼,有女都若妖,肥者腰十圍,瘦者骨峭峭。求煤擠如鯽,買米列長蛇。
忽聞有低曲,曲聲太糊涂,如愁亦如苦,如呼亦如訴,君淚忽如雨,我心更凄楚,曲聲漸嘹亮,飛躍與抑揚,恰如群雀戲,又見群鹿跳,君轉悲為喜,我易愁為笑,我問誰家笛,君謂隱士簫。
我年已三十,常聽人間曲,世上簫聲多,未聞有此調,為愛此曲奇,乃求隱士簫。披蓑又披裟,為漁復為樵,為漁漂海闊,為樵入山深,海闊路飄渺,山深路蹊蹺,飄渺蛟龍居,蹊蹺虎豹生,龍吞千載云,虎吼萬里風,云行帶怒意,風奔有恨聲。
泛舟槳已折,駕車牛已崩,乃棄舟與車,步行尋簫聲;日行千里路,夜走萬里程,人跡漸稀疏,簫聲亦糊涂。有鳥在樹上,問我往何處?我謂尋簫聲,現在已迷途。鳥乃哈哈笑,笑我太無聊,何處是簫聲,是它對窗叫。
醒來是一夢,明月在畫中,再尋同游人,破窗進清風。
在藝術表現方面此詩頗有些白居易《琵琶行》的風致,讀來像是敘事,再讀又讓人想起蘇東坡的《赤壁賦》、《后赤壁賦》。詩人看著醒時的“畫中舟”入睡,然后從夢寫起,夢到的是東南西北各處遨游。明明看透了人間的“囂囂”,卻又偏偏“愛游人間世”,這不能不說是徐訏的“隱逸”與“入世”的矛盾。現實與夢幻的糾結讓他無所適從,于是他要逃。讓他羨慕的是隱士的簫聲,于是他“日行千里路,夜走萬里程”地尋找,然而最終只換來“鳥乃哈哈笑,笑我太無聊”,這是對自己尋找出路而不得的自我嘲諷。“再尋”一次,徐訏發現“同游人”原來是“破窗”而入的“清風”。如果我們由此聯想一下蘇東坡的“清風徐來,水波不興”,那么我們就有可能與徐訏一起陶醉在大化中了。“山高月小”船也小,浪跡江湖,與世俗凡人不相聞。“水落石出”風更悠,陶然孤峰,和蜉蝣螟蛉伴余生。漁樵耕讀是徐訏向往不盡的幻夢。在《彼岸》中,徐訏自己說:“我的靈魂不是高僧的靈魂,也不是隱士的靈魂”,又說:“我的生命沒有受過一個傳統的熏陶”,這些顯然是作家在某些思想瞬間的自謙之語。
徐訏一度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最受詬病的是他的小說觀的娛樂性,詩歌創作的感傷情調,還有散文寫作的“幽默”“閑適”以及留學、訪問西方的人生經歷。但恰恰是現實的苦痛讓他尋求娛樂,現實婚戀讓他感傷,人生的糾結讓他贊賞“幽默”,留學訪問讓他眼界大長。徐訏的隱逸來自于現實的苦悶,這是他所處的那個時代青年們的普遍心態。最革命的蔣光慈、洪靈菲、陽翰笙等人也一樣要依靠自然界的風景來釋放胸中不可遏止的激情,郭沫若也同樣有對于中國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情愫。現實是人類必需面對的,但是“人雖然是人間社會的動物,可是在社會以外,一種出世的大自然宗教的空氣,也是人類所時時需要的。”[2]33即使在烽火連天的中國二十世紀前半期,全力投身于革命、社會、政治斗爭的勇士們為人類的幸福拋頭顱、灑熱血,可是他們在戰斗的間隙、思考的閑暇也同樣會感到人性中天生共有的寂寞、孤獨和恐懼。當作為個體存在的有志于社會、時代的文藝英雄們(比如魯迅、瞿秋白、胡也頻、柔石、丁玲、蕭軍等等)看慣了人間的殺戮、遍觀了俗世的喧嚷,有鑒于“孤獨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存在”[7]177,所以他們也與革命作家眼中的“通俗作家”徐訏同樣需要大自然的陶冶與釋放。而藝術家“走向自然是逼出來的。我們可從若干移情于自然的藝術品中看出這一點。他們對自然的過分迷戀和頌揚,恰恰說明他們要掩飾或沖淡什么。與其說他們走向自然,倒不如說他們是逃向自然。”[6]272徐訏也是如此,作為二十世紀的文學家,從他的行事、文論、作品中無不顯現出其對于民族家國的“現代性”關懷。這是徐訏不應該被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忽略的理由,更是向往隱逸于自然界的徐訏之所以不會被時代拋棄的潛在原因。徐訏與錢鐘書、張愛玲、無名氏們一起使1937年之后的中國現代文學幸免于被“革命”的聲音淹沒,這是對于文學“宗教”的信仰和文學精神的堅守。所以,我們相信:“徐訏的文學創作在過去、在今后都一定是有回響的,并且還會綿延不絕。”[3]172
時代氛圍與個人的生活經歷造成了徐訏的孤獨、空虛、寂寞的心態,以至于在心理、行為上使他偏好自然,他的隱逸是中國傳統士大夫面對現實壓抑所產生的“不如歸去”的精神選擇的新時代的回歸,表現在創作中就使得他的小說、詩歌、散文都有了與當時主流意識形態規約下的“革命文學”極為不同的審美特征,這是他的文學史貢獻。但是從另一方面看,正如本文開頭所述,因為他的孤獨寂寞,所以他追求文學創作中的故事性,可能是想沉浸在個人世界的無限幻想中,并從中獲得心靈的釋放,但也正是這種幻想的創作觀念使他的作品在當時飽受詬病。幻想是文學創作的源泉,我們不能如當初的主流批評家們一樣以此否認徐訏的文學價值,但這是另一個問題,已經不在本文的論說范圍之內了。
參考文獻:
[1] 吳義勤,王素霞.我心彷徨·徐訏傳[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2] 徐訏.文學家的臉孔[M].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3.
[3] 喬世華.徐訏文學論稿[M].大連:遼寧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4] 徐訏.談藝術與娛樂[M]//徐訏文集:第9卷.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5] 徐訏.從寫實主義談起[M]//徐訏文集:第10卷.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6] 曹文軒.第二世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7] 曹文軒.面對微妙[M].濟南:泰山出版社,1999.
(責任編輯:鄭宗榮)
Live in Scenery Seclusion:The Research on Xuxu’s Creation Mentality
CHENG Guangtong ZHAO Xianhua
Xuxu spent his lifetime with loneliness, which rooted in his own experience and pressure of reality. The experience and pressure would sometimes translate into fear, so it was how his epochal avoid mentality formed. Avoid mental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natural scenery. Xuxu wa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westernphilosophy, but also inherited the spiri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Xuxu; creation mentality; scenery; live in seclusion
I206.6
A
1009-8135(2016)05-0027-06
2016-04-12
陳廣通(1982-),男,遼寧大連人,遼寧師范大學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
趙憲花(1991-),女,山東濟寧人,遼寧師范大學研究生,主要研究文藝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