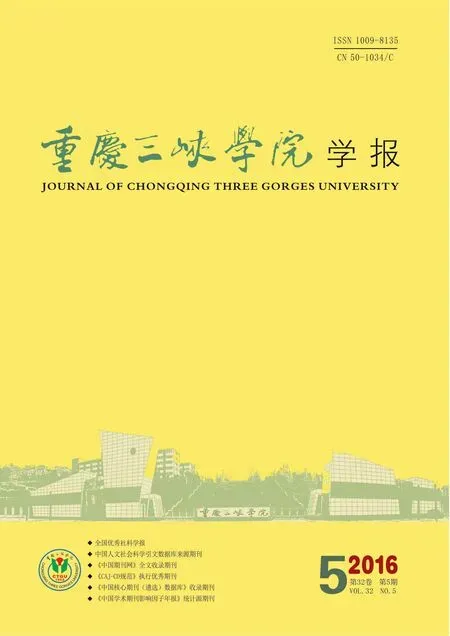全媒體視域下的文化生產、權力機制與大眾抵抗
李欣池
?
全媒體視域下的文化生產、權力機制與大眾抵抗
李欣池
(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福建福州 350007)
傳統媒介與新興媒介互滲、融合與并軌,先進的現代科學技術建立起嚴密、龐大的信息網絡,文化工業產品得以迅捷而廣泛地傳播,權力規訓機制的力量日益增強。盡管如此,大眾并未完全喪失自主性。大眾的抵抗在被文化工業所擠壓的社會空間之中展開。在原有文化資源的基礎上,大眾生產出不同于主流的符號、象征、圖像,局部性、暫時性地對現存的社會秩序與階級體系予以打擊。
全媒體;文化工業;權力;抵抗
一、引 言
隨著電子技術的發展,新型信息社會建立起嚴密、龐大的權力監視網絡,在技術的成熟與資本運作的雙重作用力之下,傳統媒介與新興媒介之間發生互滲、融合與并軌,制造出廣袤無邊的虛擬空間,信息、符號、象征、視象等形式多樣的文化工業產品通過廣電網絡、互聯網、手機平臺等多系統、多終端迅捷而廣泛地向大眾傳播,權力規訓機制的力度與作用范圍也隨之不斷增強、擴張。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消費者完全喪失了理性與判斷力,處于絕對被動的境地。文化工業所生產的符號、象征、圖像,隱藏著意識形態訊息,同時也包含了大眾反抗的可能。面對被商業邏輯、意識形態操縱的文化工業產品,大眾仍然能夠采取多種方式來進行抵制、反抗,甚至是利用、改造現有的文化產品,使之成為真正屬于大眾的文化。
二、文化生產場域中的權力操控
電子媒介時代對人的全面監視與規訓的機制已不同往日,先進的現代科學技術建立起“全景監獄”式的信息網絡,“今天的傳播環路以及它們產生的數據庫,構成了一座超級全景監獄,一套沒有圍墻、窗子、塔樓和獄卒的監督系統”[1]43。現代社會所建構的數據庫與信息網絡通過手機、電腦等私人終端設備直接對個體進行追蹤、監視以及信息采集,從而判斷個體的生活習慣、興趣品味、身份、職業等。
社會個體甚至也參與到信息權力網絡的建構中來,主動向手機應用程序、網站提供個人信息。信息社會建立了龐大而無形的權力與意識形態的傳播、規訓網絡,所有社會個體都被定位、捕捉,成為待規范的對象,“被按照一種完整的關于力量與肉體的技術而小心地編織在社會秩序中”[2]243。信息本身就是一個權力結構,提取個人信息就能夠在此基礎上對個體施行有目的的規訓。權力規訓機制從而嵌入個體的日常生活中,不再是命令式、總體化的,而是滲透性的、潛藏的,顯示出針對個體前所未有的密集而強大的控制力,“權力的增長以及其自我合法化如今正走上數據存取和信息操作性這條道路”[3]47。
信息網絡進一步控制著文化領域符號、象征的生產與制造,監視著文化的傳播與消費。借助于塊莖式無限蔓延的信息網絡,攜帶著意識形態信息的文化工業產品快速而穩定地傳播、擴散,并通過私人化、普及化的接收設備微觀而廣泛地滲透,“電話電纜和電線線路細針密縷地縱橫交叉、覆蓋著我們的世界,它們是超級全景監獄的極端手段。”[1]43信息網絡提供著文化消費品、間接規范著社會個體的行為,以微觀而可無限復制的符號、象征結構消解個體的反抗與潛能。“大眾”不再是被貶低、邊緣化的底層人民,而被“塑造”為消費主體。表面上,人們能夠操作電腦、手機等電子設備,制定節目表、自由選擇觀看時間,造成了自主消費的假象,使得大眾不再處于絕對被動的狀態。然而事實上,大眾、消費者仍然缺失主動性,他們不能控制屏幕上的影像、文字,始終是單向度的信息接受者。廣告、電影、電視節目、網絡視頻等直接面向個體言說,對個體表現出關懷、友善,邀請個體加入其所提供的情境中,而個人電腦、手機的使用強化了大眾媒介直陳式言說模式的控制力、吸引力,個性化、生動的表象遮蔽了文化工業單一的生產模式與意識形態操控手段。
由于通信網絡、多媒體視象技術的高度發達,人類的歷史、文化、自然都被投入到文化工業的生產模式中,被制造為可被全媒體無限復制、反復利用的擬像(simulation)。信息—權力網絡將不同地域、時空的人們卷入聯結為一體的后現代多元化的虛擬空間與權力規訓機制中,進入快速、碎片化的文化生產秩序中。資本與新興技術的聯合組織起新的生活、生產模式,改變著人們的空間認知與感受。文化工業所生產的消費品是片斷式的,經過剪切與拼貼的意義結構,是統治者允許大眾所看到的社會的局部。“技術性又具‘傳奇性’的編碼規則切分、過濾、重新詮釋了的世界實體。世界所有的物質,所有的文化都被當作成品、符號材料而受到工業式處理。”[4]133
當近似于真實的擬像占據了世界,真實與虛假的界限不再明晰。權力機制有意操縱民眾形象與日常生活,脫口秀、真人秀、生活紀實、家庭錄像等通過電視、手機、電腦屏幕播送。在緊密環繞著大眾的文化生產與傳播環境中,人們的感官與認知都被經過了技術與權力的處理的虛擬空間所占據。表面上,大眾媒介的碎片化拼接模式不帶有任何立場,實際上這一模式能夠有效地篩選與屏蔽信息,其所傳播的符號、象征、形象成為技術化了的意識形態,而其中的規訓信息在文化產品的消費過程中被無意識地接受和內化了。
通過大眾對文化產品的消費行為,權力機制的控制力不斷循環加強。個體只需通過日常生活中的視頻觀看、文化產品消費等娛樂活動便能為文化工業的生產秩序提供剩余價值,一些表面上與經濟利益無直接關系的行為如點贊或轉發朋友圈,實則表征了受眾范圍的大小,直接影響著資本運作邏輯下的文化產品所獲利益的多寡。媒介與大眾之間形成輸入—輸出反饋模式,人們不再是單純的使用者與消費者,而是不斷與各種媒介進行符號、信息交換,從而被權力網絡內化為其組成部件,權力機制的運作形成了一種普遍化的“機器的奴役”(machinic enslavement)。
文化是社會實踐的體現,涉及權力與社會資源權力的分配,具有內在的政治性,是權力博弈的疆域。廣義上的文化生產其范圍與強度已然超過了傳統的社會性物質、服務的生產,通過符號、象征、形象的生產,當代的文化工業控制了個體的欲望、身體、情感,制造出大眾置身其中卻毫無覺察的權力操控網絡,施行著與國家機器的公開而強硬的暴力質詢手段不同的軟性而非強制的權力操控。文化工業所生產的符號、象征具有表層與潛在的雙重意指,其表層結構吸引著大眾的注意力,提供了可購買、消費的欲望、幻想,安撫著大眾的社會、政治焦慮,卻將人們的欲望、幻想限制在其預設的深層結構之中。文化工業產品一方面壓抑著大眾的政治潛能,另一方面又預設了大眾的情感反應與行為方式,聚集、引導、利用著大眾的政治潛能為特定的利益階層服務。
“在狂歡節的廣場上……人們之間的等級關系的這種理想上和現實上的暫時取消……形成一種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有的特殊類型的交往。”[5]153然而,大眾所創造的無階級的狂歡被現代文化工業所模仿、復制,并將其利用為一種滿足大眾的規訓手段。文化工業通過現代視象技術制造出虛擬的場景,為大眾擺脫社會生存條件的束縛與限制提供了一條途徑,人們通過收看同一大型娛樂節目,被暫時性地團結在一起,遺忘自身的社會等級,形成無階級的想象性的集體。日常生活中彼此分離的個體形成一個概念、邊界模糊的大眾集合體。
人們在電視、網絡視頻所營造的幻影式的集體包圍之中不再感到孤獨,而個體所感到的愉快在虛擬的群體之中得到了放大與加強。視覺文化產品是技術與權力的共同產物,提供給大眾一種與權力機制的虛假聯結關系。“技術看起來是資本主義的一項成就,它讓民眾覺得自己也可以參與”[6]235,即使是監獄中的囚犯,通過電視與先進的技術、權力的聚焦結成同盟時也能獲得快樂。鏡頭的聚焦代表著具有控制力的權力主體,大眾通過觀看行為參與到技術性的視覺奇觀的建構過程中,仿佛能夠分享電視視象背后的權力結構。虛擬的分享、參與行為能夠短暫地將大眾從現實處境中解脫出來,使得大眾能夠參與、分享他們不可能置身其中的社會情境、社會儀式,大眾分享著維持這種制度的必要性與滿足感,工廠主與工人觀看相同的電視節目,社會秩序從未如此和諧,各階層的人們從未如此“平等”。
這些假象背后隱藏著資本的壟斷意志與權力機制。社會個體逐漸壓抑、轉移其真正的自我認知與真實需求,人們的生活方式逐漸被同化,被塑造成能夠不斷復制、再生產的單向度的人,成為文化工業、大眾媒介生產的最終產品。“由于更多的社會階級中的更多的個人能夠得到這些給人以好處的產品,因而它們所進行的思想灌輸便不再是宣傳,而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7]12視象技術與大眾媒介制造著現代社會的擬像奇觀,引誘著人們去觀看、消費,大眾被誘惑、引導著加入虛擬的狂歡,其反思與批判能力被削弱,文化工業背后的意識形態與社會秩序藉此壓抑大眾的政治潛能。
資本的無限擴張,意志與趨利傾向導致了文化產品快速、廣泛地進行工業化、標準化的生產,呈現出娛樂化、通俗化的趨勢,正如鮑德里亞所言:“商品的邏輯得到了普及,如今不僅支配著物質產品,而且支配著整個文化、性欲、人際關系,以至個體的幻象和沖動。一切都由這一邏輯決定著,這不僅在于一切功能、一切需求都被具體化,被操縱為利益的話語,而且在于一個更為深刻的方面,即一切都被戲劇化了,也就是說,被展現、挑動,被編排為形象、符號和可消費的范型。”[4]225歷史、文化被生產為淺薄、單一的表象,其本身的價值都被文化工業所瓦解,大眾媒介以強有力的誘惑、欲望結構,最大范圍地網羅受眾。
文化產品是商業邏輯操縱之下的意識形態工具,文化工業進行著模式化的批量生產,而每一個產品都是巨大的經濟機器,當手機、電腦等設備正日益成為人類身體的延伸部分,人們自律、完整的自我受到了侵蝕,不由自主地投入到碎片化且數量龐大的文化工業產品中,不斷地消費歷史、文化、自然,乃至經歷、情感與欲望。
三、媒介空間中的大眾抵抗策略
權力規訓網絡全面滲透日常生活,而大眾則是社會階層體系中相對較低且受到權力機制典型質詢的群體。由于權力機制與被規訓者之間力量懸殊,大眾無法采取激進、集中的反抗方式一舉顛覆現存的社會秩序與權力機制。而為了維持其系統性、穩固性,權力機制犧牲了機動性。規訓網絡越是嚴密、龐大,就越難以操控,其結果是用于對抗突現的局部性反抗的力量調動,難免會出現反應上的延時與打擊目標的偏離,而這些漏洞恰恰給大眾提供了反抗的可能。
因此大眾采取了迂回、緩和的權且利用(making do)策略,即被支配者利用文化工業的產品與資源,在現有資源的基礎上創造出偏離主導意識形態、全新的意義結構或是文化資源的另類使用方法。大眾在認識到文化產品背后的規訓邏輯與利益操縱的同時,不斷找尋符合自身利益的反抗方式。另一方面,大眾政治潛能是內在的、具有生產性的、與欲望相關的微觀結構,因此大眾無法被文化工業完全異化,仍然保持著一定的理性,使其既不受權力體系的制約也不被其俘獲。文化工業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復生產相似的產品,也無形中削弱了其對于大眾的誘惑力,激發了厭倦、抵制的情緒,從而使得大眾抵抗著文化工業所提供的欲望、想象結構。
“權力的原子與抵抗的原子在微觀層次上合并在一起。同樣的手勢、身體、目光和話語碎片既帶有權力的正電荷又帶有抵抗的負電荷。”[8]116-126離散而微觀的權力機制與規訓個體結合得更加緊密,使得個體的生存空間中權力結構無處不在,然而另一方面也為大眾的反抗提供了機會與空隙,使其反抗手段更為靈活多樣。當主導意識形態所提倡的主體性與個體的利益出現了偏差,大眾通過意義的再生產來對抗文化背后的意識形態,“使用這些文化的時候,賦予它們完全不同于他們被迫接受的體系的效果和所指”[9]81。微博、微信等自媒體構成了無場所的網絡空間,人們在其中記錄生活,重構個體差異性與身份認同。YouTube、Bilibili、Acfun等交互式的視頻網站的出現使得文化的傳播更加自由,人們利用現有的素材,改造、重制文化工業產品,建立了一種完全不同于權力機制所要求的意義結構。
經過大眾的解構與再闡釋,文化工業的壟斷意識形態及其預設的情感反應與行為模式被破除。大眾并沒有拒絕文化工業產品,而是運用獨特的符號修辭術對符號、圖像進行顛覆性重構,嘲諷了權力機制與主導意識形態,從而成功躲避文化產品所施加的暴力,打破文化產品意義的壟斷,使文化生產脫離文化工業單一的生產模式而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大眾通過意義再生產,建立了與社會成員局部性的團結,從而逐漸形成排斥、抵制主流的亞流文化群體。“大眾文化始終是一種關于沖突的文化,它總是涉及到生產社會意義的斗爭,這些意義是有利于從屬者的、并非支配意識形態所喜歡的。”[6]2文化領域中的符號、象征并不存在單一、固定的本質,大眾通過積極的文化再生產創造出新的言說、行為模式與觀念、價值體系,形成了具有變革意義的社會性與物質性力量。
大眾對現有文化產品與資源的“權且利用”還體現在創造出文化產品不同常規的使用方法,通過這一方式,大眾雖沒有直接再生產出文化產品,卻充分利用了權力規訓網絡達到個人化的使用目的,從而在權力的密集網絡內部開辟出逃避規訓的狹小空間。例如人們將電視作為日常生活的背景來使用,不去關注電視所傳遞的圖像與訊息,回避電視的權力結構;大眾在注冊視頻網站、手機應用程序用戶時提供虛假的個人信息,使得基于個體特征的推送機制無法真正發揮作用;為了特定的音樂、視頻等文化消費品,大眾注冊為某網站的會員,成功獲取目標后便不再使用。大眾分散、游離在權力機制中,充分利用現有的秩序爭取空間、達到目的,成功回避規訓。
無回應、無行動的沉默也是大眾有力的反抗武器。例如在選舉投票、問卷調查中,大眾采取觀望的態度,通過棄權來愚弄、對抗媒體。面對大眾媒介所傳遞的過量的信息與圖像,人們無法進行直接的抗議,而是在接受信息時保持沉默,符號、信息傳播路徑表面上已完成實際上卻是無效的。大眾如同一個信息黑洞,拒絕表現出任何反應,使得文化工業的意識形態規訓落空,大眾的沉默“把意義、操控的宏大系統、政治和信息推向終結”[10]170。媒介并沒有按它原來的意圖發揮作用,相反,文化領域內符號、象征的級數式的增長產生了更多的惰性大眾,權力的微觀規訓結構無法侵蝕大眾。大眾的潛在力量體現在拒絕與不合作的行為中,如果沉默的抵制行為得到了普遍的響應,則會形成一股廣泛而一致的抵抗力量,威脅著權力體系。
作為權力機制從屬群體的大眾通過巧妙使用戰術,“從更強有力的具有決定系統中,贏得局部勝利”[11]250。大眾通過閃電戰、游擊戰的策略,發揮自身優勢,轉變被規訓者的被動處境,用無數的小計謀愚弄主導意識形態,毀損權力網絡,局部性、暫時性地對現存的社會秩序與階層體系予以打擊。大眾的反抗行為不斷穿插在權力網絡之中,然而主流文化、權力機制并非全無對策,它們表面上主動為大眾的意義生產與反抗行為提供著生存空間,實則控制、壓抑大眾自主的文化生產,收編著大眾所創造的文化產品與生產形式。與此同時,主流文化、權力機制還利用大眾的創造性與生產力制造新的媒介奇觀,從而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
例如一些網絡流行的吐槽方式、惡搞圖片被電視節目采用,成為新的視象消費品;彈幕形式被引入受眾廣泛的電影、電視的播放中,其在亞文化群體中的對抗主流的姿態被消解,主流媒介藉此將亞文化群體創造的文化收編。而彈幕的效果極為容易通過技術手段仿造,從而制造出屏幕上大眾狂歡的幻象,導致亞文化群體的反抗行為經過主流媒介的收編后真假難辨。然而,權力機制對大眾生產力的刻意利用也可能導致與其用意完全相反的效果,如大眾媒介刻意制造話題引導大眾爭論、嘲諷某部電影或某個電視節目,從而吸引更多觀眾、獲取更龐大的經濟利益。然而結果卻是大眾并不關注原產品,反而制造出大眾媒介操控者始料未及的符號、意義的爆炸式再生產,最終權力機制本身也無法完全控制大眾的強大生產力與政治潛能。
約翰·費斯克認為:“大眾的日常生活,是資本主義社會相互矛盾的利益不斷得以協商和競爭的空間之所在。”[6]39文化生產領域十分復雜,政府、社會機構、生產者、大眾媒介、消費者等多方力量交織在一起,不斷對立、協商和整合。雖然權力的微觀規訓結構滲透大眾的日常生活,然而其規訓、壓抑大眾目的并不會徹底達成,龐大的社會網絡中無處不存在著反叛的聲音。權力的爭斗是雙向的博弈,控制與反控制并存,大眾與權力機制始終處在動態的較量之中,大眾的反抗行為不斷被權力機制收編,又不斷地找到新的突破口。雖然由于方式、規模所限,大眾反抗往往容易被擊破,但又極為容易卷土重來。對大眾而言,抵抗是沒有止境的。真正由大眾所生產的文化以“獨特的逆向、相反、顛倒的邏輯,各種形式的戲仿和滑稽改編、降格、褻瀆、打諢式的加冕和脫冕”[12]13對抗著權力體系。
四、結 語
在全面滲透、深度化的權力規訓網絡之下,大眾的覺醒十分不易。大眾抵抗行為、策略所發揮的效力、所爭取到的生存空間十分有限,但不可能為權力機制所完全鏟除。通過意義生產、另類使用與沉默等方式,大眾充分表明了自己的能力,在現代文化工業的體制內,大眾的抵抗在緩和對立雙方的權力斗爭的同時,拓展、保持著大眾的權力空間,成功抵制了社會秩序與權力機器的規訓。沉默、符號抵抗與權且利用的策略為反思、批判能力以及差異意識的培養提供了可能,也為集中、具有顛覆性的反抗行為積蓄了微觀的能量。
參考文獻:
[1] [美]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時代[M].范靜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2] [法]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M].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三聯書店,2012.
[3] Jean-francois Lyotard,Postmodern Condition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
[4] [法]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M].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
[5] [美]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M].王曉玨,宋偉杰,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
[6] [美]約翰·費斯克.解讀大眾文化[M].楊全強,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7] [法]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M].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
[8] David Haver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Social Change,Oxford:Blackwell,1989.
[9] [法]米歇爾·德塞圖.日常生活實踐·序[M]//陸楊,王毅,主編.大眾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
[10] [法]讓·鮑德里亞.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M].夏瑩,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11] [澳]格萊姆·透納.英國文化研究導論[M].唐維敏,譯.臺北:亞太圖書出版社,1998.
[12] [俄]巴赫金.拉伯雷研究[M].李兆林,等,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責任編輯:鄭宗榮)
On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Power System and Resistance of the Mass in the Field of All-media
LI Xinchi
Traditional medium and new medium have infiltrated, intermingled with each other while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established a vast network of information power. Through the network, culture industrial products can be spread quickly and widely, increases the strength of power disciplinary mechanism. However, the public has not completely lost autonomy. The resistance of the mass unfolds in a space oppressed by the culture industry. On the basis of original cultural resources, the mass produce signs, symbols, image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e mainstream culture. In that way, the existing social order and hierarchy system can be destroyed.
all-media; culture industry; power; resistance
G114
A
1009-8135(2016)05-0083-05
2016-04-16
李欣池(1990-),女,福建福州人,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臺港澳暨世界華文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