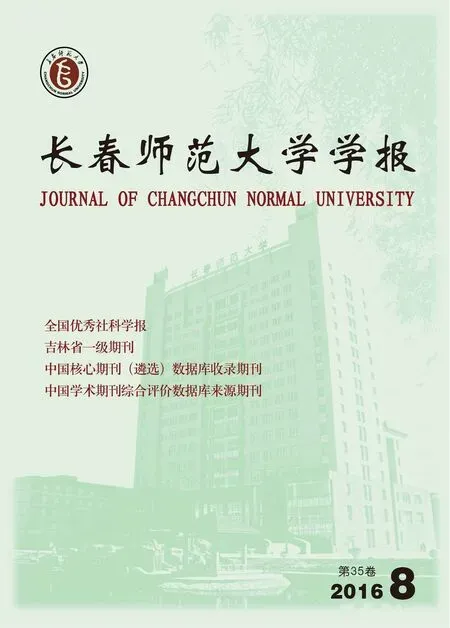數字時代中本雅明的“藝術生產”理論
莊 麗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湖北武漢 430079)
?
數字時代中本雅明的“藝術生產”理論
莊 麗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湖北武漢 430079)
本雅明的“藝術生產”理論是對馬克思藝術生產理論的豐富和發展。進入數字時代,該理論仍然有啟示意義,但也具有了新時代的特征,產生了新型的藝術生產關系,并在某種意義上被解構。這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從機械復制到數字復制;大眾占有、使用和編輯藝術作品的隨意性;平等的觀看權利與另一種“在場”;大眾參與藝術生產。
本雅明;藝術生產;數字復制
本雅明的“藝術生產”理論創造性地把藝術生產同物質生產放在同一個層面來對待和考察,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藝術生產理論的內涵。“同物質生產中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一樣,藝術技巧就構成了藝術生產中的藝術生產力,而藝術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則構成了藝術生產關系”[1]。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梳理了復制技術的發展歷程:最初是鑄造和制模,之后從木刻(及鐫刻、石刻)發展到石印術,從石印術發展到照相攝影。鑄造、制模、木刻、鐫刻、石刻、石印術等歸為一般的復制技術,照相攝影歸于“機械復制”。藝術作品中所蘊含的“生產技術”作為藝術“生產力”的重要構成部分,直接影響藝術作品本身的地位和作用。我們正經歷著數字復制技術帶來的巨大藝術生產力變革,重讀本雅明所闡發的“藝術生產”理論仍然深受啟發,但它也具有了新時代的特征,并在某種意義上被解構。
1 藝術“生產技術”本身的變革:從機械復制到數字復制
數字復制技術是藝術“生產技術”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但它并不能完全納入本雅明所言的“機械復制”范疇。“在數字世界,傳統意義的攝影、繪畫均被解析重構為數字化的像素。我們用手(操縱鍵盤或鼠標)通過改變文件中的數據來改造影像。”[2]如此,繪畫、攝影等喪失了最本真的意義。與此同時,我們也能將數字化的圖像上傳至互聯網,實現數據的共享、傳播,由此產生了數字時代新型的藝術生產關系。
相較于一般復制和機械復制,數字復制明顯具有新的特點和優勢。首先,數字復制技術可以實現大批量的藝術生產,能夠通過操縱數據實現個性化的精雕細琢;其次,從復制程序上來講,數字復制不僅能借助機器和簡單的指令實現自動化生產,又能對所復制的藝術品進行隨機的介入、修改和控制;再次,借數字復制技術生產出來的摹品則與原品真正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一致性”;最后,數字復制跳出了手工復制技術時代一對一的刻意臨摹,能夠進行多對多的網絡化復制和傳播[3]。
2 大眾占有、使用和編輯藝術作品的隨意性
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藝術作品》中論述藝術作品“光韻”消失之時,談到了“光韻”衰竭與大眾之間的關系。“光韻的衰竭來自于兩種情形,它們都與大眾運動日益增長的展開和緊張的強度有密切的關聯,即現代大眾具有著要使物更易‘接近’的愿望,就像他們具有著通過對每件實物的復制品以克服其獨一無二性的強烈傾向一樣。”[4]礙于復制技術的限制,大眾能夠實現的占有極為有限。這些復制技術也因其復制規模、傳播領域的限制,還不足以對原品的“光韻”造成威脅。但隨著機械復制技術的推進,藝術生產技術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與藝術品“原物”高度相似甚至真假難辨的復制品被大批量地生產出來,其傳播領域廣泛,拉近了藝術品與大眾之間的距離,藝術品便失去了曾經的歷史感與距離感。
在數字時代,可進行復制的資源極其豐富,復制技術更被大眾掌握,因此復制活動可以隨時隨地進行。數字復制技術的發展進一步促進了大眾對藝術品占有欲望的實現:以觀看影片為例——從購票到影院觀看,到守在電視機前按時按點收看,到購買CD觀看,到從互聯網上下載后觀看,到借助移動終端在線觀看。這種占有逐漸普遍化,具有極大的隨意性。除了占有欲望的進一步擴張與實現,大眾對藝術品的消費和使用也具有隨意性,這體現了消費者與藝術作品的新型關系——“占有”到“使用”的轉變[5]。
不僅如此,大眾在占有之后還通過簡單的操作實現多次的再復制和再傳播,并借現代技術對其進行修改、編輯。如由國內首支創意配音團隊“淮秀幫”出品的創意視頻,就是在占有藝術品(電視劇、電影)的基礎上對原作中的經典橋段進行剪輯和重新拼貼,輔之以與原音相近的對白配音,用流行的網絡用語調侃回應當下的熱點,用語詼諧,風格戲謔,故此風靡。再以名畫“蒙娜麗莎的微笑”為例,它在機械復制時代就不再是盧浮宮的專屬——從莊嚴、肅穆的博物館中“走”了出來,步入了尋常百姓家。有的人運用現代技術可以讓“蒙娜麗莎的微笑”由一幅靜止的平面視覺圖像變成動態圖。藝術作品的膜拜價值消失殆盡,其“光韻”也蕩然無存。本雅明區分過“對繪畫進行的拍攝復制”與“在電影棚中對表演過程進行拍攝復制”這兩類復制,前者被視作生產類型的復制(這是對一件完整藝術品進行的復制),后者屬于創作類型的復制(這是指通過復制技術才構成的藝術品)。后一類型的復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創作類型的復制。由此可見,在數字時代,新型的藝術生產關系便是大眾可以隨意占有、使用和編輯的藝術作品。
3 共享:平等的觀看權利與另一種“在場”
早期藝術品的產生與某種禮儀密不可分(首先是巫術禮儀,其后是宗教禮儀)。當時,多數人視早期藝術作品的“光韻”為崇拜對象,只有少數人能“在場”觀看。所以,這些藝術品獲得了“膜拜價值”。
伴隨科學技術的發展,一般復制技術逐漸演變為機械復制技術,“藝術作品的可機械復制性逐漸把藝術品從它對禮儀的寄生中解放了出來”[4],成為能夠被普通大眾輕易占有的普通物件,藝術品與大眾的空間距離被拉近,神秘感逐漸消失殆盡,其膜拜價值也逐漸讓位于展示價值,藝術作品本身的價值備受重視。而在數字時代,各種由傳統手段生成的平面視覺圖像經由數字技術的處理都直接變成了數字化的文本,更具有了可被復制、操作的便利性,藝術品本身的價值再次被強化。
不過,當下藝術作品通過某種方式能帶來的儀式感還是存在的,到影院觀看、在電視機前收看還是能夠給大眾帶來儀式感的體驗。藝術品帶給人的儀式感越來越被弱化,普通消費大眾通過網絡共享這一平臺獲得了平等觀看的權利,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也能真正得到重視和回歸。
除了上述已經作為藝術成品的視頻能被大眾共享、平等觀看之外,處于形成過程中的藝術品也可以被共享,即另一種“在場”。在數字時代,“數字復制對數字化了的感官屬性信號的復制可以實現‘無損化’,數字信號作為藝術記錄的物化語言具備了遠程瞬時傳播的特點,這時數字信號的異地調用成為可能”[6]。這樣,即使不“在場”,也看到了唯有“在場”才能看到的某些效果,甚至能見到比實際“在場”更多的精彩。大眾均通過窗口平等地觀看到同樣的畫面,這種“在場”具有廣泛性。由此,本雅明所留戀的藝術作品的“原真性”也在某種意義上得以實現。
4 大眾參與藝術生產
本雅明在“拍成電影的要求”中談到,“電影技巧也同體育運動技巧一樣,每個人都是作為半個行家而沉浸于展示技巧的成就中”,而且“每個人都能被拍成電影”[4]。除了電影業,新聞出版業的日益繁榮也使得越來越多的讀者逐漸變成作者,讀者與作者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顯然,本雅明看到了藝術生產過程中藝術品的接收者(即生產關系中的消費者)對藝術創作的參與。在機械復制時代,藝術創作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從事文學的權力不再植根于專門的訓練中,而是植根于多方面的訓練中,因此,文學成了公共財富”[4]。
結合技術發展的歷史,一般復制時代的藝術品僅能被少數人占有,也僅能被少數人生產;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品則能夠被普通大眾所擁有;進入到數字技術時代,藝術作品不僅能為普通大眾輕而易舉地占有和使用,而且可以借助現代技術和科技產品進行生產和再創造,大眾終于真正參與了“生產”,成為了真正的生產者。這就進一步實踐了本雅明所說的“更加精良的機器”“把讀者和觀眾轉變為共同行動的人”,并論證了本雅明“藝術生產”理論的正確性和預言性。
視頻分享網站中草根影像制作群體的崛起更加體現了藝術生產的大眾化。時下,普通的社會大眾只需借助一臺能連接上互聯網的電腦設備,外加麥克風、攝像頭和任何一款博客軟件,即可成為一名主播,自行進行藝術生產。以“YY”軟件為例,其中的主播有講解游戲的、有出售東西的、有唱歌的、有才藝表演的、甚至還有直播自己吃飯過程的,富有個性特色和娛樂性。數字時代中出現的視頻分享網站使大眾進一步介入了藝術生產,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本雅明的“機械復制影響傳播”觀點。
綜上所述,本雅明的“藝術生產理論”在數字時代具有了新時代的特征,產生了新型的藝術生產關系,并在某種意義上被解構。
[1]朱立元.現代西方美學史[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734.
[2]陳育新.數字復制時代的攝影藝術[J].電子出版,2000(3):59-61.
[3]張耕云.數字復制與數字藝術的創作困境[J].裝飾,2009(2):132-133.
[4]瓦爾特·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M].王才勇.譯.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
[5]紀曉宇.數字時代看本雅明的藝術生產理論[J].成才之路,2013(19):72.
[6]許鵬.機械復制還是數字復制——對新媒體藝術文化身份的辨析[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7(5):31-37.
[7]王長瀟,劉瑞一.視頻分享網站對機械復制影像傳播的解構——基于本雅明機械復制藝術理論的闡釋與思考[J].當代傳播,2013(6):24-26,35.

2016-03-03
莊 麗(1990- ),女,碩士研究生,從事文藝學研究。
J02
A
2095-7602(2016)08-018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