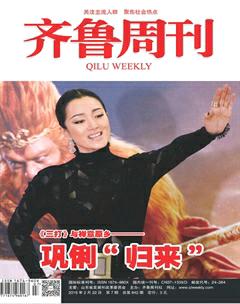魯雁:重病作家的文學良知
吳永強
2016年初,患尿毒癥三年的作家魯雁遭受到人生中又一次打擊:上一年度的透析費用無法報銷,后續治療難以為繼,生被拋棄的透析者
2015年12月31日,魯雁照常來到沂水縣醫院,準備報銷2015全年透析的醫療費,卻被告知無法報銷。
原因在這一年7月,魯雁糖尿病足發作,險些截肢,住院兩個月不見效果,后來用民間土方治療,終于有所好轉。前些天腳部再次出血,如今,他走路依舊一瘸一拐,需要攙扶。
“雙重住院,出現了時間交叉,導致年底結賬時無法報銷。”魯雁說,治療糖尿病足多花好幾萬元,“按照報銷比例,能報近70%,報銷不出來就得全額補齊。”
更大的打擊接踵而來,上一年的報銷無法進行,意味著欠費太多,接下來的2016年,醫院要求全額交齊上一年的費用才能繼續透析。其實按照國家規定,最遲2月28日之前結算就可以,“但他們元旦就停止了透析”。
尿毒癥一星期不透析,就有生命危險。“實在不行了我去求醫生,全額交費透析了一次。”之后,即使交錢醫院也拒絕透析。醫院下了通牒,如果不能及時交上錢,只能將其拉入黑名單,本地所有醫院將對他關上大門。
在朋友的幫助下,魯雁到莒縣透析了幾次,維持生命。“但也不是辦法,臨近春節,路途又遠,不能老往莒縣跑。”幸好,臘月二十七,縣紅十字會和沂蒙生活報慈善組織帶了2000元錢和一些生活用品來看望他。他用這些錢轉院到沂水縣中心醫院繼續透析,中間頗費周折。和之前的透析不同,現在是完全自費,一次500多元,2000元錢很快花光。
早在2005年,魯雁患上糖尿病。2012年,他去醫院檢查,結果出乎意料,“血糖已到了20多,腎病四期,很難逆轉。”后來“升級”到了五期,即尿毒癥。
2013年5月,魯雁終于支撐不住,病倒住院,靠每周三次血液透析維持生命。為了方便治療,他在沂水縣城租了一個小院,房子很舊,經過修整,鬧中取靜。妻子在臨沂上班,70多歲的母親趕過來照顧他。
2016年除夕,經受透析風波的魯雁在母親的攙扶下,艱難走向中心醫院,進行例行透析,過了一個慘淡的新年。
亟需修正的醫療體制
面對記者的詢問,魯雁表示自己能想得通,沒有埋怨醫生的意思,“先救命還是先掙錢,這是一個全國性的悖論。”
“尿毒癥的比例是萬分之一,一個百萬大縣大概有一百多人,每人每年補貼兩三萬元即可,這對于政府財政來說并不是一筆太大的支出。”本刊記者了解到,山東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尿毒癥已經免費,并且補貼交通費和午餐。然而,包括臨沂在內的一些落后地區仍在收費。
這些年來,魯雁經歷了余華《活著》般悲慘的人生:少年喪父;2013年4月,妹妹因癌癥去世;2015年5月,弟弟患腦溢血,全力搶救幾天,花去數萬醫療費后去世,幾個月后弟妹改嫁。
遙想當年,父親去世后,作為長兄,魯雁為弟弟蓋了當時全村最好的五間瓦房,買了車,弟弟妹妹先后成家,30多歲的他才遲遲結婚。而今一切成空,所有的奮斗化為烏有,“就剩一個老娘,75歲了還得天天伺候我,攙扶我去醫院透析。”弟弟去世后,經受生活一次次打擊的母親四個月未說一句話。
幾年來,魯雁每次都是用最低賤的透析材料,比別人的低一百多元,腳部受傷致使病情加重,再加上家庭變故連連,以及辛苦的寫作,透析不及時,病情越來越重。
魯雁有一個女兒,現在沈陽讀書,妹妹的女兒還在上高中,都要由他撫養。妻子每月收入只有兩千多元,杯水車薪,無力回天。
過去的一年,魯雁從自己綿薄的收入中分出3600元給女兒寄去。那時他正在病床上透析,接到女兒的電話,他的眼淚刷的一下流下來,“女兒連飯都吃不上了,你說我是什么感受?”
一個同學發來短信,他再次流下淚來,那是杜甫的一句詩:“文章憎命達。”
文化界的一些朋友得知魯雁的病情后,建了微信群“魯雁后援會”,浙江一個陌生讀者喊出口號:“你不是一個人在戰斗。”他的眼淚又流了下來。
死而有憾:作家的啟蒙本性
多年來,魯雁創作了大量優秀小說。半個月時間創作的長篇小說《最后的莊稼》是其成名作,評論家施戰軍稱:“讓沂蒙人幾代的心靈和命運掀了個底朝上。”11天寫就的長篇小說《草根一族》,以濟南為背景,描寫了城中村一個出租院租客的故事,評論家吳義勤稱:“在都市民間創作實踐中,展現了新品質、新內涵,實現了新超越。”
多年重病,魯雁對生命已看得很淡,至于活著的意義,“一是上有老,75歲的老娘需要養老送終;二是下有小,女兒和外甥女需要撫養;第三,自己的雄心壯志,長篇小說《齊長城下》還沒有修訂完,隨筆集正在整理,想寫的電視劇、電影還沒完成。”魯雁一聲長嘆,“現在死而有憾。”
長篇小說《齊長城下》的艱難寫作和修改,貫穿其患病始終,已改到第三稿,壓縮至31萬字。這是他獻給故鄉的一部大書,他要書寫“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精神苦旅。畢竟,我親身體驗了這片土地三十多年來的滄桑、苦難和變遷”。
同時,他還在創作紀錄片《齊魯千年古國》的劇本,曾經遍布山東的小古國蘊含了很多文化內涵,莒國、紀國、費國……魯雁一個一個梳理這些古國的往事。
在小院居住3年,坐在杏樹底下,春秋兩季種青菜,夏陪蚊子冬逗貓,他陸續產生一些感悟,將之集結為隨筆集《養病雜記》。“人除了正業還要養寵,比如:妻子上班還養貓,閨女上學還養狗,老娘種菜還養花,我讀書寫作還養病。”無限悲涼中透露出慘淡的樂觀,在醫院透析,周圍人也會受他感染,堅持走下去,“把病看成寵物,養好了很溫順,惹著它了就會面目猙獰。”
而今,眼睛視力受限的魯雁,每天堅持寫作四五個小時。就像對自己病情的認識,對于自己作為作家的處境,他說:“不能埋怨某個人,是體制造成的。同工不同酬,是文化界的普遍現象。”
一個作家,其生存意義是什么?魯雁這樣回答:“如果是行尸走肉,也沒什么意思。要有思想,盡自己的綿薄之力吶喊,哪怕只有一個讀者看了你的作品后,活得更明白,這就是作家的意義。”
他突然想起魯迅,今年恰逢魯迅逝世80周年,他在微信上多次懷念。“如果魯迅在教育部繼續當官,他只能是周樹人;如果他繼續在大學教書,也只能是周樹人;恰恰是他走向了民間,為民眾鼓與呼,吶喊和抗爭,成就了‘大先生魯迅。”
若欲提供幫助,可與魯雁本人或本刊編輯部聯系,魯雁微信:直接搜索手機15106672297,本刊電話:0531-85599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