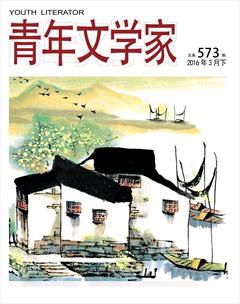墳里的夢不見輪回
張慧巖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6)-09-0-01
綠草纏綿石碑,
鍍一春之色給清明,
無聲落地的雨,
成全你衣袂飛揚。
白馬笑你戚戚,
墳里的夢不見輪回,
草色依舊年年青。
說起清明,人們難免黯然失魂,可在廢名的《清明》小文中卻未見斷魂之殤,滿目盡是厭世者筆下超然的美麗想象。厭世者本未想丟棄生命,他只是對此世的人事與生死皆超脫看待,故而他可以放肆想象。廢名在《清明》中為“墳”洗脫了陰森恐怖的傳統形象,反而表達了超脫的生死觀。在廢名的文字中,每個看官被賦予上帝視角,可探就一切變幻,而當你讀到最后一句又會恍然驚醒,那擁有上帝視角的只是詩人自己而已。這正是諸君常說的廢名文章給人一種“隔岸觀火”的感覺。
在《清明》開篇,作者勾勒出了一幅生機勃勃的美景圖:松樹腳下都是陳死人,最新的也快二十年了,綠草與石碑,宛如出于一個畫家的手,彼此是互相生長。怕也要拿一幅古畫來相比才合適。
樹深草淺,青綠層疊,石碑佇立在一片生機之中,增添了歲月的色彩,于是單純的美景更增幾分意蘊,因而如同古畫。陰天,清明,墳,必然是最易引人恐怖的,可廢名卻描繪出了這樣一番唯美景象,在小說創作中營造出詩境和畫境。先生的高明之處在于借美麗的環境描寫驅走了人們關于“墳”的心魔。驅走看官的心魔以后,廢名先生就開始自由地暢想:小林自遠處走近墳場,看到一片綠色中的兩個女孩兒,竟然瞬間感受到了永恒:
陰天,更為松樹腳下生色,樹深草淺,但是一個綠。綠是一面鏡子,不知掛在什么地方,當中兩位美人,比肩—— 小林首先洞見額下的眼睛,額上發……
叫他站住了,仿佛霎時間面對了永恒。淺草也格外意深,幫他沉默。
為何綠是一面鏡子?為何霎時間面對了永恒?鏡子不知掛在何處,只知它映照出了一片綠意和兩位美人,鏡子是虛幻的,那綠意與美人是真實的嗎?當時間凝固在這面鏡子中,所見到是瞬間的永恒。永恒何嘗是能真正窺見的,只能用心從鏡中映照一二罷了。用“鏡”做比喻是廢名先生最鐘愛的,他把時間的永恒喻在鏡中,而時間的永恒背后又隱藏了生命永恒。這樣的比喻靈感大概是緣自墳場的大環境,墳是生死的交點,亦是時間的臨界點,墳外者生,墳內者死,墳外是一個個瞬間,而墳里便是永恒。所以小林說:我想年青死了是長春,我們對了青草,永遠是一個青年。
死后進入墳中,生命回歸自然永恒的狀態。生死循環是自然之道,生命是宇宙之中的生命,不是一人之生命,所以不必恐懼死亡。青草年年春綠,而年輕的生命進入墳中,便會是個永恒的青年了,至于墳外世界中的生命又是如何更替,皆與他無關了。生死變幻皆是自然,它們并不會相互影響,所以恐懼與留戀實在是不必的。
“清明”小文中的主人公小林、琴子和細竹,他們三人對于墳是沒有恐懼之感的,甚至他們很是喜歡,這種喜歡之情直接反映出廢名先生的生死觀。文中三啞與他們的一段對話首先表現了三人對于墳的坦然:
(三啞)站了一會,看他們三個坐地,又道:
放了炮應該作揖了。
小林笑: 我是來玩的。
細竹也對了三啞笑: 你作揖,我們就這樣算了。
試想平常人家面對清明上墳這樣的“大事”會是怎樣的莊重恭肅呢?可小林和細竹反倒一笑置之,全心付在景致的妙趣上了。尤其到了后面三啞先行回去后,琴子便說了一句“回去吧”,可她依然不起身,坐得很踏實的樣子,好像那回去的話只是隨口一說,心中仍不愿離開。這里不經意的語言和動作描寫,流露出琴子的喜愛。其實任憑景致再美妙有趣,一般人都會因為這里是墳場所在而心生芥蒂,可小林三人卻留戀其中,小林更是陶醉地說:誰能平白的砌出這樣的花臺呢?“死”是人生最好的裝飾。不但此也,地面沒有墳,我兒時的生活簡直要成了一大塊空白,我記得我非常喜歡上到墳頭上玩。我沒有登過幾多的高山,墳對于我確同山一樣是大地的景致。
尋常的孩子在墳頭嬉鬧時大人們必會以敬畏之心阻撓,故而大概少有人回憶起時會津津樂道。而小林之所以能擁有這份豁達,在于廢名賦予他坦然的生死觀。這種坦然伴隨著他的成長,在《橋》中隨處可見。如“芭茅”一節中寫了小林童年的歡樂時光盡在家家墳。孩子的成長、生命的延續以“墳場”為背景,生死相依于此,顯出無限生機。廢名將死亡看作平常事,認為那是生命的另一種存在方式。佛說“緣起性空”,世間萬物不過依緣而起,本無自性,所以生生死死哪里是真的存在或毀滅呢?既然由緣起,何必多慮之?緣來則聚,緣盡則散,此后種種屬于各自新的開始。又如“鑰匙”中有“草岸展開一墳地,大概是古墳一丘,芊芊凝綠”的和諧畫面,“墳”在這田園樂土中顯出極大的生機,這何嘗不是對死亡可帶來新的生機的暗示呢?再如,在這篇“清明”小文里,廢名借小林的口說出了“‘死是人生最好的裝飾”,因為墳是伴隨小林成長,夾雜著無限童年歡情的,所以墳的美麗也增添了人生的美麗。這句話既含詩境又孕禪境,再次向諸位看官傳達了超脫坦然的生死觀,堪稱是廢名小說的一大亮點。而文中的最后一句則和這句有異曲同工之妙——想象的雨不濕人。
想象的雨并不濕人,所以何必躲避?死亡是新的開始,所以何必畏懼?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除了“清明”小文,《橋》中多次提到墳與生死,細細品來,生死描繪皆融于詩境、畫境和禪境之中。廢名眼中的死亡是唯美而蘊含希望的,因此他把視為生死交點的墳比作所有美麗想象的容器。廢名欣賞“墳”這個意象,他在《橋》的創作中賦予它詩情禪意,使之充滿生機和歡情,但他從不執著于墳內世界,可見先生向來直面生死、超然于心,其心與文方不見桎梏。
生,有希望之路,
死,是新的行走,
墳外之人何必哀歌?
墳里的夢不見輪回,
唯看草色年年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