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蘭之綠(外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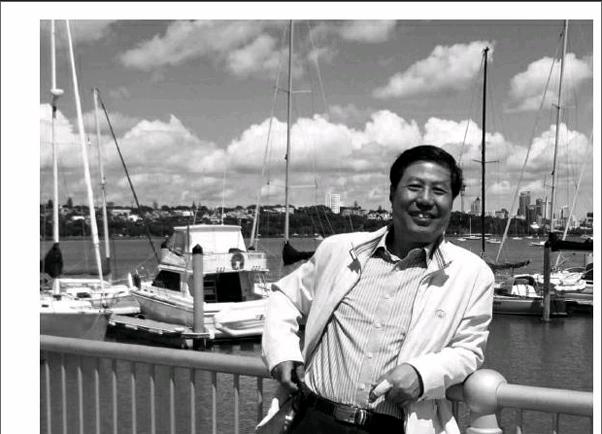
俞兆平 畢業于廈門大學研究生院文藝學專業。現為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廈門大學學報》主編、福建省美學學會副會長等。出版有《中國現代三大文學思潮新論》等10部學術專著,在海內外刊物上發表200多篇學術論文。
從奧克蘭往羅托魯瓦的途中,放眼望去,車窗外盡是綠的色調。這種綠,又是一種刷新我的生活經驗的新奇的綠,一種具有強大視覺沖擊力的綠。
在我的審美圖庫中,最早扎根的是朱自清的《綠》。這一選入中學課文的名篇,把“綠”的審美感,深深地涂抹在漢民族每一位少年的心中。那是幽谷深潭之綠,是從潤濕的巖面、草叢中“透出幾分油油的綠意”;是一張碩大的荷葉般的深潭所含蘊的“醉人的綠”;是一種有如蛋清般嫩軟的少女肌膚質感的綠;是一種只能用手輕輕撫摩的“溫潤的碧玉”的綠······若按王國維對美的類分,它屬于“優美”的范疇,偏于古雅。
但新西蘭之綠則不同了,它屬于“宏壯”。學界對美的兩大范疇的解說,曾用過形象的比喻:優美當如“杏花春雨江南”,宏壯當如“駿馬秋風冀北”。新西蘭之綠應屬后者,卻又不盡然。冀北平原,我去過多次,一馬平川,遼闊廣袤,磅礴之大氣猶在,懷古者甚至還會有凜冽的古戰場雄風、蕭勁的戰馬嘶鳴聲掠過耳旁,但因墾耕過度,生態堪憂,尤其是寒冬,綠意寥寥,四野光禿,一派蒼茫讓人徒生感傷。而新西蘭則是讓人心神為之一振的一碧無垠的芳草綠野。
新西蘭的綠是一種無邊無際、無窮無盡的綠,視野所及,除了綠,還是綠。車窗外,那草地像一匹碩大無比的綠色綢緞,在你眼前不停息地抖開,不間斷地涌來,又像是碧海的微波緩緩地退去。遠處丘陵頂端,則浮現出一團團墨綠的色塊,那是在開拓牧場時保留下來的以杉木為主的林帶,而一座座淺灰色、淺藍色、淺黃色的房舍則星星點點地綴于邊上。在藍天白云的映照下,綠野上晃動著一簇簇黑、黃、褐、白的斑點,分外醒目,那是在悠閑地吃著嫩草的牛羊群。在這里,空間仿佛為綠色之網所過濾,世間的一切紛爭仿佛都為其所凈化,顯得是如此安詳、恬靜;在這里,沐浴著綠色光波的你,才能像盧梭一樣感受到大自然母親以原初之手的撫慰。在此,我才真正理解了全球生態環境保護者的組織為何取名為“綠黨”,而綠黨為何最早出現、成立于新西蘭了。
新西蘭人為保護這一“綠色”,竭盡了全力,其法規之森嚴,處罰之嚴厲,聞之生畏。導游一再交待,新西蘭機場海關檢查之嚴格,在全球排第一位,所帶物件一定要清理好,尤其是食物,但我因疏忽卻不慎領教了一番。我們是從墨爾本轉機去奧克蘭的,前一天晚上,學生全家來旅店看望,見到孫輩,十分高興,就順手開了一袋從廈門帶去的抽真空的熟花生米哄他,小家伙沒吃完,我在整理行裝時,也沒在意,混裝入旅行箱中。到奧克蘭機場,等待過海關,才猛然想起,趕忙離隊,在一旁翻箱倒騰,找到那半包花生米拋于垃圾箱。估計我這一異常的舉動被機場監控攝像頭所錄,便列入了重點檢查對象,而我也有幸享受了一次“恐怖分子嫌疑”的待遇。安檢人員把我帶到隔離出來的單獨的一角,把我所有物件翻了個底朝天,連袋子的邊角也不放過,仔仔細細地摸捏一番,才有所不甘地放我出關,害得整個旅行團為等我在海關多呆了半個小時。為著新西蘭生態的純正與純凈,他們對異國物種的流入,有著高度的警惕,特別是植物種子更是慎之又慎,像花生米這類食品,只能是抽真空、原包裝的才能放行。好在是一次有驚無險的遭遇,我略感氣惱,又不能不為他們敬業守職的精神而感佩。
我進而悟及,新西蘭國民對于“綠”,不僅是一種珍惜之情,他們還把這一自然色質上升到人文的高度,產生出神圣之感,就像我們對“紅”的感覺一樣。“綠”,他們不只是用于“黨”的名稱,似乎還成了神明,成了宗教,這是從內心深處涌出的對大自然的一種虔誠,一種敬畏。綠,這一與人的視覺感官相對應的自然屬性,在新西蘭已積淀了人文精神的價值內涵了,或許這也是成立于1972年新西蘭綠黨的前身之所以取名為“新西蘭價值黨”的緣由吧。
回望來路,人類是該放慢點腳步了。自18世紀后半葉盧梭對科學技術所引生的負值效應質疑開始,人類就陷入科技理性與人文精神對峙、分裂的兩難境地。此間,眾多的哲學家、文學家們,如海德格爾、梭羅等,不斷地發出節制資源、尊重自然的吁求。至20世紀60年代初,卡遜出版了《寂靜的春天》一書,再次從環境保護的角度,敲響了生態危機的警鐘:人口爆炸、土地沙化、資源枯竭、能源危機、環境污染······這觸目驚心的現狀,促使人類進入到深刻反省的階段。而綠色,則成為了這一反思潮流的獨特標志。
望著新西蘭之綠,自然想到處于生態危機前沿的中國。許多人常把中國生態的惡化,歸罪于人口的爆炸,這是原因之一,但我覺得仍屬于現象層面上的追究,因為東瀛島國在人口數量與土地面積的比例上,不見得比我們低,關鍵的是國人對自然生態缺乏一種宗教性的敬畏之心。是的,中國古代哲學就有“天人合一”的觀念,強調生存主體的人與環境客體的物之間的和諧統一,但它對上天,或曰自然,仍缺乏真正的尊重,缺乏內在的誠摯。此“天人合一”的理念,或是深藏于道家玄虛的法理之中,或轉化為儒家的“天授君權”的合體,終點仍落于“人”。而在對大自然改造的勞動實踐中,更異化為“人定勝天”之舉,神話寓言中不是多有“愚公移山”、“精衛填海”之舉嗎?到了現代,“與天斗,與地斗,其樂無窮”的口號,更是震耳欲聾;“天上沒玉皇,地上沒龍王,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 20世紀50年代后期,全國性的伐木毀林、燒炭煉鋼之狂潮,席卷而去的不僅是片片綠蔭,還有那人心對“綠”意的珍重;近年來更有甚者,據說有一地區,為提高稀土采收品位,居然把整座山的草木砍光,再潑上鹽酸······古語所說的竭澤而漁、殺雞取卵的場景竟殘忍地再現。
望著新西蘭之綠,我想到,此生是沒有資格當“綠黨”了,但作為一名粉絲,應該還是可以的吧。因為我懂得了,綠,孕育著生命;綠,萌生出希望。
墨爾本的夕陽
在澳洲行走,我終于從深層品味到了也是南半球國家——智利詩人聶魯達的詩句之美:“在我的祖國,╱春天正從北方走向南方,散發著清香;╱她像一個少女,光著腳,╱飛翔在柯金波黑色的巖石上,╱飛翔在泡沫飛濺的海岸上,╱飛向那些散開的群島旁。”(《在我的祖國正是春天》)在北半球生活一輩子的人,轉眼間來到這球體的下一半,其地域位移與季節轉換剛好變成180度反差的土地上,不能不讓你感到處處新奇。但讓我最驚訝的卻是墨爾本的夕陽。
乘飛機從悉尼到墨爾本,傍晚,出機場往酒店,在市區街角下車,猛地整個人像似被拋入舞臺上聚光燈的光照中一樣,有點眩暈、迷糊。回首街口,那夕陽,居然白花花的,亮得晃眼,亮得刺眼。原以為是街道兩旁高樓玻璃幕墻聚光反射所致,但再過一條街,沒玻璃屏幕了,那街口的夕陽依然那么強烈,那么熱辣。我只能瞇著眼窺視,老天啊,這么碩大、這么白亮的夕陽,平生首次所見,令我驚嘆不已。
我住在廈門,常在環島路上騎自行車健身,那鷺島的夕陽多么柔和,在海面撒上點點金色的粼光,在椰葉縫隙中露出嬌羞的紅顏;我也曾到過邊陲,沉醉于王維的“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雄奇壯闊的詩境,但像墨爾本這般白亮的夕陽卻無論如何引發不出什么美感來了。
晚上,我的一位在墨爾本工作的博士生來旅店看望,閑聊中便扯上這一夕陽話題。他告訴我,是南極上空臭氧層空洞所致,當包裹著我們星球的大氣層中臭氧濃度減少,漸之稀薄之際,太陽紫外線的輻射量便增加了,光線就刺眼了。多年前就曾聽到的人類在環保問題上將要面臨的災難之一,居然在今日親歷一番。但我已不是隔洋觀望的淡然,不是隔靴搔癢的吁求,而是真實地暴露在這一強烈的光線的輻射下,在親身體驗過它的威力之后,再觸及這一問題。雖然隔天我就要離開此地,但那白亮亮的墨爾本的夕陽卻深深地留在大腦的記憶空間。
西方基督教徒說過:“上帝為你關上一扇門的同時,也會為你打開一扇窗。”我卻感到,上帝為澳洲打開一扇門后,卻為它關上了一扇窗。澳大利亞、新西蘭兩國,是上帝的寵兒,它們以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不但成為我們這個星球上生態保護的典范,而且還是人文環境的“綠洲”。它們遠在海天一隅,滔滔大洋衛護著國境,隔離了歐亞大陸的種種政治紛爭、種族仇恨、宗教對峙等人間紛擾;其兩國之間,又真正是唇齒相依,睦鄰友好。可謂遙遙南天,唯我獨樂矣!雖然近年偶有恐怖分子閃現,也不過是大象被虻蟲叮了一口罷了。
迎面而來是幾位澳大利亞土著人,他們挺著肚腩,悠閑自在地漫步在綠樹成蔭的街道上,看不出資本主義的功利競爭在催促著他們的腳步,更無社會主義的階級斗爭繃緊其神經,因為據說他們每周每人均可領到200澳元(接近于人民幣1000元)的津貼。當然,他們的民族在歷史的進程中,也經受過血與火的洗禮,經受過殘酷的虐待,甚至血腥的屠戮,但隨著社會文明的進展,過往的一切漸漸平息了。他們那種和平安詳、與世無爭的自足神態難道不是人們所向往的嗎?《圣經》中的超然于美丑善惡之外的伊甸園雖不可尋,西方人神往的至美至善的香格里拉也飄渺世外,但澳大利亞與新西蘭,這兩塊在全球現代化過程中,放慢節奏、節制物欲的凈土,卻給人類留下了朦朧的希望,或許這就是世界各地民眾爭相移民澳、新兩地的原因之一吧。
但這世外桃源也有“一扇窗戶被關上了”,自然生態在高天云空之上居然“漏”出一個令人恐懼的大洞!當然,這不全是澳大利亞、新西蘭民眾的責任,而是全人類走向工業化時代所催生的罪惡之果。早在1750年,人類社會的現代化剛有所萌動,法國天才的浪漫哲學家盧梭,即敏銳地預感到科學發展將引發出嚴重的負面后果。盡管他只是朦朧地猜測、疑慮,尚未有確鑿的實證,而且更多的是從人文精神被腐蝕的視角進行抨擊,但他的預見卻如巫師般讓今日的人們不寒而栗:“人們啊!你們應該知道自然想要保護你們不去碰科學,正像一個母親要從她孩子的手里奪下一種危險的武器一樣;而她所要向你們隱蔽起來的一切秘密,也正是她要保障你們不去做的那些壞事。”(《論科學與藝術》)科學這把雙刃劍,在盧梭眼前閃射出不祥的寒光;依賴科學發展而建構人類文明的樂觀性、進取性,亦即現代性,在盧梭這里遭遇到強有力的阻擊。而大自然,也只有大自然,才是盧梭心目中能讓人類托庇安寧的母親。
不錯,科學為人類帶來了物質的豐裕、生活的享受。盛夏,當你從冰箱里取出冰淇淋,那涼至心脾的感受讓你口欲頓開;酷暑,當你進入空調之屋,那清爽宜人的溫度讓你飄然欲仙……而就在此時,你則與“潘多拉之盒”中罪孽的“氟利昂”為伍了。而正是對它的濫用及釋放,吞噬了大氣層中的臭氧,制造出欲陷人類于滅頂之災的“空洞”。當然,現時人類已為之驚醒,這些年來的努力也已逐步彌補著自身的過錯,“空洞”漸之縮小,但仍有1500萬噸的氟利昂像幽靈般飄浮、游蕩在大氣層中。
白亮的南半球的太陽,對于喜愛日光浴的白種人來說,是個潛在的威脅。在旅游圣地大堡礁的沙灘,隨處可見到赤膊露臀躺在沙灘椅上曝曬的男男女女,據說澳洲白種人皮膚癌的發病率竟達到百分之八,或許這就是“上帝關上的那扇窗”的意思吧。
盧梭曾把貪婪、虛榮、奢侈等視之為人的“原罪”,用過氟利昂冰箱、空調的我也有些不安起來了。忽然,腦中會跳出像是不相關的魯迅的句子來:“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狂人日記》)在白亮的墨爾本的夕陽照射下,我仿佛有了赤裸之感,有了對原罪懺悔之悟。
責任編輯 林 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