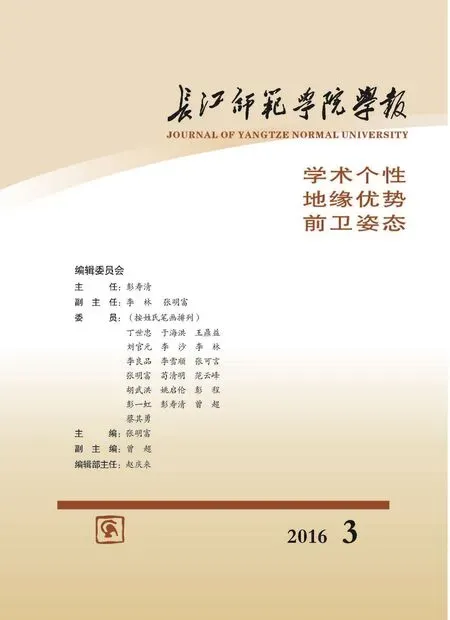“知識分子寫作”與 “民間寫作”的互文性淵源及其沖突
楊紅
(長江師范學院 文學院,重慶 408100)
“知識分子寫作”與 “民間寫作”的互文性淵源及其沖突
楊紅
(長江師范學院文學院,重慶408100)
“盤峰論爭”使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模糊不清的中國詩壇的面目得以彰顯。客觀上,“知識分子寫作”和 “民間寫作”成為1990年代以來中國詩歌觀念的兩條主脈,并對21世紀以來的詩歌觀念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里以互文性理論為依據,嘗試解析 “知識分子寫作”和 “民間寫作”的中西互文性淵源,并闡釋二者由來已久的內在矛盾性。
“知識分子寫作”;“民間寫作”;互文性;淵源;沖突
一、“互文性理論”在詩歌領域的研究現狀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自朱莉亞·克里斯蒂娃于1969年提出來后,在西方理論批評界就一直是一個熱詞,包括羅蘭·巴爾特、德里達在內的眾多理論大師們都曾對這一術語進行過再闡釋。其傳入我國后的相關研究可謂汗牛充棟,所涉及的領域極廣,幾乎涉及人文學科的各個領域。
就詩歌研究而言,互文性理論盡管還不是用得最為廣泛的,但近些年來在這方面也取得了較為可觀的成果,大致說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與詩歌相關的互文性理論的理論研究。此類成果具代表性的有:《用典、擬作與互文性》(楊景龍,《文學評論》,2011年第2期)、《論兩種截然不同的互文性》(錢翰,《學術論壇》,2015年第2期)、《互文性理論視閾的詩歌用典》(余小平,《江西社會科學》,2012年第3期),等等。
第二,互文性理論作為一種研究方法,被用來研究國內外某一詩歌創作現象、流派。這方面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雨巷”的秘密——論現代派作家作品的文際關系》(王宇平,《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互文性視角下1919-1949年美國新詩運動中的中國元素》(郭英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14年第8期)、《作為小說互文性的存在或其他——當代小說家詩歌創作現象簡析》(王萬順,《詩探索》,2012年第3期)、《“他塑”與 “自塑”的互文性建構——新世紀初詩歌中 “廣西形象”的建構方式》(羅小鳳,《南方文壇》,2014年第3期)、《“梅雨”與 “玫瑰”的新生——從 〈玫瑰之歌〉看中國現代詩和西方詩的互文性》(徐立前,《學習與探索》,2013年第4期),等等。
第三,某一位作家詩歌創作與其所創作的小說等其他文體作品之間的互文性研究。此類成果具代表性的有:《作為小說互文性的存在或其他——張煒的詩》(王萬順,《文藝評論》,2012年第3期)、《勞倫斯詩歌與小說的互文性探析》(馬若飛,《惠州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等等。
第四,某兩位作家詩歌創作之間存在的互文性研究。此類成果具代表性的有:《徐志摩與林微因詩歌互文性意象探微》(于倩、孫叔平,《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4年第3期)、《〈女人〉中的女人:翟永明和普拉斯比較研究》(張曉紅、連敏,《中國比較文學》,2007年第1期),等等。
第五,單篇或單部詩歌作品的互文性研究。此類成果具代表性的有:《〈格薩爾〉史詩文本傳承的互文性解讀》(王治國,《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開辟出 ‘少有人行的路'”——弗羅斯特在〈白樺樹〉中的互文策略》(唐瑩,《語言教育》,2014年第3期)、《“影響”解構與 “主體”重建:〈百年孤獨〉互文性分析》(李翠蓉,《西南科技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等等。
第六,某位作家詩歌創作風格的互文性研究。此類成果具代表性的有:《卞之琳詩作的文化——詩學闡釋》(王攸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年第3期)、《當代詩歌的 “南北之辨”與戈麥的 “南方”書寫》(吳昊,《江漢學術》,2015年第4期),《互文視域下的狄金森作品研究》(李健、姚坤明,《齊齊哈爾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等等。
第七,詩歌翻譯與互文性的研究。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尤其是中國古典詩歌翻譯成外語時的互文性研究,比如:《互文性視野下現代派詩歌翻譯與詩歌創作》(趙小琪,《學習與探索》,2007年第5期)。在此不再多列。
盡管互文性最初由巴赫金的 “狂歡化”而導入的 “文本/文化”理論衍生而出,但從上述所列研究現狀來看,互文性理論在詩歌研究中的有效性存在著極大的可能。也即在研究詩歌的過程中,“功夫在詩外”將成為一個有效而具有強大實踐驗證功能的命題。對文學研究而言,人類的一切社會話語體系 (包括政治、文化、語言、心理、性,等等)都可以引入文學的互文性空間,并以此來對文學研究進行更為立體、綜合和深入的探討。
中國詩歌研究界對互文性理論的自覺應用應該說是可圈可點的。詩歌互文性理論之理論研究、互文性理論的詩歌現象和流派研究、詩歌與其他文體的互文性研究、詩人詩歌作品的互文性研究以及詩歌翻譯的互文性研究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不過,就中國詩歌史來看,大多數研究仍顯浮光掠影,要么過于空泛,要么過于狹窄,要么厚古薄今,要么重洋輕內,整體來看,對一些具有連續發展邏輯性的中國詩歌現象,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詩歌現象,應用互文性理論來進行研究的成果至今仍鳳毛麟角。而1990年代以來,與詩歌相關的恰恰很多涉及 “功夫在詩外”。比如說 “知識分子寫作”和 “民間寫作”,這是貫穿整個1990年代直至新世紀的中國詩歌的脈絡,它們有著前史、今生和后世,其內涵的發展性脈絡有著極為強烈的互文性映射關系,只是可惜在這方面的研究幾乎空缺。基于這一研究背景,我們意圖運用互文性理論嘗試性地對 “知識分子寫作”和 “民間寫作”的沖突進行一定程度上的探索,以期拓展中國詩歌研究的視域。
二、 “盤峰論爭”沖突的互文性實質
(一)“盤峰論爭”事件
1999年4月16-18日,在北京平谷縣盤峰賓館舉行了 “世紀之交:中國詩歌創作態勢與理論建設研討會”。會上,后來被稱之為 “知識分子寫作”和 “民間寫作”的兩大陣營的詩人圍繞 “世紀之交:中國詩歌創作態勢與理論建設”的主題,進行了言辭激烈的爭辯。前者以王家新、唐曉渡、程光煒、西川等人為代表,后者以于堅、伊沙、沈奇、楊克等人為代表。其中,于堅強調詩歌寫作的日常生活和原創性,王家新認為詩人不可能完全和他的時代保持一致,西渡反駁了將利用西方的詩歌資源說成是 “買辦”的觀點,等等。[1]概而言之,雙方觀點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語言資源、美學趣味、詩歌經驗等幾個方面。“‘知識分子寫作'強調書面語寫作、追求貴族化審美趣味、持守超越日常經驗的人文關懷精神;‘民間寫作'則強調口語化寫作、追求平民化的審美趣味、看重日常經驗的呈現與表達。‘盤峰詩會'作為論爭的開端,它發動了整個 ‘盤峰論爭'的引擎,揭開了之后更為激烈論爭的序幕。”[2]
這次研討會之后,“知識分子寫作”和 “民間寫作”的詩人與批評家,紛紛在多家刊物發表文章,進行激烈的辯論和抨擊。①本文所列篇目僅為一部分。雙方重要論爭文章主要集中收錄于《中國詩歌:九十年代備忘錄》(王家新、孫文波,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1999中國新詩年鑒》(楊克,廣州出版社,2000年)、《2000中國新詩年鑒》(廣州出版社,2001年)等幾本書中,在此不一一詳列。這場持續近兩年的詩歌論爭被冠之以 “盤峰論爭”或 “盤峰論戰”“盤峰詩會”“盤峰會議”,還有人稱其 “盤峰論劍”(陳超語)。這場論爭是繼 “朦朧詩”之后最重要的詩歌事件,在詩歌界激起巨浪,對整個文學批評界產生了莫大的影響。“同時也勢將成為世紀末的一次具有總結與清理意義的重要會議。它既是對20年來新詩潮發展歷程的認真回顧又是對新世紀詩歌前途的認真面對,也是對詩歌在當下的處境、情狀以及詩人應持的寫作立場的認真檢討、辨析與反省。”[3]
按照相關論者的總結,認為這次論爭最直接的誘因與導火索有兩個:其一是程光煒 《歲月的遺照》和楊克 《1998中國新詩年鑒》的詩歌 “選本”之爭;其二是雙方公開的叫板[4]。盡管論爭存在直接誘因,但縱觀1990年代以來的詩歌脈絡,二者之間的矛盾深具淵源,比如1980年代中后期對詩歌復雜的命名,以及 “民間”一方不得不進行 “話語權力的爭奪”[5],所以 “‘盤峰論戰'不是什么美學之爭”[6],而是有著深遠的、飽含社會性因素的互文性內涵。
論爭之后的 “龍脈詩會”和 “衡山詩會”其實都是 “盤峰論爭”的延續,這些都對21世紀以來的詩歌的分化、發展與多元格局的產生都具有直接的影響。
(二)“知識分子寫作”“民間寫作”沖突的互文性
如何從互文性理論來看二者的沖突?不妨作以下簡略理解。克里斯蒂娃的理論認為,每一個文本都是對另一個文本的吸收和改造。如果真的如此,或者部分有理,那么 “知識分子寫作”和 “民間寫作”不管它們的風格如何、觀念怎樣,實質上它們之間并沒有天然的不可逾越的鴻溝,就像一個硬幣的兩面,本來就屬于雌雄同體。正如T.S.艾略特的戲謔之言:“小詩人借,大詩人偷。”[7]“民間寫作”向民間和國內汲取資源,“知識分子寫作”向精英和西方獲得養料,二者的寫作姿態實際上沒有本質的區別,其沖突只有聚焦到社會權力空間的爭奪上來討論才有效,才能看清事實的真相。而福柯式的話語權之爭,已與文學文本的本體沒有太大的關聯,從這一點上來看,“盤峰論爭”恰恰是能夠驗證互文性理論的一個有效個案式文本。
巴赫金所言及的 “文化/文本關系”,告訴了我們 “知識分子寫作”與 “民間寫作”的沖突溢出文學文本的范疇,而與文化根源和社會語境發生了聯系。沖突雙方都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如果雙方構成了中國1990年代以來的詩歌整體性大文本的話,那么雙方只是發出了尤如小說文本中的 “復調”聲音,“并存和相互作用”[8]成為了文學現場的一種客觀存在。“盤峰論爭”延續兩年左右的熱鬧景象及其之后的延伸性影響,又形成了巴赫金式 “狂歡節”的文學形式,這種形式本身是社會綜合文化的體現,而不單單是文學文本的側映。
(三)“盤峰論爭”互文性的延伸
外在的力量和影響會產生新的互文性文本。“盤峰論爭”中的雙方盡管也是 “歷史的”和 “政治的”因素產生的一次互文性沖突,但1999年12月在北京召開的 “99中國龍脈詩會”上,當 “知識分子寫作”一方集體缺席之時,莫非、樹才、車前子等人對 “盤峰論爭”表示不滿并順勢提出 “第三寫作”或 “單獨者”寫作的詩歌觀念,也即后來的 “第三條道路”①“龍脈詩會”之后,譙達摩、莫非、樹才等詩人編選《九人詩選》,明確提出“第三條道路”的詩歌觀念,為“盤峰論爭”后詩歌觀念的多元化趨向提供了有力的佐證。。在互文性理論看來,這同樣也是一種互文性文本的誕生。巴赫金指出:“一個人要為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指明方向,這就意味著他應把世界所容納的一切物體考慮為同時存在并從時間上的某一刻去猜想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9]“第三條道路”的詩人們瞅準了“盤峰論爭”這一時刻,欲為自己 “指明方向”而在 “知識分子寫作”和 “民間寫作”之外揉入自身來思考他們三者 “之間的相互關系”。
“第三條道路”詩人們的做法對其他詩人是頗具啟發性的。根據互文性具有 “無限組合的意義”這一點來看,在由詩人們所組成的一個巨大的互文性空間里,某一方的文本與另一方或他方的眾多文本都有可能進入一個無限交流的過程之中。后來在 “衡山詩會”上,“民間寫作”詩人內部年輕一代的代表人物沈浩波對自己陣營的瓦解,次年發生沈浩波與韓東之間 “沈韓之爭”。由此可見,即使 “知識分子”不參與 “交流”,但在多元的社會文化語境之下,“民間寫作”內部也將產生另一形式的互文性文本,這些“文本”直接體現在詩歌觀念上。正是在社會多方面互文性助推力的作用之下,才會出現 “70后”詩歌的崛起、“下半身”詩歌運動、中間代詩歌運動,等等。這些都可視作 “盤峰論爭”互文性的延伸。
三、 “知識分子寫作”和 “民間寫作”互文性淵源和對立
互文性理論一般從形式分析入手,但其視野卻延伸到整個文學傳統及其文化影響上。接下來我們將從 “知識分子寫作”和 “民間寫作”的前世出發,來追溯二者互文性的內在邏輯性發展的淵源。這可能是一個有效的觀察視角,畢竟互文性理論認為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都是其他文本的鏡子,不同文本之間彼此牽連和參照,從而才能構成某個文本的前世和今生,也即我們完全可以利用互文性理論來考察 “盤峰論爭”兩種詩歌觀念的演變歷程。
(一)“知識分子”概念和詩歌:從西方到中國
英國學者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曾經梳理過西方 “知識分子”(intellectual)概念的演變史,其對象主要是指 “有知識的、知識分子”的一類人;后來的一些西方學者則更多地將知識分子與文學、文化相聯系。在中國現代之前,類似于西方知識分子的人則有專門稱謂——“士”。余英時的 《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許紀霖的 《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新星出版社,2005年),均以西方知識分子為互文性參照來對中國的 “士”傳統進行梳辨,而且將知識分子概念與中國 “詩教”傳統緊密地結合起來。
從這點來看,“知識分子寫作”與 “民間寫作”的中西互文性以及古今互文性,就有了理論上的淵源和相當的理論可塑性。“知識分子寫作”與 “民間寫作”的內在矛盾性和發生的沖突,不僅有中外文化影響上的因素,也存在于中國古今文化過渡的某些方面。從中,我們完全可以認識到,無論是 “知識分子寫作”還是 “民間寫作”,他們從整體上來看其實都是同源的。不過,“知識分子寫作”的西方互文性相對明顯,而 “民間寫作”與中國傳統的血脈則相對密切。
具體而言,“知識分子寫作”的確更多地吸收了西方的資源,而 “民間寫作”除了在現實中沒有占據“利益性”的資源或話語權之外,也在口語化和思想上偏向于傳統的資源。兩者之間的內在性雖然具有同一性,然而沖突性卻又由來已久。二者之間復雜關系的實質,其實都應指向西方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在“五四”前后對中國現代化進程所起的推動作用。
(二)“新文化運動”以降詩歌 “貴族化”與 “平民化”的對立
在20世紀中國的社會大語境之下,略作考察,詩歌的互文性對立則有一條相當清晰的線索。其最基本的特征表現在:新詩誕生之初,從主題表現來看,詩歌的精神既與西方知識分子的精神相悖離又相融合。以胡適為代表的白話詩與中國傳統古典詩詞的知識分子性是相沖突的,但與西方的人性、人道主義相融合;稍后,從形式表現上看,新詩散文化傾向過于明顯,新詩一度出現的無難度、口水化特征,使其在相當程度上發生了偏離,而令其為人所詬病。為挽新詩于危難之中,后來的前期新月派徐志摩、聞一多提出 “三美”原則,穆木天提出純詩理論的貴族化傾向,還有戴望舒的現代詩的創建。這些又是對新詩自身的互文性沖突的表現。
針對 “知識分子寫作”和 “民間寫作”而言,在此我們不妨將其中復雜的互文性對立縮小到 “貴族化”與 “平民化”的立場上,并作簡單的論析。從新詩誕生之初即出現危機時穆木天提出純詩理論開始,新詩即已出現某種程度上的 “貴族化”傾向,當然這種 “貴族化”與新詩自身建設相關,是詩形式意義上的。差不多與此同期,無產階級詩歌的興起,則將周作人與俞平伯等人最初提出的 “平民化”觀念推向一個極端,只不過這種 “平民化”多與社會語境等外在因素相連,本質上講是對詩歌外在形式的一種補充。這兩條線索,各自經過穆旦的現代詩、“文革”時期的潛在寫作、20世紀80年代文化詩等直至“知識分子寫作”,和無產階級革命詩歌、解放區詩歌、工農兵詩歌等直至 “民間寫作”,二者之間彼此交織、對立,又平行發展。20世紀末時,由于社會語境的相對寬松以及詩歌內外環境的新變化,才使得這一互文性的對立最終強烈地爆發。這恰恰是 “盤峰論爭”得以發生最本質的內因。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降 “知識分子”和 “大眾”的尖銳沖突
我們不妨就上面一點進一步展開來闡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不斷發生的運動,很多時候對大量知識分子施行了壓制政策,張賢亮、昌耀等因寫詩而被打成右派即為其中最為典型的事例。不過,這些運動均是以更為廣泛的民眾作為參照來進行的,至少是打著 “人民”或 “大眾”的旗號。在全國范圍內,包括詩人在內的眾多知識分子,都相繼接受貧下中農的 “再改造”。新詩的 “貴族化”徹底沒有了市場,完全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代之以 “大躍進”詩歌、小靳莊詩歌、紅衛兵詩歌,等等。社會的政治導向使 “大眾”處于絕對的優勢,無論是政治還是文學,“大眾”在相當長一個時間內都呈現為狂歡的局面。這一態勢直到“新時期”的到來才有所遏制。
這種由社會、政治因素而影響到文學、詩歌文本的現象,則完全可以由互文性理論來進行闡釋。“新時期”之初的朦朧詩論爭,其實是貴族化詩歌的一次回歸,是對之前過于極端化的平民大眾詩歌的一次反撥。同時,也是繼 “五四”時期借助西方話語資源在中國進行的又一次思想層面的再啟蒙。與此相呼應的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文化詩的一度興起。不過,在朦朧詩到文化詩的發展過程中,第三代詩歌運動也如火如荼般開展起來。以 “詩到語言為止”“拒絕隱喻”為詩學追求的第三代詩歌不同于以往歌謠式的大眾詩歌,其呼應的是后現代的語境,帶有解構的意味。當海子兼有貴族和民間特質的詩歌遭遇1989年的困境之后,詩歌的貴族性和平民性裹挾而含混地進入1990年代。值得一提的是,當女性主義傳入中國時,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中期即有翟永明詩歌的橫空出世與其呼應,這也能體現國外理論與中國詩歌的互文性關系。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中國女性主義詩歌又出現跨文體的互文性現象,林白、陳染的 “私人寫作”即為其中杰出的代表。
20世紀90年代,當社會語境轉換的標志性事件——鄧小平同志 “南巡講話”發生后,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詩歌在市場化和大眾化面前,文學邊緣化的命運已不可避免,然而這又是一次文學離自身最近的時期。詩歌內部的紛爭已開始醞釀,沖突遲早都要發生。當政治與文學已開始相互疏離,當文學不再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文學內部的建設或分歧將會加快步伐。20世紀末情結之下,中國整個20世紀詩歌的貴族化與平民化兩道流脈交匯、融合、沖突,最終形成 “知識分子寫作”和 “民間寫作”的劇烈沖突,導致了1999年 “盤峰論爭”的爆發。
四、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不妨對 “知識分子寫作”與 “民間寫作”的互文性淵源及其沖突做出如下的小結:其一,在互文性理論之下,“盤峰論爭”的雙方沖突實際上是持兩種不同詩歌觀念的批評家之間的沖突,于詩歌本身而言,本身上是雌雄同體的。其二,在互文性理論之下,作為詩歌觀念并非固定不變的,不管持何種觀念,都是流動性的。這可以用來解釋 “盤峰論爭”之后,為什么 “知識分子寫作”和 “民間寫作”在某種程度上都在向對方吸收和轉化,這也可以用來解釋當時略顯優勢的 “民間寫作”內部為何也不斷發生分化的現象。其三,在互文性理論之下,詩歌或文化觀念的發展、變異不僅僅是文學內部的事,在很大程度上還受到社會背景和文化語境的極大影響。
[1][3]張清華.一次真正的詩歌對話與交鋒——“世紀之交:中國詩歌創作態勢與理論建設研討會”述要[J].詩探索,1999(2).
[2][4]周航.中國詩歌的分化與紛爭(1989-2009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4.
[5]姜濤.中國詩歌:九十年代備忘錄[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137.
[6]孫基林.世紀末詩學論爭在繼續——99中國龍脈詩會綜述[J].詩探索,1999(4).
[7][美]卡爾·貝克森,[美]阿圖爾·甘茨.文學術語詞典[M].[美]紐約:努恩戴出版社,1989:129.
[8][9][俄]米哈伊爾·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英文版)[M].[美]安阿伯:阿迪斯出版社,1973:20-23.
[10]周航.中國詩歌的分化與紛爭(1989-2009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1][英]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M].劉建基,譯.北京:三聯書店,2005.
[12]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3]許紀霖.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責任編輯:志洪]
I206.7
A
1674-3652(2016)03-0087-05
2016-02-25
楊紅,女,湖南雙峰人,青年骨干教師武漢大學訪問學者。主要從事語言學和比較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