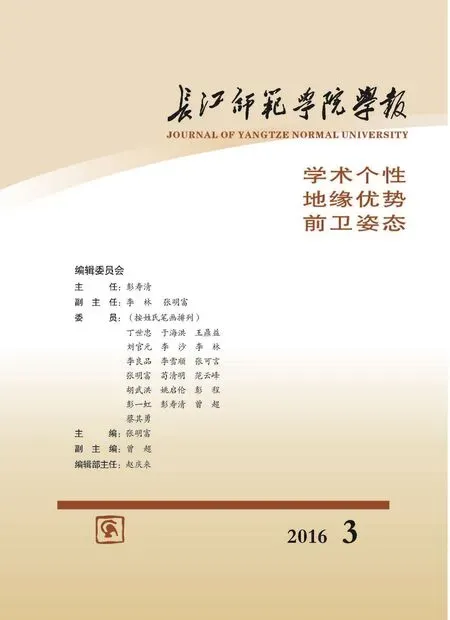倫理學視域下蘇格拉底悲劇探析
李銀兵,劉發(fā)順
(1.貴州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貴州 貴陽,580001;2.玉溪師范學院 政法學院,云南 玉溪 653100)
倫理學視域下蘇格拉底悲劇探析
李銀兵1,劉發(fā)順2
(1.貴州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貴州貴陽,580001;2.玉溪師范學院政法學院,云南玉溪653100)
蘇格拉底之死之所以被稱為悲劇,是因其死亡背后存在著諸多的意蘊和價值。單從倫理學視角去看,其悲劇背后存在的倫理難題、善惡主題、倫理功能表現(xiàn)十分突出,意義也最為重大。蘇格拉底以一己之力 “舉起”了整個世界,啟迪著人類智慧。就此而言,蘇格拉底悲劇是人類的 “喜劇”,悲喜之間,人類德性和靈魂得到了一次大的洗禮,這是蘇格拉底悲劇最大的價值。
蘇格拉底;倫理思想;悲劇
黑格爾曾經(jīng)說:“蘇格拉底的特殊貢獻,就是他建立了一個新的概念,亦即他把倫理學加進了哲學。”[1]的確,在蘇格拉底以前,希臘的哲學主要研究宇宙的本原是什么,世界是由什么構成的等問題,后人稱之為 “自然哲學”。而在自然哲學和蘇格拉底哲學之間的智者學派雖然開始關注人,并提出了 “人是萬物的尺度”這樣的經(jīng)典話語,但是他們卻又有使哲學走向相對主義的傾向,哲學的重任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蘇格拉底、柏拉圖及亞里斯多德這些標志性人物的身上了。蘇格拉底認為,再研究自然哲學這些問題對拯救當時的國家沒有什么現(xiàn)實意義,哲學應該回歸于人本身,特別是要去關注人自身的發(fā)展問題。于是蘇格拉底就把哲學從天上帶回了人間,開始研究人類本身,即研究人類的倫理問題。蘇格拉底的倫理思想把人和社會從自然世界中區(qū)分開來,突出關于人和社會的知識的重要性,引導人們關注人類自身的問題,這種人文主義精神對后世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可以這樣說,蘇格拉底的倫理思想成就了蘇格拉底在整個西方哲學思想史上的地位,但也直接導致了其悲劇的誕生。有鑒于此,這里從倫理學視角,著重從蘇格拉底悲劇背后存在的倫理難題、善惡主題及倫理功能入手去探析蘇格拉底悲劇產(chǎn)生的原因,以期從其悲劇中發(fā)現(xiàn)些許大義,以求教于方家。
一、蘇格拉底及其悲劇
蘇格拉底 (Socrates,前469-前399年),古希臘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蘇格拉底與他的學生柏拉圖,以及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被并稱為 “古希臘三賢”,更被認為是西方哲學的奠基人。在蘇格拉底一生中,提出了 “德性即知識”“自知無知”“無人故意作惡”等著名言論。前399年,蘇格拉底被雅典法庭以 “敗壞青年”和 “不敬神”兩項罪名控告,并最終被判處死刑。自此,他的死成了希臘的悲劇,更成了整個人類的悲劇。悲劇起源于古希臘,由酒神節(jié)祭禱儀式中的酒神 (狄奧尼索斯)頌歌演變而來。在希臘神話中,日神是理性、進步、樂觀的象征,酒神是非理性、無序、沖動的代表。悲劇就是就酒神和日神之間永無歸結的運動,是理性和感性沖動之間形成的一種命運,人解不開這個命運之謎,卻勇敢地接受命運的挑戰(zhàn),讓生命境界從原始的生命沖動中超升,讓痛苦的體驗作為培育人的精神家園,從而書寫生命的壯美。希臘悲劇基本上取材于神話與傳說,以古代的英雄故事為主要內(nèi)容,其目的是通過高尚人物的悲慘命運和恐怖場面,激起觀眾的憐憫心和同情心,讓心靈得到凈化。希臘悲劇由神的悲劇、英雄的悲劇發(fā)展成為人的悲劇。總之,“從劇情上看,悲劇是人在客觀世界面前所面臨的矛盾沖突和不幸命運。從歷史角度看,悲劇不過是對一個處在急劇變化中的社會的倫理沖突的藝術寫照,它以一種驚心動魄的方式表現(xiàn)了個人的自由意志與客觀必然性之間的深刻矛盾。其實質(zhì)是對立的倫理力量之間的相互沖突。”[2]說蘇格拉底之死是一場悲劇,是黑格爾首先提出來的。黑格爾認為,蘇格拉底的遭遇具有高度的悲劇性,他的遭遇不僅是他本人的悲劇,而且是雅典的悲劇、希臘的悲劇,而這些悲劇只是借蘇格拉底表現(xiàn)出來而已。在蘇格拉底的遭遇中,一直有兩種力量在互相對抗。一種力量是雅典當時的法律、宗教信仰和習俗,它要求人們在這個傳統(tǒng)中自由的、高尚的、合乎倫理的生活,在這里我們可以把它稱為客觀必然性。以此相反,另一個力量則是蘇格拉底內(nèi)心的意識和法律,這個法律是他自身的知識和理性,是他辨別善惡的價值判斷,它指引著蘇格拉底不斷地追求真理和至善,在這里我們可以把它稱為自由意志。我們將看到這兩股矛盾力量一直困擾著蘇格拉底的思想和生活。
二、倫理沖突下的蘇格拉底悲劇
倫理學所境遇的問題都是難題,都是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的產(chǎn)物,而倫理學之為倫理學的關鍵在于其面對這些問題時,不是忽視,也不是躲避,而是在一定價值指導下的判斷和選擇。具體而言,倫理難題指的是那些源于不同價值觀沖突、誘發(fā)倫理抉擇、訴諸道德責任感的帶有倫理特性的難題。同時,這些經(jīng)常讓我們感到為難的難題不僅僅是一個個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而且矛盾雙方還勢均力敵,都有其合理性,這就加重了人們選擇的難度。倫理學是一門實踐科學,其實踐性就在于它要為解決問題而存在,因此,當遇到倫理抉擇矛盾時,我們并不是避而不談,而是要勇于去做出判斷,進而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總之,倫理難題的這些屬性充分展現(xiàn)了倫理學學科的特點,也就成為了我們研究倫理問題、分析倫理矛盾的開始。在蘇格拉底悲劇產(chǎn)生過程中,同樣面臨著這樣或那樣的倫理沖突和抉擇,蘇格拉底悲劇是倫理難題的表征。
第一,一神與多神、內(nèi)在神與外在神的沖突。蘇格拉底一直強調(diào),他的內(nèi)心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在指引著他,并賦予他使命。蘇格拉底自稱經(jīng)常受到靈異的警示。蘇拉底所說的 “靈異”(神靈)并沒有真正在蘇格拉底面前所顯現(xiàn)出來,蘇格拉底也沒有對這個神進行過描述,它的出場乃是一種 “聲音”,一種來自蘇格拉底自己內(nèi)心深處的 “聲音”。實際上,蘇格拉底的靈異就是蘇格拉底自己,靈異的聲音就是他自己內(nèi)心深處的聲音,體現(xiàn)在哲學里,這就是他個人的自我意識和個體意志。而雅典人所信仰的神是從古老的神話傳說中流傳下來的,它們種類繁多且譜系分明。并在此基礎上,雅典人建立了他們的城邦、法律和傳統(tǒng)習俗。蘇格拉底在自己靈異聲音的召喚下,把批評雅典多神教和外在神看作神給他的神圣使命,這種使命感和由此而來的思考探索,便成為他生活與哲學實踐的宗旨,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蘇格拉底用自我確信的精神和自我決定的理性確立起了道德主體原則。而雅典人一直在原有的神圣法律、信仰和習俗中自由并合乎倫理地生活著,他們認為自己的法律是公正的,并且堅信自己的習俗是倫理的,但蘇格拉底卻對此提出批評。因此雅典人認為蘇格拉底的行為是叛逆的,他的行為傷害了雅典人的精神和倫理生活,雅典人必須對他的行為做出懲罰。
第二,城邦民主興衰變換下的蘇格拉底悲劇。歷史總是這樣:當一個城邦或國家興盛強大的時候,人們便制定規(guī)則,而當城邦或國家腐敗沒落時,人們便極力維護規(guī)則。蘇格拉底從出生到被處死,經(jīng)歷了雅典奴隸主民主制從盛到衰的整個過程。他對民主制的態(tài)度也是從擁護而逐漸變?yōu)榉磳ι踔脸鹨暤摹kS著民主制的沒落,蘇格拉底意識到,治理城邦需要一支專業(yè)的隊伍,這支隊伍必須具備專業(yè)的政治知識和管理能力,而不能像現(xiàn)在把國家的權力分散在一些沒有政治知識和管理知識的普通公民手中。因為隨著社會生活的進一步發(fā)展,國家機器也要求進一步完善,公民也需要一定的專業(yè)知識,以便更有效地行使國家機器的職能。但當時雅典的民主制已經(jīng)沒落,不能選舉出強有力的政府領導班子,因為當時參加公民大會的城市貧民在蠱惑家的煽動下已經(jīng)失去了理智和基本的判斷能力。在這種情況下,雅典人就再也沒有選出過一個有知識和能力的政府領導班子。在蠱惑家的煽動下,選舉可以在轉(zhuǎn)瞬之間改變意見,甚至改變政制形式。在這里,每個公民都有選舉的權利,但當每個公民在大會上都擁有完全的平等權利時,唯一能做出決定的是多數(shù)的表決。可是由于公民本身的局限性,多數(shù)的意見往往并不代表真理,而時常被某些偶然情緒所左右,當多數(shù)的意見與這個階級的根本利益發(fā)生矛盾時,人們就會在 “意見”與“真理”之間劃出愈來愈嚴格的界限。柏拉圖曾經(jīng)也說過,多數(shù)人的意見有時并不能得出正確的判斷,只有根據(jù)知識,才能得到正確的判斷。因此,蘇格拉底是從一個普遍的原則,即統(tǒng)治者要具有統(tǒng)治的專門知識來反對當時的雅典政制的。
蘇格拉底面對著這樣的一個轉(zhuǎn)型社會,表明看起來恰恰是這個社會的時勢變遷帶來了蘇格拉底的選擇困難。其實不然,在時勢變遷的背后,則更有另外一番邏輯,比如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民主與專制、自由與和諧、機遇與挑戰(zhàn)等,矛盾后面面臨著不同的結果。“因此,蘇格拉底的死是一個悲劇,死于雅典的民主,而民主制度是歐洲文明的源泉之一,這是矛盾的,也是辯證的。”[3]
第三,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碰撞下的蘇格拉底悲劇。內(nèi)在信仰和民主興衰的事實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蘇格拉底在面對社會變換時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碰撞與選擇的問題。蘇格拉底根據(jù)自己內(nèi)心深處靈異思想的召喚,確立起了他自己的價值觀,雅典人也根據(jù)自己的傳統(tǒng)與信仰過著他們認為合乎倫理的生活。蘇格拉底看到雅典民主制的沒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而雅典人卻還在極力維護沒落的民主制。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蘇格拉底的思想似乎與雅典的傳統(tǒng)格格不入,他陷入了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發(fā)生沖突時的選擇困境中。他的哲學思想與雅典傳統(tǒng)相矛盾,他的政治主張也同雅典民主制背道而馳。這兩種思想在當時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蘇格拉底又必須從這二者中做出選擇,于是他進入了選擇的困境中。誹謗者最后以 “褻瀆神靈”和 “教壞青年”罪名起訴蘇格拉底,代表當時社會已經(jīng)衰落的500個公民被蘇格拉底激怒,最終陪審團把蘇格拉底送上了斷頭臺。蘇格拉底在可以選擇生也可以選擇死的情況下,為什么會做出走向死亡這樣的選擇呢?答案在于他的倫理思想,在于其對內(nèi)在的道德的強調(diào),在于他那種對真理的熱情,就是這些精神使希臘哲學導向了一個新的方向,“可以說他是第一個將倫理道德作為關注中心的哲學家”[4]。
三、價值判斷視野下的蘇格拉底悲劇
上面我們談到蘇格拉底陷入了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發(fā)生沖突時的難題選擇中,但難題不是不選,而是要做出價值判斷,判斷的標準何在?不同的倫理學家有不同的認識,但總的來說,善惡問題作為倫理學基本論題,則可作為倫理判斷的依據(jù)和歸宿。“倫理學研究的問題很多,但最基本的問題還是 ‘善'與‘惡'的問題。因為善與惡是倫理學范疇的核心,善與惡的矛盾是道德中特有的矛盾,只有在道德中才存在善與惡的問題,也只有在倫理學中才研究善惡矛盾,同時善與惡的問題是古今中外一切倫理學家,一切倫理學派普遍注意研究的重大問題,并且善與惡的矛盾貫穿在人類道德生活的一切領域并貫穿道德生活的始終。”[5]就蘇格拉底悲劇而言,其倫理判斷背后的善惡則是建立在蘇格拉底自身的哲學基礎上。
與其他哲學家一樣,蘇格拉底最初也在研究自然哲學,但隨著國家的衰落和人民的墮落,蘇格拉底認為再研究自然已經(jīng)沒有任何意義,于是他將研究方向從關注自然科學轉(zhuǎn)到了倫理學上,開始研究人自身的德性和幸福生活。因此,蘇格拉底提出了 “善”的觀念,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倫理價值觀體系:知識—德性—至善。蘇格拉底說:“自然萬物真正的主宰和原因并不是物質(zhì)性的本原,而是它的內(nèi)在目的,亦即 ‘善'。由于認識自然的本性為我們的能力所不及,因而哲學的真正對象不是自然而是人自己,亦即認識人自生中的善。”[6]蘇格拉底首先從 “認識你自己”出發(fā),得出自己的無知,從而不斷地追求知識。在蘇格拉底看來,追求知識不僅是人之為人的本性和使命,而且是治愈雅典民主制沒落的良藥。蘇格拉底說:“認識人自己就是認識心靈的內(nèi)在原則,亦即認識德性。”[7]“‘善'是自然萬物的內(nèi)在原因和目的,具體到人身上,就是 ‘德性'。德性是人的本性,由神平均分配給了每一個人,因而人人都具有德性。但是說人人都有 ‘德性',并不是現(xiàn)實的擁有,而是潛在的擁有。換言之,人并不是生來就符合人的本性,只有在理性指導下認識自己的德性,才能使之實現(xiàn)出來,成為現(xiàn)實的和真正的善。所以蘇格拉底認為,未經(jīng)理性審視的生活是沒有價值的,一個人只有真正認識了他自己,才能實現(xiàn)自己的本性,完成自己的使命,成為一個有德性的人。因此,他把德性與知識等同起來,得出了 ‘知識即德性,無知即罪惡'‘無人有意作惡'的結論”[8],進而建立了以內(nèi)省為基礎的道德知識。
在蘇格拉底看來,趨善避惡是人的本性,沒有人自愿追求惡或他認為惡的東西,是行善還是作惡,關鍵取決于他的知識,因而每個人在他有知識的事情上是善的,而在他無知識的事情上則是惡的[9]。那么,為了做到趨善避惡,人們就應該不斷地獲取正確的知識,而知識來源于理性的反思,理性又內(nèi)在于人的靈魂之中。所以人首先要關注自己的靈魂,通過靈魂對事物本身精心反思,才能獲得純粹的知識,從而達到至善。自此,蘇格拉底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倫理價值體系,并在內(nèi)心靈異聲音的召喚下,蘇格拉底帶著這套體系踏上了他的使命之路。他到處找人討論各種各樣的問題。例如,什么是虔誠?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氣?什么是真理?……意在使人們認識到在這些對于人至關重要的問題,從而不斷地去追求知識。但由于他的提問方式與眾不同,經(jīng)常會讓很多人顏面掃地,因而一部分人對他產(chǎn)生了恨意。同時他的方法也被很多年輕人學去,這些人用同樣的方法去問他們的父母、長輩,經(jīng)常使他們的長輩理屈詞窮。所以雅典人禁止他教授修辭學,并說他腐化青年,并將他告上法庭。
現(xiàn)在,我們再回過頭來看蘇格拉底的死,就不難得出他的死是在自己的倫理價值觀體系的指引下做出的。表面上看,蘇格拉底始終堅持自己的信念,要做一個好公民。作為公民,蘇格拉底認為善就是遵守雅典的法律,所以當雅典法律判他死刑時,他接受了。同時蘇格拉底還認為,不正當?shù)纳钍遣恢档眠^的,逃亡是不正當?shù)模詯簣髳阂彩遣粚Φ模油龊蟮纳顩]有價值,不應以逃亡的手段報復國家對他不公的判斷。實質(zhì)上,蘇格拉底這種善惡觀是以內(nèi)在意識為基礎的,這和以外在法制為基礎的已經(jīng)衰落的民主城邦的價值善惡標準是有很大的出入,但也存在很大的聯(lián)系。作為城邦公民,蘇格拉底很好地詮釋了城邦個人與公民之間的關系。公民善惡觀和城邦善惡觀的直接沖突導致了蘇格拉底的死亡,因此我們可以說導致蘇格拉底之死的原因不在外在,而是在于蘇格拉底自己。因為蘇格拉底是用自己的生命踐行了他的趨善避惡、他的知識觀以及他是城邦合格公民的信念,踐行了其力求過 “有德性的生活”的人生格言。
四、倫理功能下的蘇格拉底悲劇
“道德行為具有促進個人和社會利益發(fā)展的傾向,具有弘揚自己的人性、實現(xiàn)人的價值、使人不斷發(fā)展、完善的能量或功用;道德規(guī)范具有協(xié)調(diào)人我?guī)兹旱雀鞣N關系,使個人和社會的生活成為可能的職能或作用;道德意識則具有幫助人們認識自我與人生,確立人生的目的和意義以引導人發(fā)展起屬于人的各種心理、意識和精神活動的效力或能力。具體來說,道德的功能表現(xiàn)在命令、規(guī)約、教育、認識、調(diào)節(jié)、激勵等方面。”[10]蘇格拉底雖然死了,但他的死卻對后世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不斷求知。追求確定的真知識,是歐洲文化脫離神話傳說以來的傳統(tǒng)目標,蘇格拉底也不例外。直到死亡的前一刻,蘇格拉底還在與朋友討論學術上的問題,這充分體現(xiàn)了蘇格拉底對知識、真理的追求。他的這種精神正是古希臘求知精神的體現(xiàn)。蘇格拉底雖然死了,但他的精神卻為后人樹立了榜樣,激勵著人們對知識、善、真理進行永無止境的追求。因此,我們應以蘇格拉底為榜樣,抱著求知的心態(tài),不斷的去學習知識,追求真理。
第二,做到自知。蘇格拉底的 “認識你自己”是從自知無知開始的。蘇格拉底得到神諭說自己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但他對這個神諭迷惑不解,于是他到處走訪那些被公認為最有知識的人,結果發(fā)現(xiàn)那些人在對自以為有知識的事上面其實是無知的,于是他發(fā)現(xiàn)神說他是最有智慧的人,原因在于他知道自己是無知的。蘇格拉底的自知無知意在喚醒當時雅典人們對現(xiàn)有價值體系的心滿意足,去追求一種德性的、善的生活,而這種關于德性的、善的知識才是人應該努力去掌握的知識。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知識是廣博的,學習是無止境的,我們應正確認識自己的知識水平。我們不應不懂裝懂,而是要老老實實承認自己的無知,不能因為自己懂得一點就沾沾自喜,固步不前。相反,我們應不斷地反思、正確地認識自己的優(yōu)點與不足,發(fā)揚自己的優(yōu)點,改正自己的缺點,并抱著一顆求知的心態(tài),不斷地去學習、探索、創(chuàng)新以便使自己更加完善。
第三,堅守良知。當法庭宣告蘇格拉底有罪后,他在法庭上做了申辯,并始終認為自己無罪。在這里就出現(xiàn)了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既然蘇格拉底認為法律的判決是不公正的,而公民又有義務不服從不公正的法律,他自己也在申辯中闡述了自己無罪,為什么他又拒絕逃亡而選擇服刑呢?原因在于蘇格拉底的良知。蘇格拉底一再強調(diào)要達到至善就要盡量避免去做不正義的事。同時他也說過不得以不正義反對不正義。他認為逃跑是不正義的,作為雅典公民,他有義務維護雅典民主制和法律的權威。相反,如果在這個時候逃跑的話,雅典人只會認為蘇格拉底逃跑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因此,當法律判處他有罪時,最好的辦法就是接受死亡。這樣做不僅不違背自己的良知,也只有以這種方式去赴死才有可能喚醒沉睡希臘人,使他們意識到當時法律的弊端,從而起來糾正它們。蘇格拉底反對他的控告,認為自己無罪,這表現(xiàn)為一種不服從;而當法律判處他死刑時,他坦然接受了,這表現(xiàn)出一種服從。蘇格拉底正是用了這種不服從中的 “服從”來反諷希臘社會中的弊端,并借此喚醒希臘人重新審視希臘社會。當他的思想與雅典傳統(tǒng)產(chǎn)生矛盾時,他依然堅守著自己的信念,那就是永不停止的哲學實踐,并以改善人的靈魂,樂于教人為天職,并寧愿以死喚醒雅典民眾。堅守良知,是我們每個人都知道的道理,但是能真正做到堅守的人并不多。因為良知總是徘徊于堅持與動搖之中,有的時候甚至會出現(xiàn)堅守比放棄還難的無奈。這時我們千萬不要被利益沖昏頭腦,為了一己私利而放棄良知。我們唯有堅守自己內(nèi)心的價值判斷,保持內(nèi)心的寧靜,不受外界干擾,堅持做應該做的事,才能做到堅守良知,達到人生的至善。
魯迅曾說:“悲劇是把有價值的東西撕碎給人看,喜劇是把沒有價值的東西組合給人看。”古希臘悲劇之所以流傳至今,永不衰老,其根本緣由就在于其悲劇中凸顯了希臘人對于人生、生活、做人、做事的看法,而這種看法充分地展示了希臘人熱愛知識、熱愛自由、充滿理性的民族個性。蘇格拉底悲劇就是這個悲劇中最為悲劇的一頁,蘇格拉底以一己之力 “舉起了”整個世界,啟迪著人類智慧。就此而言,蘇格拉底悲劇是人類的 “喜劇”,悲喜之間,人類德性和靈魂得到了一次大的洗禮,也許這就是蘇格拉底悲劇最大的價值。
[1]金玉雙.蘇格拉底之死及其人生倫理意義[D].河北大學,2011.
[2]趙林.西方文化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46.
[3]陳樂民.歐洲文明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22.
[4]馬克垚.世界文明史(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218.
[5]魏英敏.新倫理學教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12-115.
[6][7][8][9]張志偉.西方哲學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56、56、57、57.
[10]魏英敏.新倫理學教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215.
[責任編輯:慶來]
B12
A
1674-3652(2016)03-0101-05
2016-02-25
李銀兵,男,四川資中人。博士,教授。主要從事倫理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