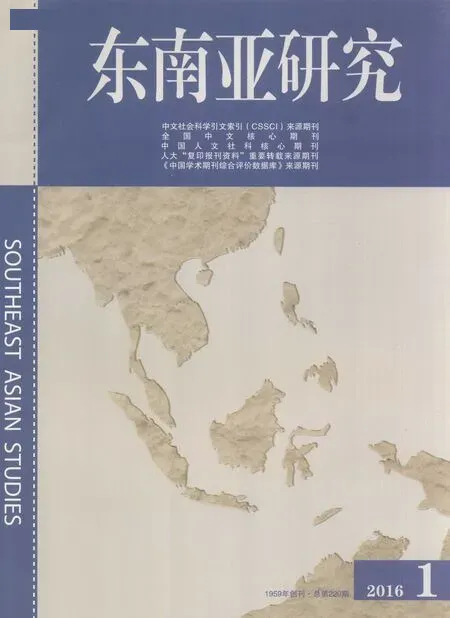緬甸包容性政治的建構:協和民主的適用性
項 皓 張 晨
(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江蘇蘇州 215123)
?
緬甸包容性政治的建構:協和民主的適用性
項皓張晨
(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江蘇蘇州 215123)
[關鍵詞]緬甸;協和民主;多民族國家;包容性制度;橫跨性忠誠
[摘要]緬甸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當下正處在政治轉型的關鍵時期,因而如何建構一套維護國家統一和政治穩定的制度,保障民主生根發芽,同時維護不同民族群體的利益是其面臨的一大挑戰。本文試圖評估協和民主作為解決緬甸民族分裂問題方案的適用性。盡管協和民主在操作層面有一定局限,但其倡導的大聯盟、精英和解以及提升民族間的交叉認同都能夠促使多元分裂的異質性緬甸社會得到穩定。緬甸作為中國“一帶一路”戰略中的重要成員,其國內政局的動蕩和政治轉型的進程值得我們持續地關注。
Abstract:As a multi-ethnic state, Myanmar/Burma is now undergoing a critical point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refore it is a great challenge for Myanmar to build a set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nation’s stability and democracy. This paper regards the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as an efficient solution to ethnic conflicts, the advocacy of grand coalition and overarching loyalty may promote the understanding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s. Myanmar is an essential member of China’s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thus its domestic ethnic conflicts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worth our much attention.
自2011年文官政府掌權后,緬甸結束了長達49年的軍政府統治,重新與世界聯系起來,但政治發展進程卻飽受民族紛爭的影響。截至2015年上半年,緬甸和平監察站的調查報告顯示,緬甸政府軍和民族武裝組織僅在2015年1月到6月底就交火了231次。與緬甸政府軍關系最緊張的是德昂民族解放軍、克欽獨立軍和果敢同盟軍[1]。頻繁的戰事嚴重影響到緬甸的政治轉型進程。長期以來,研究第三波民主化和民族問題的學者都關注到民族問題和民主發展之間的關聯,本文希望通過梳理民族與民主之間的邏輯和緬甸憲法中規定的制度設計來探討在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協和民主條件下,緬甸的“民族—國家”和民主化是否能形成互補的邏輯,從而解決緬甸嚴峻的民族沖突問題。緬甸民主政治的建構涉及政府武裝和少數民族地方武裝的停火,和平的關鍵在于建立一套具有包容性和妥協性、權力分享的政治制度,讓民主得到社會各團體的理解和信任。
一多民族社會與協和民主的邏輯
對于多民族社會而言,建立和鞏固民主制度是困難的,政治學家一般認為社會同質和政治共識是民主政治得以建立的前提,也是民主建設的重要推動力。多元民族社會中多樣化的文化、宗教和地域等差異,往往會給民主政權帶來不安定因素。
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世界范圍內族群沖突和族群暴力的急劇增加又佐證了這樣一種認識。于是,研究分裂社會和憲政制度設計的大多數學者都傾向于認為嚴重的民族分裂對民主而言是毀滅性的打擊,在這種社會里建立和穩固民主政府要比在同質的社會中困難很多。反過來,學者們也認為在民主尚未建立的國度中,民族和其他類型的社會分裂要更加嚴重。第三個得到廣泛認同的結論是,在分裂社會中建立一個成功的民主政府需要兩大要素,即權力分享(power sharing)和群體自治(group autonomy)*參見A. Lijphart,“Constitutional design for divided societies”,Journal of Democracy,Vol.15,No.2,2004,pp.96-109.權力分享是指政府的一種制度模式,即保證各少數民族在參與政策制定時都有自己的代表和發言權;群體自治是指保證少數核心族群至少有本地區的區域自治權力(group regional autonomy ),見Lars-Erik Cederman, Simon Hug, Andreas Schadel & Julian Wucherpfennig,“Territorial Autonomy in the Shadow of Conflict: Too Little, Too Lat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9,No.2,2015,pp.354-370.。基于此,為了安撫各民族的利益紛爭,憲政設計者嘗試通過一些途徑減少沖突,其中較有影響力的有三種模式:第一種是聚合機制*參見Donald Horowitz,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以及霍諾維茨之后的著作和文章。,第二種是協和機制*參見A. Lijphart,“Consociational Democracy”,World Politics,Vol.21,No.2,1969,pp.207-225,以及利普哈特1969年之后的著作和文章。,第三種是隔離機制*參見Chapman, Thomas & Philip G. Roeder,“Partition as a Solution to Wars of Nationalism: The Importance of Institution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1,No.4,2007,pp.677-691等。。在細節的設計和認知上,三種模式各有利弊,但都特別關注到中央權力和地方自治的關聯。緬甸的民族構成(如地理性集中)和歷史傳統都有實行利普哈特“協和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的有利條件,因此這里考察的是協和民主在緬甸的適用性。利普哈特所提出的協和民主可以通過四個特征來進行界定:首先是由多元社會各重要區塊的政治領導人組成大聯盟(grand coalition)政府。其二是相互否決或協同多數原則(mutual veto),這種設計是為了額外保障關鍵少數的利益。第三,是在政治代表、公職任命和公共財政配置方面,堅持比例性原則(proportionality),也就是運用“多議員選區-政黨公開名單-比例代表制”,即在政黨名單上,選民有權選擇候選人的當選順序,選舉結果最終根據選民投票的比例決定。第四,在每一區塊上實現高度的自治(segmental autonomy),尤其是在文化和教育事務上,由民族地方自身決定。而做到這一點的前提則在于,國家的行政區域規劃應當體現“同質性”原則,讓一個行政區域內的民族構成盡量單一化[2]。
利普哈特的協和民主思想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首次提出,21世紀之后,通過對全世界各大洲民主政體的詳盡考察,利普哈特又提出“共識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事實上,兩者都是主張分享權力的“非多數民主”模式,后者在前者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它們主張的特征也有一些重合之處。但是,協和民主主要是以社會的種族、民族分野以及與之相聯系的文化分野為前提的;而共識民主關注的焦點并不局限于民族與種族,還包括宗派、財富、階級、地域等各個方面的社會沖突和政治沖突,視野更加廣闊,而且適用于更多國家。第二,協和民主是一劑猛藥,它要求將所有重要的社會集團都納入到分享權力的過程中來;共識民主則要溫和一些,它提供了各種制度上的誘因,旨在通過這些誘因來促成廣泛的權力分享。第三,反映在制度設計上,共識民主贊成比例代表制和巨型聯合內閣,但不提倡少數派否決權和局部自治[3]。因此,這里選用協和民主作為緬甸民族問題的解決方案,更多看重的是協和民主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的策略性,能夠適應緬甸這種人口區塊之間存在深層分歧且社會對于民主統一性缺乏共識的國度。
緬甸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國家。根據緬甸官方的數據,緬甸的民族分布比較龐雜,其主體民族緬族主要生活在交通、文化相對發達的中部平原和南部沿海地區,而少數民族則各自聚居在山區,經濟落后,交通不便,農業生產力較低。緬甸各民族分布情況可見圖1。

圖1 緬甸族群分布情況一覽
資料來源:The Data Team, “An unfinished peace”,the economist.com,Oct.15th,2015,http://www.economist.com/blogs/graphicdetail/2015/06/myanmar-graphics
同時由于歷史發展中遺留下來的各種原因,緬甸各少數民族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也與緬族存在較深隔閡,加上政府一直沒有特殊傾斜的民族政策,導致單一政策平等的表相后隱藏的是發展結果巨大的不平等,最終引發20世紀60年代以后緬甸國內民族矛盾的激化,從而導致少數民族反政府武裝力量的產生。緬甸的民族紛爭以及國家認同不強,重塑了緬甸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同時也對緬甸的改革進程產生深遠的影響。但在理論分析上,多民族并不必然意味著民族矛盾。如果民族構成過于分裂,每一個民族都無法占有絕對優勢,反而會促進民族之間的民主合作[4]。因此,盡管在多民族國家中,人口越多,政治就越加復雜,就民主問題達成一致意見也越困難,但這并不意味著在多民族國家中民主就不可能實現,這只是意味著必須對民主的規范、行為和制度等進行認真的設計,從制度上為民族主義和民主化進程搭建起通暢的渠道,這樣才能解決緬甸的族群紛爭和民主內在不兼容的問題。
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在于,協和民主如何能在緬甸這類多民族國家中使得民主成為可能?我們的假設是,在多民族的背景之下,協和民主的政策更具開放性,能認可平等的公民權;在政治議程當中,比例代表制可以更好地代表在空間上分散的少數民族,通過協和民主建立起一整套匹配的政策和協商方式,最終建立一種包容性政治制度。這種制度強調各民族群眾具有平等的政治權利,他們能夠參與政治活動,選舉領導人,任何人都有成為領導人或政策制定者的機會,不會因其民族出身而得到不公正的待遇。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golu)和羅賓遜(James Robinson)認為,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含兩個不可或缺的方面: 民主的多元化和有力的中央集權[5]。首先,包容性政治制度下政治權力分散在社會中,包括民族的區塊。其次,包容性政治制度的關鍵在于也擁有有力的中央集權,這樣國家才可以順利推行法令,保護產權,進行公共投資以鼓勵經濟活動。對于緬甸如今的經濟狀況而言,協和民主的特性可以促進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建立,而正是這一點將使緬甸民主轉型的進程成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徑和手段。
二協和民主與緬甸的民族國家建設
緬甸少數民族在獨立時作為自愿加入、政治平等的群體簽署了《彬龍協議》,希望建立一個聯邦并實現各邦自治。1947年的緬甸憲法甚至有保障“每個邦在獨立后十年都有脫離聯邦的權力”的條款,然而在其后的半個多世紀,緬甸陷入無休止的內亂和紛爭當中,事實上演化成了半聯邦制的國家,甚至具有單一制國家的內涵,被一個叫做緬族的單一民族控制了聯邦所有的國家權力[6]。一方面,政府積極要求將國家建設成為“一種語言、一個民族、一種文化”的單一民族國家,在推動民族國家建構的過程中,采取的是相對保守的族群政策。另一方面,緬甸內部眾多的小族群則一直頑強抵制中央政府的“國家建構”政策。
對于獨立后的緬甸而言,“民族建構”與“國家建構”的任務都亟待展開。“民族—國家”概念暗示了民族建構和國家建構常常是孿生的過程,但是它并不代表民族建構一定和國家建構相伴相生。世界上存在有民族而無國家的案例,如巴勒斯坦和庫爾德人,也存在有國家缺乏民族的案例,比如伊拉克和阿富汗復雜的案例。緬甸剛好是民族建構和國家建構都進展緩慢的一個國度[7]。
緬甸的統治者(從吳努到丹瑞)都希望借由民族建構來建立一個同質化的國家,進而完成國家建構。比如1961年10月吳努將佛教定為國教,選擇宗教同化的方案,而奈溫則將緬甸語定為唯一的官方語言,以統一語言文字的政策來創制單一制國家。這樣的“國家建構”事實上導致少數民族被強迫同化,除了接受這一點,各少數民族只能付諸武裝斗爭,不斷強化本民族的民族認同感和歸屬感。
吳努到奈溫時期的政策及其效果表明,緬甸作為多民族國家,其內部的民族矛盾和沖突是國家建構的嚴重阻礙。對于緬甸的少數族群來說,他們首先將自己看作是族群的成員,其后才是作為緬甸國家的公民。而在新軍人政府上臺后,緬甸少數族群作為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仍然得不到實現,因此少數民族地方武裝的抗爭從來沒有真正停歇過。
當我們系統地來觀察緬甸國家建構和民族建構的策略以及將協和民主運用到其間的可能性時,可采取林茨(Juan Linz)和斯泰潘(Alfred Stepan)的類型學分析框架來研究(如表1)。

表1 多民族政治體系中的國家、民族和民主建構戰略的類型
資料來源:〈美〉胡安·J.林茨、阿爾弗萊德·斯泰潘著,孫龍等譯《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南歐、南美和后共產主義歐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8頁。
根據國家建構戰略和民族建構戰略這兩個維度,可以將一個國家的民主—民族策略劃分成上述四個類型。這種劃分不是固定和精確的,隨著一個國家觀念和政策上的變化,在這四個象限會呈現運動的趨勢,如圖2所示。
在類型I當中,政治精英對民族問題采取強烈的排斥態度,把非主導民族的少數族群排斥在政治體系之外,并且有可能通過一些歧視性的政策來隔離少數族群,通過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格逼迫其遷回原居住地。在類型II中,政治精英明確了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區分,因此對公民資格采取排除性的戰略,少數民族在經濟生活中有立足之地,但國家政策只是給予非主導民族之外的人民以一定的公民權利,而不是政治權利。緬甸獨立后實行的“一個民族”可以看作是這樣的一種類型。民主轉型前的軍政府既沒有在各民族之間培養出共同的國族認同感,也沒有將少數民族同化和融合,這成為緬甸建立民主政府的一個巨大障礙。第III種類型是在公民資格問題中采取包容性的策略,結合民族身份與公民身份,也就說,仍然存在少數民族與主導民族之間的區分,只有當少數民族融入到主流文化當中,才被允許進行政治性的參與。政治精英設計出很多同化的政策,但對于一些因歷史文化、宗教等因素不能或者是不愿意被主導民族同化的人來說,在政治層面他們相當于事實上的二等公民,這樣造就了一個多樣的社會,但并非是一個多元包容型的社會。在最后第IV種類型中,無論是對于國內主導民族還是少數民族而言,公民資格都是完全等同的。人民當中所有常住居民都被視為政治實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政治精英給予少數族群以不同程度的政策照顧,這種政策傾斜體現在政黨組建、宗教寬容和文化教育等多個方面,這種社會可以被稱為完全多元化的具有包容性的社會,也是協和民主期待建立的社會。

圖2 民族—國家建構戰略的類型變化
緬甸從軍政府的獨裁統治向民主政治緩慢過渡,目前我們從緬甸憲法中觀察到的大約是從類型II向類型III的嘗試,如憲法中規定少數族群也有表達、集會和組織的自由;少數民族可以組織政黨(這一條其實在1990年大選中就得以體現);為少數族群在民族院中提供一定的席位;少數民族群眾可以通過和平手段來分享政治權利。因此,少數民族擁有進入政治體系的資格,文官政府也嘗試通過同化來促成民族國家的構建。這種政策能否發揮理想的效果,不僅取決于政治精英建設的目標,也取決于少數民族的成員是否準備好放棄對本民族認同的堅持。如果處理不好的話,可能會由類型II退回到類型I的場景,即國家同化戰略淪為失敗,而少數民族在政治轉型中成為被排斥的對象。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兩個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其一是緬甸的少數群體(包括少數民族和少數宗教團體)的利益需求及不滿情緒能不能得到公開的表達。少數民族得到議席的保障并不必然促使少數群體中的個體得到特定的好處,因為在多數民主當中,少數群體獲得的利益可能較小。而少數民族自身的愿望往往是要求實現類型IV中的模式,即得到直接分享權力的機會。其二,在國家層面,如果少數群體分成派系,擁有一定的代表資格,那么在選舉和組建政府的過程中,多數群體就需要與少數群體結成明確的派系或是潛在的聯盟,政治精英也需要得到少數群體及其代表的支持,在這種條件下,少數群體能夠分享到利益最大化的政治權力。類型III的弊端在于由緬族主導的同化過程可能會導致其他民族產生挫敗感,進而變得激進,嚴重的話可能會導致暴力沖突的惡性循環,從而威脅到民主的穩定和國內秩序的和平。而按類型IV建立起來的政治體系則能夠孤立種族、文化和宗教少數群體中的極端分子(并不意味所有的極端民族沖突都可以完全避免)。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領導人大體上是依靠少數群體中的忠于國家的精英人士的支持,從而削弱極端分子對于整個政治社會的影響。如此一來,民主的理念也能得以鞏固,因為民主政體將一切暴力活動都定義成不可寬恕的罪行,無論是在多數群體還是在少數群體當中。所以,民族暴力沖突將會得到妥當的處理并最終走向消亡。
由此看來,協和民主的基本主張在民族—國家建設層面可以部分促進緬甸的民族政策向穩定的類型IV轉變,因為首先要建立的是一個包容各族人民的大聯盟,讓多元社會所有重要區塊的政治領導人在大聯盟中合作,進而治理國家。雖然大聯盟達成共識的效率一直倍受懷疑,但事實上在許多國家,在關鍵性的過渡時期,都是通過大聯盟平息黨派之間的情緒并加強共識,從而實現國家的統一與穩定。大聯盟的實現需要很多前提,溫和的態度和妥協的愿望是形成大聯盟的先決條件,對于軍政府非此即彼的同化性民族政策,緬甸上下必須形成妥協的愿望和精神。其次是賦予少數民族相互否決權,這也是保證大聯盟的附帶條件,只有這種否決權才能保證每個少數民族得到同等的政治保護。相互否決可以是一種非正式和不成文的彼此諒解,也可以是一種正式的憲法規則,連接了部分與整體的利益。一個民族過于頻繁地運用否決權事實上是不太可能的,為了提升自我和整體的利益,每個民族都會格外小心地使用這個權力。第三是在選舉中充分保證各族人民的代表性。在緬甸各族力量分布不均的形勢下,現行憲法中的比例代表制只是反映了各民族的力量對比,不能夠消除決策中緬族與少數民族的對抗,比如盡管全國各民族兄弟大聯盟(NBF)聲稱自己的成員要在選舉中獲得大約150個席位[8],但結果能否如意,充滿變數。因此憲法可以考慮給予緬甸境內民族黨派以超額的代表權,使得緬族不會在決策層面一家獨大,因而起到制約的效果。最后就是民族自治,在少數民族專屬的事務領域,由少數民族自己來統治,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財政按比例配置給各民族,少數民族地方的稅收也要考慮到地方的特色。緬甸的自然資源集中在礦石和森林上,而這些又聚集于少數民族地區,中央政府的經濟來源仰仗于此,因此必要的惠民措施也一定要施及此處。民族自治將強化一個多元社會的多元性質,為了保證國家不會四分五裂,緬甸的民主政府必須許諾給予少數民族更多的福利和更多的權力。
但是,針對緬甸的案例,實行協和民主也具有一定的困難。緬甸的人口構成中有68%是緬族,其后的兩大民族是撣族和克倫族,分別只占總人口的9%和7%[9]。這導致緬族在緬甸的政治局面中占據絕對優勢地位,但又不完全擁有絕對支配的統治力量,從而阻礙了大聯盟的形成。再者,緬甸的民族分野與政治、文化、經濟等社會分層高度重合,這導致經濟政治不平等和民族身份捆綁,社會其他方面的沖突都會輕易轉化為民族沖突,從而動員大規模的群眾參與進去。民族間的矛盾因區域性的經濟發展差異顯得更為巨大。緬甸各民族在地理上趨于集中,并沒有被水平的社會經濟分化橫切為“垂直”群聚,這樣一個結構也被霍洛維茨稱為“平行群體”[10]。因此少數民族彼此之間不愿意相互遷就,相互否決的機制可能會導致政治議程設定較為困難。最后一點就是緬甸落后的經濟發展水平對政治發展的阻礙(已有很多文獻論述了經濟水平與民主之間的關聯,政治常在第三世界里呈現衰敗和倒退的景象),“低度發展最大的諷刺在于,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越低,其內在的不平等反而越大。”[11]但是緬甸特殊的國情也有適合實現協和民主的特點,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在于緬甸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都比較集中,例如克倫族在克欽邦占大多數,華人主要聚居在果敢,符合高度區塊隔離的有利條件。如此一來,少數民族在地方具有一定權力優勢,可以在每一個區劃范圍內實現高度的自治。
三緬甸實行協和民主應注意的問題
利普哈特的協和民主提出之后影響了比較政治學的研究,同時也影響了一些國家的政體轉型和憲法設計,但是一些學者也“在借鑒國際學術界前沿研究的基礎上,立足于研究方法,從概念界定、研究設計、經驗證據與因果機制四個方面入手,對共識民主理論進行系統的檢討和反思。”[12]因此對處于政治轉型關鍵時期的緬甸,不加鑒別地將協和民主作為其憲政設計的模板可能會造成誤導,但是協和民主所倡導的一些基本要素在緬甸處理民族問題上是可取的。對于任何一個社會來說,政治轉型與民主化都是一場影響深遠的大變革,作為一種精英統治制度,協和民主的成功實施,必須依靠執政精英們的表現。這些精英既要對自己所代表的族群有足夠政治影響力,又要有善于妥協、積極合作的品質。具體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
1.現行的選舉制度要保證各民族地區之間代表性的平衡
賴利(Benjamin Reilly)在論文中提醒過,在民族沖突激烈的國家,選舉制度的設計應當得到人們的格外重視[13]。如果某一地區擁有明顯的多數,其地方精英勢力就可能試圖支配敵對的少數,而不是選擇與后者進行合作。比較權力的二元分化和極端的多元分裂可發現,適當的二元分化最能夠適應政治的穩定和博弈,而二元化社會的問題在于它會導致霸權或者不穩定的平衡。高度分化的社會由于參與協商群體數量增加,它們之間的合作也變得更加困難。只有適中的多元結構才能避免政治決策被詮釋為零和博弈。最合適的選舉制度在于每一個民族都能關注自己的所得,但同時也能考慮到整個決策的代價。選舉制度是復雜的憲政體系中的一個榫合,一旦出現差錯,就會使整個體系趨于崩潰[14]。
2.建立區塊化的多黨體系
緬甸2015年大選中涌現了一批基于民族地方利益的政黨,這種區塊政黨對于協和民主是有利因素,它們能夠充分當好對應區塊的政治代表,并具有與大聯盟競選領袖的可能性。關于政黨體系和民主的質量,各方都有論述。多黨制盡管有利于廣泛地凝聚利益,但很可能也會加深內部的分裂,且多黨制在決策制定和執行的效率方面也遠不如兩黨制。從緬甸大選的結果來看,民盟和鞏發黨作為緬甸政壇深具歷史淵源的兩大政黨,壟斷了大部分選票;雖然給予少數民族平等自由的選舉權,但少數民族勢單力薄,沒有聯合起來,在政治上未能形成第三股抗衡的力量。這樣純粹性的“執政—反對”模式,有利于建立責任清晰的政府。民盟贏得了2015年大選的勝利,即將組建的受立法多數支持的內閣應當既要考慮到民盟和鞏發黨的利益,也要兼顧各少數民族政黨的需求。
3.共建精英和解的傳統
協和民主的本質是一種精英民主,如果政治領袖們致力于聯合而不是對抗性決策,多元社會就可以享有穩定的民主政府。協和民主承認區域之間的差異,并且給予地方自治權,因此協和民主建立的前提就在于預先促成一個傳統,讓政治領袖采取溫和與合作的態度,達成精英的和解。在軍政府時期,由于政府對民族問題采取強硬的態度,導致民族間對立的情緒十分嚴重,但同時鎮壓的成本(來自國內外的壓力)過于高昂,于是軍政府開始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改革,釋放一系列妥協的信號,通過允許民主轉型的制度和政策來緩和階層及族群之間的矛盾,試圖滿足民眾的自主需求。
4.促進交叉認同,建立橫跨性忠誠
橫跨性忠誠(overarching loyalty)是協和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國家統一政權的穩固有關鍵性的影響。在緬甸這樣的多民族社會中,橫跨性忠誠意味著各個民族都能認同和忠誠于一個更大的實體,國族認同是緬甸現代化和政治轉型的一大目標。有學者早就關注到,在亞洲和歐洲的發展中國家,由于人口、族群之間的深層分歧和統一性共識的缺乏,政治發展有兩個維度的意向,其一是要實現國族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或國家建構(nation building),其二是要實現民主化[15],因而緬甸政治民主化的過程是深刻依賴其國族整合的。在可能的范圍內,緬甸的政治制度要能夠激發各族人民共同的政治忠誠。單一的民族主義助長了民族地方武裝的野心,并對整個國家的權威構成挑戰,緬甸的分離傾向必須得到緩和與消除,否則中央政府將失去對領土和人心的控制。緬甸的少數民族分布在國家版圖的邊緣部分,這又容易引起外部爭端,如果延續主體民族緬族帶有挑釁性的民族建構政策,疏遠少數民族,那么憑借地理位置的便利性,后者極易尋找鄰國的支持,這時發生沖突的可能性將大為增加,而“民族化國家—少數民族—境外祖國”三股勢力相博弈的場域一旦形成,民主化進程必將受到極大的傷害。民主的一大內涵是強調公民而非國民,政治精英應當發揮自己的力量,促進包含多樣和全面認同的國家觀念向合法化方向發展,而不是加強公民資格的排他性。緬甸的民主轉型要伴隨更開放的國家政策,從憲法層面到實際操作層面,讓平等的公民權利覆蓋到更廣闊的范圍,使得各族人民的利益都能得到民主政府的保護,這樣一來,民主鞏固的機會將會大大增加。具體來說,在政治選舉層面,緬族人民不能有過多代表(over-representation),各民族在政治法律上是平等的;在公民社會層面,學校和大眾媒介允許民族語言的使用,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措施;在法治層面,法律體系要考慮到地方的風俗和歷史習慣;在經濟社會層面,土地和資金分配在各民族之間也應該是公平的。綜上所述,建立各族的交叉認同要求在民主化進程中充分避免大緬族主義,設計出更多具有共識性的政策,建立包容性的政治制度。
2015年,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進入全面推進階段, “一帶一路”的深入實施與相關國家的國內政局發展密切相關。緬甸國內面臨民主政權的穩固、民族沖突、宗教矛盾等多重不利因素,因此,對緬甸國家建構及其政治風險進行評估應當成為當前中國國際問題研究的任務之一。目前,對于中國在緬甸的投資,其政治風險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民主化改革帶來國內政治穩定的問題。盡管現行的緬甸憲法對既有格局的穩定性做了一定的保護,但鑒于國內外民主勢力的發展,改革引起的常規風險仍然可能對緬甸的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產生負面的影響。二是緬甸的民族問題。緬甸的民族和宗教相互糾纏,一直是國家內部的不穩定因素,因此緬甸的民主化進程與民族問題息息相關。協和民主有一套包容性政治制度的設計,緬甸政府可以參照協和民主的一些理念,從制度層面解決民族沖突,建立穩固而有效的民主政府,實現民主轉型。
【注釋】
[1] 林夕:《緬軍和民族武裝組織半年交火200余次》,緬甸在線,2015年6月28日,http://v2.myanmarol.com/News/Article/71343
[2] 〈美〉阿倫·利普哈特著,劉偉譯《多元社會中的民主——一項比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頁。
[3] 同[2],譯者前言。
[4] Reilly, B.,“Democracy, ethnic fragmentation, and internal conflict: Confused theories, faulty data, and the ‘Crucial Case’ of Papua New Guinea”,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5,No.3,2001,pp.162-185.
[5] 范世濤:《包容性制度、汲取性制度和繁榮的可持續性》,《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3年第1期。
[6] 〈緬〉連·H.沙空著,喬實譯《緬甸民族武裝沖突的動力根源》,《國際資料信息》2012年第4期。
[7] Monique Skidmore & Trevor Wilson, “Perspectives on a Transitional Situation”, Nick Cheesman, Monique Skidmore & Trevor Wilson eds.,RulingMyanmar:FromCycloneNargistoNationalElectio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10,p.20.
[8] Moe Myint, “Ethnic bloc seeks powerbroker role in next parliament”,TheIrrawaddy, 22 July 2015.
[9] Network Myanmar, “The Union of Myanmar-Basic Data”, http://networkmyanmar.org/images/stories/PDF/stats
2009.pdf
[10] 關于這一說法可詳見Donald L. Horowitz,“Constitutional Design:Proposals versus Processes”, in Andrew Reynolds ed.,TheArchitectureofDemocracy:ConstitutionalDesign,ConflictManagementand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9-24.
[11] Pierre L.Van den Berghe, “Ethnicity: The African Experience”,InternationalSocialScienceJournal,Vol.23,No.4,1971,p.514.
[12] 包剛升:《共識民主理論有“共識”嗎——對利普哈特研究方法的學術批評》,《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4年第5期。
[13] Reilly, B.,“Democracy in Divided Societies”,ElectoralEngineeringforConflictManage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1,p.31.
[14] Reynolds, A.,“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in southern Africa”,JournalofDemocracy,Vol.6,No.2,1995,pp.86-99.
[15] Lucian W. Pye,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al Culture”,in Lenard Binder er al.,CrisesandSequencesinPolitical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117.
【責任編輯:吳宏娟】
The Construction of Inclusive Politics: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in Myanmar
Xiang Hao & Zhang Che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Keywords:Myanmar;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Multi-Ethnic State; Inclusive Politics; Overarching Loyalty
[中圖分類號]D733.7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6099(2016)01-0023-07
[作者簡介]項皓,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理論專業2013級碩士研究生,蘇州大學老撾—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張晨,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收稿日期]2015-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