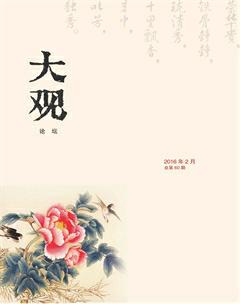塑霜操勁節
李霓
觀世間芳菲,賞四時風物,光風霽月,煙霞巒川,皆可攜來細細玩味。從來雅人有深致,在端起壺把盞品茗的同時,實在有必要領略一些關于其人其壺的敘述和詠嘆。那些平矜釋燥、怡情悅性的風骨與韻味,都記錄在一把小小的紫砂壺中。紫砂藝術的魅力莫過于此。紫砂是中華傳統陶瓷文化藝術中的一朵奇葩,先不論紫砂礦土的得天獨厚,那種古老的用雙手制作的技法技巧其過程就有著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獨特魅力。
喜歡竹子可以說是中華傳統士大夫群體的通病,崇尚君子,而竹是最能借代君子的雅物,無數歲月傳承下來,幾成文化階層的專利。紫砂壺之崛起源自于文人壺品的大量出現,正因為有了“文”的介入,紫砂才有了別的陶制品所沒有的魅力,所以紫砂創作以有文人氣息為美,紫砂壺的造型便常常以竹子入壺,正所謂重塑霜操勁節,君子氣息坦蕩,摶造捏塑皆簡括率意,煉十取一,透析出特有的疏朗和松靈,顯示出作者不俗的造型功力。修簧美竹高標逸韻,超軼凡塵,哪會比不上朝花綽約、紅醉綠酣?這樣的作品往往似蟬蛻于塵埃之外,只生生揉進了一抔紫泥中。人與草木之間的靈犀相通、色授魂與的深情默契,沛然不可御。從而造就了一種鮮活靈動的民間意趣,往往令紫砂壺別生情致。
但凡造物造形總有規律可循,像物總是從模仿開始,揣摩一件東西的神韻,表現在每一根線條的實踐之中,而每一次成功的表現都能夠不斷加深創作者對這一造型的認識,竹子在這江南水鄉乃常見之物,物態親切,如伴云生,所以在觀察它的時候,有時總會忽略掉一些本該注意的東西,文字和圖像可以無限的對竹子進行美化,并且省略到
所有不必要的細節,但紫砂塑竹卻并非如此,造物造形必有其規律,無法做到隨性所欲,而用紫砂陶土來造物造形,則又必須遵循紫砂材質的規律,這樣一來造型的局限性就此產生,而要將這種藝術性發揮到文字繪圖同樣的藝術效果,就需要紫砂創作者擁有上述兩者的更高的智慧了,這件紫砂作品“錦竹”壺便是如此了。
該壺選用了上等紫砂泥料,胎質細膩,表面的光澤柔和,色澤淡雅怡人,保持了紫砂一貫古色古香的本質。壺整體的造型參照紫砂經典器中的“三足圓腹”形態,不過鼎足之器通常作一光器,而這件作品則是在其基礎上拓展衍化的花器。壺身筒采用了經典的圓身鼓腹的形式,充分運用了線條柔和度的作品,壺形穩定。壺腹至壺底的轉折相當圓潤,這樣的塑造可以讓作品看起來更加圓潤敦實,壺底部的三足也在視覺上相當平穩。壺口壺蓋皆為通常的圓形,稱作束口,將壺身上下切割成兩個塊面,上下平行顯得非常規整,壺口棱線與壺蓋相互層疊,層次分明,穩定中顯出變化。
除此之外“錦竹”壺的變化便從其壺流、壺把、壺鈕的竹節造型開始,三者造型不同但兼容相顧,描繪了竹子多變而又統一的自然面貌,壺流短而豐實,分為兩節,圓形的壺嘴猶如竹節的枝杈,蜷曲的竹枝裝飾延伸出貼塑于壺身的扁平竹葉,延伸擴展有蔓延之感,此塑造偏于傳統,精雕細琢,無需多變;豐厚敦實的壺把節節生長狀若等分,節牙隱發,恰如其分的延續了竹子真實的一面;一截竹鈕卷曲彎拱,配合貼塑裝飾與壺蓋表面的竹葉,便猶如落在了竹林深處,自然寫意的同時亦兼顧了壺品的實用性與裝飾性,將立體的影像映照成腦海中平面的畫景,回味無窮。
該作品在塑造的過程中,著鐘于“畫”卻并不局限于畫,是一種傳統與新穎的結合,同時無論是整體還是局部的塑造都做到了精益求精,這種凝神于匠的制作風格實際上為作品整體的氣質提升很多,也正是由于這份專注,“錦竹”壺的壺體平衡做的非常巧妙,將三角形態的穩定感詮釋的淋漓精致,這是一種根據造型與裝飾的表現,新舊之風皆有。
綜上所述,一件優秀的壺品,引入文化的氣息,除了基礎要扎實之外,最重要的是關于其氣質的塑造,而展現一件作品的氣質的方式有很多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壺如其人,創作者的意志會潛移默化的滲入自身的作品,所以個人的修養即可視作藝術作品的修養,這一點亙古不變。
藝術有傳承即有斷絕,有守舊亦會有創新,不過藝術之所以為藝術,究其原因還是因為有一群為之沉迷付出的人,當代的紫砂藝術是一份職業,亦是一份責任,為了讓這個古老的行業綻放更多的光彩,紫砂藝人責無旁貸。在不斷的發展過程當中,有許多優秀的造型設計與制作技藝需要我們去研究、總結、借鑒,同時,注重尋求其中美的規律,真正地深入了解和學習傳統,掌握其精髓,才能更好地繼承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