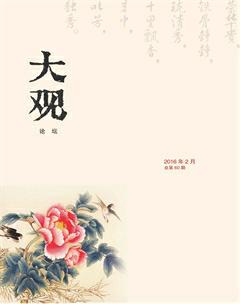成鷲和尚的嶺南遺民僧特點(diǎn)研究
阮宏
摘要:嶺南遺民僧是明末清初嶺南地區(qū)的一個(gè)特殊的群體,對(duì)清代嶺南社會(huì)以及區(qū)域文化有著極之深遠(yuǎn)的影響,并延續(xù)至今。本文嘗試以成鷲和尚的生平為例子來分析南遺民僧特點(diǎn),探求其背后深層的社會(huì)歷史原因。
關(guān)鍵詞:嶺南;遺民僧;特點(diǎn)研究;成鷲
明清鼎革之際,嶺南地區(qū)作為南明政權(quán)與清王朝對(duì)抗的要地區(qū),也是三藩之亂的主要地之一,社會(huì)動(dòng)蕩不安,社各階層面臨著生存與死亡、隱逸與出仕、抵抗與投降、舊主與主的抉擇;或成忠烈或作遺民 或作貳臣,政治上凸顯了多元態(tài)。遺民逃禪成為遺民僧正是政治生態(tài)多元化的反映 本文嘗試以成鷲和尚為例,分析清初嶺南遺民僧的特點(diǎn)。
一、成鷲和尚其人
在清初嶺南佛門中,成鷲的生活道路具有最典型的遺民僧的特征。清初嶺南的著名高僧成鷲,字跡刪。俗名方顓愷,字麟趾。生于明崇禎十年三月二十一日,廣州府番禺縣韋涌鄉(xiāng)人。成鷲天性聰慧,卓犖不凡,少年時(shí)即有神童之號(hào)。十三歲時(shí),曾應(yīng)南明永歷朝童子科試,被錄為博士弟子員。清征服嶺南后盡棄制科業(yè),以硯耕為生,在廣州及周邊地區(qū)設(shè)席課士。成鷲早年以“晚世之真儒”自任,曾為淳民,氣化風(fēng)俗而孜孜以求。但四十一歲那年,康熙十六年時(shí)卻忽然放棄持奉多年的儒家價(jià)值觀而遁身佛門。出家后曾先后在西寧(今云浮郁南)翠林僧舍、羅浮山石洞禪院、瓊州府(今海南)會(huì)同縣靈泉寺、佛山仁壽寺、香山(今中山)東林庵、仁化丹霞山別傳寺和肇慶鼎湖山慶云寺禪修。康熙四十年,入主座落在廣州珠江南岸的大通煙雨寶光古寺。康熙四十七年后,應(yīng)合山大眾之請(qǐng)入鼎湖主法,成為慶云寺 第七代方丈。六年后退席,還居大通寺。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圓寂。
二、嶺南遺民僧的特點(diǎn)
(一)儒釋合流,佛門中儒學(xué)色彩濃厚
嶺南遺民僧在出家前,大多數(shù)都是明末的士大夫階層,正統(tǒng)的儒學(xué)思想教育對(duì)其有著深遠(yuǎn)而又主導(dǎo)性的影響。他們文化水平高,或擅長詩文,或在書畫方面有杰出貢獻(xiàn),他們往往以文學(xué)的形式,這種往往是儒家士大夫最喜歡的形式來表達(dá)他們的儒釋合流的思想以及他們對(duì)前朝的情懷。
成鷲學(xué)問博洽,才氣縱橫。清代文學(xué)家沈德潛則說成鷲“所著述皆古歌詩雜文,無語錄偈頌等項(xiàng),本朝僧人鮮出其右者。”[1]其一生著述頗豐,作品有《楞嚴(yán)直說》、《紀(jì)夢(mèng)編年》、《金剛經(jīng)直說》、《老子直說》或作《道德經(jīng)直說》、《注莊子內(nèi)篇》、《鹿湖草》、《詩通》、《不了吟》、《自聽編》、《鼎湖山志》、《漁樵問答》及《咸陟堂集》等。在嶺南佛教史上和文學(xué)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成鷲還“擅長草書,嘗見其‘廉頑立懦四大字,字徑三四寸,筆奔放,頗似茅筆書。其所書壽陳喬瞻(子壯之弟)詩軸尤奇,興酣下筆,滿紙狂草,志在新奇無定則,古瘦漓驪半無墨,大有顛素遺風(fēng)焉”。[2]
作為遺民、和尚和詩人的統(tǒng)一體,成鷲的詩藝是有獨(dú)特的詩論為指導(dǎo)的。成鷲的詩文創(chuàng)作,在清代詩壇上得到高度評(píng)價(jià):“快吐胸臆,不作禪語。無雕琢摹仿之習(xí),仍是經(jīng)生面目。”[3]其理論體系,包括“詩品”說和“詩通”說。第一,他為詩立三品,認(rèn)為將詩分為貴本色、貴出格、貴超方三個(gè)層次。他追求的最高境界,并不限于詩禪合一,而是要求自我超越,創(chuàng)造出一種無風(fēng)雅氣又無煙霞?xì)獾幕顫姖姷纳鷼狻5诙麖?qiáng)調(diào)詩人應(yīng)心與天通:“天地之故,無不通也,無不詩也。我操其道而旁通之,可風(fēng)、可雅、可頌、可騷、可賦、可律,暢其道于四肢百骸,無不可者。否則強(qiáng)之使通,如倏與忽,日鑿混沌之竅,七日而混沌死,又何風(fēng)雅騷賦詩律之足云!”[4]可知,他在詩歌創(chuàng)作實(shí)踐中是堅(jiān)持主體與客體、精神與自然一致的。這與清初士大夫間提倡的“經(jīng)世致用”思想一致,強(qiáng)調(diào)學(xué)問的實(shí)用性,證明成鷲和尚在詩文創(chuàng)作方面帶有強(qiáng)烈的儒學(xué)色彩。
(二)僧服儒心,希望恢復(fù)漢人統(tǒng)治
嶺南遺民僧他們僧服儒心,在清初出家的遺民中,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徹底幻滅,真正看破紅塵;二是不得已而為之,宗教只不過是個(gè)保護(hù)傘而已 嶺南遺民逃禪者中后者占大多數(shù),他們都曾對(duì)南明政權(quán)給予了極大的期望,故逃禪前多入仕南明政權(quán),或?yàn)樗鲋\劃策,或直接起兵抗清,皆為恢復(fù)明朝,他們寧可戰(zhàn)死沙場(chǎng),馬革裹尸,也不愿作為功名利祿而變節(jié)投降之徒。
成鷲出家的原因就很能說明這個(gè)特點(diǎn),成鷲提到自己與佛門有夙緣是因?yàn)槠淠冈谏跋υ鴫?mèng)見老僧入室,又說其母一生崇信三寶,敬佛態(tài)度對(duì)自己有影響。但這些顯然并不構(gòu)成其離俗的決定因素,否則他早就出家了。而不至于拖到四十一歲,仔細(xì)析讀《紀(jì)夢(mèng)編年》會(huì)獲得某些信息。“是時(shí),丁巳歲五月五日也,余年四十有一矣。聞變而起,仰天大笑曰:‘久矣!夫吾之見累于發(fā)膚也。左手握發(fā),右持并剪,大聲疾呼曰:‘黃面老子從今而后還我本來面目,見先人于西方極樂之世矣。”[5]“聞變而起”四字透露了成鷲的出家與當(dāng)時(shí)的政局有密切關(guān)系,成鷲所言之 變是指“三藩之亂”被清廷平定。三藩之亂在性質(zhì)上本是地方割據(jù)勢(shì)力與中央王朝勢(shì)力之間的利益爭斗,但是由于吳三桂是打著“興明討虜”的旗號(hào)來與清廷相對(duì)抗的。因此當(dāng)時(shí)有不少人產(chǎn)生了錯(cuò)覺,以為大明的天下恢復(fù)可期。當(dāng)時(shí)大名鼎鼎的逃禪又還俗的屈大均就跑到吳三桂的隊(duì)伍去任監(jiān)軍,便是受了這種錯(cuò)覺的支配。作為一名曾參加過南明科舉的漢族知識(shí)分子,成鷲顯然曾對(duì)三藩的前途抱有過期待,然而讓他感到失望的是經(jīng)過雙方的較量,獲勝的一方卻是清廷。“滇黔之炎炎者,將見撲滅;閩廣之滔滔者,漸覩安瀾;冠冕之峨峨者,又不免于裂冠毀冕,退修初服矣!”[6]這個(gè)結(jié)果給成鷲潑了一盆冷水并最終促成了他的離俗出家,“聞變而起”等語清楚地表明他是因?qū)φ维F(xiàn)實(shí)失望而出家的。
作為一名漢族知識(shí)分子,他在內(nèi)心中對(duì)以異族入主中國的滿清統(tǒng)治者是持排斥態(tài)度的,對(duì)明朝的天下是懷有留戀之情的,他還是希望恢復(fù)明朝的統(tǒng)治。他在《紀(jì)夢(mèng)編年》中真切地反映了他當(dāng)時(shí)的政治立場(chǎng),載“(成鷲)年十有五,歲在辛卯,嶺南底定。文宗李名颋,馳檄遠(yuǎn)近,歲例校士,士子一名不到,以叛逆罪罪之。永謝場(chǎng)屋,先君既有命矣。至是公令嚴(yán)督,自憑血?dú)庵拢囊灾倚⒅闳徊桓啊!盵7]這分明是欲以身家性命來與新朝對(duì)抗 如果不是當(dāng)時(shí)未赴考的士子太多 誅不勝誅 成鷲很有可能要丟腦袋 在《咸陟堂集》的某些文字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他對(duì)奮起抗擊清軍征服的人士所懷有的同情和敬意。他的《仙城寒食歌四章》的第三首所抒發(fā)的便是對(duì)南明隆武帝的哀悼之情。成鷲還公開表彰陳邦彥英勇抗清、矢志盡節(jié)的精神。他還高度評(píng)價(jià)了屈大均《成仁錄》所載守衛(wèi)廣州城的抗清志士為國死節(jié)的義舉。同樣,他為今釋作《舵石翁傳》亦是基于同樣的立場(chǎng)。
還有一點(diǎn)值得注意的是,成鷲和尚極有可能與當(dāng)時(shí)的抗清勢(shì)力有密切聯(lián)系。康熙年間任廣東高明知縣的鈕琇,曾記述過一則與成鷲有關(guān)的逸聞:“康熙丙子(三十五年,1696),粵僧方趾麟親訪祖述,具得其詳。”所“詳”何事?就是這位名為“祖述”的海中介公之孫在崇禎壬午(十五年,1642年)造舶泛海的奇遇。雖有濃厚神話色彩,但仍透露出在海外神霄殿里“玉音宣問南方民事、北方兵象”的真相。所謂“神霄殿”是子虛烏有的,但“玉音宣問”的內(nèi)容涉及明清之際的政局,則顯而易見。祖述這位神秘人物,海商而兼海客,可能肩負(fù)特殊使命。聯(lián)系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成鷲的瓊州之行,他作為身在佛門的遺民,確實(shí)蹤跡突兀,情系海南,似乎參與過某種通海的密謀。康熙三十六年(1697),成鷲住澳門普濟(jì)禪院。但成鷲對(duì)此事輕描淡寫,未必就是無足輕重。其實(shí),從他在普濟(jì)禪院所寫的詩,不難覺察當(dāng)年他的復(fù)雜心境。如《寓普濟(jì)禪院寄東林諸子詩》云:
但得安居便死心,寫將人物報(bào)東林。
蕃童久住諳華語,嬰母初來學(xué)鴂音。
兩岸山光涵海鏡,六時(shí)鐘韻雜風(fēng)琴。
只愁關(guān)禁年年密,未得閑身縱步吟。[8]
“東林”是廣州的詩社。他用詩歌給社友傳達(dá)信息,反映了自己在彼時(shí)彼地的精神狀態(tài)。名為“死心”,實(shí)想“縱步”,成鷲盡管在禪院安居,決不是心如古井的。至于那首《英雞黎(英吉利)畫詩》,詞意就更明顯了:
尺幅云林幻也真,無端聞見一翻新。
丹青不是支那筆,花木還同震旦春。
弱水東流終到海,越裳南去即通津。
年來頗有居夷愿,莫怪披圖數(shù)問人。[9]
成鷲的“居夷愿”有什么具體意圖,不得而知,僅僅這個(gè)念頭的萌發(fā)和“披圖數(shù)問人”的舉動(dòng),就說明他去國之志決非一時(shí)即興的狂想了。
(三)市井性強(qiáng),有明顯的嶺南地域特色
嶺南遺民僧仍保留很明顯的市井性。世俗性可以說是嶺南佛教的一大地域性特點(diǎn),南方文化強(qiáng)調(diào)個(gè)性的發(fā)展,而五嶺把嶺南與中原之地分隔,造成了嶺南相對(duì)于中原的封閉。因而誕生了市井僧這種異于其他地區(qū)佛教的群體,可以說市井僧是嶺南經(jīng)濟(jì)文化發(fā)展不平衡的產(chǎn)物。他們貧富懸殊,各行其道,不受佛門清規(guī)的制約,經(jīng)商娶妻,僧其名而俗其實(shí)。在明清易代之際,這些遺民逃禪者雖然不得已走上原本不愿意的道路,遁入嶺南佛門,但其中他們都保留了很強(qiáng)烈的市井性,甚至是保留了很多佛家仍為是惡習(xí)的市井行為。如當(dāng)時(shí)的嶺南高僧澹歸法師曾不甘寂寞,給平南王尚可喜歌功頌德,獲得大量財(cái)物;同時(shí)期定居在嶺南的江南名僧大汕和尚,生性風(fēng)流,還喜歡畫春宮圖并送給友人,甚至以為好色惹上官司。
成鷲的世俗性表現(xiàn)在他從小就好任俠、愛抱打不平的性格上。《紀(jì)夢(mèng)編年》記載成鷲“年僅七歲,膂力過人,舉重負(fù)汲,能倍壯夫之任,群兒弗若之也。俎豆嬉戲,奉為牛耳。長時(shí)明祚式微,盜賊蜂起,里巷皆兵。予率群兒效之,竹馬楮旗,斬木揭竿,學(xué)布陣于堂下。已而塵飯涂羹,犒師振旅,群兒麾退”。而且其隨著年齡的增大,其好爭長短的性格愈發(fā)明顯。“夙習(xí)尚存,往往見獵心動(dòng),日與鄉(xiāng)里惡少交游,舉重扛鼎,運(yùn)槊劍,橫行市井,莫敢誰何。幸而廉恥尚存,殺盜淫妄未嘗破犯耳。出遇不平,奮臂而起,鋤強(qiáng)扶弱,不避權(quán)貴,敬賢疾惡,不擇親疏,慨然以任俠自許,郭解、荊卿無多讓也。倒行逆施不可盡述。”[10]盡管隨著時(shí)局的變化、家境的衰落以及父輩的強(qiáng)烈反對(duì),成鷲兇悍之性,為饑渴所撻,漸次消磨。開始擯棄這些舞刀弄槍的習(xí)慣。但成鷲還是習(xí)氣沒改,幾年后“居無何,鄉(xiāng)有大會(huì),角力睹勝……出而觀之,見獵心動(dòng),果如郭子之言,攘臂而起,擎巨鐘若挈瓶然,眾皆驚以為神。自是日與市人狎習(xí),平生所恃以見長者不覺畢露,學(xué)業(yè)漸荒矣”。[11]成鷲又曾經(jīng)遇到一奇人,“言少時(shí)曾得是書于異人,潛心久矣,未窺其奧。今所授者,方諸前書。互相徑庭,茫然不知所擇。”但成鷲仍“聞命憮然而退,歸館數(shù)日,終不能忘情。”[12]
成鷲在出家后,雖然其時(shí)已經(jīng)是四十多歲的中年人,但爭強(qiáng)好勝的習(xí)性仍沒見改變。這可以從當(dāng)時(shí)的兩位高僧對(duì)他的評(píng)價(jià)中可以得知,成鷲四十四歲時(shí)到西寧僧海跟高僧湛慈學(xué)習(xí)禪學(xué),湛慈對(duì)其的評(píng)價(jià)是“子見地高遠(yuǎn),惟習(xí)氣未凈耳”。而隨后他回華林寺跟隨他的恩師石洞和尚,但石洞和尚卻對(duì)他說:“子性稟孤高,不能容物,出則恐為眾的,只可住山,不可為人。”[13]讓他趕快回羅浮山修禪。五十多歲時(shí),與其他僧人相處時(shí)仍是十分不合群,以致自己辭而離開。晚年但任鼎湖山慶云寺住持時(shí),對(duì)于寺內(nèi)僧人散漫、不重視佛寺的行為大為不滿,并對(duì)此嚴(yán)加整治,讓慶云寺煥然一新,讓禪宗有了有了新的發(fā)展。
三、結(jié)語
成鷲和尚作為嶺南遺民僧的典型代表,體現(xiàn)出遺民僧的各種特點(diǎn)以及其鮮明的歷史社會(huì)特色,為我們研究遺民僧這一獨(dú)特的群體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材料,同時(shí)成鷲和尚的相關(guān)史料仍有很大一部分仍未進(jìn)行深入細(xì)致的研究和利用,所以關(guān)于成鷲和尚這一極具傳奇的嶺南高僧的研究希望能為以后這方面的學(xué)者提供一個(gè)有價(jià)值的突破口。
【參考文獻(xiàn)】
[1][3][4]沈德潛 清詩別裁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5.
[2]李公明.廣東美術(shù)史[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
[5]蔡鴻生.清初嶺南佛門事略[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6][7][10][11][12][13]釋成鷲.紀(jì)夢(mèng)編年[M].清同治二年.1863年嶺南遺書本
[8][9]釋成鷲 咸陟堂集[M].清道光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