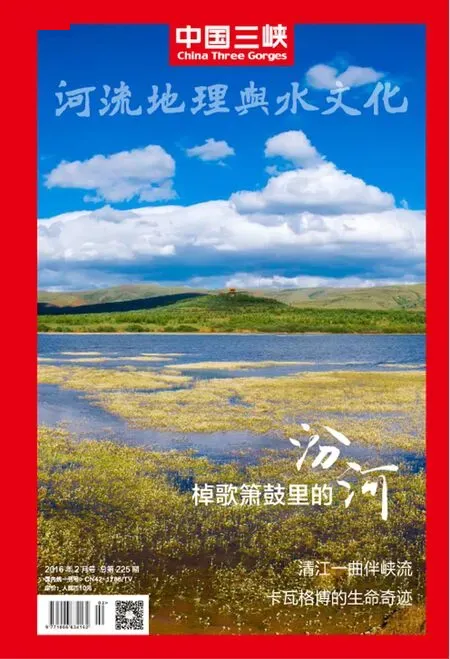淌過歲月的汾河記憶
文/丹菲 編輯/吳冠宇
?
淌過歲月的汾河記憶
文/丹菲編輯/吳冠宇
最早淌過我兒時記憶的汾河,一是它的支流——瀟河,它維護了我童年時對一條河流的鮮活記憶,非常幸運地沒有被現代歲月無情地吞噬;一是與河相伴隨著的民間風俗娛樂——背鐵棍,它從遙遠的時間里來,讓清貧的生活鮮活快樂。

冰凍汾河。 攝影/王牧
我忘了為什么過河,和哪一位家人,去做什么,是出發還是回來,統統記不清了。但它至少證明了在我童年時,流過我們村北與洛陽村南的瀟河上還有擺渡,證明那時的河流有多寬廣深刻。
在我的個人史中,汾河最早是以它的支流瀟河流淌的。
瀟河,是汾河的第二大支流,名稱由“小河”的諧音而來。30多年后,當我回到童年時的老屋,我驚訝地發現它還在,靜悄悄地流過村北的水泥大橋后,匯入汾河。它維護了我童年時對一條河流的鮮活記憶,非常幸運地沒有被現代歲月無情地吞噬。
我出生于太原市最南端的一個大村莊——王吳,14歲以前,一直生活在此。水,從來都是我玩耍的一個重要伙伴。從我家的院子里往南望去,便是一大片水塘,那是成年累月的雨水積攢下來的。水中有兩個土包,像小島似的,是生產隊的舊磚窯,因時常被水淹沒,早被遺棄了。在水位低的時候,便出現一條隱約的細細的土路通往小島,我們這些勇敢的孩子,挽起褲腿,小心翼翼地沿著土路往前走,但最后總是被越來越深的水阻止,那個要上島探秘的夢想從未實現過。
這一大片的水對于我的童年來說就是一個樂園。夏天撈蝌蚪,捉青蛙,都是在水邊進行的。雨后,我拿了一只臉盆、一只柳編笊籬,去水邊撈蝌蚪。黑黑的、圓嘟嘟的蝌蚪很快就被我撈了小半盆,倒在院子里,喂雞吃。現在想起來,真是殘忍。但在那時,好像蝌蚪是無限的,是水書的小逗號,沒完沒了。可以證明小小年紀的我偶爾撈起的蝌蚪,對水的生態并沒產生任何副作用的是,夜晚枕邊此起彼伏的蛙聲。尤其在雨天里,鋪天蓋地的蛙聲如同交響樂,成為我奢侈的催眠曲。
捉青蛙,我只有一次,是跟幾個鄰居家小男孩一起的。他們在水邊挖了洞,將青蛙一只又一只捉來放進去,然后故意將水洞的頂端蓋住,聽它們在里邊呱呱叫。我弄得渾身是泥水,玩得不亦樂乎。那些被關起來的青蛙,我惦記了許久。
大片的水也有給村人帶來悲傷的時候,幾乎每年它都會吞沒一個孩子的生命。即便存在這樣一個可怕的魔咒,夏天來臨時,總有愛游泳的男孩子們躲過大人的叮嚀,脫光了,跳入水中。村里邊淘氣的男孩都自學會了游泳。
村莊從不缺水,除了種植高粱、小麥、谷子,還種植水稻。水的概念不斷地出現在我的童年記憶里。每每雨多了,雨大了,我就會聽到大人們說,瀟河的橋又塌了。
瀟河橋是我們村往北邊任何一個地方的必經之地。那個年月,架在我們村和洛陽村之間的瀟河橋一直是毛橋,是人們用一些滾木、莊稼秸桿、泥土搭建的。這樣的橋不但供行人和自行車通過,還供馬車、拖拉機通過,所以可想而知,連續的大雨之后,橋就被損壞或者倒塌了。修好后,又塌了,再修。整個夏天,我能聽到好幾次這樣的橋梁事故。但這對于村子里人們的生活來說,根本不起什么波瀾,也沒有聽到因橋塌而人畜受傷的事,只是人們需要繞很遠的路才能到達目的地。
我是很少外出的,所以那座毛橋的健康與否幾乎對我沒什么影響。不過,有兩個對瀟河和毛橋的記憶卻是格外清晰的。
說不清那是幾歲,我和一群人站在一艘古老的大木船上。船是那種灰白的老木頭,速度幾乎可以忽略。我忘了為什么過河,和哪一位家人,去做什么,是出發還是回來,統統記不清了。但它至少證明了在我童年時,流過我們村北與洛陽村南的瀟河上還有擺渡,證明那時的河流有多寬廣深刻。
另一個記憶是在這之后了,我至少是一個五六年級的小學生。一次,學校宣傳隊在晚上到公社演出。運送我們去的是大隊的拖拉機。演出場景幾乎沒什么記憶,我只記得回來時,有人擔心瀟河橋會不會塌。因為我們所有人都站著擠在車兜里,毛橋是否承載得了一輛裝滿了人的拖拉機,是許多大人們要考慮的。而對于我,卻只有隨大流的簡單,我甚至忘了那輛超載的拖拉機是怎樣顫顫微微地在黑燈瞎火中通過一座毛橋的。
不管一座毛橋多么的落后貧窮,橋下的河流是富饒豐沛的。
瀟河在洛陽村南匯入汾河。就在我寫這篇文章時,特意去了一趟老家。橋早已不是兒時的毛橋了,許多年前就已修了寬闊堅固的水泥大橋。但是瀟河幾年再見,水質明顯不如從前,這是唯一讓我感到遺憾的。我的記憶仍然停留在幾年前回老家時,突發奇想去看童年的河流,沒想到它還是那么歡快健康地從大橋下流過,周邊長著高高的蘆葦,有零星的野花開著。我想去瀟河入汾河的地段看看,但三表姐說,那邊沒有路,車開不過去,需步行去。也就幾百米遠吧,一些莊稼地擋著。但我最終還是放棄了步行去的念頭。
小時候沒少到鄰村清徐龍家營看正月鬧紅火。我們擠在熱鬧的人群里,仰頭望鐵棍上高高立著的濃妝艷抹的小女孩,心里羨慕極了:“要是也讓我站在上面多好啊!”這是那個年代所有小伙伴們的夢想。
水和河流貫穿一個人的記憶,與之相伴的民間風俗娛樂則讓人生鮮活快樂。汾河邊有許多古老的民俗表演至今依然活躍在街頭。“南莊的火,太谷的燈,徐溝的鐵棍愛煞人 。”這是一句流傳在山西中部的民謠,說的是山西傳統鬧紅火項目,其中說到了徐溝。徐溝現在是太原清徐縣的一個文化特色鄉,先后被山西省文化廳和國家文化部命名為山西民間藝術之鄉和中國民間藝術之鄉。徐溝背鐵棍這一藝術形式于2008年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清徐縣,古稱梗陽,始建于春秋,隋開皇十六年 (596年) 置清源縣。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于縣之東境置徐溝縣。1952年7月,清源、徐溝兩縣合并,取兩縣縣名首字,稱為清徐縣。其背棍、鐵棍的淵源,根據民間傳說、民間故事、廟宇壁畫等考查,可推至明嘉靖三十九年(1561年)。這一年,徐溝境內發生嚴重旱災,老百百以“抬閣”的形式,即抬著一座移動的小小廟宇,游神祈雨。之后,每有旱象,百百即抬神祈雨,漸漸地,有人將這種祭神形式改制為《鳳凰拉車龍打傘》的神閣,并將侍神的童男童女由赤腳大漢扛在肩上顛擺過市,以示虔敬,稱之“走閣”。抬閣和走閣的祭神形式就是背棍、鐵棍的雛形。再后來,內容與形式都有改革,單純的祭神儀式消失了,更多地成為一種融合傳統戲曲、神話故事為一體的民間文藝活動。名稱也改為背棍、鐵棍。400余年來,久演不衰。
所謂背棍,即一個大漢在肩背部綁一只特制的鐵架子,鐵架子上再綁上一個或兩個兒童。通過寬大飄逸的古裝衣服遮掩和巧妙的機關銜接,使外表看起來流暢、自然和優美。觀眾永遠看到的是一個大漢單手托著某個戲曲人物行走自如,而被托舉的孩子最大的也就七八歲,最小的只有兩歲,他們隨著底下大漢的步伐和節奏擺動,兩者渾然一體。

背棍表演。 攝影/劉朝暉
鐵棍,則是多人合力抬一張桌子制成的舞臺,舞臺上凌空立三個戲曲人物,也是由小孩子們扮演。抬鐵棍的最少8人,還有10人的,新時代下竟然有不遜男兒的女漢子們抬起了鐵棍。抬鐵棍,更注重團隊合作精神,這樣,一臺鐵棍才可能彰顯出不一樣的風采和神韻。而臺上立著的小孩子們,也要依靠下邊的漢子們發出的節奏起伏,扮好自己的角色。
無論是背棍還是鐵棍,并不是僵化地讓戲曲或神話中的人物出來擺個姿勢就算了,而是完整地演繹了戲曲或神話的靈魂,其道具、布景、造型、人物關系等,都自有講究,這里邊蘊含著豐富的民間智慧。一些人只是看熱鬧湊高興,而另一些人則評頭論足非要將出力的漢子們和小孩子們當成專業演員。
不明就里的人會以為背背棍的只是一些粗漢子,有力氣就行。其實這絕對是一個技巧要求高的文藝表演。比如起步時,表演者要先將托道具的右手臂向前輕送,緊接著向后拉,同時右腿一提,才算順利地邁出了第一步。就如用毛筆寫楷書一樣,起承轉合一定要筆到意到,這樣才能發出優美的旋律,同時也甩動了上面的小孩子開始表演,好像一棵完整的樹,樹干、樹枝、葉子和花朵,上下一體。抬鐵棍也同樣有嚴格的步伐、細節動作和節奏,那樣行動起來才會省力,像一個活動著的舞臺,澎湃大氣。通常,8-10條背棍和一臺鐵棍為一組,自有陣勢和結構。
小時候沒少到鄰村清徐龍家營看正月鬧紅火。我們擠在熱鬧的人群里,仰頭望鐵棍上高高立著的濃妝艷抹的小女孩,心里羨慕極了:“要是也讓我站在上面多好啊!”這是所有小伙伴們的夢想。但是我們王吳村沒有這樣的節目,所以小伙伴們只能是做做白日夢了。記得有一次看《西廂記》表演,有人就看出,那個高高地站在一摞文房四寶之上的長著大眼睛的小紅娘太愛自我表演,雙臂和腰肢搖擺得節奏太過均勻,一看就知道是自己擅自行動,根本沒有押著抬棍者的韻律,小伙伴們就對她指指點點,很不滿意。而她旁邊的小崔鶯鶯則一副大家閨秀的矜持溫雅,一臂輕扶小張生的左肩,一臂擺得自自然然,不慍不火。小張生是一個清秀的男孩扮的,右手上托著棋盤(戲劇中紅娘用來遮著張生進入花園的關鍵道具),棋盤上摞著文房四寶,文房四寶的上面站著那個愛表演的大眼睛紅娘。其實后來長大了才明白,那個小紅娘為什么表現得那么活潑,小伙伴們當時還不明白聰明伶俐的紅娘所表現出的是一副成人之美以后的得意神態,這是非常符合劇情的。

汾河邊的牧羊人。 攝影/王牧
中途休息時,有人用長棍子舉了糖塊,送到背鐵棍上的小演員們嘴邊,當小孩子們朱唇微啟時,我們幾個小伙伴同時咽下了口水。童年上過背鐵棍的小女孩,長大了最是媒人嘴里的寶貝,明顯占盡了挑夫婿的優勢。
在全國范圍內,也有類似的民俗表演,只是名稱不同,細節和特色有別。廣東一帶稱之為“飄色”,福建一帶稱之為“鐵枝”,山東一帶稱之為“芯子”,還有的地方稱之為“高臺”、“高抬戲”、“背桿”等。其中比較通用的,稱之為“抬閣”的較多。有人將徐溝背鐵棍的表演藝術特點總結出四點:無言的戲劇、空中的舞蹈、流動的雜技、活動的雕塑。的確是這樣一種藝術,立體的融合以及精益求精,再加之時代的多元發展,背鐵棍娛樂狂歡的屬性已嚴實地遮蔽了古時祭祀祈請神靈的實用功能。
但人們更多的時候是依靠現代科技手段,回歸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樸素思想,也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時需要的內在滋養。

背棍鬧春,三晉民間絕藝古韻背棍,是中國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 攝影/樊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