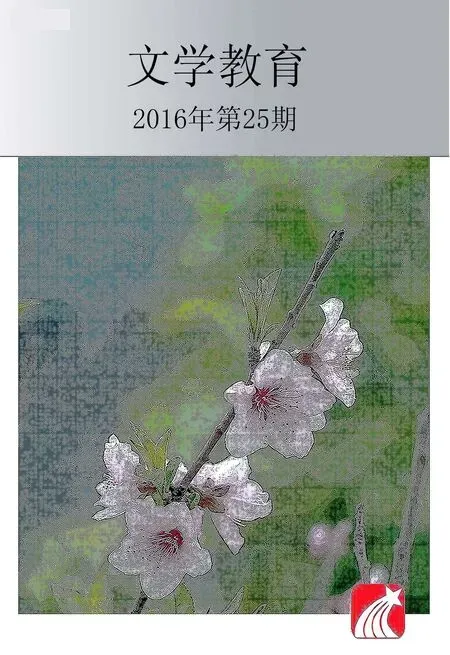從《天涯》“民間語文”看當下草根寫作的話語特性
向勇燕
從《天涯》“民間語文”看當下草根寫作的話語特性
向勇燕
內容摘要:“草根寫作”作為一個相對寬泛的研究對象,目前在國內研究較少,且大都局限在定義及傳播方式等的相關研究上,從話語角度進行解讀的并不多見。把“草根寫作”的典型文本——《天涯》雜志“民間語文”欄目視為一種社會話語實踐,運用話語理論進行分析研討,以期在話語領域里得以探究,具有現實意義。
關鍵詞:民間語文草根寫作話語特性話語權
《天涯》雜志“民間語文”欄目倡導“關注民生、關注底層”,欄目中收集了日記、書簡、記錄、匯報、契約、文案、詞匯歌謠、網絡文本、啟事、調查報告、吊唁挽詞等文本內容,是我國草根寫作者發表言說、呈現思想、表達內心的前沿陣地。這種倡導“非作家”的寫作立場與“精英寫作”在視角上成俯仰之勢,其強烈的正義訴求與草根大眾持久壓抑的表達欲望一拍即合,以一種向下的文學與更廣闊的社會生活及民眾建構關系,其言說方式與言說內容在某種程度上具典型性和代表性。通過對草根大眾話語特性的疏理與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底層,關注民生。
一.以“小視角”書寫“大社會”
在“民間語文”欄目,可以發現“草根寫作”話語的言說姿態具有“小視角”的典型特征。這是與正統或主流表達的“大視域”相對的,“小視角”的“小”主要表現為如下兩方面。
1.地位低下
草根言說者往往是名不見經傳的底層大眾,如務工人員、個體商販,底層農民及閭巷市民等,大都為身份卑微,處于社會邊緣地帶。身份的底層性使得他們慣常以無名的方式進行書寫,同時言說無法像知識分子話語那樣具有啟蒙性,也無法像政府話語那樣富于權威,而只是拘囿于底層生活的簡單敘寫。
2.視野狹小
草根們一般只立足于自己生活的小圈子,以描摹底層生存境遇、抒發個人小情緒為主,無知識分子之承擔也無主流專業人士之顧忌,其寫作只是揶揄生活、發泄情感。在“民間語文”里,不管是個人信札、日記,還是各種匯報、記錄都只是普通人最為常見的文字表述,是廣大無名作者的經歷敘說。他們會喋喋不休地討論柴米油鹽的艱辛,嘮嘮叨叨親人孩子的起居,甚至悉悉索索地抱怨蔬菜水果的價位和生活的各種小感慨小憤怒,很少有涉及國計民生的宏大敘事,也不追慕時代政治風云。至于方言、民間歌謠以及各種網絡文本和流行語等,也只是“小人物”生存哲學與處事智慧的一種集體創作而已。
但“小視角”盡管“小”,卻是“大社會”的一個影射,它以民間姿態植根底層,以個人抒寫扎根現實,以客觀筆法抒寫生活,因此,在表達上往往能起到“四兩拔千斤”的效果,俘獲更多的同情與理解。如2000年第一期的《下崗女工日記》只是底層下崗工人為生活所迫在尋求生存過程中各種感慨、困惑的真實描摹。2000年第六期的《裝修日記》是對裝修過程中各種瑣碎事情的簡單記錄。2004年第四期的《春節經商日記》對春節期間經商中各種辛酸的感慨,展示小商小販掙錢糊口的不易。還有大量的情書、家書更只是普通老百姓一些平鋪直敘的情愫抒發。這些話語都只是地地道道的底層草根以民間的“小視角”來書寫身邊之事,以親身經歷為百姓立言,說“百姓事”訴“百姓苦”傳“百姓情”。
二.庶民話語權力的彰顯
米歇爾·福柯認為,話語是一種權力,人與世界的關系是一種話語關系,這種關系與權力,知識和社會身份緊密結合在一起。長期以來,我國官方的政治意識形態話語在當代思潮中很具影響力,這種以深厚政治背景為前提的主流話語,通常以犧牲、遮蔽龐大的草根發聲為代價,憑借得天獨厚的條件掌握最大的話語權力和言說空間,以實現對社會施加影響的目的。與這種權勢話語相比,廣大草根話語因受其挾持與遮蔽,很難找到一個發聲的平臺,顯得異常邊緣化,言說的內容也常常遭受忽略,不為權威所齒。因此,“草根寫作”話語作為一種與“精英寫作”話語相抗衡的言說形式,在個人話語權力表達上是非常微弱的。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個人自我意識的不斷覺醒,這些被壓抑的草根大眾有了表達的平臺,他們通過大量個人日記、交代材料、書信口述等方式大膽從權威話語的批判威勢下走出來,其內容陳述也極少受某些權威思想與宏大使命的束縛。在“民間語文”欄目里,有對官樣經典的不自覺反駁,有對正統話語的不自覺顛覆,他們往往不拘于已有的表達程式,也不擔負某種公眾輿論的無形使命,更不和現實權利相勾結,而是敢于突破陳規,表述大膽,話題不羈,勇闖言語禁區。草根大眾正是靠對各種語言禁忌自發破除,從而觸及到主流話語不敢碰觸的事實禁區并實現“庶民的狂歡”,這種狂歡背后有對主流話語權的蔑視和消解。
如2000年第五期的《遇難打工妹書信一束(1991-1993)》通過資料提供者從火災廢墟中收集的遇難打工妹生前與親人朋友交往的信件,真實再現了某港商獨資企業觸目驚心的剝削內幕,讓我們看到了經濟繁榮景象背后處在社會底層脆弱無力的生命個體在乖戾時空中的艱難處境,而火災引發的真實內情以及遇難打工者的確切數據在相關報道里卻被“粉飾”掉了。2001年第三期的《“肉票”自述(1932-2000)》講述被綁架者親歷的生死較量,其中涉及權錢交易、官匪勾結的真實情狀,細節之詳實,背景之隱晦,恐怕難為一般主流話語(媒體)所接受,但草根話語不畏強權,大膽對其進行披露。
草根話語通過無意中建構的這個相對冷靜的觀察空間,對禁忌進行不自覺的破除與發掘,從而實現對官方話語或主流意識形態的抵制和拆解。
三.草根話語的意識形態矛盾
草根話語盡管在庶民話語權上打開了一個小缺口,對主流意識形態進行一定程度的消解和排拒,但主流意識形態就像黏合劑,總是設法以一套信仰或思想觀念對社會進行整合,并使其具有“合法性”,“規定”某些觀念、價值是“合法”的,其他的則是“不合法”的,并期待所要主導的價值觀念在“潤物細無聲”中自然地被人們所接受。因此,官方的政治意識會采取各種方式對草根民眾進行宣傳,并試圖滲透以影響底層民眾的思想意識,而進行教化。經過官方意識形態“洗腦”后的草根民眾便會“習得性”讓主流意識先行,以迎合的姿態受制于主流意識形態不自覺采用官方話語,或試圖靠近精英話語,從而導致話語的含混或悖論。如2002年第一期的《吸毒者日記(1999-2001)》中的描述:“我希望端正人生觀,珍惜自己的生命,對毒品的誘惑,我會有很大的決心戒除它……吸毒其實就是一種變態的、不合常規的、反傳統的生活方式……阿紅(作者女朋友)和一個有名的同性戀者外號叫‘亞志’的男人婆同居了……從阿紅的身上,真的是折射出當今社會一群所謂‘邊緣人’的生存狀況,他們的一舉一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定環境中的某種特殊心態……吸毒是社會現實中的丑惡現象,毒癮之難除,眾所周知,樹立一種正確平和的心態至關重要。”[1]
在主流意識形態里,“端正人生觀,珍惜生命”才是“合法”的價值取向,“吸毒是社會現實中的丑惡現象”,“是一種變態的、不合常規的、反傳統的生活方式”必須予以擯除。摘文中的吸毒者很顯然對主流價值規范持認同態度,盡管吸毒成癮,三番五次戒毒不成,仍以主流的規訓來告誡自己,希望“樹立一種正確平和的心態”。吸毒者的這些話語都是官方意識形態在價值規范上的符號表征,卻被不自覺的挪用,以此形成官方意識形態話語與草根話語的混雜編碼形式。學者談育明、金林南曾指出:“人是社會性動物,每一個人都有歸屬意識,都會通過各種方式使自己歸屬于某個共同體。人們主要通過各種共同體的信仰符號、行動綱領、價值規范等意識形態符號使自己獲得精神上的歸屬與身份上的認同。”[2]
吸毒者作為“當今社會一群所謂的‘邊緣人’”,一方面以歸屬意識尋求社會身份認同,另一方面也隱含著一種被官方“規訓”后的“招安”意味。
當然,“草根寫作”駁雜豐富,“民間語文”欄目只是“草根寫作”話語的縮微表征,欄目呈現的有限文字僅為這個繁復寫作現象中的冰山一角。不過,管中亦可以窺豹,將“民間語文”欄目所呈現的話語視為“草根寫作”話語的一種具體實踐,借此來研究我國底層老百姓的意識形態、身份認同和價值觀,有其時代價值。
參考文獻
[1]李敏.吸毒者日記(1999—2001)[J].天涯,2002(1):66-79.
[2]談育明,金林南.嵌入的政治——意識形態本質論析[J].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4):48-52.
(作者介紹:向勇燕,長沙師范學院初等教育系文學教研室教師,研究方向:文學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