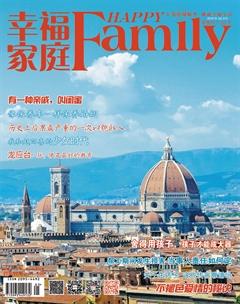雀喧禾黍熟
望著一望無際的麥浪和麥浪中時落時起的鳥雀,我總覺得王維老先生這句“雀喧禾黍熟”就是描寫麥收季節的。鄉下麥收的那些天,城市一下子空曠了許多,回去的不僅僅是那些來城里打工的農民,還有那些每天在我們窗前嘰嘰喳喳的麻雀。
麻雀是戀舊的,是不嫌家貧的,是標標準準的“土著”,無論是城里還是鄉下,到處都有它們的身影。就是這小小的生靈,就是這可愛的鳥兒,中外都曾經誤解過它們,把它們當做敵人捕殺過。普魯士腓特烈大帝見櫻桃園里的櫻桃常被鳥雀啄食,于是下令捕殺,并規定殺死一只麻雀可有6芬尼的獎勵,瞬間無數麻雀慘遭厄運。但很快人們就發現,一時間麻雀雖然少了,但害蟲卻泛濫成災,不久,腓特烈大帝果斷地收回圣令,讓麻雀又有了生存的空間。
上世紀50年代,我國也有過捕殺麻雀的運動,那年月,城鄉到處敲鑼打鼓,搖旗吶喊,大人小孩、男女老幼,把那些可憐的小麻雀追趕得無處藏身。人們除了以彈弓擊殺,以網、篩誘捕麻雀外,還深夜架梯去掏鳥窩,大有斬草除根之勢。與普魯士一樣,人們很快發現,麻雀少了,害蟲多了,科學家研究也證明,麻雀吃的糧食遠遠少于它吃害蟲所保護下來的糧食,所以,我國這次捕殺麻雀運動也沒有堅持多久,很快麻雀又在城鄉快樂地歌唱了。
其實不單單是麻雀喜歡吃新麥,記得小時候,麥子還是青青的時候,我們小孩子就開始搓著吃新麥了。先掐一把麥穗在火上燎去扎手的麥芒,等麥子發出清香時用手一揉,吹去麥糠,就可以吃了。
當然,愛吃新麥的,也不只是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就是古代的帝王,也把新麥當做美味佳肴。據《左傳》記載:“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這是晉景公姬獳如廁的故事。晉景公姬獳想吃的新麥已經到嘴邊了卻未能如愿,真是沒有這個口福呀。
想想古人多以麻雀為伍,根本不在乎它們吃的那幾粒糧食。“汝家繞朋侶,我家多鳥雀。”“禽雀知我閑,翔集依我廬。”“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看看,無論是南北朝的王僧祐,還是唐朝的儲光羲和杜甫,哪位詩人不把麻雀當做自己的好朋友!當代的齊白石老先生更是畫麻雀的高手,有人說他畫麻雀先是以兩筆淡墨畫出麻雀的體形,又一筆赭墨勾出麻雀頭,用重墨一橫折和兩個墨點就畫出了麻雀嘴和麻雀眼,再一道重墨勾出雀胸,最后六筆短線畫出雀爪。一只麻雀不過十九筆,簡潔傳神,令人嘆為觀止。
人們愛麻雀,就是因為麻雀極愛與人們親近,麥田里陪伴莊稼人最多的小鳥就是麻雀了,它們吃糧食更吃害蟲,不過當年人們對它的誤解,也是情有可原的,誰愿意讓辛勤汗水換來的糧食被動物糟蹋呢?在那顆粒歸倉的年代,我還與小朋友們一起拾過麥田里落下的麥穗哩。很小的時候,我就知道愛惜糧食了。識不了幾個字的母親更背不了幾首唐詩,但她卻把“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這首詩背得爛熟。愛惜糧食的美德就是母親言傳身教給我的。
想想看,我們碗里的每一粒飯粒,的確來之不易。白居易的《觀刈麥》之詩最能概括農民收麥的辛勤:“田家少閑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讓人過目難忘。回頭再吟唱王維的“雀喧禾黍熟”,想想功大于過的麻雀曾經背過的黑鍋,就更覺得麻雀的可愛了。 (摘自《甘肅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