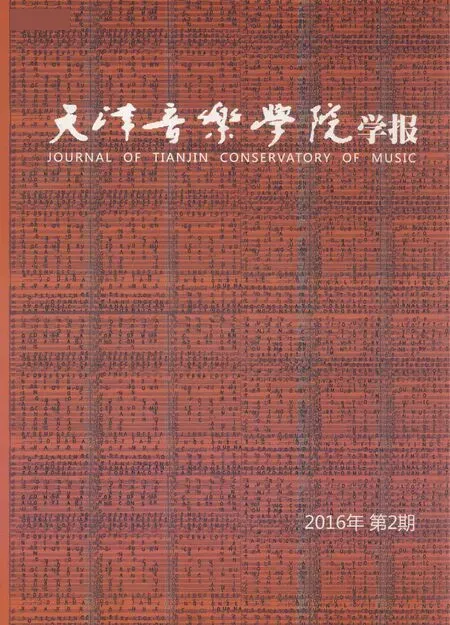伊斯蘭音樂考
王雅婕
?
伊斯蘭音樂考
王雅婕
在早期的伊斯蘭文化中,無論是從宗教的角度,亦或是世俗的角度,音樂都受到了諸多的限制,此種情況直到科學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仍未絕跡。長久以來,這一現象也或多或少地影響了學者們對于伊斯蘭音樂研究的展開。那么伊斯蘭對于音樂的認識與現實又究竟如何?我們又應該怎樣對伊斯蘭的音樂進行理解呢?本文將首先對伊斯蘭教教義《古蘭經》和《圣訓》進行研讀,并對伊斯蘭歷代統治者對音樂的態度,以及伊斯蘭不同教派、教團的音樂情況進行全面的梳理。進而對伊斯蘭音樂發展擴大后滋生的伊斯蘭本土文化與世界文明的矛盾、伊斯蘭自我傳統與外媒審視的矛盾,以及伊斯蘭文化融入非伊斯蘭傳統多元社會的矛盾等多方面關系進行剖析。力求對伊斯蘭的音樂類型、發展軌跡及研究方法等問題深入解讀與思考,為伊斯蘭音樂的研究澄清事實,提出新的見解。
宗教音樂 伊斯蘭音樂 伊斯蘭音樂研究地域化
緒言
伊斯蘭有音樂嗎?誰抑制了伊斯蘭的聲音?我們又該如果面對伊斯蘭音樂的問題?
筆者最初對此發問是由于在參加如國際傳統音樂學會(ICTM)第42屆世界大會(2012年7月,上海)、第七屆東方音樂學會國際研討會(2012年11月,寧波)等國際、國內會議并論及伊斯蘭音樂及其相關問題時,總會有專家、學者對伊斯蘭音樂是否存在及其合理性等問題有所質疑和提問。而后在筆者實地考察上海滬西清真寺、小桃園清真寺,蘭州東關清真寺、西關清真寺,以及對我國新疆南部及印度北部伊斯蘭地區的一些阿訇、信徒等進行采訪、交流時也發現“音樂”一詞對于他們的復雜性和多意性。
帶著這一問題查閱文獻可見,關于伊斯蘭禁止音樂的觀點,雖未見到專門的論著,但從一些散見的記載中仍可看到。比如我國唐代旅行家杜環于寶應初年(762年)由阿拉伯回來所寫的《經行記》中記載:“大食一名亞俱羅,其大食王號暮門,都此處。……系銀帶,佩銀刀。斷飲酒,禁音樂。”①(唐)杜環原著、張一純箋注:《經行記箋注》,中華書局2000年4月,序言第3頁。而在伊斯蘭地區,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后,其最高精神領袖的霍梅尼也曾聲稱:“音樂就像麻藥與酒,麻痹人理性的判斷力”。②柘植元一:《西亞的音樂文化》,《黃鐘》2001年第3期。
雖然在音樂學界的研究當中,尚未見到直接指出伊斯蘭無樂或者禁樂觀點的論文,但是類似的傾向卻有很多,特別是在認為伊斯蘭沒有宗教音樂方面。比如說岸邊成雄提出的:“由于伊斯蘭教的學者把音樂作為信仰上的禁條,因此,伊斯蘭教的宗教音樂是不存在的。”③岸邊稱雄著、郎櫻譯:《伊斯蘭音樂》,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9月,第20頁。英國學者、阿拉伯音樂研究專家法瑪也曾指出“然而嚴格地說,在我們的傳統觀念上,伊斯蘭沒有宗教音樂。”④“Strictly speaking,however,Islam has no religious music in our normal sense of the term,since there is no service in the Muslim mosque comparable to that in the Christian church.Yet music in praise of Allah has always found a place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Muslim places of worship.”Farmer,The Science Of Music in Islam,Eckhard Neubauer,1997.而其反對面的言論也有不少,比如我國學者梁書琴在《金寨回族鄉清真寺宗教儀式音樂研究》一文中指出:“以往由于我們對回族音樂文化沒有進行認真的調查總結,再加上受到一些世俗和偏見的影響,……如說‘伊斯蘭教沒有宗教音樂’、‘回族沒有獨特的音樂文化’等。致使回族音樂長期不被人們所了解,回族音樂的研究和介紹工作也一直處于空自狀態。”⑤劉同生:《概說回族音樂》,《中國音樂學》1989年第3期。《阿拉伯通史》中也指出“穆斯林的宗教生活與音樂也不無聯系。……縱然一般阿訇對帶有聲韻的讀法,只說是念,不承認是唱,而實際仍是歌唱。”⑥轉引自白玉深:《試談伊斯蘭教和音樂》,《中國穆斯林》1988年5月。《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一書則更明確地論述了一些伊斯蘭宗教音樂類型,并提出:“伊斯蘭教在各種場合使用的極為豐富的吟詠和歌調都屬于音樂的范疇。”⑦田聯韜主編:《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上冊),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1年10月。
可見,目前有關伊斯蘭音樂的問題仍存在著種種爭論,但眾多的音樂實例表明,伊斯蘭不僅有各種類型的音樂,并且隨著伊斯蘭的世界化,更呈現出非常繁榮的景象。而要解決筆者開篇所提出的問題,理清伊斯蘭音樂觀的原委,則首先要從伊斯蘭教法教義對音樂的論說中談起。
一、伊斯蘭教義經典記載中的情況
伊斯蘭教的經典《古蘭經》原意為“誦讀”,全書共30卷114章6236節,記載了二十三年間真主對先知穆罕默德的啟示,在伊斯蘭世界,可謂穆斯林生活和行為的最高準則。《圣訓》的地位僅次于《古蘭經》,是穆罕默德及其弟子生前言行的結集,對《古蘭經》有著補充和闡釋的作用。翻閱并理解伊斯蘭教的經典和行為指導《古蘭經》、《圣訓》中對音樂的不同觀念和態度,是我們在伊斯蘭精神層次對其音樂進行理解的首要步驟。
(一)教義中記載的宗教音樂
傾聽(Samā)是在《古蘭經》(第39章18節)中出現的唯一與音樂相關的詞匯,因此也被認為是區分合法與非法音樂的界限。Samā一字阿拉伯文原義為“聆聽”的意思,后被擴大解釋為“聆聽到的聲音”,由于“傾聽”與《古蘭經》誦讀、贊詞、叫拜調、蘇非靈修儀式等都有著密切的聯系,故筆者認為“傾聽”對伊斯蘭音樂的形式首先有著比較明確的宗教音樂(音聲)指向性。比如在《古蘭經》第二十一章第1節中記載:“每逢有新的教誨,從他們的主降臨他們,他們傾聽它。”(240)第四十六章第29節記載:“當時,我曾使一伙精靈,走到你面前,來靜聽《古蘭經》。”(380)這里的靜聽《古蘭經》,既是一種宗教修行,又可表現為一種靈修儀式。伊斯蘭教義、典籍中也大量記載了“真主最愛聽的聲音”——《古蘭經》吟誦。但由于一些原因(文中第三部分具體論述),故在伊斯蘭世界《古蘭經》吟誦并不被稱為音樂。
但蘇非教團的“聆聽”情況則有所不同,其與“傾聽”有關的靈修儀式齊克爾(Zikr)和薩瑪(Samā)所衍生出的音樂形式,它們是伊斯蘭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齊克爾”意為贊頌、懷念,是蘇非教團贊頌真主的一種修煉,其基本特征是反復不斷地重復贊念真主的名字,以使人們將真主銘刻于心。一般可分為“齊克爾杰利”(高聲贊念,念給別人聽的)和“齊克爾哈非”(低聲贊念或默念,只勸誡自我)兩種類型,后來屬于高聲贊念派的契什提教團⑧印度伊斯蘭教蘇非派兄弟會組織。教義強調萬物存在的統一性,認為均系安拉所創造。提倡知足、簡樸、苦行、安貧、克己。反對參與政事,反對使用暴力。不注重表面上的信教,堅持內心的真正歸信,其信徒主要分布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參見百科全書編委會:《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契斯提教團”條,四川辭書出版社2007年4月。把音樂和歌舞引入齊克爾儀式,這種通過音樂和歌舞來贊念真主的樂舞活動即被稱為薩瑪。薩瑪活動主要在伊斯蘭修道堂舉行,通常眾蘇非圍坐在一起,一邊傾聽《古蘭經》、神秘主義詩歌,一邊冥想、修行。而這種靈修方式也是后來在伊斯蘭世界各地發展起來的比如印-巴格瓦利(Qawwali)等音樂體裁的雛形。而這些蘇非音樂本質上也是宗教性質的,但隨著時代的發展,使其逐漸有了走下圣壇,融入世俗音樂的形式。這里所聆聽的內容則又擴大性的指向了文學性的詩歌和旋律性的音樂等。
教義中雖沒有提到這些音樂的俗樂形式,但就其宗教的類型除了對其念誦的聲調、音高有限制之外,則明顯的肯定甚至是提倡的。
(二)教義中記載的世俗音樂
雖然在《古蘭經》當中并沒有出現音樂(music)一詞,也并沒有對音樂做過直接的褒貶評價。
1.肯定音樂的記載
《古蘭經》及《圣訓》對音樂記載最多的指向是“歌唱”,對應阿拉伯語中的Ghinā一詞,僅指世俗性的演出。雖《古蘭經》中并沒有過多的言辭論述歌唱,但正如埃及伊斯蘭學者霍利(Kholy)所指出,《古蘭經》第三十五章《創造者(Creator)》所載:“真主對于萬事確是全能的。無論真主賞賜你們什么恩惠,絕無人能加以扣留;無論他扣留什么恩惠,既扣留之后,絕無人能加以開釋。”⑨馬堅譯:《古蘭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8月,第324頁。一句雖并沒有記載音樂相關的內容,但神創造的恩惠中理應包括優美的歌聲,既然神創造了優美歌聲,那也就肯定了歌唱、肯定了音樂。⑩參見Samha Amin El-Kholy,The Function of music in Islamic Culture.Cairo:General Egyptian Book Organization,P17.
《古蘭經》、《圣訓》和《穆罕默德傳》等也較為完整地記錄了阿拉伯-伊斯蘭地區的音樂類型和形式。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一些關于“歌唱”的故事。比如《穆罕默德傳》中的記載“圣人從白德爾回到麥地那時,人們出城迎接。姑娘們敲著手鼓,載歌載舞歡迎圣人。歌中唱道:先知從賽尼雅圖勒韋達來到我們的家鄉,他象皎潔的圓月把我們照亮。感贊安拉是我們的天職,我們愿作人間的穆斯林。先知給我們帶來了伊斯蘭教,我們都昄依了這美妙的正道。”(P119)這里是一首宗教歌詞的歡迎歌。而在吳侯德圣戰中的記載“當兩軍交錯格斗,混戰砍殺,戰斗白熱化時,為了鼓舞士氣,敵軍陣里的婦女開始擊鼓高歌。她們唱的是:‘主呀!我為你而戰,你佑助我們出擊吧!你是我們的保障,你是多么好的主宰!’”(P134)這是一首求真知賜福的軍歌,而在早期阿拉伯世界的傳統中,軍歌不同于其他國家由戰士自己演唱,而是由婦女演唱的,目的是為了鼓舞戰士們的斗志。在壕溝圣戰中的記載,為了克敵,“圣人與穆斯林一起參加挖壕勞動,他一邊運土,一邊反復唱著阿卜杜拉·本·拉瓦海的這首歌:主啊!沒有你,我們就得不到引導,沒有你,我們哪能懂得天課,禮拜和祈禱。請你賜給我們鎮靜和堅毅,并指引我們戰勝頑敵。多神教徒固執偏見把人欺,要我們離開正道,萬萬不能依。”(P160)這里表現了一首宗教性質的勞動歌曲,祈求真主賜予力量。另外,婚禮音樂的記載也多有出現,比如有一位婦女即將嫁給安薩(Ansar)男子為妻,穆罕默德詢問其妻阿依莎(Aishah)在婚禮中是否有準備任何娛樂性節目,當阿依莎回答沒有時,穆罕默德說:“安薩人是一個喜歡詩歌的民族,妳應該帶一些能夠唱歌的人去。”①“安薩”阿拉伯語原為幫助者(helper)之意,指的是公元622年(回歷元年)穆罕默德移居麥地納時,所有原來居住在麥地納的居民。事實上,“安薩”指的并不是單一民族的名稱,而是當時所有住在麥地納居民。轉引自蔡宗德:《伊斯蘭世界音樂文化》,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2月,第108頁。表現了婚禮音樂的使用。而圣訓【4001】中記載:據穆安威茲之女魯班婭傳述,先知與我結婚的第二天早晨來坐在我的床上,如同你與我坐在一起。小姑娘們敲著手鼓唱歌挽吊白德爾戰役之日被殺的我祖先,其中一個姑娘唱到:“我們中有先知,他知道明天的事。”先知說道:“你不許這樣說,你就唱你原來的歌。”(第三卷P12)這里說明了挽歌體裁在伊斯蘭世界的應用,類似的內容還在《圣訓》【5147】中有所記載。以上這些歡迎歌、節慶歌、軍歌、勞動歌、婚禮歌、挽歌等均從屬于伊斯蘭音樂的類型,可見各類民俗化的音樂類型實際上遍布于伊斯蘭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
除單純的歌唱之外,從以上記載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鼓的伴奏頻頻出現。這些有關“鼓”的記載,實際上很多指的正是伊斯蘭教義當中唯一承認的樂器達甫(Duff)鼓的運用情況,而用鼓來伴奏歌唱的形式也正好符合了伊斯蘭初期阿拉伯地區較為普遍的以聲樂為主的音樂形式,如沙漠駱駝隊歌曲“胡達”等大多是一些淳樸、簡單的唱詩,描繪阿拉伯人的游牧生活以及與自然的關系等內容,采用單聲部的音樂線條,演唱者往往即興而歌,樂句沒有規范的長度和韻律,多用達甫鼓伴奏。而除鼓之外,《圣訓》第四十三節還記有“吹號角”一節,記載穆賈希德說:“號角形似喇叭。”(第四卷P155)可以看出號角的使用。以上是為伊斯蘭宗教教義和典籍當中音樂運用的實際情況的記載,也是伊斯蘭音樂觀中對音樂持肯定態度的證明。
2.否定音樂的記載
然而另一方面,據《布哈里圣訓實錄》①祁學義譯、朱威烈、丁俊校:《布哈里圣訓實錄全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12月。四卷本的記載,其中有關音樂的言論幾乎都圍繞著這樣一個關于歌唱的故事。《圣訓》【949】載:“據奧爾沃傳述,阿伊莎(求真主喜悅她)說,真主的使者來到我跟前,當時我跟前正好有兩個女孩[敲著手鼓]唱布阿斯歌謠,使者睡在床上轉過臉去。這時艾布·伯克爾走進來呵斥我說:‘先知跟前豈能有惡魔的歌聲?’真主的使者轉過來對他說:‘別制止他倆!’乘艾布·伯克爾不注意,我給她倆使了眼色,她倆變溜了。”(第一卷,P198)同樣的記述還出現在《圣訓》的【952】【987】【2906】【3931】當中。其中【952】進一步解釋道真主的使者說:“艾布·伯克爾啊!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節日,今天是我們的節日。”(第一卷,P199)證明這個故事發生的背景是在節日當中,【3931】則更為明確稱此為“有一次開齋節或宰牲節”(第二卷,P404)。根據這條記載的表述,似乎透露出阿布·伯克爾是反對音樂的,而先知也只是在節日的時候放寬了某種對音樂的限制。那么阿布·伯克爾是何人,他又為何反對音樂呢?
阿布·伯克爾是伊斯蘭教最早的皈依者,穆罕默德逝世后的第一任正統哈里發,執政時間是公元632-634年,同時他也是穆罕默德的岳父。而阿布·伯克爾對音樂的嚴禁是有一定客觀社會原因的,在皈依伊斯蘭初期的阿拉伯社會,仍存在很多陰郁、感傷、軟弱和頹廢的曲調,一些男人們常常模仿打扮成婦女的樣子歌唱,從而腐蝕了堅硬的意志,失去了男子氣概,終日消沉、墮落、無所事事,嚴重影響了正常的社會生產勞動和戰爭武力,甚至導致社會上有一部分人已經開始探求新的信仰。并且買賣歌女的行為和挑逗性的歌女賣唱等消極娛樂也嚴重影響了社會風氣和長治久安,這些現象對剛剛建立的伊斯蘭教政權可以說是一個極大的威脅,統治者立刻感覺到這樣的氛圍如長此以往,必將擾亂穆斯林虔誠的信仰和祈禱,影響社會的穩定和安寧,故對音樂采取了排斥和禁止的態度。
而先知穆罕默德本人也對音樂持有此種態度的言語在《穆罕默德傳》②埃及穆罕默德·胡澤里著、秦德茂、田希寶據買買提·賽來維吾爾文轉譯:《穆罕默德傳》,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中也多有體現。比如圣人說:“我從幼兒時起就厭惡偶像。我只有兩次有過循行蒙昧時代之事的念頭,但真主兩次都使我以幸免。有一天晚上,我把自己放牧的羊群托付給一起放牧的伙伴,自己也象別的青年人一樣走進麥加城,準備參加人們的夜談。進城后,路過第一座院落門前時,從里面傳出了舉行婚禮的歌聲、手鼓和嗩吶聲。于是我就坐下來聆聽。可是真主不讓我聽,使我熟睡過去,直到第二天早晨太陽照到我的身上,我才醒來。結果我什么也沒有干。第二次也是這樣。從那以后,直到真主賜我為圣之后,我再未起過任何邪念。”(P9)此處我們可以看到穆圣否認音樂的原因大抵應該是因為音樂屬于“蒙昧時代”之事,并稱音樂是一種“邪念”。而事實上,蒙昧時期及其音樂形式的確令伊斯蘭感到過不滿、憤怒和恐慌,比如《穆罕默德傳》中記載“在蒙昧時期,……,伯克爾部族有個人歌唱譏諷圣人,被胡扎兒部族人聽到,把唱歌的人狠揍了一頓。”(P221)而伊斯蘭教興起前在麥加地區占統治地位的一個阿拉伯氏族古萊什部落勢力猖狂,長年征戰,《穆罕默德傳》記載:“古萊什人集合好隊伍,帶著女仆、樂器和美酒出發了……他們命令女仆唱著嘲諷穆斯林的歌曲,定在隊伍前頭。”(P134)可見,蒙昧時期留存的音樂傳統危害并挑釁了伊斯蘭的尊嚴和權威,故伊斯蘭教政權建立之后,其首要任務之一也確是與蒙昧時代的行徑劃清界限,并排斥和打擊多神教,因此,伊斯蘭初期先知否定音樂的行為的初衷也就變得容易理解了。
對于這種禁樂行為的理解借用《古蘭經》中關于伊斯蘭禁酒的記載進行說明來看,《古蘭經》載“對某種惡習的戒除,往往是在這種習俗引起了某種遭到非議的事端時,才能得到多數人的贊成,并產生深遠的影響。”酗酒滋事以及穆斯林酒后禮拜會念錯禱詞就是“飲酒”所引起的事端。《古蘭經》還說:“他們問你飲酒和賭博的律例,你說:‘這兩件事都包含著大罪,對于世人都有許多利益’。”(2:218)(P144)因此,盡管“阿拉伯人一般都有把賭博收入施舍給窮人的習慣,飲酒則可強壯身體”(P144)還是要一并禁止。同理,由于音樂所引發的種種事端,故而即使音樂是對人們有好處的,也應在宗教法度上全面禁限。這里其實也透露出所謂宗教人士對于伊斯蘭音樂的一種態度:即使承認音樂可以是美好的、有積極作用的,但在說法上還是不能夠明確的肯定或稱贊。這是一種矛盾、曖昧的態度,也是日后伊斯蘭音樂問題含混不清的最初原由。
(三)教義中所記載的音樂審美觀
《古蘭經》中雖然沒有對音樂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評判,但也卻表示出了其所崇尚和排斥的聲音類型。如第31章《陸克曼(Luqman)》的第18節中,安拉這樣告誡人們不可傲慢、自以為是:“你應當節制你的步伐,你應當抑制你的聲音,最討厭的聲音,確是驢子的聲音。”(308)可以看出,《古蘭經》要求人們“抑制聲音”,并對不協和且粗糙的“驢子的聲音”進行了貶斥,從而揭示出伊斯蘭音樂的審美標準——低沉美好的聲音。類似的意涵還如第二十章:“一切聲音將為至仁主而安靜下來,除足音外,你聽不見什么聲音。”(237)第二十八章:“不要狂喜,真主確是不愛狂喜者。”(295)第四十九章:“信道的人們啊!不要使你們的聲音高過先知的聲音,不要對他高聲說話,猶如你們彼此間高聲說話那樣,以免你們的善功變為無效,而你們是不知不覺得。”(387)等。可見,伊斯蘭對聲音的負面態度僅針對那些高亢粗陋的聲音,而更崇尚一種謙和寧靜的聲響。而在《圣訓》等中也同樣有相同意思的描述,因篇幅原因,此處不再贅述。
綜上可以看出,伊斯蘭首先是肯定宗教音聲的,而在世俗音樂中各種題材的歌曲也大量存在,并且存在一些簡單地伴奏形式。結合《古蘭經》和《圣訓》記載時代的語言環境和社會背景,客觀分析《古蘭經》和《圣訓》中所提及的音樂內容來看,阿拉和先知穆罕默德的語論并沒有反對音樂的想法,而只是強調應該適時、適地、適度、適宜地演唱歌曲和運用音樂,這也完全符合伊斯蘭政權建立時期,音樂與歌女與惡俗及其它非伊斯蘭宗教有著密切聯系的客觀事實。
二、歷代伊斯蘭統治者和各教團的情況
由于《古蘭經》和《圣訓》都沒有表達對于音樂的明確態度,伊斯蘭歷代的統治者以及各教派、教團之間便開始依照主觀評判來對音樂進行褒貶和定位,伊斯蘭的音樂觀附加著每個時代和個人的不同喜好,甚至是方便統治的政治化色彩。
(一)統治者對音樂的不同態度
從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后,伊斯蘭教結束“先知時期”進入“四大哈里發時期”①哈里發在阿拉伯語中是繼承人的意思,伊斯蘭教的哈里發就是穆罕默德的繼承人。正統哈里發指的是穆罕默德逝世后最早的、由選舉產生的四個哈里發,他們是阿布·伯克爾、歐麥爾、奧斯曼和阿里,從公園632年-661年,共統治了29年,這個時期在阿拉伯歷史上就叫正統哈里發時期。阿里以后,即從伍麥葉王朝起,哈里發職位改為世襲。參見薩米·哈菲茲:《阿拉伯音樂史》,人民音樂出版社1980年,第17頁。,期間的統治者對音樂的態度也因整體、環境、喜好等因素各有不同,現列舉一二以窺之。
為了鞏固伊斯蘭教政權,頭兩任哈里發艾布·伯克爾和歐麥爾(執政時間:公元634-644年)都嚴禁音樂、歌曲活動。到了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執政時間:公元644-655)時代,音樂轉而重新受到重視,人們開始創作悠揚動聽、內容豐富的歌曲,這些歌曲給人們帶來了歡樂的情趣,音樂的愛好者逐步增多,對美好聲音的渴求形成了一種良好的社會風氣,音樂也越來越被積極地加以利用,甚至于娛樂性和世俗化的音樂也逐漸受到了認可。進而到第四任哈里發阿里時期,阿里本人就是一位詩人和歌手,他積極提倡科學和藝術的發展,并且還經常親自參加穆斯林民眾的歌舞集會,此外,當時社會的一些著名的伊斯蘭學者麥地那大教長、圣訓學家馬立克等本身也是歌手出身。①參見薩米·哈菲茲:《阿拉伯音樂史》,人民音樂出版社1980年,第16-22頁。一時間,音樂在社會上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轉變和提升。
在阿拉伯社會進入伍麥葉王朝(公元661 -750)和阿拔斯王朝(公元750-945)時期,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達到了一個全盛時期,與此相應地,阿拉伯-伊斯蘭音樂也進入了鼎盛發展的階段。首先伍麥葉王朝的幾任統治者例如穆阿維葉、葉茲德·安瓦魯、卜杜勒·麥利克等都對音樂和藝術有著將強的興趣,他們推崇展開一些音樂的活動,肯定音樂人的地位等。此外,正如英國阿拉伯音樂研究專家法瑪的解釋那樣,伍麥葉王朝歷代哈里發之所以如此支持音樂活動,除了是由于對音樂的喜愛外,事實上也是為其政治目的所服務的。就阿拉伯本土而言,歌手們猶如現今的記者一樣往來于眾多城市與部落之間,因此有較多機會與一般老百姓接觸,了解他們的生活與思想,再通過歌唱反映出來,有助于哈里發們了解民眾真實的一面。②參見Henry George Farmer,A History of Arabian Music:To the XIII Century,London:Luzac&Co&Co.Ltd,1994,P66.加之此時阿拉伯社會的對外交流逐漸增多,與波斯、希臘、印度等外來文明的交流和沖撞也使得其音樂果實枝繁葉茂,相應的音樂觀念也必然有所轉變。因而伍麥葉和阿巴斯王朝留給了音樂一個較大的發展空間。特別是發展至阿巴斯王朝時的整個伊斯蘭世界的音樂文化空前繁榮,樂器種類、演唱演奏方法、旋律和節奏體系等都相應地進行了改革和完善,而在音樂理論基礎雄厚發展和鋪墊的同時,各類音樂的表演藝術家也層層輩出,活躍在阿拉伯音樂的舞臺。
近代的阿拉伯-伊斯蘭地區對音樂的態度和音樂發展的情況也受到了統治階層和社會因素的很多限制。例如在伊朗,隨著1979年革命和原教旨主義的宗教政治接管,所有公共音樂都陷入了停滯狀態:廣播電視中停放音樂、關閉音樂學校、停止各類樂團的演出等。然而,在幾年后政府也開始意識到這些苛刻的措施是站不住腳的:音樂并不能從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刪除,隨之又出現了大量的音樂復蘇跡象。③參見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No12,“Iran”,2001,P535-537.
可見,在阿拉伯-伊斯蘭各統治時期,音樂盡管沒有擺脫東方社會中作為政治和文化附庸的特點,但也是逐步受到重視和不斷發展著的,然而也必須承認的是,這些音樂形式和音樂觀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社會、權利,亦或是個人喜好程度等因素的制約,并且往往與伊斯蘭教法沒有非常大的關系。
(二)伊斯蘭各教團的情況
與上述統治階層出現的縱向上的時代音樂觀分化相似的,穆罕默德去世后,橫向上伊斯蘭教也逐漸形成了遜尼派、什葉派、蘇非教團等不同派別,由于地域、歷史背景與文化語境的差異,同樣信仰伊斯蘭教的不同教派之間,對音樂的看法、態度也是有所差異的,以下逐一剖析。
1.遜尼教派
遜尼派被認為是伊斯蘭教的正統派,擁有約占全世界穆斯林85%以上的信徒,信奉《古蘭經》,并依據《古蘭經》謹慎地引用《圣訓》作為指引,該派為伊斯蘭教派內部對音樂的態度最為嚴格的一派,其四大教法學派皆極力反對音樂。
其中,罕百里法學派最為苛刻,幾乎徹底排斥音樂;哈納斐法學派認為歌唱本身即是一種原罪(kabira),歌者與器樂表演者會引起動蕩不安,故不應為社會所接納;馬立克法學派同哈納斐法學派類似,認為歌女的身份以及買賣歌女為奴的行為都應該受到社會譴責,并進一步指出《古蘭經》的誦唱應該為純粹的誦讀,而不應加入任何旋律的裝飾;沙斐伊法學派的觀點較以上三派來看則較為緩和,這首先表現為沙斐伊法學派認為音樂在《古蘭經》與圣訓中并沒有被明文禁止,并且準許在《古蘭經》中加入人為旋律化的成分來詠誦,但該學派對世俗音仍然持堅決反對的觀點,比如主張真正虔誠的穆斯林不應去聽世俗音樂,也不應將演唱世俗音樂作為職業等。①參見王慧芹:《穆斯林的音樂觀》,《世界文化》2009年6月。
從遜尼派對音樂的態度看,除排斥娛樂性、世俗性、挑逗性的歌曲、器樂曲這些伊斯蘭世界共同反對的聲音之外,遜尼派的特點是一些教法學派甚至排斥以旋律的方式吟誦《古蘭經》,其原因是為何呢?正如極其反對音樂的遜尼教學者伊本·泰米亞(Ibn Taymiyyah)所認為的:穆罕默德先知給的是一個完整的宗教,當我們在討論通往神的路時,應盡可能平淡、簡單的遵循神所給予的,唯一能夠決定音樂的只有神的律法。所以,加上了人為旋律誦讀的《古蘭經》,即非神所給予的,當然也就是多余的且不符合神的律法。②參見蔡宗德:《傳統與現代性:印度尼西亞伊斯蘭宗教音樂文化》,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41頁。而在實際運用當中,由于地域的不同,遜尼派的禮儀音聲還是能夠找到不少例證的。比如我國新疆喀什艾提尕清真寺的主麻日禮拜和節日會禮,往往都是由阿贊(呼禱調)、克拉埃特調(《古蘭經》吟誦)、呼圖白(發表宣教演說)、牟陸特(圣贊詞)等維吾爾族遜尼派伊斯蘭教禮儀音聲構成。而新疆吐魯番、伊寧、鄯善魯克沁鎮等的“牟陸特”儀式(圣紀日紀念儀式)的儀式音聲也各有特點,體現了伊斯蘭遜尼派宗教音聲的運用。
2.什葉教派
什葉派是伊斯蘭教第二大教派,擁有占穆斯林人口10%的信徒人數,只信奉《古蘭經》,不將《圣訓》作為經典。其對音樂的態度與遜尼派比較起來較為寬松,這表現為其承認《古蘭經》誦唱、呼禱調、禱念詞等宗教性的吟誦,但仍對聲樂或器樂作品有著嚴格的限制。
什葉派有較為寬松的音樂態度,在其學者的言論當中多有證明,比如什葉派學者塞丁指出:“每一條指引人通往神的路都是合法的,如果音樂指引人通往它的路,那音樂也是合法的。假如音樂促使人背離神的道行并削弱人的精神,使人們走向罪惡、錯誤與犯罪的話,那音樂就是非法的。”③王慧芹:《穆斯林的音樂觀》,《世界文化》2009年6月。而身為什葉派伊斯瑪依(Ismailism)支系的“精誠兄弟社”也并不否定所有音樂類型,他們指出了伊斯蘭不贊同音樂的理由:“人們常把音樂用在賢哲所做以外的事;他們把音樂用在娛樂與游戲,用在引誘世俗欲望以及詐騙之上。”④蔡宗德:《傳統與現代性:印度尼西亞伊斯蘭宗教音樂文化》,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42頁。由此可見,什葉派并不是否定所有的音樂類型,而只是否定那些所謂惡俗、混亂的音樂。什葉派嚴格禁止歌唱的主題、內容、態度等違反伊斯蘭教義的音樂,比如酒歌、令人產生世俗欲望的歌、伴隨性暗示的歌,或者是過分夸張、冗長的歌等。提倡人們節省花費在合法娛樂上的時間,來進行宗教活動。
由于什葉派對音樂的態度相對寬松,我們也可以看到其代表性的樂器使用和音樂體裁類型。首先在樂器方面,“什葉派唯一較常始用的樂器是一種名為彈布爾(Tanbur)的伊朗長頸彈撥樂器”⑤同上。,這種樂器在土耳其稱為薩孜(Saz),并在在我國的新疆,特別是南疆的喀什、和田、庫車一帶都有廣泛的使用,這種樂器之所以在伊斯蘭世界中的什葉派能夠得到運用,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其性質上具有鮮明的宗教意義,比如“其琴身象征阿里的身體;琴頸象征阿里的用劍;十二條弦則象征十二伊瑪目(Imam)”⑥同上,第42頁,腳注。等。而這種宗教意義在整個東方社會當中都有著普遍的存在,比如祆教意義上的箜篌、佛教意義上的琵琶,以及符合“天地人”理念的古琴等。
除樂器之外,什葉派還有一種戲劇表演藝術體裁——塔茲葉(Ta'ziye,安慰的意思)。一般來講,由于伊斯蘭反對偶像崇拜,所以能夠體現人物形象的戲劇表演在伊斯蘭音樂當中的數量非常少。而什葉派的塔茲葉的出現和形成也與什葉派的教史、教派情懷、教徒心理有著密切的聯系。什葉派是在阿里黨人①穆罕默德逝世后,穆斯林內部曾在由誰擔任哈里發的問題上發生分歧。有人主張穆罕默德的權力應由其親屬中信教最早、追隨穆罕默德傳教有功的阿里來繼承,從而逐漸形成一個擁護阿里為哈里發的派別勢力,被稱作阿里黨人。反對伍麥葉王朝的斗爭中逐漸形成并發展的,其歷史發展中的標志性事件是:公元680年,阿里的兒子侯賽因(Husayn)作為當時先知穆罕默德僅存的外孫和阿里黨的領袖,在伊拉克的卡爾巴拉城進行的反對伍麥葉王朝的斗爭中被殺害。這一事件成為今天什葉派悲情心結的歷史起點。因此,什葉派的音樂也多表現為緬懷侯賽因的哀歌,及以他的受難為劇情的宗教戲劇——塔茲葉,紀念侯賽因的殉道是它的主要劇情和內容。
可見,在什葉派中,凡內容以伊斯蘭宗教、倫理、道德為主的音樂和樂器,基本上是合法且可演出的。
3.蘇非教團②文中之所以稱蘇非教團而不是蘇非教派主要是因為其不平行于伊斯蘭正統教派中,討論哈里發繼承權問題的遜尼派和爭論教法、教義是非問題的什葉派,因此,對它的稱呼一般用蘇非教團(sufi order或者sufi path,暗指伊斯蘭教派中的一個分支),而不適合被稱為蘇非教派。
蘇非教團于7世紀末到8世紀中葉形成于阿拉伯帝國統治的阿拉伯半島,是伊斯蘭教內部的神秘主義派別,更準確地說它是隨著阿拉伯帝國對外征戰的勝利,下層虔誠信徒對統治者產生嚴重不滿,而在伊斯蘭教內部產生的一種社會思潮。蘇非教團以《古蘭經》和《圣訓》為其學說的根據,沒有統一的教義。蘇非信徒專注于穆斯林品性的修養,通過認識真主,敬愛真主的修行,追求靈魂凈化。而他們實現這種修行和凈化的途徑即為音樂。
蘇非通過音樂達到修行的方式自然受到了如伊本·泰米亞等一批伊斯蘭正統派學者的批判。而就蘇非本身而言,他們一方面認同音樂的外在表現是一種誘惑,但更承認其內在所呈現的是一種勸誡,蘇非聆聽藉由音樂所指引出來的勸誡內含,來達到靈修和敬拜的目的。因此,音樂對蘇非來說是有著重大宗教意義的一部分。蘇非們相信音樂是精神食糧,它不僅能夠取悅真主安拉,并且可以幫助人們追求神的旨意,遠離世俗的煩惱,消除內心的私欲,達到與真主合一的精神修煉目標。因此,從伊斯蘭音樂發展的角度來說,蘇非教團貢獻巨大。
伊斯蘭蘇非的音樂廣泛分布在我國的西北地區、東南亞地區、西亞北非地區、北印度和巴基斯坦地區等,并作為世界音樂的一支逐漸取得了世界性的地位,為世人所熟悉和喜愛。比如我國新疆有大量的伊斯蘭蘇非音樂,周吉先生在多年南疆宗教音樂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指出:“現在所填唱的《十二木卡姆》的唱詞作者納瓦依、胡威達、夏麥西熱甫等人都是蘇非派伊斯蘭教的信徒。”③周吉:《中國新疆維吾爾族伊斯蘭教禮儀音樂》,新文豐出版社1999年。此外,伊斯蘭蘇非流浪歌手阿西克(意為癡迷于真主者),以及一些薩瑪儀式的蘇非音樂也都比較豐富,都塔爾、薩塔爾、熱瓦普、薩帕依、蘇乃依等樂器也是在新疆蘇非信徒的宗教音樂中廣泛使用的。而在印度尼西亞等非阿拉伯地區的伊斯蘭國家中,受佛教、印度教等其他宗教和當地傳統文化共同影響的蘇非伊斯蘭音樂、舞蹈類型也不在少數,比如北印度-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宗教歌Qawwali就是伴隨著伊斯蘭入侵印度,在傳入的薩瑪形式的基礎上于十三世紀前后發展成熟的。
此外還需補充的是,盡管伊斯蘭蘇非神秘主義十分強調音樂的重要性,更視音樂為人與真主阿拉溝通的主要媒介,卻也并不是所有音樂形態都被蘇非接受的,比如那些容易使人墮落、萎靡不振的音樂以及無法辨認其內容的純粹器樂作品也同樣是遭到禁忌的。伊斯蘭學者伊本拉杰(Ibn Rajab)就認為除了嚴肅音樂與以苦行為內容的音樂不應該被禁外,那些輕率與激發人們不良欲望的音樂都要禁。而純粹的器樂曲因無歌詞,不易辨認其內容,基本上也應該被禁止。原因是如果沒有正確的導引,音樂仍然有可能因為外在的誘惑而使人遠離阿拉的正道。總之,蘇非的立場和觀點對音樂在伊斯蘭世界的發展是一種維護,同時也是音樂使用的一種樣本,即在道德允許或者積極向上的情況下是可以使用音樂的。
通過上述論證可見,盡管伊斯蘭不同時代的政權統治者,以及各教派、教團對音樂的態度各有不同,但其基本原則和宗旨也同《古蘭經》和《圣訓》一樣,即僅排斥奢靡及不正當的音樂。
三、伊斯蘭擴張后地域文化語境中的音樂
根據美國皮尤調查公司發布的“全球穆斯林人口地圖”數據顯示,截止至2009年,穆斯林人口共16億,占全球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更有57個國家的大多數居民為穆斯林群體,伊斯蘭教也是近十年來全球擴張范圍最快、最廣的宗教。而脫離阿拉伯本土地區的背景后的地域伊斯蘭文化往往不能完全擺脫侵入地文化的原始風貌,呈現出宗教與政治的矛盾、本土文化與世界文明(特別是西方文明)的矛盾、自我傳統與外媒審視的矛盾、思維定式與現代社會發展的矛盾,以及離開穆斯林多數國家融入多元社會時如何生存的矛盾等等。這也直接使得原本就難以理清的伊斯蘭的音樂類型和音樂觀念變得更加復雜。
(一)本土文化與世界文明的矛盾
在阿拉伯世界內部即存在很多不同的音樂與音樂觀念劃分,且是與我們一般的思想認識以及西方的音樂理念所不同的。
首先在阿拉伯語地區的原始語境中,有很多與我們概念中與音樂相關的詞,但又都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概念上的音樂(Music)。它們分別是前文中論述過的Samā(傾聽)、Ghinā(歌唱,音樂實踐)以及Mūsīqī(音樂理論)等。在阿拉伯-伊斯蘭音樂文化當中,音樂實踐和音樂理論是被嚴格分開的,這是因為阿拉伯人認為比起善于推理和思考的音樂理論家來說,音樂家的社會地位很低,僅僅是簡單的實踐化和口頭傳播的工具;并且由于部份伊斯蘭宗教學者對音樂持有負面看法,不想讓宗教性吟誦與世俗性音樂混為一談之故,在伊斯蘭教的觀念中,宗教音樂和世俗音樂分屬于兩個不同的范疇,并在不同的范疇內有著各自的概念體系,應分開討論。
可見,無法用統一的詞匯(音樂,Music)涵蓋所有的伊斯蘭音樂,是對伊斯蘭音樂形式與音樂觀產生爭議的癥結之一。
(二)自我傳統與外媒審視的矛盾
作為世界三大宗教文化、五大地域文化之一的伊斯蘭文化,產生于公元7世紀的西亞、中東和北非,是在伊斯蘭信仰的基礎上,由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和突厥文化融合發展而成的。它有著西亞輝煌文明的古老根基,和強大的東方文明體系支撐。伊斯蘭對音樂的觀念、理解和稱呼自然也與西方社會,或者是現世較為流行的音樂觀念有著巨大的差異。
比如,呼禱調與《古蘭經》、穆罕默德生日誦唱等體裁聽起來都具有明顯的旋律、節奏等音樂要素,但穆斯林卻不將其列入音樂的范疇。其原因正是由于這種不同的文化環境對音樂的認知性與界定的差異。首先,由于《古蘭經》主要討論誦讀學、發音方法等理論,而不是討論實際的旋律、節奏等音樂問題,并且其音調樣式也是盡可能保持統一而不能有自由的發展,這與我們一般意義上的“音樂”有所不同,故不能稱其為“音樂”。而從宗教認同的角度來看,能夠嚴格履行伊斯蘭宗教修行的人,通常認為伊斯蘭宗教音聲以外的世俗娛樂音聲才是“音樂”,不能嚴格履行伊斯蘭宗教功修的人,則有可能認為宗教音聲也屬“音樂”范疇。一些年長或者是傳統的阿訇堅決捍衛伊斯蘭誦經音聲的宗教尊嚴,認為僅可稱其為“念”或“誦”,而不能用“唱”;而有的年輕阿訇以及普通教民則認為念經的“調”(音調)也可算為是“音樂”,只是大家一般不會這樣去講。甘肅臨清清真北寺掌教王阿訇所言就很好地概括了這種伊斯蘭宗教背景下的音樂觀:“清真寺是清靜之地,不可能有‘音樂’這樣的形式在此活動,盡管我們當中有不少教民愛聽京劇,但沒有人會在這里唱或哼上半句。我們其實也知道,單純從聽覺上來說,我們平常誦讀《古蘭經》和高聲贊圣就是一種‘音樂’,但說就不能那么說,因為那是一種褻瀆。”①王新磊:《宗教認同、族群認同與文化認同——從幾個不同角度淺議臨清回族人的音樂觀》,《藝術探索》2009年第6期。
不同身份背景和不同知識結構的人,或者說伊斯蘭宗教的局內人和局外人對于伊斯蘭音樂的理解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孰是孰非,也終究是一項糾纏不清的民族學問題,難下定論。因此,為了避免不同的觀點影響到這一傳統的完整性,音樂學者們開始使用“音聲”、“類音樂現象”、“聲音的藝術”等詞匯來嘗試解決類似的問題,以便體現穆斯林文化的獨特性。這也就如同在佛教、道教,以及各類儀式中使用“音聲”一詞來代替“音樂”一樣,其實際上是一種不同身份、文化、背景的人群對于同一事物叫法上的爭議和討論。
因此,局內與局外的不同稱謂與指代,是對伊斯蘭音樂形式與音樂觀產生爭議的癥結之二。
(三)伊斯蘭文化融入非伊斯蘭傳統多元社會的矛盾
隨著伊斯蘭在阿拉伯地區的發展和成熟,也逐漸開始向世界各地散播,原本信仰多神教、佛教、印度教等,并有著自己豐厚歷史與文化的諸多國家和地區逐漸改信了伊斯蘭教,縱然伊斯蘭教教義在對于異教傳統的改造上不斷發揮著作用,但也終究不能使之完全擺脫原始的本土傳統和文化遺留。于是,擁有豐富音樂舞蹈傳統的改信地區,在吸收了伊斯蘭的影響之后所形成的地域性伊斯蘭音樂的伴奏方式、歌詞內容、演出性質等都產生了多元化的發展,表現為世界各地伊斯蘭音樂枝繁葉茂的景象,與原生的伊斯蘭音樂文化具有了不同的形式和意義,有的甚至受到原伊斯蘭教義的否認和排斥。
以我國的地域化伊斯蘭文化為例,中國伊斯蘭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首先是“中國封建社會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中國穆斯林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的直接或間接的反映。”②馬啟成:《論‘中國伊斯蘭的大文化屬性’》,《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6期。在這種社會和文化背景的作用影響下,中國與伊斯蘭有關的維吾爾族、回族等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音樂中,伊斯蘭教沒有進入前的本土特色與伊斯蘭文化本身產生不同程度的碰撞,從而引發新的結果。
這一方面表現為在吸收伊斯蘭文化之后,原有音樂形式或整體音樂氛圍逐漸消亡的情況。這樣的情況主要發生在一些傳入地區本身不具有較為豐富且獨立的傳統音樂文化的地域,故當伊斯蘭教傳入之后,當地傳統無力呼應,只能無限服從伊斯蘭的傳統,由于當地文化與伊斯蘭文化之間的碰撞較少,缺少一種文化沖擊和改造的過程,因此,在這樣的地區的音樂中,除了原始阿拉伯吟誦音調之外,其它音樂形式的本真就會越來越相對弱化,甚至消失。例如我國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長期與漢族插花居住,客觀上的不穩定因素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其在進行民族文化的建設發展上勢單力薄,加之儒家“非禮勿視,非禮勿動,非禮勿聽”,墨家“不侈于后世,不靡于萬物,不暉于數度”等觀念的交叉影響,使得其發展極為滯后,造成的結果正如劉同生先生所說:“回族的音樂已經日趨衰落下去,造成了人們認為的‘伊斯蘭沒有音樂’的論點表面上的成立,但這事實上也不完全是伊斯蘭教規的影響。”③參見劉同生:《概說回族音樂》,《中國音樂學》1989年第3期。同理還有以伊斯蘭教教義為信仰之根本的撒拉族等。
另一方面表現為在吸收伊斯蘭音樂文化之后,再次并多次激發出某種文化的活力和生機(盡管有些事實上是背離伊斯蘭傳統的)。例如原本具有豐富音樂歌舞形式的維吾爾族,由于其長久以來一直保留著活躍的歌舞藝術形態,伊斯蘭文化進入后,也并沒有泯滅他們天生的載歌載舞的特性,反而使得這種民族文化在新的信仰當中萌發出更強烈的生命,木卡姆、阿西克、巴西克、薩瑪等伊斯蘭音樂形式在維吾爾族發展得十分成熟,且具有自己的特征。但其中大量所謂“伊斯蘭俗樂”的體裁有很多是從屬于伊斯蘭教傳入前的異宗教或異文化范疇的,比如我國西北伊斯蘭地區的花兒或宴席曲在我國西北地區早有流傳,不僅伊斯蘭信徒喜愛,漢族人也大量演唱,這部分音樂與伊斯蘭的關系較少,并且曖昧復雜,但卻有存在于信仰伊斯蘭教的地區,因此,由于排斥這類音樂而造成的“伊斯蘭禁樂、無樂”觀點也一定程度地存在著。
因此,受非伊斯蘭傳統的當地影響,使得伊斯蘭世界難有統一的音樂觀。是對伊斯蘭音樂形式與音樂觀產生爭議的癥結之三。
結語
綜上,由于伊斯蘭教義《古蘭經》和《圣訓》中沒有對音樂的內容做出贊同或排斥的明確規定,使得伊斯蘭在各歷史發展階段,以及不同的教派、教團依照各自的利益和喜好規定自己的音樂觀,使得音樂的應用和音樂觀在伊斯蘭世界產生不同層面的理解與解釋,未形成固化的體系。而后世的學者和民眾往往受西方觀念的影響,拿音樂(music)一詞去與伊斯蘭音樂相對應比照,并較少考慮到地域化的伊斯蘭音樂等原因,就不免引起了一些對伊斯蘭音樂問題的爭論,使伊斯蘭音樂的研究陷入窘境。對此我們必須承認的是,在伊斯蘭教史上,確實有過某些國家的統治者禁止音樂或娛樂的事情,也有過關于音樂是否合法的爭論。而事實上,伊斯蘭宗教、派別、地域、文化、體裁等的復雜多樣性才是造成我們如今難以界定伊斯蘭音樂類型的關鍵之所在。
針對以上伊斯蘭音樂的分析,筆者進一步對伊斯蘭音樂研究的方法做幾點初步的思考,期待著伊斯蘭音樂研究的展開。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對伊斯蘭音樂做幾個歸類和區分,而不應一概看待。首先,阿拉伯地區的伊斯蘭音樂與世界化的伊斯蘭音樂,以及正統派的伊斯蘭音樂和蘇非教團等的伊斯蘭音樂不應一概而論,它們應有各自的概念、所致及特征。其次,伊斯蘭宗教音樂、伊斯蘭世俗音樂、伊斯蘭宗教-世俗音樂、伊斯蘭宗教儀式音樂等伊斯蘭音樂類型也應各有內涵、區分看待。第三,伊斯蘭音樂內部的歌唱、器樂、音樂理論等形式也應在研究時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樣,伊斯蘭發展過程中果斷形成的復雜音樂觀念和音樂形式,才能夠得到清楚的梳理和正確的認識。
[1]希提著、馬堅譯:《阿拉伯通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79年。薩米·哈菲茲著、王瑞琴譯:《阿拉伯音樂史》,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0年。
[2]【埃及】穆罕默德·胡澤里著、秦德茂、田希寶譯:《穆罕默德傳》,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
[3]岸邊稱雄著、郎櫻譯:《伊斯蘭音樂》,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9月。
[4]約·阿·克雷維列夫著、樂峰等譯校:《宗教史》(下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
[5]劉同生:《概說回族音樂》,《中國音樂學》1989年第3期。
[6]艾哈邁德·愛敏著、納忠譯:《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商務印書館1990年。
[7]劉富禎:《西北伊斯蘭文化板塊分割析論》,《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
[8]肖海林:《談阿拉伯文化的世俗性》,《阿拉伯世界》1991年3月。
[9]馬堅譯:《古蘭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10]田青主編:《中國宗教音樂》,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5月。
[11]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Stanley Sadie,2001。
[12]金宜久、任繼愈:《伊斯蘭教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13]蔡宗德:《傳統與現代性:印度尼西亞伊斯蘭宗教音樂文化》,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8月。
[14]布哈里著、祈學義譯:《布哈里圣訓實錄全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1月。
[15]馬蘭:《呼和浩特市回族伊斯蘭教音樂的調查與研究》,內蒙古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
[16]王慧芹:《穆斯林的音樂觀》,《世界文化》2009年6月。
[17]王新磊:《宗教認同、族群認同與文化認同——從幾個不同角度淺議臨清回族人的音樂觀》,《藝術探索》2009年第6期。
[18]蔡宗德:《伊斯蘭世界音樂文化》,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2月。
2016-05-11
J608
A
1008-2530(2016)02-0062-11
王雅婕(1986-),女,上海音樂學院2013級博士研究生(上海,20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