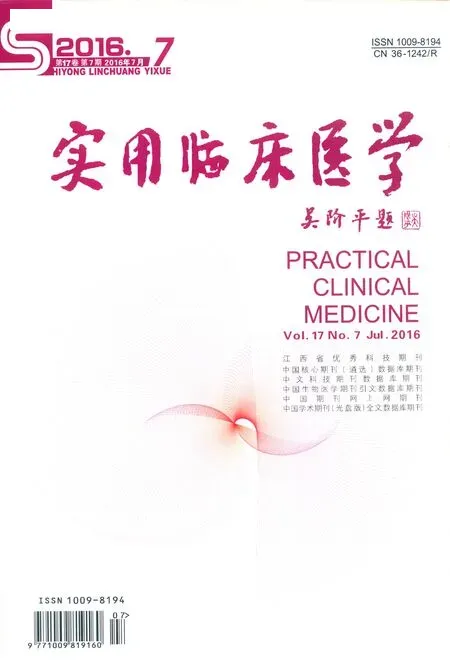兒童膿毒性休克的診療進展
劉 赟
(南昌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兒科,南昌 330006)
?
兒童膿毒性休克的診療進展
劉赟
(南昌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兒科,南昌 330006)
膿毒性休克; 膿毒癥; 兒童
膿毒癥在早期被定義為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SIRS),是創傷、燒傷、感染及休克等臨床危重癥患者最嚴重的并發癥,也是誘發膿毒性休克及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MODS)的重要原因之一[1-2]。而在2012年的膿毒癥國際指南[3]中,膿毒癥定義為存在可以或證實的感染,并伴有感染的全身系統表現。其中關于兒童膿毒性休克,目前我國的診療指南在國際指南[3]的指導下制定了2015版《兒童膿毒性休克(感染性休克)診治專家共識》[4]。第三次膿毒癥和膿毒性休克定義國際共識中定義膿毒癥是指感染引起的失調的宿主反應導致危機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礙,這個定義強調感染引發的非穩態宿主反應的重要性,這種反應超出直接感染本身的可能致死性[5]。共識進一步對臨床診斷標準做出了調整并提出了使用SOFA評分(序貫性器官功能衰竭評估)對臨床感染可疑病例中進行篩選,而該評分只制定出針對成人評估的定義跟標準,在基層醫院兒童感染病人中,SOFA評分2分以上者病死率達10%[6-7],膿毒性休克的病死率達40%。由于兒童生理發育的特殊性,尤其是新生兒,活產嬰兒中發生膿毒癥的概率為1/1000~21/1000,其病死率達30%~69%[8]。
國內兒科專家對兒童膿毒性休克的定義作了一些調整,更早更好地診斷兒童膿毒癥及膿毒性休克是及早干預治療的基礎,本文對兒童膿毒癥及膿毒性休克的診療進展作一綜述。
1 病因及發病機制
1.1病原
膿毒癥最常見的致病菌為革蘭陰性細菌,而在兒童膿毒癥的病原學檢查中以大腸埃希菌、克雷伯桿菌和銅綠假單胞菌等為主。近年來,隨著致病因素復雜、細菌耐藥性不斷變化,特別是耐萬古霉素金黃色葡萄球菌、耐萬古霉素腸球菌的出現,使得膿毒癥的致病菌變得多樣化(革蘭陽性菌膿毒癥的發病率逐年上升,其中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位居首位)。在我國兒童病原學分布,李斌等[9]對所在醫院近10年的診斷膿毒癥住院患兒68 419例研究中得出結論,革蘭陽性球菌感染占主導地位,病原菌前5位依次為凝固酶陰性葡萄球菌(CNS,以表皮葡萄球菌為主)、大腸埃希菌、非發酵菌、腸球菌、沙門氏菌,有別于成人。
1.2發病機制
膿毒癥的發病機制復雜,病理過程涉及炎癥、免疫、凝血功能及組織損害等一系列問題,并與機體多系統、多器官病理生理性改變密切相關。
1.2.1炎癥
膿毒癥炎癥的發生與促炎因子、抗炎因子及炎癥細胞嚴密相關,并由多種信號通路介導炎癥的發生。1)促炎性因子:如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白介素(IL)-1、IL-6、高遷移率族蛋白B1(HMGB1)等,促炎因子通過促進自由基、緩激肽、組胺等物質的產生,激活補體,加重組織的損傷,這種機制主要涉及促炎因子,TNF-α、IL-1、IL-6均屬于早期促炎因子,而HMGB1被認為是晚期促炎因子,參與晚期脂多糖(LPS)的致病過程。2)抗炎因子:如IL-4、IL-10、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在膿毒癥期間,抗炎因子的濃度逐漸升高,能抑制炎癥反應,而膿毒性休克的患者往往由于炎性細胞不能得到有效激活,抗炎因子產生不足,促炎因子和抗炎因子之間的動態平衡被破壞,機體發生免疫抑制,導致膿毒癥病情加重[10]。3)炎癥細胞:如中性粒細胞、單核細胞/單核巨噬細胞、T淋巴細胞等。膿毒癥早期,T淋巴細胞亞群的選擇性缺失將促進病情進展[11],而減少T淋巴細胞的丟失有利于機體清除病原體,促進膿毒癥患者的康復。不同的輔助性T淋巴細胞(Th細胞)在膿毒癥中具有不同的作用,Th1細胞生成IL-2、IL-12和IFN-γ等促炎因子,促進炎癥反應。Th2細胞生成IL-4和IL-10等抗炎因子,抑制炎癥反應。調節性T淋巴細胞是一種具有負性調節作用的T淋巴細胞亞群,通過抑制Th1細胞活性或增加Th2細胞活性,調節促炎、抗炎平衡,發揮抗炎作用。4)在膿毒癥時,這些炎癥的發生發展是炎癥因子通過激活多種信號通路,從而實現對體內炎癥發生的調控,加重或減輕組織的損傷。常見的信號通路有核因子κB(NF-κB)通路、絲裂原激活蛋白激酶(MAPK)通路、JAK/STAT通路及磷脂酰肌醇3激酶通路(PDK/Akt通路)。
1.2.2免疫
嚴重感染及膿毒性休克能迅速激活機體的炎性應激反應,動員全身免疫系統參與應激過程。近年來,有學者[12]發現在膿毒癥的發病過程中,機體免疫激活狀態呈連續性、變化性,在嚴重創傷、感染及膿毒性休克時機體不僅出現過度的炎癥反應,而且存在嚴重細胞免疫功能紊亂。除中性粒細胞、單核細胞/單核巨噬細胞及T淋巴細胞這些參與的免疫調節之外,尚有自然殺傷T細胞(NK-T細胞)及樹突狀細胞(DC細胞)。NK-T細胞的活化在膿毒癥早期調節免疫、調節全身炎癥反應及改善生存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膿毒癥的早期,NK-T細胞能精確地啟動和調節炎癥和免疫級聯反應,在LPS誘導內毒素血癥模型中,NK-T細胞含量增多,可產生大量γ干擾素(IFN-γ),促進炎癥的發生,但抗炎因子IL-4含量微乎其微,從而使組織細胞受損。幼稚NK-T和NK細胞檢測出CSaR和C5L2 mRNA表達,提示CSaR缺乏的NK-T細胞血清中IFN-γ和TNF-α減少,生存率大大提高。DC細胞在病原體識別和誘導特異性免疫反應以消除感染宿主病原體中非常重要,它們是專職抗原遞呈細胞,擅長瞄準、俘獲抗原從二級淋巴組織運輸到淋巴器官。DC細胞在不同條件下展現不同的功能來實現生物效應,當非特異性免疫系統被抗原微生物和器官損害所激活,DC細胞在遞呈外源性抗原和同質抗原的同時,也激活T淋巴細胞,誘導Treg增值,從而決定炎癥和抗炎的免疫反應的類型。
1.2.3凝血
嚴重的膿毒癥總是伴隨著凝血功能的改變,經常導致彌漫性血管內凝血,導致過多的纖維蛋白沉積的原因主要有3個:凝血系統激活、抗凝機制受損或者纖維蛋白溶解系統受損[13]。
凝血功能異常在膿毒癥早期即出現,貫穿于膿毒癥病理發展過程,嚴重時導致患者死亡,是影響膿毒癥發生、發展和預后的關鍵因素。血小板為人體主要凝血活性物質之一,從病理角度分析,血小板異常往往預示著體內較嚴重的血栓和炎癥,其直接區域為損傷血管內皮系統,從一定程度上標志著微循環系統的衰退,死亡危險因素增加。謝云惠等[14]通過對小兒膿毒癥死亡的臨床指標及原發病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血小板為小兒膿毒癥的獨立危險因素。
纖維蛋白的積聚促進凝血,包括以下幾個關鍵環節:1)組織因子的活化,組織因子是多種細胞均可表達的一種跨膜糖蛋白;2)削弱抗凝機制,包括CRP系統和抗凝血酶;3)抑制纖溶系統引起的交聯的纖維蛋白;4)分子鏈接、蛋白水解活化酶受體形成凝血和炎癥之間的分子鏈接[15]。因此可見,凝血功能主要通過凝血因子產生大量的纖維蛋白,而天然的蛋白C能特異性抑制部分凝血因子,如Ⅴa和Ⅶa,從而改善膿毒癥的凝血功能及預后[16]。
1.2.4組織及器官損傷
Merx等[17]在研究中發現,膿毒癥患者中有近50%存在心功能異常,而心肌組織失控性炎癥反應是導致膿毒癥心肌損傷的關鍵環節[18-19],炎癥反應對組織和器官的損傷均由血管內皮屏障功能障礙引起[20]。膿毒癥心肌損傷發病機制極其復雜,是多因素和多通路參與的結果,其中血清中存在許多可引起心肌抑制的物質,如細菌毒素、Toll樣受體(TLR)、補體系統、巨噬細胞移動抑制因子(MIF)等,這些物質相互作用、共同參與膿毒癥心肌損傷的發病過程;此外NO、心肌細胞鈣穩態失衡、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RASS)的改變、自主神經失調及腎上腺信號肽的改變均參與了心肌損傷的過程[21],而心肌線粒體損傷、氧化應激、細胞凋亡被發現是膿毒癥心肌損傷最重要的機制之一。
膿毒癥過程中腎臟的內皮細胞同樣是炎性因子首要攻擊的靶細胞之一,刺激后生成炎性因子。在臨床工作中,膿毒癥合并腎臟功能受損時,治療難度明顯增加,耗費巨大的醫療資源和巨額醫療費用,預后大多不佳。膿毒癥致急性腎損傷的機制可能與感染病原體所釋放的毒素、活化的炎性細胞及炎性介質釋放,激活Toll樣受體4,經過一系列級聯信號傳遞,相互促進,形成炎癥瀑布,進而啟動后續的一系列病理生理改變,導致急性腎損傷。孫小聰等[22]研究表明降低中性粒細胞明膠酶相關脂質運載蛋白(NGAL)、尿腎損傷分子-1(KIM-1)、血清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劑C(CysC)、IL-18水平,對膿毒癥所致急性腎損傷具有一定的腎臟保護作用。
有研究[23]發現,膿毒癥患者血管內皮表層受損,導致血清內皮細胞硫酸乙酰肝素蛋白聚糖(HSPG)及多配體蛋白聚糖(SDC-1)濃度增高,肺血管內皮細胞HSPG及SDC-1脫落,導致中性粒細胞黏附,誘發炎性反應。HSPG和SDC-1在維持血管通透性、抑制細胞間黏附中起重要作用,Nelson等[24]研究發現,膿毒性休克患者血漿葡胺聚糖鏈與多配體蛋白聚糖濃度顯著高于健康志愿者,且葡胺聚糖鏈濃度與死亡率呈正相關。脂多糖、局部缺血再灌注、高血糖等均通過蛋白酶破壞糖萼蛋白,進而導致HSPG和SDC-1脫落,使血管內皮表面黏附分子外露、中性粒細胞黏附,導致微血管滲透性增高[25]。HSPG是蛋白聚糖中最具生物活性的一類,具有維持血管壁的抗凝表面、維持血管通透性、抑制細胞黏附等多種生物學功能[26]。SDC-l屬于黏附分子整合素跨膜黏結蛋白聚糖家族成員,可抑制白細胞的黏附,抑制促炎因子的活性,參與炎性反應[27]。
2 診斷
2.1膿毒性休克
嚴重膿毒癥被公認為無效,而膿毒性休克被重新定義為出現組織灌注不足和心血管功能障礙的膿毒癥患者,在兒童病人中具體表現如下。1)低血壓(血壓<該年齡組第5百分位,或收縮壓<該年齡組正常值2個標準差以下)。2)需用血管活性藥物始能維持血壓在正常范圍(多巴胺5 μg·kg-1·min-1或任何劑量的多巴酚丁胺、去甲腎上腺素、腎上腺素)。3)具備下列組織低灌注表現中3條,①心率、脈搏變化:外周動脈搏動細弱,心率、脈搏增快(各年齡組心率變量:≤1周,180次·min-1<心率<100次·min-1;1周~1個月,180次·min-1<心率<100次·min-1;1個月~1歲,180次·min-1<心率<90次·min-1;1~6歲,140次·min-1<心率<60次·min-1;6~12歲,130次·min-1<心率<60次·min-1;12~18歲,110次·min-1<心率<60次·min-1)。②皮膚改變:面色蒼白,可見大理石樣花紋,肢端濕冷,暖休克則表現為四肢肢端溫暖、皮膚干燥。③除外環境溫度影響下毛細血管再充盈時間(CRT)延長(>3 s),暖休克時CRT可以正常。④意識改變:早期煩躁不安或萎靡,表情淡漠;晚期意識模糊,甚至昏迷、驚厥。⑤液體復蘇后尿量仍為0.5 mL·kg-1·h-1,持續至少2 h。⑥乳酸性酸中毒(除外其他缺血缺氧及代謝因素等),動脈血乳酸>2 mmol·L-1[4]。
2.2膿毒性休克分期
2.2.1代償期
兒童膿毒性休克的診斷不一定具備低血壓。當患兒感染后出現上述3條或以上組織低灌注表現,即使血壓正常也診斷為膿毒性休克代償期。
2.2.2失代償期
代償期灌注不足表現加重伴血壓下降,則進展為失代償期。各年齡組血壓變量:≤1個月,收縮壓<60 mmHg(1 mmHg=0.133 kPa);1個月~1歲,收縮壓<70 mmHg;1~9歲,收縮壓<70+2×年齡 mmHg;10歲,收縮壓<90 mmHg)[4]。
2.2.3休克分型
1)冷休克:除意識改變、尿量減少外,皮膚蒼白或可見花斑紋,四肢肢端濕冷,外周脈搏快、細弱,CRT延長。休克代償期血壓正常或稍有降低,而休克失代償期則可見血壓降低。
2)暖休克:可有意識改變、尿量減少或代謝性酸中毒等表現,但皮膚尚干燥,無皮疹,四肢溫暖,外周脈搏有力,CRT正常,心率快,血壓降低。
毛細血管充盈時間、外周脈搏搏動、皮膚花斑是判斷冷休克與暖休克的標準;毛細血管充盈時間≤2 s或外周脈搏搏動有力或無皮膚花斑即為暖休克,反之則為冷休克。
3 治療
3.1初階復蘇目標
一經診斷為膿毒性休克,應在6 h內達到下一初階目標:CRT≤2 s,血壓正常(同等年齡),脈搏正常且外周和中央搏動無差異,肢端溫暖,尿量1 mL·kg-1·h-1,意識狀態正常。如果條件允許,可向實現以下目標:中心靜脈壓(CVP)8~12 mmHg(11.064~1.596 kPa),中央靜脈混合血氧飽和度(ScvO2)≥70%,心臟指數(CI)3.3~6.0 L·min-1·m-2),初始液體復蘇時血乳酸增高者復查血乳酸至正常水平,血糖和離子鈣濃度維持正常[28-29]。
3.2抗感染
要求在使用抗生素前,取得血培養及其他感染源培養,診斷為膿毒癥或膿毒性休克1 h內應選用靜脈使用抗感染藥物治療,選擇合適的抗生素,在血培養及藥敏結果未出之前,應根據對感染的部位等情況及當地應用抗生素的敏感性情況來選擇,一般首選廣譜抗生素。如果之后各種檢查結果,如血培養、降鈣素原等不支持感染,那么可以考慮停用抗生素,以免產生耐藥。此外,規范選取清創術、引流、沖洗、修補、去除感染裝置等輔助措施,盡快確定和去除感染灶顯得同樣重要。有研究[30]表明,烏司他丁可增強抗生素的作用,必要時可選用。
3.3呼吸循環支持
有膿毒性休克的患兒,因組織低灌注,體內各組織器官呈現缺氧缺血表現,因此一旦診斷膿毒性休克,需早期給予氧療以保證各組織臟器功能,在保證氣道暢通的情況下,先給予高流量鼻導管供氧或面罩氧療,如鼻導管或面罩氧療無效,則予以無創正壓通氣或盡早氣管插管機械通氣。在插管前,如血流動力學不穩定應先行適當的液體復蘇或血管活性藥物輸注,以避免插管過程中加重休克。如果患兒對液體復蘇和外周正性肌力藥物輸注無反應,應盡早行機械通氣治療。通過液體復蘇達到最佳心臟容量負荷,應用正性肌力藥以增強心肌收縮力,或應用血管舒縮藥物以調節適宜的心臟壓力負荷,最終達到改善循環和維持足夠的氧輸送。
3.3.1血管活性藥物
在液體復蘇無效的膿毒性休克,可加用血管活性藥物治療,如多巴胺、多巴酚丁胺、腎上腺素和去甲腎上腺素等。在兒科,這些正性肌力藥物為一線藥物,如果患兒心臟功能較低下,也可選用米力農,注意藥物使用時間以免產生蓄積性中毒。
3.3.2液體復蘇
膿毒癥尤其是并發有膿毒性休克患兒,目前關于是否采用積極的液體復蘇治療存在著爭議,從常規的病理生理分析來看,積極的液體復蘇有助于恢復循環血量,保護各組織臟器。但也有研究[31-32]表明大量快速的液體復蘇可導致液體負荷過重,進而引起臟器組織水腫,加劇多臟器功能衰竭的發生。因此,在使用液體復蘇治療的同時,應嚴格監測患兒意識、心率、尿量、血壓等指標。
3.4糖皮質激素
糖皮質激素是最早應用于膿毒癥治療的藥物,能抑制免疫反應,從而降低TNF-α、IL-1、IL-6、IL-8和IFN-γ等促炎因子的合成與釋放,同時抑炎因子IL-10水平較前增高。目前對使用糖皮質激素使用的看法尚不統一,有部分學者[28]發現持續使用低劑量或生理劑量糖皮質激素對腎上腺功能低下的膿毒癥患者是有益的,但長時間使用糖皮質激素有免疫抑制的風險,該觀點尚存爭議。2012版《嚴重膿毒癥與膿毒性休克治療國際指南》[3]指出對成人膿毒性休克患者,需先予充分液體復蘇和血管升壓治療,如可恢復血流動力學穩定,則不需使用糖皮質激素;若不能恢復穩定,則建議給予氫化可的松200 mg·d-1靜脈注射,并建議不采用促腎上腺皮質激素(ACTH)刺激試驗來確定哪些亞組患者應接受糖皮質激素治療,而且對于無休克的膿毒癥患者,不推薦應用激素。
3.5強化胰島素治療
高血糖與胰島素抵抗在膿毒癥患者中很常見,高血糖因其可能導致凝血功能異常、誘導細胞凋亡、降低中性粒細胞功能,導致傷口感染概率增高,傷口愈合時間延長,被認為是死亡率升高的獨立危險因素之一,影響膿毒性休克患者的預后。而胰島素具有抗炎、抗凝和抗凋亡等活性,利用強化胰島素治療能降低死亡率,還能降低敗血癥、需要透析的急性腎功能衰竭、輸血的發生率,同時機械通氣的時間會不同程度的縮短,還可降低血清CRP水平[33]。
3.6調節凝血功能
2001年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將重組人活化蛋白用于膿毒癥的輔助治療,使嚴重膿毒癥死亡率降低了6.1%[34],不僅對蛋白C水平較低的膿毒癥患者有效,對蛋白C水平正常的其他膿毒癥患者同樣有效,且長期使用對器官功能也有所改善,曾經重組人活化蛋白是唯一上市的用于防治膿毒癥的藥物。但2011年活性蛋白C已正式退市,目前尚無切實有效的藥物防治該疾病。
3.7連續血液凈化
膿毒性休克由于組織灌注功能降低,易出現急性腎功能損傷(AKI)或急性腎衰竭。以下3種情況均建議使用連續血液凈化治療:1)AKI Ⅱ期;2)膿毒癥至少合并一個器官功能不全;3)休克糾正后存在液體負荷過多經利尿劑治療無效,總液量負荷超過體質量的10%[35]。
3.8體外膜肺氧合
如醫療條件允許可對難治性休克或伴有ARDS的嚴重膿毒癥患兒行體外膜肺氧合治療。
3.9其他
3.9.1血液制品
若紅細胞比容(HCT)<30%伴血流動力學不穩定,可酌情輸注紅細胞懸液,使血紅蛋白維持100 g·L-1以上。如病情穩定后或休克和低氧血癥糾正后,則血紅蛋白目標值]為70 g·L-1即可。血小板10×109L-1(沒有明顯出血)或血小板20×109L-1(伴明顯出血),應預防性輸血小板;當活動性出血、侵入性操作或手術時,需要維持較高血小板(≥50×109L-1)[4]。
3.9.2丙種球蛋白
對膿毒癥及膿毒性休克患兒可考慮使用靜脈輸注丙種球蛋白。
3.9.3鎮痛、鎮靜
使用機械通氣的膿毒性休克患兒應給予適當鎮痛鎮靜治療,能降低氧耗和有利于器官功能保護。
3.9.4營養支持
膿毒性休克的患兒在能耐受腸道喂養的情況下應盡早予以腸內營養支持,如不耐受則予以腸外營養。
4 小結
目前臨床的各種治療方案如氧療、液體復蘇、廣譜抗生素、機械通氣、糖皮質激素、強化胰島素治療和重組人類活化蛋白 C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膿毒癥的治愈率,膿毒性休克的死亡率仍居高不下。盡管目前對膿毒癥的研究一直在繼續,但是在臨床工作中,該病進展迅速,預后不佳,在治療上仍未取得重大突破。相信在急救醫學對膿毒癥的機制及治療研究發展中會有新的靶點及突破,最終將有效控制膿毒癥。
[1]O’Brien J M Jr,Lu B,Ali N A,et al.Insurance type and sepsis-associated hospitalizations and sepsis-associated mortality among US adults: a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J].Crit Care,2011,15(3):R130.
[2]Haasper C,Kalmbach M,Dikos G D,et al.Prognostic value of procalcitonin(PCT) and/or interleukin-6(IL-6) plasma levels after multiple trauma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 or sepsis[J].Technol Health Care,2010,18(2):89-100.
[3]Green J P,Adams J,Panacek E A,et al.The 2012 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management of severe sepsis and septic shock:an update on the guidelines for initial therapy[J].Curr Emerg Hosp Med Rep,2013,1(3):154-171.
[4]中華醫學會兒科學分會急救學組,中華醫學會急診醫學分會兒科學組,中國醫師協會兒童重癥醫師分會.兒童膿毒性休克(感染性休克)診治專家共識(2015版)[J].中華兒科雜志,2015,53(8):576-580.
[5]Singer M,Deutschman C S,Seymour C W,et al.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definitions for sepsis and septic shock (sepsis-3)[J].JAMA,2016,315(8):801-810.
[6]Seymour C W,Liu V X,Iwashyna T J,et al.Assessment of clinical criteria for sepsis: for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definitions for sepsis and septic shock (sepsis-3)[J].JAMA,2016,315(8):762-774.
[7]Shankar Hari M,Phillips G S,Levy M L,et al.Developing a new definition and assessing new clinical criteria for septic shock:for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definitions for sepsis and septic shock(sepsis-3)[J].JAMA,2016,315(8):775-787.
[8]Fanos V,Caboni P,Corsello G,et al.Urinary (1)H-NMR and GC-MS metabolomics predicts early and late onset neonatal sepsis[J].Early Hum Dev,2014,90(S 1):S78-S83.
[9]李斌,肖曙芳,何娟.小兒膿毒血癥病原分析[J].中國現代醫藥雜志,2014(10):45-48.
[10]Boomer J S,To K,Chang K C,et al.Immunosuppression in patients who die of sepsis and multiple organ failure[J].JAMA,2011,306(23):2594-2605.
[11]趙劭懂,葛許華,蔡愛東,等.T細胞亞群選擇性缺失對小兒膿毒癥發生發展的影響[J].實用兒科臨床雜志,2010,25(18):1386-1388.
[12]黃鶴,田昭濤,黎檀實.膿毒癥免疫調節機制研究進展[J].中華實驗外科雜志,2016,33(3):841-845.
[13]Levi M,van der Poll T.Inflammation and coagulation[J].Crit Care Med,2010,38(S 2):S26-S34.
[14]謝云惠,沈曉翠.小兒膿毒血癥死亡的相關危險因素分析[J].醫學理論與實踐,2015(12):1559-1560.
[15]Warren H S,Suffredini A F,Eichacker P Q,et al.Risks and benefits of activated protein C treatment for severe sepsis[J].N Engl J Med,2002,347(13):1027-1030.
[16]李益星,陸二梅,楊勇,等.膿毒癥的發病機制研究[J].藥學研究,2016,35(5):290-294.
[17]Merx M W,Weber C.Sepsis and the heart[J].Circulation,2007,116(7):793-802.
[18]Rudiger A,Singer M.Mechanisms of sepsis-induced cardiac dysfunction[J].Crit Care Med,2007,35(6):1599-1608.
[19]Li L,Hu B C,Chen C Q,et a1.Role of mitochondrial damage during cardiac apoptosis in septic rats[J].Chin Med J,2013,126(10):1860-1866.
[20]London N R,Zhu W,Bozza F A,et a1.Targeting Rob04-dependent Slit signaling to survive the cytokine storm in sepsis and influenza[J].Set Transl Med,2010,2(23):23ral9.
[21]耿麗娟,李素瑋,張永利,等.膿毒癥心肌損傷發病機制的研究進展[J].中華內科雜志,2015,54(1):77-80.
[22]孫小聰,邵義明,黃河,等.烏司他丁對膿毒癥急性腎損傷腎功能的保護作用[J].中華實驗外科雜志,2015,32(4):910-912.
[23]Steppan J,Hofer S,Funke B,et al.Sepsis and major abdominal surgery Lead to flaking of the endothelial glycocalix[J].J Surg Res,2011,165(1):136-141.
[24]Nelson A,Berkestedt I,Schmidtchen A,et al.Increased levels of glycosaminoglycans during septic shock:relation to mortality and the antibacterial actions of plasma[J].Shock,2008,30(6):623-627.
[25]Curry F E,Adamson R H.Endothelial glycocalyx:permeability barrier and mechanosensor[J].Ann Biomed Eng,2012,40(4):828-839.
[26]Schmidt E P,Yang Y,Janssen W J,et al.The pulmonary endothelial glycocalyx regulates neutrophil adhesion and lung injury during experimental sepsis[J].Nat Med,2012,18(8):1217-1223.
[27]Teng Y H,Aquino R S,Park P W.Molecular functions of syndecan-1 in disease[J].Matrix Biol,2012,31(1):3-16.
[28]Dellinger R P,Levy M M,Rhodes A,et al.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for management of severe sepsis and septic shock:2012[J].Crit Care Med,2013,41(2):580-637.
[29]Brierley J,Carcillo J A,Choong K,et al.Clinical practice parameters for hemodynamic support of pediatric and neonatal septic shock:2007 update from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J].Crit Care Med,2009,37(2):666-688.
[30]張思敏,徐俊,李俊華.烏司他丁增強抗生素治療兒童細菌致膿毒血癥療效的機制研究[J].中國生化藥物雜志,2014,34(2):125-127.
[31]Maitland K,Kiguli S,Opoka R O,et al.Mortality after fluid bolus in African children with severe infection[J].N Engl J Med,2011,364(26):2483-2495.
[32]ProCESS Investigators,Yealy D M,Kellum J A,et al.A randomized trial of protocol-based care for early septic shock[J].N Engl J Med,2014,370(18):1683-1693.
[33]祝益民.兒童膿毒癥高血糖控制的研究進展[C]//中華醫學會急診醫學分會第十五次全國急診醫學學術年會論文集.長沙:中華醫學會急診醫學分會,2012:205-206.
[34]Bernard G R,Vincent J L,Laterre P F,,et al.Efficacy and safety of recombinant human activated protein C for severe sepsis[J].N Engl J Med,2001,344(10):699-709.
[35]中國醫師協會重癥醫學醫師分會兒科專家委員會.中華醫學會兒科學分會急救學組,中華醫學會急診醫學分會兒科組.連續血液凈化治療兒童嚴重膿毒癥的專家共識[J].中華兒科雜志,2012,50(9):678-681.
(責任編輯:鐘榮梅)
2016-06-16
R631+.4
A
1009-8194(2016)07-0097-05
10.13764/j.cnki.lcsy.2016.07.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