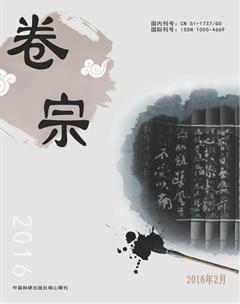玄燁的理學成就對滿族哲學發(fā)展的意義
摘 要:滿族哲學在一定意義上帶有一定宗教性,其中的宗教觀和天命觀在與儒學的融合交流中發(fā)生了轉(zhuǎn)變,儒學是提倡入世的哲學,對滿族哲學在治世安民上有一定借鑒意義。康熙統(tǒng)治年間,為了鞏固清王朝的政權(quán),大力提倡程朱理學。玄燁本人也是提倡真理學,反對假理學,提倡實學。這些哲學文化思想觀念一方面維護了清王朝的統(tǒng)一,另一方面也促進了滿漢哲學思想文化的交融互進。我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由多民族交流融合形成的多元文化,對包括滿族哲學及其代表人物在內(nèi)的少數(shù)民族哲學及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我國多民族文化的整體繁榮,有利于進一步增強民族團結(jié)和社會和諧穩(wěn)定。
關(guān)鍵詞:玄燁;理學;滿族哲學
基金項目:西南民族大學研究生“創(chuàng)新型科研項目”(CX2015SP451)成果。
清朝康熙帝玄燁是一位頗富影響的治者,又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哲人、思想家。他非常推崇程朱理學,并且體現(xiàn)在他的政治思想中。他踐行以“理”治國,強調(diào)實學,他的認識論思想帶有經(jīng)驗論和重實踐的特點,這點與理學“知先行后”說有很大差別,對滿族的文化、歷史及哲學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通過例舉清朝康熙帝玄燁對程朱理學的推崇,來揭示作為儒學的程朱理學對滿族哲學思想的融合與促進,對玄燁治國理政實踐活動的影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玄燁的理學思想是與經(jīng)世致用之學相融合的,對改善當時社會風氣、發(fā)展社會生產(chǎn)力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1 玄燁的理學成就及其特色
第一,堅持“理本論”。玄燁堅持“理本論”這一觀念,并認為“天地古今,大本大原,只是一理”由天到地,從古至今的萬事萬物的本原皆在一個“理”字,僅由這一句還不能看出玄燁口中的這個“理”字的具體屬性。“有一事必有一事之理,有一物必有一物之理,從此推去,自有所得,求之而失于過,不得其理也;求之而失于不及,亦不得其理也。唯一中即是無私,無私而后得其理。”此句表明一件事情的存在是有它存在的道理的,一個事物的存在也有它存在的道理,按照這個邏輯來推理,便可有所體悟。但是如何去尋求這一“理”呢?過于強求的話是體悟不到的,功夫不及之處也無法體悟,只有匡正其心摒棄私欲才可體悟到“理”的存在。玄燁所謂的“理”是精神性的而并非物質(zhì)性的,并且與朱熹的“理”有所不同。玄燁所學雖然秉承朱熹,但是由于二人身份地位的差異,使得他們對“理學”的內(nèi)涵及功用的看法有所不同,如果把朱熹的“理”概括為封建社會倫理綱常之理的話,那么玄燁的“理”就可以理解為是治國安邦之理。朱熹的主要思想是為封建統(tǒng)治服務的,因此深受當時統(tǒng)治者的推崇,他的思想可以幫助統(tǒng)治者把天下百姓教化成“順民”,磨滅他們的反抗意識,成為天子的絕對擁護者;而玄燁則是站在更高的角度來論及的,他要力證封建秩序存在的合理性,他深知理學對中原人士的影響之大,因此通過對理學的推崇與弘揚征服了廣大中原人士的心。除此之外,通過對玄燁宇宙觀的研究可以看出,他認為宇宙是具有雙重屬性的,即自然性和神秘性。自然屬性是因為他學習接受西方的天文歷法知識,懂得宇宙運行有其固有規(guī)律;神秘性是指他認為“理”對世間萬物的存在及發(fā)展產(chǎn)生影響,而這個“理”是看不見摸不到的,不具備物質(zhì)形態(tài),且“理”的規(guī)定性又是人為而定的。因此,雖然逃出了主觀唯心主義,但是受時代局限所困,在本體論認識上仍具有模糊性和落后性。
第二,求真務實的知行觀。康熙八歲繼位,在位六十一年,在他執(zhí)政前期,面臨著內(nèi)憂外患的政治局勢。政權(quán)穩(wěn)固之后,由于統(tǒng)治對象為多民族且主要為漢族,漢族文化與滿族文化相比在維護封建統(tǒng)治上具有一定的優(yōu)勢,因此統(tǒng)治者選擇繼續(xù)重用漢族士大夫,并把程朱理學作為官方的統(tǒng)治哲學。玄燁推崇朱熹的理學,并稱“至于朱夫子,集大成而繼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guī)。”“讀書五十載,只認得朱子一生居心行事。”玄燁認為,朱熹是繼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圣人,而且只有朱子真正繼承了孔孟所學,自稱為學五十余年,尤其覺得朱子才是真正用心做學問的人,對朱熹給予了至高評價。與此同時,玄燁又是“提倡真理學,反對假理學”的。他認為“自有理學名目,彼此辯論,朕見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矣。終日講理學,而所行全與其言悖謬,豈得謂之理學乎?若口雖不講,而行事自然吻合,此即真理學也。”指出自理學誕生以來,眾人都樂于互相辯論,但是所言與所行之間卻大相徑庭。每日對理學夸夸其談,所作所為卻完全相悖,這怎么能說是對理學有所研究呢?假使從不言何謂理學,但是行事遵循理學的訓誡與教導,這才是真正的理學。作為一位講實學重實干的帝王,玄燁十分提倡親歷親見,反對閉門空談,“朕平日讀書窮理,總是要講求治道,見諸實行,不徒空談耳”,認為理學即是日用平常之理,不必追求虛名。從書中獲得真知灼見之后要用于治道,付諸實踐,而不僅僅是坐而論道。“誦讀之功固不可廢,躬行實踐尤為至要,務時勤職業(yè)也。”表明讀書為學需要踏實認真,但是不可忽視實踐的重要性,要把書上的學問用到日常事物中去。因此,在他統(tǒng)治期間,勵精圖治,勤政為民,把從西方之學和程朱理學中的所學用到治國實踐中去,清朝的疆域在鞏固中有所擴張,經(jīng)濟發(fā)展穩(wěn)定,百姓生活也比較殷實,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礎。
第三,崇儒重“道”的倫理思想。玄燁曾說“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講究服膺,用資治理,爾師生勉之”。這里所謂的“圣人之道”大抵可以理解為“孔孟之道”。玄燁南巡時曾拜孔廟,賜匾額,撰碑文,都表露了他對儒學創(chuàng)始人孔子的敬仰之情,并視孔子之道為“天道”,希望群臣百姓都可以借此道勉勵自己。“朕惟天生圣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tǒng)之傳,即萬世治統(tǒng)之所系也。……道統(tǒng)在是,治統(tǒng)亦在是矣。歷代賢哲之君,創(chuàng)業(yè)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講明斯道”可以看出玄燁把“孔孟之道”提升到了國家統(tǒng)治思想的高度,試圖把“道統(tǒng)”與“治統(tǒng)”相結(jié)合起來用以治理國家。他思及那些先賢圣人,為人君為師長,使得“道統(tǒng)”在千百年后流傳至今,“治統(tǒng)”以“道統(tǒng)”為載體也得以流傳,“道統(tǒng)”和“治統(tǒng)”是可以合為一體為統(tǒng)治服務的。孔孟講仁,重視仁愛孝悌之理,玄燁推崇儒家學說,尊奉孔孟之道,因此十分重視推行以“孝”為核心的人倫道德,提倡以“仁”為核心的社會公德。“臨民以主敬為本,昔人有言,一念不敬,或貽四海之憂;一日不敬,或以致千百年之患。《禮記》首言毋不敬,《五子之歌》始終皆言敬慎,大抵誠與敬,千圣相傳之學,不越乎此。”與百姓相處要以主“敬”為根本,過去的人有這樣的說法,有一個念想脫離了“敬”,有可能會給整個天下帶來憂愁與煩惱;一天不主“敬”,有可能會招致長達千百年的禍患。《禮記》開篇就說明了主“敬”的重要性,《五子之歌》從頭至尾都在講述并告誡要主“敬”,千百年來的先賢圣人所傳授下來的道理學問大概可以歸結(jié)為“誠”與“敬”吧。玄燁把內(nèi)容繁雜的程朱理學歸結(jié)為一個“敬”字,認為人君若想治國安民首先要做到主敬。從孔孟之道的“仁愛孝悌”到程朱理學的“誠敬為本”,玄燁總結(jié)提出了著名的“圣諭十六條”并頒行天下,使之作為治國安邦的基本準則,也借此來教化約束百姓的日常行為,促進了清朝政治、經(jīng)濟、文化、生活的發(fā)展,使?jié)M漢及各族之間可以共同進步,友好相處。
第四,重民本的社會歷史觀。玄燁十分注重百姓的物質(zhì)生活,他說“從來與民休息,道在不擾。與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朕觀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勞民傷財,紊亂舊章,上下訌囂,民生日蹙,深可為鑒。”主張與民休息,根本就在于不去打擾百姓生活,農(nóng)忙時節(jié)給百姓充裕的勞作時間,懂得置民之產(chǎn)。縱覽前代的君王大臣,常常想要建立顯赫的功業(yè),既勞民又傷財,使得整個朝廷及社會的正常秩序被打亂,進而直接影響普通百姓的生活,值得深刻的反省借鑒。康熙朝前期,由于軍事及政治需要,推行了開墾、開礦、開海以增加財政收入,此番政策推進了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及商業(yè)的迅速恢復與發(fā)展。但是到了后期,西方文化及宗教入侵嚴重,受當時海內(nèi)外環(huán)境的影響及保守官員的諫言,下令禁礦、封海,對后世發(fā)展產(chǎn)生了消極影響。康熙帝曾言“古圣人之治無他道也,惟在因民心而已矣”,圣人治世是依民心而為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夫民雖至愚且弱,莫不各懷所欲。順之,則易與之為治;拂之,則日趨于非。此必至之勢也”。他認為百姓是愚昧懦弱的,但是都各自懷有私欲。承認并滿足其私欲,對他們的管理工作就相對容易,若是一味的打壓控制,便會引起不滿,時間久了就會造成不可挽回之勢。在今天看來,玄燁認為百姓愚昧懦弱的觀點是錯誤的,事實證明人民是社會進步的根本力量。但是在一個封建時期的封建帝王眼中,受時代及身份等因素的限制,他還看不到也也不愿承認這一點。但是,他允許廣大民眾合理的私欲,重視百姓的物質(zhì)生活,予民為便,予民以利,這便是他民本思想的體現(xiàn)。“臣為邦本,必使家給人樂,安生樂業(yè),方可稱太平之治。”他本心懷天下,也要求大臣們恪盡職守,不可以擾亂民生,要為百姓謀福利,對貪官污吏嚴厲打擊,保證了社會的正常發(fā)展。
2 玄燁理學對滿族哲學發(fā)展的意義
(一)、玄燁在理學中融入西方科學和唯物主義自然觀,對滿族哲學提升科學精神具有積極意義。
明末清初,隨著西方傳教士的到來,除了傳播宗教以外,西方的文化、科技、自然科學等也有所滲透。玄燁對數(shù)學、天文歷法、地理等有著濃厚的興趣。南懷仁、湯若望、徐日升等都曾受到玄燁的禮遇,并且這位中國皇帝勤學上進的作風得到他們的贊揚與認可,玄燁求學最大的優(yōu)點就是努力做到學以致用,而不僅僅只是“作秀”。他學習了幾何原理之后提出要用此學作些實地測量工作,不能僅僅停留在書本上。他的天文學知識在他對“道”的體悟中也有所體現(xiàn),是含有一定的科學因素在內(nèi)的,如“……因數(shù)之當合者合之,當分者分之。如度天之三百六十之度,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星有恒星、五星。五星轉(zhuǎn)太陽而行,恒星隨天體而動,……歷之可數(shù),象之可察,日月之可評,星辰之可定,圣人則之,而惟人時之。……天之所運,雖有紛綸交錯,圣人之道,實有精一全體,所以五氣順布,四時和行,以此敬天授時,其道豈可易乎!”在封建社會時期,帝王祭祀拜天、農(nóng)民安排作物種植等都要參照歷法而行。玄燁繼位初期也曾面臨新法舊法之爭,但是他不盲目推崇舊法,也不冒然接受新法,而是讓兩派接受科學檢測,以此來判定新法舊法哪個比較精準,選擇推行更科學更準確的。玄燁還認為萬事萬物自有它運行的規(guī)律,雖然當時還沒有提出“物質(zhì)”這一科學概念,但是不難看出其在物質(zhì)和精神誰是第一位的問題上,堅持了物質(zhì)先于精神。“天地育萬物”,“天不可量,地可量”,這里所言天和地的屬性是物質(zhì)的而非精神的,雖然這里的“物質(zhì)”只是指人們熟悉的具體事物,但是至少肯定了萬物并不是依靠人們的感覺或意識而存在的。在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方面,玄燁不僅自己勤學,還教導群臣百姓要主動求學上進,促使整個民族乃至國家培養(yǎng)求實務真的品性。雖然,玄燁并沒有建立起一支科學團隊來為國家日后的發(fā)展提供動力,但是在他的統(tǒng)治時期,我國的天文、數(shù)學、醫(yī)學及農(nóng)業(yè)種植等方面都有較大發(fā)展,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
(二)玄燁保留天命更重人為的思想,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所屬民族在宗教方面的消極作用,促進滿族哲學的積極發(fā)展。
薩滿教對滿族影響深遠,除此之外,佛教、道教、天主教在當時也有所發(fā)展。玄燁對宗教的態(tài)度比較理性,基本做到了“信而不迷”。薩滿教作為滿族土生土長的宗教,沒有成文的教義、沒有統(tǒng)一的組織、儀式等,因此其影響力日漸衰弱。同時,隨著時代發(fā)展一些上層教徒逐漸轉(zhuǎn)到了佛教、基督教或伊斯蘭教等教派當中,薩滿教只剩在民間有較大的影響力。統(tǒng)治者入關(guān)以后更是發(fā)現(xiàn)了儒學對于凝聚人心的巨大力量,玄燁尤其推崇程朱理學,把它作為統(tǒng)治人心的首選標準。一些受到玄燁禮遇的外國傳教士,借著傳播西方科技與學術(shù)的噱頭,大力宣傳基督教,在早期內(nèi)曾得到統(tǒng)治者的默認。但是,基督教作為一種組織性較強的宗教,發(fā)展起來比較迅速,到了一定規(guī)模便引起了統(tǒng)治者的警惕與限制。一旦其影響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習俗,與孔孟之道相悖,最后以禮儀之爭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統(tǒng)治者便立即下令禁止。比如,基督教嚴禁教徒參加祭祀、祭祖等活動,此一點就受到眾多官員和百姓的不滿,基督教勢力也因此受到打壓。此外,佛、道兩教宣揚的是出世的思想,對社會發(fā)展有一定的制約作用,玄燁也視之為“虛寂之道”,認為其對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發(fā)展并無益處。清初統(tǒng)治者意識到這些問題,因此并未選則基督教、佛教、道教等作為國教來大肆發(fā)展,而是選擇了積極入世的儒學來武裝統(tǒng)治階層的思想。玄燁尊崇孔孟之道,但是他更加推崇程朱理學,尤其是朱子的“主敬”學說,“人君治天下,但能居敬,終身行之足矣。”他把“誠敬之德”用在天人之際的溝通上,認為只要擁有“誠”、“敬”之心,便可與天溝通。比起“天命”,玄燁更加看重“人為”,他也用自己勤勉奮進的一生做出榜樣。“人之一生雖云命定,然而命由心造,福自己求。……若日行善事,命運雖兇,而可必其轉(zhuǎn)吉。”玄燁不否認“天命”對人生的影響,但是他又認為“命”受“心”的影響,福報也都是自己用心求來的。倘若一個人一直做善事,即使他的命運里充滿兇險,那么也一定能夠轉(zhuǎn)為吉祥。對“人為”的看重與肯定使人們不再沉迷于宗教的束縛與困境,對鼓勵百姓積極勞作,靠自己的雙手勤勞樸實的創(chuàng)造幸福生活有著積極意義。
(三)、玄燁推崇程朱理學,增強了儒學與滿族哲學的交融互進。
清政府是一個滿族貴族統(tǒng)治者當權(quán),漢族封建士大夫參政的統(tǒng)治機構(gòu)。由于受統(tǒng)治的群體主要為漢族及其他少數(shù)民族,數(shù)量要多于滿族,在維護封建統(tǒng)治這一層面上儒學文化也比滿族文化更加成熟,因此,作為儒學的特殊發(fā)展階段的理學盛極一時。玄燁本人極力推崇朱熹的理學,并對其加以改造使之更有利于維護其統(tǒng)治。不僅他自己崇尚理學,還因此發(fā)展并重用一批理學名臣,如熊賜履、李光地等。除了恢復了一系列祭孔尊孔的活動之外,在日常生活中他還身體力行的鉆研學習儒家經(jīng)典。玄燁接受了大臣熊賜履的意見,開始為歷代帝王舉行日講和經(jīng)筵,從儒學經(jīng)書之中學習君王之道和治國安邦之理。八旗子弟和官員學生也要系統(tǒng)學習儒家經(jīng)典,使?jié)M朝上下都接受儒學的洗禮。他命儒臣重新編纂修訂《性理大全》、《性理精義》、《周易折中》等,并親自為部分著作寫序,然后頒行于天下。但是,這些著作是通過對原著有選擇的尋章摘句加以編訂的,是玄燁為了籠絡漢族士大夫,維護封建統(tǒng)治及鞏固政權(quán)而采取的措施,因此可能有斷章取義之嫌。從積極的方面來看,滿族統(tǒng)治者學習理學對促進滿漢文化交流,加強儒學與滿族哲學的交流互進是有推動作用的。這樣一來,滿族文化在接受了先進文化的同時也對儒學的發(fā)展產(chǎn)生促進作用,儒學提倡的仁愛孝悌、居敬守誠、君臣父子等倫理綱常對滿族構(gòu)建新的社會秩序、人倫秩序有積極意義。在統(tǒng)治者的大力推崇之下,滿族也涌現(xiàn)出一批儒學學習者,如阿克敦,著有《德蔭堂集》,其哲學思想受《易傳》及《洪范》影響較大;愛新覺羅·載湉即清末光緒帝,著有《光緒御制文集》,他的哲學思想仍以儒學為正統(tǒng)。這些都豐富擴展了滿族文化,又為儒學的全面發(fā)展添磚加瓦,促進了儒學與滿族哲學的交融互進。
哲學與宗教在某些功用上具有相似性,尤其是在早期,哲學并未發(fā)展成完整的科學體系的時候,宗教一定程度上充當著哲學的作用,讓人們在困境中找到出路。儒學自產(chǎn)生伊始,后經(jīng)董仲舒、朱熹等人的封建改造,漸漸被推到統(tǒng)治階級思想領(lǐng)域,對我國歷朝政治文化的發(fā)展有著重要影響。各朝帝王及眾多學者的推崇或是打壓不斷改變并重塑著儒學的形態(tài),理學就是儒學在特定時期的一種存在形態(tài),被玄燁發(fā)現(xiàn)并給予重用,對滿族乃至整個中華民族哲學文化的發(fā)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值得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1](清)玄燁:《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四集),卷二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99-549-550頁。
[2]玄燁:《太極圖說》,《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二集),卷三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98-627頁。
[3]宋德宣:論康熙與朱熹理學觀的異同.湖南師大社會科學學報,1989年。
[4](清)玄燁:《朱子全書序》,《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四集),卷二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99-534-535頁。
[5]《清實錄》(第五冊),《圣祖實錄》(二)卷一一二,中華書局影印本,1985年,第157-158頁。
[6]《康熙起居注》(第一冊),中華書局1984年,第66頁。
[7](清)玄燁:《諭日講官起居注侍讀學士牛鈕》,《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一集),卷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98-80頁。
[8]《清圣祖御制文一集》卷十九《日講四書解義序》。
[9]陳峻嶺:希冀道統(tǒng)/治統(tǒng)之合膺——康熙玄燁獨尊程朱理學的文化選擇探賾,滿族研究,2001年第2期。
[10](清)玄燁:《講筵緒論》,《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一集),卷二十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98-225頁。
[11]李燕光:康熙皇帝.遼寧大學學報,1983年第6期,第55頁。
[12]王妍:康熙帝“真理學”思想探析,滿語研究,2014年第1期,第125頁。
[13](清)玄燁:《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四集),卷二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99-549-550頁。
[14]《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
[15]圣祖仁皇帝庭訓格言﹒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作者簡介
董曉青(1989—),女,漢族,河北石家莊人,西南民族大學政治學院,中國哲學專業(yè)2013級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