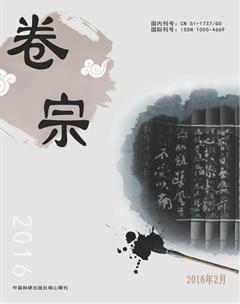才情兼備,酸甜并存
摘 要:《教坊記》作為唐宋史料筆記,記錄了許多唐代關于教坊的真人真事,有利于人們去了解研究唐代的社會生活。文章探究了唐代教坊藝人的生活狀況及思想觀念。唐代的教坊藝人能歌善舞,有才華,重感情,但他們的地位并不高,只是統治階級的服務工具。當然,他們并不為命運悲嘆,而是組織香火兄弟,自娛自樂,活出自我。
關鍵詞:唐代;教坊藝人;生存狀態;香火兄弟
1 《教坊記》的價值地位
唐代很早便設置教坊,至開元時趨于鼎盛。《教坊記》一書,記述唐開元時代教坊制度、藝人軼事、著錄教坊曲名三百二十四,樂曲之內容及起源,保存了唐代樂曲的豐富資料,是研究唐代音樂,百戲的重要原始資料,對我國音樂史、戲劇史、詞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意義。
《教坊記》作為唐宋史料筆記,記事真切可信,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正如崔令欽自序云:“開元中,余為左金吾倉曹,武官十二三是坊中人。每請祿俸,每加訪問,盡為余說之。”可見他是很熟悉唐教坊中的人與事的。
2 唐代的教坊及藝人
教坊,唐高祖時開始設置的,專管雅樂以外德音樂、歌舞、百戲的教習、排練、演出等事務。主要是為滿足統治者需要而在唐代宮廷樂舞機構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新唐書.百官志三》記載:
武德后,置內教坊于禁中,武后如意元年,改曰‘云韶府,以中官為使,開元二年,又置內教于蓬萊宮側,有音聲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優雜伎,自是不隸太常。以中官為教坊使。
除在長安蓬萊宮側的內教坊,延政坊設左教坊,光宅坊設右教坊,在洛陽明義北、南還分別設左、右教坊。《教坊記》載:
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蓋相因成習。東京:兩教坊俱在明義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坊南西門外,即苑之東也,其間有頃余水泊,俗謂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
唐代藝人,圍繞教坊、梨園,唐代宮廷有著數目龐大的表演歌舞、俳優、雜伎和百戲等得藝人群體,即教坊藝人。這些主要在宮廷為統治者表演,供統治者娛樂的藝人因其卑微的社會地位及角色、有著獨特的生活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教坊藝人與當時的娼妓要區別開來。這里不作具體闡述。下面我主要就唐代教坊藝人的生存狀態談幾點看法。
3 教坊藝人的生存狀態
(一)才華與情誼
1、才華橫溢藝術魂
(1)、能歌善舞。教坊中的藝人,無論是誰來自哪里,他們都具備一定的技藝。如:能歌善舞的龐三娘、嚴大娘及才貌雙全、能弄《踏謠娘》的張少娘;筋斗絕倫的小兒、箏木侯氏,還有任智方的四女。他們都是憑借自己的技藝吃飯,每個人都有用武之地。尤其是在他們演出大型劇《聖壽樂》時,無論是從動作表演,服飾的搭配設計,還是整個故事的發展,都令人出其不意,嘆為觀止。
(2)、化妝技術的高明。 唐代教坊中的藝人除了具備能歌善舞的才藝外,高超的化妝技術。畢竟這些藝人們是要登上舞臺表演給觀眾觀賞的,她們已經注意到了妝扮的重要性,即使一些上了年紀的女人依舊可以在舞臺保留她們的青春。如《教坊記》記載:“龐三娘善歌舞,其舞頗腳重,然特工裝吏。又有年,面多皺,帖以輕紗,雜用云母和粉蜜涂之,遂若少容。”“有顏大娘,亦善歌舞。眼重臉深,有異于眾;能料理之,遂若橫波,雖家人不覺也。”這兩段記載已向我們展示了唐代化妝術的高妙。它已為藝術表演扮飾的發展及成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對藝術的執著追求。教坊藝人把一生的青春都奉獻在了教坊的歌舞表演上,他們演奏出了大量出色的作品,如:曲折蜿蜒,令人蕩氣回腸的《烏夜啼》;故事悲傷、催人淚下的《踏謠娘》;婉轉悠揚、生動形象的《春鶯囀》。這些極具觀賞性的作品娛樂了唐代人們的生活,使唐代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也為后代的戲劇史,音樂史的研究提供了史料。
2、香火兄弟姐妹緣。教坊中的姐妹,聚在一起,結為香火兄弟,她們同病相憐、惺惺相惜,她們一起分享秘密,排解壓抑,苦中作樂,這樣的她們過的簡單卻快樂,面對命運的不幸,因為能生活在一個大集體中,因為有了姐妹們的陪伴,生活才不再那么枯燥,那么孤獨。如《教坊記》曰:“坊中諸女,以氣類相似,約為香火兄弟。……兒郎既娉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我兄弟相憐愛,欲得嘗其婦也。”可見,教坊中的藝人以“香火兄弟”相稱,因為相互有愛,心態也變得平和寬容,豁達率真。所以,雖然她們是卑微的,然而,她們的亦是自由,快樂,無拘無束的。
(二)酸甜與苦辣
1、地位低微辛酸淚。教坊的藝人身份特殊,雖然和唐代的娼妓有所不同,但是他們是被普通的“良人”所排斥、歧視的,大家都把他們看成是低賤的,以致于他們自己也認同的世俗人的評價。生活陪伴在皇帝身邊的他們,只能隨皇帝的喜好生活,他們的喜怒哀樂是受他人所支配的,得不到半點的自由。
(1)、教坊中藝人亦有高低、貴賤、等級之分。教坊藝人的等級分明,根據 《教坊記》記載,教坊藝人有如下等級:
首先是進入宜春院的“內人”,又曰“前頭人”。內人是教坊藝人中姿色、技藝最高者,常在皇帝御座之前表演歌舞。其次是來自云韶院,屬于賤隸的“宮人”,亦稱“云韶”。宮人是教坊中一般的歌舞伎。再次是“搊彈家”。“搊彈家”是平人女以容色入教坊,學習琵琶、五弦、箜篌、箏等樂器演奏,主要扮演伴奏角色。最后是兩院“雜婦女”。雜婦女不善歌舞,經常成為眾人取笑的對象。如《教坊記》中云:“有肥大年長者即呼為‘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即云‘康太賓阿妹,隨類名之,僄弄百端”。
當然,內人也是按等級來分的,不同的等級,其稱呼也不同。《教坊記》記載:
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頭也。其家得在教坊,謂之“內人家”,四季給米。其得幸者,謂之“十家”,給第宅,賜亦異等。初特承恩寵者有十家,后繼進者敕有司給賜同十家。雖數十家,猶故以十家呼之。每月二日、十六日,內人母得以女對。無母則姊妹若姑一人對。十家就本落,余內人并坐內教坊對。內人生日,則許其母、姑、姊妹皆來對,其對所如式。
內人也有“內人家”、“十家”的區分,他們所受到的恩賜也是不同的。“內人家”只是四季供米。而“十家”卻供宅第。可見,即使是在教坊這個小世界中,仍然留下封建統治者的印記。教坊藝人的命運仍然與高低等級的不同而有差別。看得出,這是唐代封建社會統治制度在教坊內的縮影。
(2)在教坊中,無論男女藝人,都是為統治者服務的工具。他們把男藝人當成“婦人”,這是對男藝人最大的凌辱。如《教坊記》記載:“教坊中一小兒,筋斗絕倫。乃衣以繒彩,梳流,雜于內妓女之中。”再如:“蘇五奴妻張少娘,善歌舞,亦姿色,能弄踏謠娘。有邀伢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欲得其速醉,多勸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雖吃?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鬻妻者為五奴,自蘇始。”女藝人只是男人支配的工具。他們不僅靠自己的技藝維持生活,還要出賣自己的肉體幫丈夫賺錢。
(3)教坊藝人大多數都是年輕貌美的,他們靠的是容顏和技藝生存。當他們人老色衰時,等待他們的只有辛酸與淚水,那也將是他們命運最悲涼的時刻。
2、低調含蓄抗爭史
生活之艱辛,命運之多舛。那是不是就意味著這些教坊藝人們沒有任何的歡樂了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些有才華卻備受世人歧視與壓迫的有血有肉的藝人們,被束縛在統治者為其規劃的牢籠里,他們的命運由他人支配,他們心有不甘,他們渴望平等,期待被重視、被關愛。所以教坊藝人用自己獨特的方式詮釋著命運對他們的不公與無奈,表達自己對現有社會制度的不滿及對理想及幸福生活的追求。如《教坊記》記載:
坊中諸女,以氣類相似,約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輩。有兒郎聘之者,輒被以婦人稱呼:即所聘者兄,見呼為新婦,弟,見呼為嫂也。兒郎有任官僚者,宮參與內人對同日。垂到內門,車馬相逢,或褰車簾,呼阿嫂若新婦者,同黨未達,殊為怪異。問被呼者,笑而不答。兒郎既娉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學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相憐愛,欲得嘗其婦也。主者知,亦不妬,他香火即不通。
教坊藝人中主要以女性為主,男藝人較少。香火兄弟是教坊藝人自發的組織,既是對男權社會的效仿與不滿,又是其自身生活的潤滑劑。藝人們來自五湖四海,自知身份低微的他們依靠相聚的這種緣分,團結力量,一起分享喜怒哀樂,一起排憂解難。
香火兄弟這一被統治階級默認的組織,雖然不像歷史上反抗封建統治的起義軍那樣明顯與暴力,但是它在某種意義上無不透露著對封建男尊女卑社會的不滿與反抗,表達了強烈想要改變現狀的愿望,想要彰顯女性的地位。當然這種抗爭是隱性而低調的,因為他們的生活狀態是依附在統治階級的基礎之上的,如果沒有皇帝的支持他們的這種組織只會瞬間瓦解。一切都在統治者的掌握之中,教坊藝人只是他們操縱的棋子。
總而言之,從《教坊記》中我們窺視到了唐代教坊藝人生活的苦澀與艱辛,命運的卑微與不幸,同時也領略到了他們個性的張揚,簡單的幸福以及與命運抗爭的堅強。
參考文獻
[1].(唐)崔令欽.教坊記(外三種)[M].北京:中華書局,2012.
[2].〔宋〕歐陽修、宋祁. 新唐書 百官志 三[M].北京:中華書局,1975.
[3].張曉蘭.《教坊記》中“戲”之探考[J].文藝評論,2009(1).
[4].寧俊紅.談《教坊記》中“戲”的涵義[J].社科縱橫,1998(4).
[5]岳永逸.眼淚與歡笑:唐代教坊藝人的生活[J].民俗研究,2009(3).
作者簡介
楊小英(1986-),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戲劇與影視學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