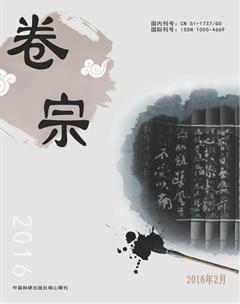民族政策體系視野下的民族識別問題研究
劉琳 馬雪 張力
摘 要:近幾年來伴隨著對中國民族政策的全面反思,民族識別成為其中一個爭議焦點。介于蘇聯、中國、南斯拉夫、越南等國都同為社會主義國家、民族成為這些國家在國內的一種制度安排之客觀現實,從特定的民族政策體系框架內對民族識別問題進行解讀可以幫助我們從一個新的視角理解相關問題。
關鍵詞:民族識別;民族政策體系
1 民族識別的概念闡釋
民族識別是指對一個民族成份的辨認。是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落實民族政策的一項基本工作。在舊中國,由于存在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許多少數民族的民族成份不能確定。新中國建立以后,為改變舊中國民族成份和族稱混亂的狀況,有利于保障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自1950年起,由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務機關組織科研隊伍,對全國提出的400多個民族名稱進行識別。加上原來已經公認的民族1983年共確認了55個少數民族成份。
2 社會主義國家民族政策體系之下的民族識別
民族政策從來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不僅涉及領域廣,其政策制定、實施再到效果評估的整個流程都是一個甄別與選擇的過程,因此,我們說政策體系本身就是一個綜合性的分析框架。
(一)民族識別是社會主義國家民族政策體系的一個衍生現象
迄今為止,學術界對民族的理解主要在兩個層面。一是與民族國家相聯系的國家民族,有學者將其稱為政治民族。二是指具有某些文化特征的人們共同體,即文化民族。我們所謂的多民族國家。就是由若干個后者所共同構成的統一的主權國家。當年社會主義陣營中的絕大多數國家基本上都沒有完成民族國家的建構,是各種各樣的“多民族國家”。
當民族成為一個國家的制度安排,當民族平等、團結、共同發展成為處理國內民族問題的基本價值追求的時候,了解本國民族共同體的名稱、數量、特點就成為其政策實踐最基本的要求,民族識別,不論采用什么方式,就會應運而生、無法回避,使民族識別成為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民族政策體系的一個衍生現象。
(二)對中國民族識別的研究
中國有自己獨特的國情,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也就是一部多民族發展的歷史。眾多的歷史古籍都涉及到一些諸如華夏、漢人、夷、蠻、戎、狄、胡人、匈奴、羌人等文化差異明顯,具有不同稱謂的多種“族體”。這些人們共同體的存在和交往不但豐富了中國的歷史和文化,還積累了關于民族的大量知識及相關的政策、經驗和教訓。孫中山當年提出“五族共和”主張顯然與這份歷史遺產直接相關,他不但看到了中國多民族共存的現實,還認為“現在說五族共和,實在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因為實際上我國“何止五族”。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大漢族主義居于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少數民族被看作漢族的“宗支”。對此,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指出“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否認中國多民族存在,而把漢族以外的各少數民族稱之為‘宗支”是“大漢族主義的錯誤的民族思想和錯誤的民族政策”,并提出支持孫中山先生的民族政策,幫助少數民族爭取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解放和發展。新中國成立后,為落實這一主張,中國必須首先摸清自己的家底,以便有的放矢的制定相關政策。費孝通教授曾說“解放以來,我們的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民族識別工作。
3 對民族識別學術爭論的幾點認識
從社會主義國家民族政策體系的角度思考民族識別,也許并不能夠解決當前相關的學術爭論,但是,至少讓我們從中獲得這樣幾點認識:
(一)民族識別涉及的方法論問題
如何看待民族識別首先存在一個方法論問題。即:對物質第一性還是意識第一性的選擇。不可否認,民族識別的對象——民族,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爭議的概念,對民族不同的解讀會導致對民族識別認識上的差異。美國康乃爾大學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教授在其《想象的共同體》一書中關于民族屬性與民族主義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民族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的觀點,在學術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力。按照這種觀點,民族只是一種主觀構建,識別民族的過程就會演變成政府或者利益集團主觀認定的過程,主觀認定一般都具有隨意性的特點,民族識別的科學性就受到質疑。民族概念的主觀論對民族識別的“人為”說提供了理論支持。相對而言,由于斯大林的民族定義強調的語言、地域、經濟生活、共同心理素質這四個要素,在確認過程中需要從語言學、歷史學、民俗學、民族學多個學科進行甄別并且可以依據各個族體的歷史和現狀進行操作,因此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客觀標準。
我們認為,采用單純的主觀標準或者單純的客觀標準識別民族,用即非白即黑的思維方式是有缺陷的。因為實際上它們二者都是交織在一起的。主觀標準需要正視各種客觀存在并且進行歸納提煉,客觀標準也同樣要借助思維邏輯進行分析。如果說事物的一分為二性質和馬克思主義的物質第一、意識第二的基本原理僅僅從理論上奠定了對民族識別的方法論基礎,那么我國的民族識別實踐,則展示了一個現實操作的標本。
(二)民族識別是確認民族和創造民族的對立統一過程
民族本身就是一種動態的社會現象。在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自成地理單元的獨特生存空間中,我國各民族分別經歷了異源同流和同源異流的漫長而復雜的過程。從縱向看,由于各民族的社會發展水平差距非常大,以至于在新中國建立之際有學者用“一部活的社會化石”來形象地反映這種狀況。再從橫向看,在同一民族內部,各支系之間的差異也是客觀存在的。按照當初民族識別的初衷,基于對“這是一項必須以科學研究為基礎的工作”的認識,我們注意到一個現象,我國民族識別的第一階段完成識別的是那些公認無異議民族的身份確認,這些民族往往人口數量較大,有自己傳統的聚居地方,歷史文化傳統深厚,文化特征鮮明,民族意識明顯,對他們的識別實際只是對客觀情況的一種官方確認而已,即使沒有這種官方承認,無論其本民族成員還是異民族成員都不會對這些民族的存在產生異議,因為他們已經客觀存在,已經取得人們的廣泛認可。進行民族識別就是對民族差異的一種客觀尊重,不是憑空制造出來的。民族識別的難點往往是那些民族內部支系比較多且客觀特征的一致性不突出、甚至其自稱、他稱、史稱交織且邊界模糊的各種族體,最終是通過統一民族稱謂而“創造性”地完成了民族識別。
(三)民族識別的結果是一柄雙刃劍
如果我們堅持對事物一分為二的分析方法,就應該看到民族識別的效果具有積極作用與消極影響這樣兩個方面,這也是符合事物發展內在邏輯的。今天我們觀察到的也許正是“一種具有辨證意義的兩面性遺產”。如前所述,當民族共同體成為一種制度安排,在此條件下的民族識別便具有合理性、甚至具有必然性。但是另一方面,若干國外經驗也使一些研究者這樣呼吁:“政治主權永遠不能與族屬相聯系,因為這種聯系會導致民族主義的危險爆發”。
近年來,國內一些對民族識別提出質疑的學者把一些群體性事件的爆發、民族意識的普遍增強等現象與民族識別這一基礎性工作聯系起來進行思考,試圖通過解釋它們之間的內在關系去尋求破解相關問題的出路。我們認為:不論這種嘗試是否有效,但至少啟發我們去關注今天一些民族問題的產生是否確實存在某些過去的政策或舉措方面的問題,至少將民族問題政策的科學決策問題用一種亡羊補牢的形式提供給學術界進行爭論、至少將民族共同體本身的存在將有若干變數的事實展示出來,這對學術的發展是有利的。當然,就這些觀點本身而言,仍然有值得商榷之處。
參考文獻
[1]馬戎,族群關系去政治化[J]南風窗.2008(26):50.
[2]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關系與民族認同[M]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1-3.
[3]施聯朱、黃光學,中國的民族識別[M]民族出版社.2005:62-63.
[4]納日碧力戈,現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構[M]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109
[5]王希恩,中國民族識別的依據[J].民族研究.2010.(5):3.
[6]馬戎,“理解民族關系的新思路——少數族群問題的去‘政治化”[J]北京大學學報2004(11):124-130。
[7]劉琪等問,墨磊寧答,“民族識別”的分類學術與公共知識建構[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8(6):23-24
[8]范宏貴,越南民族與民族問題[M]廣西民族出版社.201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