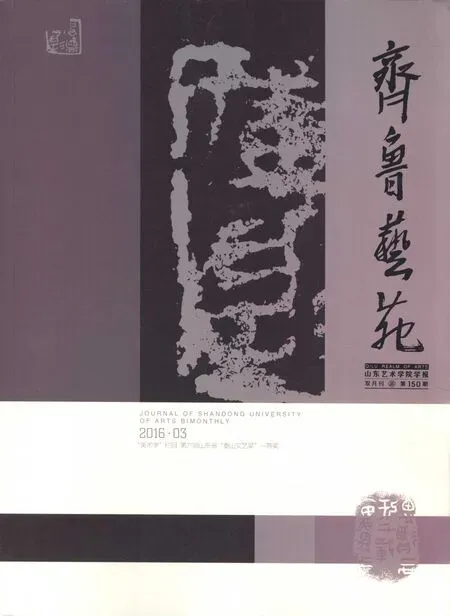“異托邦”視野下藝術群落的社會異質屬性
王智洋
(南京藝術學院人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0013)
?
“異托邦”視野下藝術群落的社會異質屬性
王智洋
(南京藝術學院人文學院,江蘇南京210013)
法國社會學家福柯的空間哲學體系體現了他對人類社會中異質空間的重新思考和獨特認識。以福柯的理論進行觀照,城市落敗地區出現的藝術群落是一種介于現實與理想間的異托邦空間,其發展與變遷的過程具有特殊的內在邏輯。作為一種異質性空間,這些藝術群落具有話語權上的反抗意義、時空上的并置能力、精神上的補償效用,系統上的開閉特質以及社會上的規訓功能等社會屬性。
異托邦理論;藝術群落;異質屬性;福柯;空間社會學
一、社會學空間轉向背景下“異托邦”概念的提出
在很長一段時間中,“空間”(Space)這一概念被簡單的理解為地理上自然、靜止和非辯證性的客觀條件,從而遭到學術界的忽視。20世紀70年代以后,伴隨著現代社會結構屬性的日趨復雜,后現代社會學家們才逐漸認識到對空間研究的缺乏,他們期望通過“空間轉向”(spatial turn)這一歷程,重新認識空間概念在社會中的其他意義和隱喻。
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作為一位后結構主義者(盡管其本人拒絕承認自己屬于某一流派),對空間有著獨特的思考研究。他認為雖然時間和空間都是物質存在的前提,但學術界在長期對社會現實、歷史演進等問題關注的同時,忽視了對空間的思考探究。過往認知中對歷史情境的過分聚焦,扼殺了地理空間探索上的創造力。因此,有必要反思并顛覆傳統時間哲學和經典社會理論中對空間概念的誤解偏見。
福柯重新審視并解讀了空間、知識和權力三者之間的關系,他在《瘋癲與文明》、《規訓與懲罰》、《知識考古學》等著作中,都論及了自己空間化的知識觀和權力觀。他認為空間建構于復雜的社會關系之中,必然與社會中的種種知識與權力聯系在一起。在現代社會中,知識體系賦予空間功能以合法性,并最終表現為特定的權力關系。因此,空間不僅是權力存在的場所容器,也是權力運作的媒介途徑。
在此基礎上,福柯提出了“異托邦”(Heterotopia)的概念。作為其空間哲學重要的一部分,“異托邦”一詞首次出現在他19世紀60年代出版的《詞與物——人類科學的考古學》中,并在《地理學問題》、《知識、權力與空間》等一系列訪談中不斷被完善。1984年,福柯在《異質空間》(Des Espaces Autres)演講中的“差異空間學”(heterotopology)部分,正式對“異托邦”的概念進行了闡述分析。他認為異托邦是一種在人類社會中實現了的烏托邦形式,在這些烏托邦中“在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文明中可能也有真實的場所——確實存在并且在社會的建立中形成——這些真實的場所像反場所的東西,一種的確實現了的烏托邦……因為這些場所與它們所反映的,所談論的所有場所完全不同,所以與烏托邦對比,我稱它們為異托邦。”[1](P54)
二、“異托邦”的定義、特性及分類
異托邦“Heterotopia”一詞源于希臘文,其中“hetero”有“其他的、錯位的、異質的”之意;而“topia”則代表著“拓撲、場所、空間”。福指出,異托邦是一種由地理位置、物理構成、自然景觀、想象思維、虛擬符號等具有差異性元素組成的空間場域。
異托邦作為一種特殊的異質性空間,具有生成性、真實性和多元性等特點。因此,現代社會中的空間概念既不是中世紀及之前充滿著不平等的“等級空間”,也不是伽利略等提及的“延伸空間”,更不是巴什拉(Bachelard)所言的“內在空間”。區別于真實存在的現實世界(real place)與托馬斯·莫爾文學中虛幻的“烏托邦”(Utopia);“異托邦”在福柯的視角下是一種處于現實、虛幻共同交織下的“第三空間”。對于異托邦自身內部的這種復雜特性,福柯解釋道:“在這些烏托邦中,真正的場所,所有能夠在文化內部被找到的其它真正的場所是被表現出來的,有爭議的,同時又是被顛倒的。這種場所在所有場所以外,即使實際上有可能指出它們的位置。”[2](P54)換言之,雖然異托邦既不是一種真實可觸的現實世界,也非一種建立在完全幻想之上的烏托邦世界;但其自身的中介屬性,卻可以使這兩種截然相反的世界在其內部找到關聯性的映射。
根據相應的空間屬性,福柯將異托邦劃分為“危機型”和“偏離型”兩種。“危機型異托邦”主要存在于原始社會中;由于宗教禁忌、等級特權等的存在,一些特殊而弱勢的危機群體(如剛出生的幼兒、生理期的婦女以及虛弱的老人等)會被有意識的孤立于群體之外。危機型異托邦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減少,并逐漸被其他形式取代。而“偏離型異托邦”主要生成于近代社會中;福柯指出,現代社會中人們的一切言論行動都需要符合一定的標準和規范(如法律和道德),只有當這些條件滿足時,主流社會才會接納他們,并賦予其相應的知識結構和權力體系。然而在此之外,社會中依然存在著一些特殊的個體,他們自身的言行偏離異常于一般的社會準則。因此其被主流社會排擠,被隔離在特殊的空間之中。這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關押著違背主流社會法律法規的罪犯群體的監獄,以及收容了對抗主流社會道德標準的精神病群體的精神病醫院。
三、現代社會中的藝術群落
城市作為構建現代社會的基本單位,在規劃、設計和建設過程中總帶有一定的理想主義色彩。但在現實中,城市在地理學上的空間結構與社會學上的功能秩序,往往難以達成完美的同構與一致。階層差異、種族背景、宗教信仰等因素使得城市在發展過程中自發的生成一些區別于主流社會的特殊場所。失業人口、低收入者以及外來移民等社會邊緣化群體在此聚集,形成了諸如城中村、貧民窟、荒蕪農田、廢棄工業區等城市中的異質空間。
源于城市中主流居民對藝術工作者創作手法、思想言論、社交方式等的誤解、抵觸甚至是排斥,以及由生活成本費用上升帶來的壓力,城市周邊地帶的藝術群落在此情況下應運而生。一部分藝術家,特別是年輕的當代藝術家選擇離開城市中心的繁榮地區,遷往城市周邊低生活成本的地域生活和創作。經過一段時間的聚集和發展后,理論研究、策展規劃、商業銷售等相關行業的藝術從業者都會逐漸到來,并最終在一定的地理范圍內形成一個個獨立于主流城市社會、自給自足的藝術群落。
藝術群落作為一個由社會中“非主流”成員組成的城市孤島和綠洲,其中的參與者基于對彼此的認同感和對藝術的相似趣旨,自發的形成了一種情感、文化以及利益上的命運協同體。這些群落并非以道德與法律上的強制性為基礎,而是基于心理、認識、情感等方面的共識——人們彼此尊重、認同并默認形成一種價值觀,分享相似的集體記憶。他們相互依賴、共同進退,以群體的力量抵御外界輿論對其的質疑和攻擊。雖然藝術群落有別于大眾所生活的主流社會,擁有相對自由寬松的氣氛與環境,但同時其仍然要受到道德、法律、人性等基本社會準則的約束,故而又并非是完全脫離世俗的。因此,這些城市周邊藝術群落在空間本質屬性上而言,既不同于符合主流社會價值觀的現實世界,也并非完全虛構理想的烏托邦空間;而是更加趨近于介于二者之間的異質世界——異托邦。
四、“異托邦”視野下對藝術群落社會屬性的研究分析
福柯的“異托邦”理論體系,為我們研究現代社會中的復雜現象提供了多重視角。處于“野外”狀態的藝術群落是一種在社會現代性歷程下產生的碎片化異質空間。它的存在不僅在地理上填補了城市與城市之間的郊區地帶,也在心理上聯接了不同亞文化群體在思想上的關系紐帶。因此,有必要將藝術群落定位于異托邦這一異質空間,以福柯的理論視角對其相關社會屬性加以審視分析。
(一)藝術群落對社會主流話語權的反抗屬性
空間作為一種權力爭奪的場所和媒介,必然充斥著種種沖突矛盾,話語權作為決定合法地位和場域位置的陳述體系資源,體現了一種“排除的法則”(rule of exclusion)。因此,在成熟穩定的話語體系中,空間往往依照話語權的利益進行建構、配置和生產。“這些真實的空間是相互斗爭的空間(counter-sites),它們同時再現,斗爭與倒轉,有效地形成了虛構的空間,權力的空間化。”[3](P46)通過這一過程,主導話語權的階層不斷界定并干預空間中的事物及其秩序,并由此產生一定的等級關系,從而馴服和扼殺那些反抗話語權的對象。
然而在后現代社會的多元化發展趨勢下,官方與主流的敘事架構逐漸將部分話語權讓位于多元、異質的民間“稗史”(Petites Histories)。特定的評判標準和參數體系開始失去往日的宰制性地位,亞文化群體的文化自覺意識開始崛起。出于對金錢、名利、輿論等世俗約束的抗拒,作為城市生活“邊緣人”(marginal person)的藝術家,在遠離于主流社會之外的藝術群落中構建出一種波西米亞式(Bohemia style)的生活狀態。無論是在17世紀孕育出眾多激進文藝思潮的巴黎左岸(La Rive Gauche);還是20世紀初充斥著女權主義、反戰文化、性解放運動的曼哈頓東村(East Village);亦或是上世紀80年代末,容納了大批放棄體制內、工作、挑戰戶籍制度藝術家的圓明園畫家村;其內部的成員都生活在一種反抗主流社會價值體系的狀態之中——相對于巴黎右岸的物質求實、紐約的紙醉金迷以及北京首都的集體主義生活;左岸、東村和圓明園則分別對應著先鋒理想、朋克精神和個人主義——在不平等的社會文化結構中,亞文化群體相對主流社會而言處于一種邊緣的地位。
分析國內外諸多藝術群落后不難發現,盡管廉價的房租和生活成本等經濟原因,在群落產生初期起到了重要的影響作用。但在隨后的發展過程中,維系藝術群落的卻是來自于藝術家們相似的看法和態度。“這種畫家群體內部人與人構成一種‘初級關系’(primary contact),就是說類似于家庭、親屬、鄰里、戰友一樣的關系。”[4](P20)唯有對藝術有著共同追求的人,才能夠彼此認同和尊重,從而在群落中以一種完全不同于城市居民的生活狀態聚居。
藝術群落這一社會現象的出現,預示著該城市在多元性、異質性上已接近發生質變的臨界點。處于體制外的藝術家開始與主流價值觀進行抗爭,并在社會中爭取屬于自己的發聲渠道和權利歸屬。作為異托邦存在的藝術群落,以及其中種種“異常”的生活行為方式,在本質上體現了作為城市非主流群體的藝術家群體,對主流社會格局及秩序進行挑戰、反抗和改革的一系列的技術實踐。
(二)藝術群落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并置屬性
異托邦的多元和復雜性源于其能夠在時空上將互不相容的各種元素包容并置于同一個真實的場所。福柯在這里例舉了舞臺、地毯和電影院進行解釋。首先,在同一舞臺上同時表現的幾個相互獨立的場景與劇情,在觀眾的視角中構成了戲劇故事的異托邦空間。其次,波斯地毯在有限的空間中集中表現了大量的動物、花木和建筑,是現實花園及阿拉伯人宇宙觀在平面中的異托邦體現。最后,電影院中“在其后面人們可以看到一個投射到二維銀幕上去的三維空間”[5](P25),從而在有限的平面幕布這一異托邦中,創造出情節發展的無限可能性。在異托邦這一真實空間中,可以混淆糾纏并包含多個在時空上間離沖突的空間。碎片化和片段化的時空元素在此融匯交織,并通過聯想、指涉等方式重構出新的隱喻。
在現實生活的空間中,不同社會屬性群體之間的聯系是暫時、偶然及不穩固的。而城市周邊的藝術群落通過時空上的并置性將這些來自于不同群體之間松散、不確定的結構關系聯系在一起。群落中的藝術家之間的關系并非建立在制度化的理性邏輯之下,而更多的是一種以思想認同為基礎的感性結合。這也就意味著這些異托邦中在審美上擁有更多的包容性;而這一特質則為現代藝術自由、個性、反傳統等本質訴求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條件。上世紀50年代美國的戰后移民潮中,房租低廉的紐約曼哈頓東村吸引了大量不同國家和民族的移民。其中來自德國、波蘭、意大利以及東亞地區的移民藝術家們重新定義了這個過去被認為是醉鬼、癮君子及流浪漢代名詞的破敗街區。紐約東村在不斷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一個容納、吸收不同矛盾文化的異托邦——在橫向的空間維度上,來自全球不同國家和民族的藝術活動在這里同時進行;在縱向的時間維度上,50年代“垮掉的一代”、60年代的嬉皮士、70年代的朋克族在這里交相呼應,以一種“異托時”的方式將代表不同年代的文化重構組織在一起。
(三)藝術群落對城市生活的補償性屬性
異托邦中非真實的虛幻世界完美有序,是對真實空間的一種補償;其的存在幫助人們對真實世界進行重新認識和理解。福柯將異托邦空間喻為一個連接現實與虛幻世界的鏡子:一方面,鏡中并不存在一個實體的世界,因此其是虛幻的;另一方面,鏡子中出現的物象又是現實世界中真實物象的映射,因此其又是真實的。通過玻璃與水銀的折射,世界上真實的客體出現在了一個不存在的鏡中世界;鏡子的存在使真實世界的客體和虛幻世界的客體連接在了一起。因此“反抗的可能性和條件就包含在現實之中,是此時此地存在的,任何一個場所都存在一個與他相反的他者空間。”[6](P14)
區別于普通大眾日常生活的城市空間,藝術群落作為一種獨立于主流社會之外的異質化次級空間,在社會中扮演的就是這樣一個“反身之鏡”的角色。無論是隨處可見的裝置藝術、先鋒雕塑,還是頻繁出現的紅色標語、文革海報,亦或是精心規劃的園林景觀、形色植物;當下中國各個城市的藝術群落,都在有意識的與高密度、快節奏、忙碌繁復的城市生活劃清界限。通過世外桃源式的風景、人文藝術氣息的布置等一系列象征性符號,帶領參與者或穿越歷史或體驗異域風情;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創建出與主流社會截然不同的“體驗性”空間,成為城市生活特征的“補集”。其“補償性”的社會屬性不但迎合了藝術家對創作環境的要求,也引起了城市中產階級的青睞和關注。在某種意義上,藝術群落的存在滿足了社會中不同個體對夢想中遙不可及美好世界的想象,并以一種最易接近與獲得的方式,營造出了一個可以讓人暫時逃脫生活壓力與現實煩惱的場所。
(四)藝術群落的開放性與封閉性屬性
福柯認為異托邦并非可以隨意進入,而是一個既開放又封閉的空間,“兩個‘異托邦’之間既是隔離的又是相互滲透的。”[7](P24)異托邦對一部分群體發出召喚的同時,也將另一部分群體排斥在外;從而形成一個既獨立又可滲透的開合系統。福柯在此以教堂、監獄、軍營為例解釋:任何人想要進入并成為其中的一員,都必須接受一個“儀式”的過程(如接受宗教洗禮、法院裁決或新兵入伍)。異托邦通過一種程式化、技術化的方式,對“什么是內、什么是外,誰可以分享內在的愉悅作了保護性卻是具有可選擇性的界說。”[8](P27)這一措施約定了異托邦中的基本規則和底線,從而對其的內與外、認同與否定、屬于與不屬于等本質上的身份認同問題作出了區分界限。
藝術群落自身作為一個矛盾體,內部隱含著種種悖論。其作為異托邦存在的價值及意義,并不在于其中聚集了大量的著名“藝術家”——相反,剛畢業的學生、民間藝術家以及業余藝術愛好者構成了群落中的主要人群;這些個體大多是在主流藝術界、學院派系中郁郁不得志的藝術家。藝術群落寬松多元的環境,接納了這批游離于體制之外的群體。此種狀態下,作為異托邦的藝術群落對這些人而言是開放的、可滲透的。
但在現實中,并非每個藝術參與者都是愿意為自由和理想犧牲的殉道者;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對很多藝術家而言,依舊具有著重大的意義與吸引力。由于其社會身份的變化,藝術群落也顯示出了雙向性的排他性和間離化:一方面,功成名就的藝術家們開始逃離體制外的藝術生落,轉而去追求體制內的職務、工作與榮譽;而另一方面,群落中的其他藝術家則對他們產生了陌生和排斥感,認為其背離了當初的信仰初衷,已不再屬于此群落。在此狀況下,作為異托邦的藝術群落則是封閉的、排他的。在社會媒體語境下,藝術群落在封閉的狀態中,呈現出一種動態的、流動空間化(space of flow)的趨勢。群落中的藝術家不斷與群落中的話語權發生聯系和互動,從而將主體的實踐活動和群落的空間結構予以實時的同步。
(五)藝術群落的社會規訓屬性
除了藝術群落內部的開放與封閉性調整外,外部的社會也在不斷對其進行“去儀式化”的改造,福柯將這一過程稱為“規訓”。他認為宏觀社會中占據主流的話語權階層通過對空間的改造,逐漸消除“癲狂主體”的黑暗與野蠻狀態。理性思維通過自己所設定的特權和制度,控制異托邦中非理性主體的行為。
具體而言,這種“規訓”建立在一種“觀看”機制之上,經過這種主體性的壓制、解放與拯救,完成了對社會異質群體的管理和約束。社會通過對藝術群落的包容,將其有限度的暴露在大眾生活當中。在長期的規訓和同化下,許多充滿對抗性的藝術群落逐漸轉變成了溫和世俗的商業區、旅游景點;而相應的,許多離經叛道的先鋒藝術家也逐步褪去了其反社會的色彩。隨著個人名氣的提升和作品價格的上漲,一部分藝術家開始嘗試接近并融入市場、學術界等主流藝術場中。憤世嫉俗、眾醉獨醒的行為固然灑脫自由,但在市場的引誘和體制的誘惑下,不少藝術家選擇了妥協。獲取傳統學院中的教授身份、加入官僚體制、亦或是與商業資本合作開發衍生品拓展市場,成為許多成名于藝術群落中藝術家的最終訴求及歸屬。
社會規訓通過大眾對群落“全景監獄”(Synopticon)視角的“觀看”使藝術群落這一異托邦中的個體逐漸走進公共生活,并由此完成自我身份的重建和社會主體意識的回歸。這一過程通過社會中無處不在的“權力的眼睛”進行隱蔽且具有生產性“全景敞視主義”監視實踐,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異托邦中社會異質特質的對抗屬性,使得社會維持在一種穩定平衡的狀態中。
結語
藝術群落作為社會中的一種異質空間,它的社會屬性不僅僅是地理和物質領域的,也是心理和精神層面的。福柯社會學理論體系中對空間概念的關注,體現了他對空間社會學的獨到認識和探索;其不但凸顯了這些群落中思想觀念與實踐行為的特殊性,也強調了權力和知識在其中的規訓作用。因此在“異托邦”視野下,勾畫和還原這些于復雜社會條件下生成的藝術群落,為研究這些異質空間的社會屬性提供了有效的信息與創新的思路。
[1][2](法)米歇爾·福柯.另類空間[J].王喆譯.世界哲學,2006,(6).
[3]趙福生.Heterotopia:“差異地點”還是“異托邦”?——兼論福柯的空間權力思想[J].理論探討,2010,(1).
[4]于長江.在歷史的廢墟旁邊——對圓明園藝術群落的社會學思考[J].藝術評論,2005,(5).
[5][8](法)米歇爾·福柯等.后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M].包亞明主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6]汪行福.空間哲學與空間政治——福柯異托邦理論的闡釋與批判[J].天津社會科學,2009,(3).
[7]尚杰.空間的哲學:福柯的“異托邦”概念[J].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3).
(責任編輯:杜娟)
10.3969/j.issn.1002-2236.2016.03.023
2016-02-26
王智洋,男,南京藝術學院人文學院2013級藝術學理論碩士研究生。
J022
A
1002-2236(2016)03-0116-05
項目來源:江蘇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創新計劃項目“國內藝術生態群落發展現象的社會學研究”(項目編號:KYLX 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