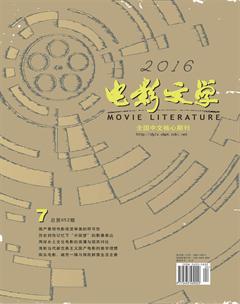“傳統文化電影”的價值傳承及未來之路
段新和
[摘 要] “傳統文化電影”是中國電影百年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類型,是中國電影在世界影壇所獨有的特殊類型,它的發展儼然已經成為中國電影未來的決定性因素。這類影片不僅聚集了中國文化的精粹,使人們在觀賞電影的同時也領略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風貌;更在藝術形式上動用了它的專屬特點,成為人們認識中國文化最有效的媒介,在我國的電影歷程中留下了最濃重的一筆。相比過去,傳統文化電影有著怎樣的傳承變化和藝術價值?未來又將如何發展?本文將加以闡釋。
[關鍵詞] “傳統文化電影”;新世紀;美學風格
從20世紀初開始,“傳統文化電影”雖然作品不多,但是風格各異,其中既有著英雄們為國犧牲的慘烈壯舉,還有處處充滿正能量、引人發笑的電影以及帶有農村特色的藝術作品。電影工作者們在努力突破,創造新品。
一、新世紀“傳統文化電影”的創新及價值
在1990年之前,“經典電影”大多數都是根據已有的劇本經過翻譯后編寫成的。通常來說,改動幅度并不是太大。不過,自21世紀開始,各種別出心裁的電影逐漸興起,且均凌駕于原有的劇本之上,由此導演們對原有劇本的改動也越來越多。
電影《生死擂》和原著《解擂》相比,前者著重于角色的情感變化描寫。這其中,主角對國家、兄弟以及自己的妻兒等的感情更是令觀影者記憶猶新,且成為整部影片的看點。影片的最后,借助主角的一系列情感變化,便順利地將劇情推入了擂臺賽的高潮,使觀眾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復。電影《山鄉情悠悠》和原劇《柳暗花明》相對比,人物描寫同樣也尤為突出:首先,《山鄉情悠悠》刪去了原著的開篇與結尾,刪掉了女二號;其次,原著更加偏向男性描寫,而改編后的電影則是著重于女性的情感變化。《六尺巷》則是最近一段時間被大家津津樂道的一部作品,盡管內容和名字與原著一樣,且它們的主旨都是描寫爭奪房子的所有權,不過無論是對人物的刻畫,還是電影所要表達的內容,都建立在了原著所想表達的內容之上。只不過原著《六尺巷》的主要內容是兩大家族因政治原因所進行的“地盤爭奪戰”;而電影的主要內容卻是兩家因科舉落第而做出的一系列爭風吃醋的行為。無論是原著還是電影的主旨都是在提醒人們以禮為先。
在20世紀末期,共有16部為人熟知的黃梅戲,但是這些黃梅戲中只有一部的拍攝靈感來源于安徽。由此推斷出,編劇們并沒有在中國歷史和現代社會發展需求方面投入過多的精力。不過自2000年之后的題材卻大多取自安徽,并由點及面地將中國歷史展現在世人面前。
電影《山鄉情悠悠》取材于一個貧困山區的農村,同時將一幅山村畫展現在觀影者面前:“山巒如聚,波濤如怒,綠水青山。”這里有著高低不一的石板橋、少有人至的深山老林、高大偉岸的青山……于青山綠水間挖掘出鄉情的淳樸。
作為黃梅戲的故鄉,安徽承受著世界人民的向往。但是在黃梅戲中,卻很少出現能夠刻畫出安徽人民形象的作品。2000年過后,隨著電影的盛行,安徽文化逐漸被人們所發現,也漸漸造就了一個個經典電影形象。電影《生死擂》就著重對蘇月英、趙大江、鄭京生三位主角進行了刻畫。其中,蘇月英是一名賢惠、儒雅的淑女,在丈夫趙大江戰斗失敗后,蘇月英挺身而出,為夫而戰,并取代了原來的擂主。她是一個典型的女強人,但在丈夫趙大江面前卻成為一個柔弱的小女子,并且她的言談舉止也頗符合中國古代俠客的形象。趙大江是一個剛強豪爽的人,對待事物不喜歡拐彎抹角,所以當他看到自己的妻子和仇敵對擂的時候,很直接地就誤認為自己的妻子與鄭京生“破鏡重圓”。不過在明白一切都是自己的妻子想方設法緩解自己與仇敵間的關系的時候,他立即深感愧疚,并且當機立斷地放下架子向妻子道歉。趙大江是一個粗中有細、有時迷糊卻能夠亡羊補牢的人物。另一位主角鄭京生是一個感情十分細膩的人,對自己所追求的東西從不會放棄,在知道自己成為罪人后便立刻去了少林寺了卻塵世。
電影《山鄉情悠悠》的女主角是一個懂得忍讓的農田知識分子,一名堅持不懈的女青年,男主人公在意外事故中失去雙眼,不過他仍然希望回家繼續對未完成的課題進行研究,但父母卻執意要他們回去工作,最后他只能在一處破敗的屋子里繼續研究,經過一次次的失敗后,最后終于成功。女主角是一個條件很好的知識女性,同樣在城中有著不菲的收入,但是當男主角失去雙眼后,女主角毅然決然地拋棄了一切跟隨男主角回鄉,她從來沒有對誰抱怨過一句,任勞任怨,充分體現出安徽人民的自強不息、重情重義的性格特點。
電影《六尺巷》中,最使觀影者難以忘懷的是姚香蘭、知縣兩個主角。姚香蘭是一個溫柔大方的賢惠女人,而知縣卻是一個隱藏在愚笨外形后的聰明人。姚香蘭在與人吵架后,被婆婆誤解,忍受著別人的指責并主動大方地去向人賠禮道歉,展現出書香門第的氣量。男主角在一開始希望和平解決,為此他也曾低三下四過,但當他得知張英被“炒魷魚”之后馬上變臉要嚴肅審理,但他最初的目的也只是想擺脫掉張英這頂大山公正地審案,所以,從知縣這個人物身上充分體現出了桐城人民機智幽默的個性特征。
二、“傳統文化電影”發展的不足
人們在看黃梅戲的時候,雖然能夠感受到黃梅戲文化的成長,但是這些電影仍然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人物沖突是一部電影的關鍵所在,觀影者認為,一部電影中的人物矛盾愈激化,電影的好看度也隨之增長,同時表達的含義也隨之深刻。現在的黃梅戲電影,在劇情內容方面是不如經典電影的,盡管有些電影顯得有著很大的潛力,但是卻沒有觀影者所喜愛的宏大場面,例如人們熱衷的戰爭場面。大部分黃梅戲在電影高潮的時候十分無力,無法使觀影者感受到跌宕起伏的劇情。又如,在電影《山鄉情悠悠》中,整部電影的高潮部分當屬女主角錯把男主角當成父親,通過自己表明心跡最終取得了父親的理解,但是僅僅用語言來展現出的高潮無法使觀影者滿足。再如,在電影《六尺巷》中,僅僅用幾張紙解決了整部電影中令人頭疼的矛盾,觀影者對矛盾本來是充滿好奇的,但是結局卻給人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有部分觀眾認為,若可以通過努力來解決矛盾,在最關鍵的時刻讓書信出現,那么好看度會相對提高。
通常,一部電影內容的平淡無奇會造成很多結果:首先,故事無聊,觀影者無法抓住整部影片的主線內容;其次是無法塑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最后是無法占據經典潮流。人,不經過磨煉,怎會有多余的情感去向別人表達?觀影者怎能感受到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劇情?在內容的要求上,現代黃梅戲電影并沒有在經典黃梅戲電影上做出突破,依舊停留在從前的才子風流、忠邪之爭上,和現代觀眾的審美特點還有著相當大的距離。
值得一說的是,黃梅戲電影的編劇逐漸對某一定格鏡頭的拍攝和描繪產生興趣,并拍攝出不少這樣的鏡頭。在電影《生死擂》中,鄭京生在回歸的路上,觀眾看到的是:在遠處,鄭京生淡然坐在竹筏之上順流而下,寒葉飄落,在江中倒映出山的影子。這幾個片段,給予觀影者一種悵然若失的心緒,并描繪出一幅花開花落花暗香的畫面。鄭京生的“粉墨登場”,塑造出一個空靈的環境,使得觀影者從畫面中觸碰這一傲視一切的才子。
不過,就所有電影而論,能夠做到把握鏡頭的遠近長短,并將其充分融入電影中的導演編劇是很少的,更多的導演喜歡著手于內容,但他們忽視了一些細節,使得整部電影大大減少了應有的“活力”。相對電影來講,現在的年輕人更加反感戲劇,他們大多認為戲劇的音樂過于難聽,但專家們認為這個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前面沒有任何背景、鋪墊以及內容,直接上場演出;其次,戲劇的舞臺僅有一處,無法給予觀眾異彩紛呈的視覺沖擊;最后,對于整部戲劇的整理少得可憐,尤其是青少年觀眾所反感的音樂。
觀眾對一種藝術作品價值取向,首先要看這部作品的品質和其他人的評價,其次要看這部作品的所屬類型以及可發展度。盡管現代黃梅戲電影與經典電影相對照,做出了相當可觀的改動,而且獲得了人們的認可,但是,能夠流傳成經典的現代黃梅戲電影還沒有被創作出來,人們所了解的還是那些經典的黃梅戲和前期的黃梅戲電影,現代的作品品質還有著很大的發展空間。
除了這些,2000年后的黃梅戲電影,在特征上保留了經典電影的清純簡樸,換句話說,被保留的都是黃梅戲的樂曲。在電影的領域,對電影起著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卻沒有得到很好的調整與確定,能夠統領黃梅戲電影的大師級導演還沒有出現。
三、“傳統文化電影”的未來之路
作為傳統文化電影,“傳統”元素在現代的發展過于迅速,能夠給予人們的文娛形式也越來越多。因此,能夠吸引觀眾的因素就在于這部作品的“特性”和“未知領域”的大小。一部作品想要抓住觀眾的眼球,務必在一開始就抓住觀影者的好奇心,使其在影片開始對整部影片的背景、內容以及發展產生濃厚的興趣。創作者必須在電影的情節、配樂、鏡頭的操控等方面做出細心的調整,這樣,觀眾才會寧愿拋棄一切并“毫不勉強”地帶著興致去看一部影片,也只有這樣,觀影者得到的感覺才會是煥然一新的,便自然不會感覺自己是在浪費時間。觀眾在觀看的過程中感受到作品的深刻內涵后,心情也會被劇情牽絆,對作品的印象自然更加深刻。
當導演把自己當成了觀影者,不停地找出自己的毛病,挑自己的錯誤,就能發現,過于枯燥乏味的故事是無法滿足觀眾需求的,必須有能夠抓住大眾好奇心的因素:令人羨慕的愛情故事、一波三折的情節、耳目一新的音樂、出神入化的演出……同時,也包括觀影者在最開始就被牢牢吸引、不能自拔,到最后忘掉煩惱、忘掉時間地融入戲劇之中……不過做到這些是很難的,這需要創作者積累經驗和持之以恒的努力。
經典電影的發展歷程提醒人們,眾多藝術形式的發展離不開初始概念的提出,例如,美國的理想主義電影、蘇聯的蒙太奇電影等。就現在的情況而言,黃梅戲這種藝術形式在銀幕上出現的次數并不少,無論是大銀幕,還是在電視上。當然,在電影方面上的體現要少于電視節目,而且絕大多數情況都是針對一個作品的評述。一些老一代藝術家和學者覺得,從今以后要針對黃梅戲的發展和影片的概念進行開發,就務必要向其他類型的電影學習,如果能夠延續他者的優點,便可助力于黃梅戲的發展。
榮獲多種獎項的影片《悲慘世界》,其創作靈感來自于同名的經典名著。電影一開始的鏡頭就給觀影者留下了一個非常大的遐想空間:在蒼茫的大海上,狂風卷積著烏云,在海平面的另一端,一艘輪船“冉冉升起”,在驚濤駭浪中進入港口,這時畫面一轉,一些帶著手鏈腳銬的犯人緩緩走下船,輪船附近,執法者在嚴厲地監視著這些犯人。
影片對幾個長短不一的鏡頭進行描寫的同時也向觀影者展示了這部影片的特色:宏偉雄壯、“毛骨悚然”,在之后鉤心斗角的戰斗中也將這種特色充分地體現出來。緊接著,情節開始發展:警察釋放一部分犯人,犯人很激動,但是警察卻提醒犯人們,別忘了今天的恥辱。這一段短暫的前戲,不論是在畫面上還是配樂上,觀影者可以體驗到一種嚴肅的氛圍,并對犯人們接下來的遭遇抱有很大的期望。與此對比,黃梅戲應該做出一系列的調整,并對發展前途做出合理規劃。從概念的提出,到后臺工作人員的工作,都要對這些內容做出改革和創新。同時,還可以利用目前流行的藝術形式,盡量揚長避短,將黃梅戲電影發揚光大,使其成為一門新的國粹。
四、結 語
當今時代,電影逐步向著流水線作業形式發展,“傳統文化”電影作為一種特殊的藝術類型,同時也代表著我國的文化,從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來講就應該一邊發展一邊繼承和學習。作為現代活躍度較高的一種電影形式,黃梅戲電影和“傳統文化電影”的結合,可以徹底地打破中國電影質量差和中華民族文化發展斷層的僵局。
[課題項目] 本文受湖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黃梅戲藝術研究中心”資助(項目編號:2013003503)。
[參考文獻]
[1] 米建榮,杜玉生.在電影中回歸中國傳統文化[J].電影文學,2009(22).
[2] 何春耕.傳統文化與時代精神的審美超越——謝晉電影創作觀念略論[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04).
[3] 席格.論本土電影的傳統文化故事講述[J].中州學刊,2011(03).
[4] 徐文明.論香港“邵氏”電影中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彰顯[J].浙江萬里學院學報,2006(04).
[5] 胡譜忠.敘事策略:主旋律電影中的傳統文化[J].當代電影,2001(04).